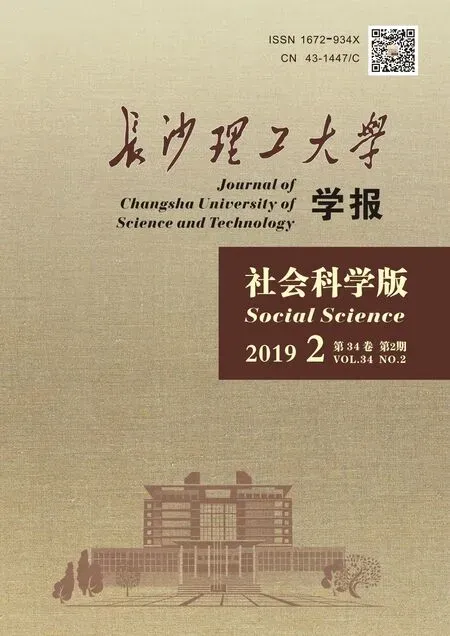南怀瑾伦理思想疏解
陈万球,廖 莉
(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湖南 长沙 410114)
南怀瑾(1918-2012),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丰富而独特的人生行履使其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之努力备受世人赞誉。
一、深沉的民族情怀和敏锐的时代感悟
南怀瑾一生把握时代脉搏及耕耘传统文化,其伦理思想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怀和敏锐的时代特性。
“峡谷柔情天付予,临风玉树立中衢,知君关心两件事,世上苍生架上书。”友人送他的这首诗表明南怀瑾一生专注两件大事:关心苍生与文化。1976年冬,南怀瑾作褐云:“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国与谋身,谁识此时情。”[1](P159)唯具高高山顶立的智慧,才有洞彻世情的冷峻目光;也唯有深深海底行的悲愿,才有民胞物与的火热情怀。
南怀瑾成长于祖国山河破碎的时代,处在“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中”。抗战爆发后,南怀瑾满怀一腔爱国之情投笔从戎,跃马于西南边陲,而后执教金陵大学、中央军校。他认为,“时代的盛衰演变中,文化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2](P31),执意于从事文化复兴来力挽狂澜。二十六岁时,他在峨眉山许下宏深誓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续中国文化断层。他作诗为证:“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他要做“收拾河山”的事情,就是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尔后六十多年,南怀瑾矢志不移,坚持做一件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续传统文化之脉。
在批判外国文化的基础上,凸显民族自豪感和传统文化自信心。他认为,美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标杆,但其民主自由并不适合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对于有五千年以上历史文化的中国,更不适宜”[3](P258)。他坚信,“美国文化不是人文文化的指标”[3](P265-267),作为青年人应该认清,“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文化思想的实质,否则“于国于家,后果均不堪设想”[3](P265-266)。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与外国相比,“只有我们的历史值得自豪”[2](P775),只有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的标准”[3](P613-614)。他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坚信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4](P11)这不是那种狭隘民族意识下的中国人统治世界的想法,而是对融合几千年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精神而成为世界大同世纪的预言。“那将是一个融合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的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纪这才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真义。”[5](P97)
清末以降,中华民族历经百年苦难,文化命脉面临存亡绝续。所谓“中国文化存,则中国兴;中国文化绝,则中国亡。”他自认为是“民族优越感最强的人”[3](P256),“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爱好中国文化的分子”[2](P619),是“顽固地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老顽童”。亡国还能复国,而“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断绝了,就会永无翻身的日子”[2](P615)。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惊涛骇浪中幸存而屹立不倒,凭借的是“中国文化统一的力量”。“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2](P272)字里行间,一肩挑尽古今愁,国家天下,尽在其中。基于这种思考,南怀瑾致力于重续传统文化之脉,通过口述讲述传统文化,数十大本著作,洋洋数百万言,其心可鉴。
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传统文化的拔根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异常艰辛。即便如此,南怀瑾发出了“西方文化仍然不是世界文化的坐标”的呼号。及至晚年,他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国家若想发展,就得彼此合作,实现共赢。因此,他认为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放眼世界变化的同时始终立足国家实际,走自己的文化自强之路。也正是在中华民族大踏步、高效率的发展中,南怀瑾伦理思想在时代的变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其时代性也更加鲜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科学昌明,物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道德滑坡,信仰匮乏,内心空虚,无所归宿。基于这种认识,南怀瑾认为:中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更注重对人民进行传统道德文化的培养,要摘取传统文化之精华,融汇儒、释、道三家,结合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来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精神烦恼和思想困境。所以,他反复说:“整理固有文化,以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6](P347)这件事“是任重而道远的,要能耐得凄凉,甘于寂寞,在默默无闻中,散播无形的种子。耕耘不问收获,成功不必在我。必须要有香象渡河、截流而过的精神,不辞艰苦地去做。”[6](P347)正因为如此,南怀瑾的思想切应时代的需要,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南怀瑾伦理思想的基本脉络
南怀瑾学问体系博大精深,如何梳理其伦理思想的脉络与层次,需费一番周折。南怀瑾曾说:世上种种学问,譬如哲学、科学和宗教,都是为生命而建立的。因此把握其基本脉络,需从“生命的起源”入手,通过“生命-人性-教育”这个理路来进行。
(一)生命的起源: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非常神秘,南怀瑾用通俗的话剥去了其神秘外衣,有助于理解其思想。他认为中国传统诸子文化,就是一个“道”,也就是今天的“生命科学”。他认为哲学也好,宗教和科学也好,都是基于此,只是至今尚未得出结论来。所以,研究伦理道德不得不探究宇宙和生命的由来,继而到达第一要义,而佛教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在传统儒释道文化中阐述得最为清楚。
南怀瑾认为,宇宙自性本体的功能就是一个:起用而变化成万相,哲学上叫做本体,一切生命只是这个本体的变化而成的现象。整个人类文化,不论中西,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追寻生命问题。就人的生命而言,是由精虫卵子结合,再加上灵魂,三缘和合而成。生命是轮转变化而来,过去有过去的生命,未来有未来的生命,前生往世的生命会带来这世的种性,变化成当前自己一生的遭遇;而现在所造的“业”,又将会变成来生的果报。他说,佛法的基础建立在三世因果与六道轮回之上,一般人虽然可以勉强相信,真要求证那是非常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南怀瑾指出,到达定境的三禅以上,许多佛经陈述的内容才能在定中看清楚,那才差不多会真相信。可是修持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我们无法通过文字直接证明,但修行人之外,许多学者也都认可南怀瑾先生体道之深,当世鲜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二)道德的生发:人性
在南怀瑾看来,人性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为道德可能性之根据。人性为善还是为恶?其根源如何?如何去恶存善?“这都是中西哲学上的大问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几千年的悬案。”[3](P354)
古代关于人性善恶观的争辩历来界说不清。南怀瑾剖析了孟子、告子、荀子、杨雄、王阳明等人的理论,指出:孟子“以水就下,肯定形容人性的本善,确实有所商榷的余地”[3](P355)。告子所谓人性“无善无不善”的理论也不能苟同,而荀子的性恶说与孟子的观念成为强烈的对照,与西方文化中的性恶论似乎相同。汉代扬雄提出人性的善恶混杂的观念,“好像很有道理,严格推究起来,到底言无所宗”[3](P356)。后世大儒王阳明的学说,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他得出结论:各派学说只从建立行为道德的要点上争论人性本善本恶,并没有先行严格探寻所谓人性的本身究竟是什么?而界说关键在于:人性是先天-形而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还是指有了生命以后的人性?最后只能“混淆不清,弄得一头雾水,因此论说纷纭,便成为众盲摸象,各执一端的流弊了”[3](P358)。
他指出,大乘佛学克服了传统哲学各家众盲摸象,各执一端的流弊:“截然确立形而上(先天)的性理本元,与形而下(后天)的人欲界限,建立一个理论完整、体系井然的思想。”[3](P363-364)大乘佛学人性论要旨为:其一,秉承原始人性本净论,认为原始的人性本来便是光明清静,含容万象万类,极其圆满,既非有善,亦非有恶。其二,原始本净的人性因后天缘起而迷失本净。其三,需要通过“人性”的自觉而返回人性本净,破除由执为小我的后天“我执”,而返还到先天无余大我的自性清净,归到非善无恶的圆满自性之境界。可见,南怀瑾十分推崇大乘佛学的人性理论。
在论述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南怀瑾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人性自然生发产生道德。“人性的善恶问题,也就成为理学论据的要义。”[3](P354)也就是说,道德义理产生于人性善恶。他认为,人类的五伦不是法律规定,而是人性自然发生的。
(三)道德的养成:人文教化
人性先天本净,后天缘起迷失本净,故而需要人文教化,使人性回归圆满自性之境界,这便是南怀瑾道德养成的逻辑理路。
南怀瑾认为:教育同人性密切相关,教育最高的目的是培养人性,指向人性,启发引导人性向好的路上走。“教育以变化气质为目的。”[7](P0-51)教育担负的最大责任不是传承知识,而是移风易俗!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改正人性,使人向善良的方面走”[7](P51)。人之所以作奸犯科,往往是后天的习性使然。后天的习性是如何养成的呢?南怀瑾认为,追根溯源和人欲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要通过人伦教育,反省克念,匡扶人心,去尽人欲,使天理流行,才能恢复人性本善的面目。而究竟怎么教是个大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对教育的方法,教育的诱导,向哪一条路上走,很值得研究。
三、南怀瑾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作为一代文化巨擘,南怀瑾的伦理思想丰富而庞杂,涉及到政治道德、家庭伦理、人生哲学、身性修养等,而他对生态哲学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南怀瑾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德为本”。他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是“公天下”。从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服从,才是王道。”[2](P102)就政治家而言,“想做好一个领导人的,必须具有领导的基本道德与学问。领导的基本条件很多,中外有关的书籍也很多,但都是讲权术,不是道德,都不行。真正的领导要以道德为基础。”[2](P763)“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2](P103)“处事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他认为,为政实际上一种牺牲,需要智、仁、勇齐备,为政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有见义勇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情怀[2](P106)。只有这样,为政之人方能“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2](P103)。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基础,基于此他提出了“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思想。他通过中西方对比来把握中国传统的孝道精神。他批评西方爱的哲学文化是断头哲学,爱的文化是断头的文化:“西方文化……只知道爱下一代,下一代长大了,结婚了,就是夫妇。对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他们自认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这个十字架断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为没有上半截了。”[2](P12)在南怀瑾看来,东方文化的孝道是最浅近的人文基础,也是做人的底线。中国的孝,在西方文化中叫作“爱”,也就是回过来还报的爱。中国人却巧妙地将孝道建立在真性情的心理基础之上。孝道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在南怀瑾看来,一是孝道运用在现实中,孝道需要人们主动去进行人格的修养,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二是用真心去投入,孝道的实现不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而是靠真性情;三是运用合理方式。南怀瑾先生认为:孝道绝非简单的养活父母,而在于其背后的人文精神。所以在孝的方式上一要敬;二要态度合理。他还提出了恋爱哲学问题,认为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是两性关系问题[2](P137)。 “年轻人谈恋爱,应该懂得恋爱的哲学。”[4](P16)“真正的爱,只有付出,没有占有。”[8](P331)
在丰富的人生践履中,南怀瑾把握人生哲学真谛。他认为,人生哲学关乎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大课题。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是从大处着眼,成为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事业。“人类的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些曲折艰难,是件好事。”[2](P373)他告诫年轻人:“人生永远是明天,不要看昨天,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也没有,因为说今天,今天也已经过去了。”[8](P331-332)他认为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德薄而位尊”,自己的道德与学问不够,但位置很高;“智小而谋大”,自己没有智慧,做官想越大越好,生意赚钱越多越好;“力小而任重”,自己力量不够,偏要挑一个大责任。如果犯了这三大戒,“一定倒大楣,很少有例外的”[8](P560-561)。最后他得出结论:“人要有自知之明。”[8](P561)他还提出人生之乐不在于物质,知足是人生至福。南怀瑾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是孔子最有名的话,而且在文学境界上写得最美。“一个人要修养到家,先能够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进一步摆脱了虚荣的惑乱,乃至于皇帝送上来给你当,先得看清楚应不应该当……人生的大乐,自己有自己的乐趣,并不需要靠物质,不需要虚伪的荣耀。不合理的,非法的,不择手段地做到了又富又贵是非常可耻的事。”[2](P285-286)
在道德修养上,南怀瑾认为一个人通过“内圣外王”及“内外兼修”,方能成就一生事业。“内明之学”即是修身养性。南怀瑾认为,曾子是“内圣外王”的大手笔,所著《大学》既是“内明之学”,亦是“外用之学”。作为“内明之学”,《大学》是“万古帝王师之学”。“内明之学”涵盖五德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修身养性,就是正心、修心,是“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外用之学”即是建功立业。人格修养的完成,由内而外,“外用”就是利世利人和建立功勋。对于普通人来说,“外用之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建功立业,就是利国、利人、利事。事实上,南怀瑾既是一个成功的人,也是一个富有的人。他精通儒道释三家,将其融会贯通,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被世人誉为“国学大师”。他身负盛名,可谓“成功人物”。
此外,南怀瑾融传统儒释道“仁爱”思想于一炉,提出“照临万类”的生态保护思想。他说,“人类是地球文化,他们离不开这个地球,也就是离不开这个土地。”[8](P310)他为人类保护地球敲响了警钟:“电脑网络的发达,可使人们完全进入‘迷心逐物’的境界,却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我们现在所用的资源,都是取自这个生命的内部。”[9](P107-108)
四、南怀瑾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创新发展
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进步总是在对自己的传统道德资源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前进的。南怀瑾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有着传统思想的深厚滋养,他在内敛中萌发新枝。为了解决传统道德文化衰微之势,他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将传统道德哲学与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相融合,并进行了创造性转换的有益尝试。他说,“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2](P12)南怀瑾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优秀的传统道德哲学加以改造、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时代内涵和新的表达形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道德哲学的形式转换、内容转换和作用转换。
对传统道德哲学的形式转换,即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语言、概念、范畴的转换。对于古人的语言,有的只能作为历史的概念、范畴加以了解和认识,不可为今所用;有的可以直接继承,有的则可以通过改造、更新加以继承。南怀瑾完全按着自己的领悟和受众的需要,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别裁”和“他说”。他将距离今人生活遥远的“陈词滥调”改写成大众喜闻乐见的“另一个”版本。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解读不是正解,而是“别裁”“旁通”“他说”“杂说”“别讲”。“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2](P5)
对传统道德哲学的内容转换,是将传统文化中的命题和观点进行新的诠释,赋予新的内涵意义。“新旧文化交流互变的冲击时代,只好采取配合时代趋势的方法来研究。”[4](P321)南怀瑾对中国古代哲学中“义利之辨”“仁义道德”“知行合一”“人性善恶”“内圣外王”等进行分析,并将其进一步提高与升华。
对传统道德哲学的作用转换,这是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转换的立足点问题。南怀瑾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有一种宏观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他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通过对传统伦理文化中积极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系统的转换,寻求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民族智慧、经验教训,为解决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提供思想方法、历史启迪,用以补充与丰富现实斗争的智慧和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南怀瑾之所以较为成功地将传统道德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了转化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是南怀瑾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他一生没有离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这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中国新文化创造之根。二是因为他具有深深的民族情怀,使得他对传统文化的转换始终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南怀瑾首先是一个思想家,而后才是文化大家,这种特点,使他注重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三是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成熟的思考,他逐渐从社会实践中体悟和升华了传统伦理文化的真谛。“我们文化深厚,就是历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辈的经验太多了,我们读书也是为了吸收这些做人做事的经验。”[2](P565)四是因为他在创造性转化中采用一些全新的方法,概言之有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依文体义等。
古人研究经学往往是“不通诸经,不足以治一经”,南怀瑾则提出了一种“以经解经”的主张。与古人不同,他将唐宋以后的批注推开,依靠熟读原文来理解传统经典。经典中前文的意思往往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只要前后篇章贯而通之,自然能解其意。他指出,“我们做学问的办法,最好以经注经”,“有时你读它的本文,前边不懂的地方,等你读了后边。那前边的也就懂了。即使错了,也错得很少,不会离谱。假使看古人的注解,有时候错下去,一错就是几十年,回都回不来,临死后悔也来不及了。再说一家有一家的注解,各家的注解太多了,多得让你没有辨识的能力。所以说以经解经才是读经最好的方法。”[8](P285)
经史合参是南怀瑾先生解释《论语》《孟子》《易经》以及其他传统经典的主要方法。经史合参就是将文化经典与历史记载进行对照、比较,来参究经典所表达的思想。“经”是常道,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史”是记载这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2](P60)
此外,南怀瑾还提出了“依文体义”之法,在了解传统经典原文字面含义的基础上结合人生经验加以体会。此种方法,注重结合人生经验体会,而不是拘泥具体文字的解释。
五、结语:时代的智者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人们对南怀瑾文化人生的写照。为实现接续中国文化断层的大愿,南怀瑾从青年时代起历经半个多世纪,奔走呼号于大陆与台岛,气壮如虹,成绩卓著,他无愧于当代中国弘扬传统文化的先驱称号。先生常常引用北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自己的胸襟,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的大智慧,彰显了一个时代智者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