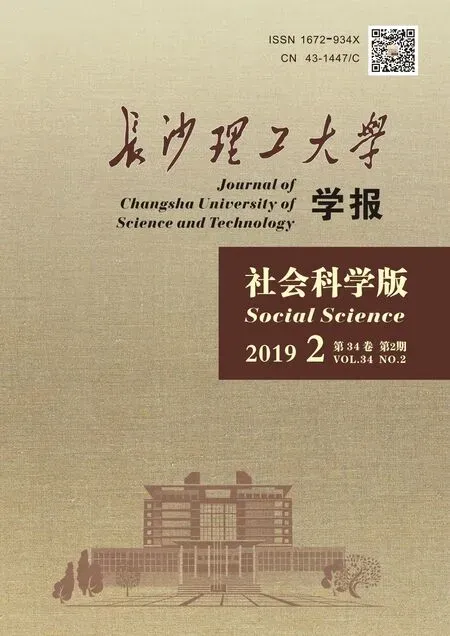张枣的戏剧化技艺
胡苏珍
(宁波大学 中文系,浙江 宁波 315211)
张枣诗歌的元诗书写追求不再是小圈子的秘密,但是具体到他的每一首诗,仍机心难勘,让读者抓耳挠腮。以抒情传统视阈来看,张枣所作的诗都“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1],他自然是个纯粹的抒情诗人。但作为一个把写诗看成类似偷“惊叹号”[2]的艺术享乐主义者,他钟情虚构,好作纯想象力的冒险,认定诗歌陌生化的旨归,在超现实虚构和语词的腾挪变换中,还精于戏剧化面具与戏剧化场景。张枣偏向寻找历史、神话、经典作品中某一具体情境中的角色作为自己说话的“面具”,在重写中融入自己的生命经验,角色的意识实为诗人自身的体验。这种写作是通过呈现具体“面具”化角色在某一特定、具体时空片断下的心理状态,隐含性地表达诗人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情思。张枣的“面具”说提炼于1990年代,但这一写作个性早在1980年代就呈现出来。从形象来看,张枣不少诗作把写者自我虚构成几个角色,构拟某个具体的他者的动作、心理情境,或在角色间交叉人称变换制造戏剧化关系,诗人自己则藏身在“面具”当中。在体量玲珑的抒情诗中如此调动戏剧化角色形象,自然形成“他非他、我非我”的阅读效应,值得一番深察。
一、自我化身或分身带来的奇妙调式
张枣写诗器重调式,找到一种奇妙的语调或语态,就实现了他写诗最重要的一步,这个调式往往由说话者和人物情境推动。这或许引发一个问题:诗人的调式不是个性化的吗?的确,诗人总体声音趋势有稳定的风格。但调式是具体的,不同情境,说话者面对的不同人物关系,诗篇选择的语汇、节奏都有细腻变化,可以说,诗人所写的每一首诗,都由最初构拟的语气、情景决定走向。张枣曾在访谈中透露:“我总爱用假设的语气来幻出一个说话者,进而幻出一个情景,这情景由具体的、事理性的也就是说可还原成现象和经验的图像构成,然后向某种幻觉、虚构或说意境发展。”[3](P113-115)把握张枣这一诗歌密道,能对他繁复曲奥的人物创设增加几分了明。
张枣的成名作《镜中》,体现了诗人对人物关系、调式的高超编织能力,近年来得到不同名家的阐释,但妙解不一。柏桦说,“《镜中》是一声轻轻感喟……多少充实的空虚、往事的邂逅,终于来到感性一刹那”[4](P21-22),这是直觉式评论。钟鸣取专业技术法,从该诗抽绎出八种交错、隶属的人称关系及其诗学反叛意图,即对传统主题、汉语及物性、封闭语言机制的反叛[5]。不过,该诗戏剧情境中的“我”“她”“皇帝”几个角色到底指向什么,仍可进一步探讨。根据张枣自况的诗学观,他早期作诗,全凭“幻美的冲动”[3](P111-115)。他对“元诗”作过宏篇专论,提出诗歌的形而上学:“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6]。张枣的元诗写作,余旸概括为“没有一首诗歌是及物的,直接诉诸于我们的直接经验”[7]。以“元诗”观照《镜中》,“她”不必然是宫女,“皇帝”不一定暗讽权力,戏剧化角色解读可跳出经验层面。
在本文看来,除了参照张枣的元诗诗学和他对鲁迅《野草》的元诗角度赏析,解读《镜中》还可从张枣其他诗篇找到蛛丝关联,并打开张枣构拟自我写者形象的一个语词谱系。《镜中》意象、人设在张枣其他元诗中都有呼应。如《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中的“贝多芬的提琴曲嘎然而止,/如梯子被抽走”,“梯子”在该语境中隐喻音乐的升降;如《深秋的故事》,“而我渐渐登上了晴朗的梯子/诗行中有栏杆,我眼前的地图”,以诗行“栏杆”作上下文,“梯子”大致比喻诗兴的前进、上升。由此,“梯子”在《镜中》不是现实物象,而很大程度上是元诗拟象。又如“皇帝我紫色的朋友在哭泣”(《星辰般的时刻》),“你翻掌丢失一个国家,落花拂也拂不去”(《十月之水》),联系两首诗上下文,皇帝、国王,喻指的是诗歌写者,史蒂文斯的《冰淇淋皇帝》便有元诗书写的意味。而“游过来呀,/接住这面锣”(《春秋来信——致臧棣》),“在对岸,一定有人梦见了你”(《十月之水》),游泳、对岸也并非指向现实经验,而是指诗人从现代游回传统的审美追求,“对岸”即古抒情时代。至于“骑马”“骑手”,在诗歌中作为诗人身份的暗喻已是常识,张枣在《何人斯》中,也有“马匹悠懒,六根辔绳积满阴天”的元诗书写。互文参照下,《镜中》的“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看她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及“羞惭着脸,回答着皇帝”,都可看成诗人写者姿态的戏剧化呈现。也就是说,游泳、登上梯子、骑马的“她”和“皇帝”都是诗人的自我镜像想象,这些镜像又在镜中互相折射、互相窥探。
从诗学逻辑看,《镜中》能幻化出几个戏剧化自我,依靠的是“只要……便”的假设语气和“镜中”这一核心情景。“镜中”折射出写者“我”的不同姿态——“她”“皇帝”;幻化出写者的不同动作和情态——游泳、登梯、骑马、羞惭;“比如”“固然”“不如”等虚词则推进诗的发展,形成无理而妙的调式和语气。而“危险”作为审美、写作行为的性质,马拉美就曾提出“冒那在永恒中失足堕地的危险”[8],张枣也引用过荷尔德林《帕忒摩斯》中的书写危险及营救[6],并具体谈过诗人逃离“废词”“暴力之词”而可能面临空白[9]。回到元诗立意看,落满南山的“梅花”,也指向诗人的语词、诗绪。至于吸引联想的“后悔”一词,更像是为了“落满南山”的诗绪的起兴和“梅”的联韵,并无追忆之类的实际情感信息。诗中的古典语象、古典情境都改变了原来的情感内涵,被张枣进行了洋气的现代转化。
对写者姿态和对话诗学的迷恋,对自我镜像的寻找,构成了张枣诗歌想象的双翼。《昨夜星辰》中他如此直抒:“有谁知道最美的语言是机密?…… 我只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一边/名垂青史,一边热爱镜子”。张枣并非袒露现实中的自恋感,只是倾心在诗中穷尽写者自我。最早期的诗《影》就露出这一情结:“在月光下/我惊奇地发现了自己/诙谐的影”,“为什么我今像个/梦境里的人/奋不顾身的四肢/竟然缚在一片虚无之中”。这些都属于“幻美的冲动”。现代诗人对主体的寻求,有的从时代环境中觅取,如天狗、凤凰式的譬喻;有的从青春伤感中印证,如“我是一个单恋者”(戴望舒);有的从历史儒道传统中沟通,如整体主义诗歌。张枣则落在“汉语诗人”这一主体性上,他有写者的骄傲和抱负,又牢系着“汉语性”这一纽带,不断和汉诗长河中遥远一端的诗人对话,反复呼唤那个神秘的“你”来和自己相遇。然而,隔着时空,远方神秘的对话者始终不露面孔,张枣又返回自身,想象从外面深入自己内在的、当下的丰富戏剧化自我。如《高窗》中“对面的邈远里,或许你 是一个跟我/ 一模一样的人。是呀,或许你 /就是我”,把当下真实的“我”幻化出一个“你”,“我”看着剥橙子的、写诗的“你”。总之,在文化传统长河中,在当下情境中,张枣都要找“你”来观察、证明“我”。故而柏桦说,“他终其一生都在问:我是哪一个。”[4](P19)
正是对“我是哪一个”的执迷,张枣魔术般地变出了“我”的不同化身和分身。颜炼军对张枣把握得全面且深入,他说,“张枣一直致力于发明自我戏剧化结构,来探究和呈现主体复杂性”[10]。与此同时,有了分身,也带来了张枣追求的调式变化。其中最值得分析的是他的双性自我对话,诗人虚构男女语吻,很容易引发两性故事的误读,其实是他对元诗写作和丰富调式的苦心经营,典型的是《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柏桦见证过该诗“令同行胆寒”[4](P35)的历史,傅维补充说里面“写了多为女性”[11],宋琳指认其中的“元诗结构”[12]。张枣此诗可能受叶芝启发,叶芝在《学童中间》中曾以舞者和舞蹈隐喻艺术的有形和抽象、瞬间和永恒,而张枣此诗是对诗艺之美的舞台化隐喻。该诗分上下片段,前者是男性“我”看见“她”为我舞蹈:“姣美的式样”“四肢生辉”“声色更迭”“变幻的器皿/模棱两可”“舞台,随造随拆”“衣着乃变幻:许多夕照后/东西会越变越美。”女舞者的样式、身段、声色、器皿,可以通向诗人的形式感、手法、语吻、语词材料库。后半段是女性“我”的独白,“我看到自己软弱而且美,/我舞蹈,旋转中不动。/他的梦,梦见了梦,明月皎皎,/映出灯芯绒——我的格式/又是世界的格式;/我和他合一舞蹈。”舞者的软弱、旋转中不动,指诗歌的消极颓废美和永朝一个中心的坚定,因此,两片段看似两个主体的言说,舞者和观者,其实都是诗人自我的化身。女舞者说的“只因生活是件真事情”“只因技艺纯熟(天生的)/我之于他才如此陌生”,就是张枣的诗观和自视。该诗虚构戏剧化角色传递张枣两个诗学策略,一是“我”可以分身为作者和读者,二是分身为男女两性,前者融进读者的反观,表达诗人关于技艺的标准和自信,后者增加女性甜柔、弱婉调式,整体上达到了张枣追求的圆融、甜润的汉风。而“灯芯绒”越旧越美的格式,正是张枣着意的古典美的先锋感。
进一步探看,张枣不少诗中的女性角色都是诗人写者自我另一面的戏剧化出演。“我听见你的自语/分叉成对白,像在跟谁争辩”(《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这是张枣敞亮的对话诗学。从写诗初始,张枣就找到对话的诗意建构奥妙。其中的诗学效应,既有余旸所说的“把‘传统’转变为一个倾诉的对象‘你’”[13],也合乎萧开愚感觉的“是一个好像因为住得太远,形象显得虚幻的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分享到春风般的甜滋滋的爱意”[14]。张枣的戏剧化写者自我,可以是“忽而我幻想自己是一个老人”(《早晨的风暴》);可以是一个娇美的女性,“隔壁的女人正忆起/去年游泳后的慵懒”(《杜鹃鸟》),“你晴天般的指尖向我摸索”(《四月》)。对自己钟爱老人幻觉,张枣给了这样的美学阐释:“中国人由于性压抑,所有人只向往青春的荣耀,仅有几个人想到老年”[15]。显然,张枣疏离诗坛年少冲动型的青春写作,对他而言,老人意味着深思熟虑、技艺老到。而虚构女性口吻,一是古代诗人代拟、代内书写的传统,何其芳的《休洗红》、戴望舒的《妾薄命》、卞之琳的《妆台》都作了现代发展;二是张枣个人需要的调式创新,他传诵最广的《何人斯》,幻美氤氲全篇,但美中蕴谜,说话者和聆听者到底是谁,颇为难解。陈东东既视该诗把传统化为一个老人,又说诗中“我”和“你”只是“一片雪花转成两片雪花”般分开的自我[16]。结合前述,“我”也可视为张枣写者自我中的女性角色扮演,对着诗歌美学传统中的神秘知音倾诉“你我一体”的亲密情感,诗篇把女性的音色、语气、语态发挥到极致:“你此刻追踪的是什么?/为何对我如此暴虐?”“我抚平你额上的皱纹”“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这种女性语吻,正是张枣喜好的“燕语呢喃”调式。
分身或化身的戏剧化书写,既是张枣调皮聪慧的性子使然,也是他对一切封闭、限定突围的需要。他坚信,诗歌产生于关系而不是幽独中。他进入戏剧化角色体验中,不是去反映生活现实,而是在角色中凝神、相遇、谛听,再吐纳微妙的倾诉,呈现彼此的绚烂光华。即便面对本来唯一的那个“我”,他也要找一个“之外”的“她”,来对话,来互观、互赏。《深秋的故事》是张枣将写者自我分身为两性的另一典型作品。“我”登上梯子,“接受她震悚的背影”,这是写者形象分身,“我”站在外边看里面的“她”如何惊艳;“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暗示“我”跟着“她”的思绪、想象飞跃;“情人们的地方蚕食其它的地方/她便说江南如她的发型”,“们”喻指写者自我两身,他们的语词、想象所合成的作品一如江南式的婉转清丽,一如她的“发型”。后文的“乳燕”隐喻诗意的精灵;“她的袖口藏着皎美的气候”,是对诗歌变幻技艺的自我确信。如果不结合《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等张枣整体诗作,不紧扣他的元诗理想,诗中“她”的背影、发型、袖口,加上“故事”的鬼脸,《深秋的故事》被理解成恋爱主题也顺理成章。关于张枣的女性面具,臧棣似乎给过知情者的暗示:“最好的妙计依然是美人计”[17]。可以说,张枣的戏剧化功夫实现了他诗歌美学中“机密”的一面。
二、作诗意策源地的戏剧性处境
“变”是艺术家的宿命追求。张枣在不同的写作时期,还采用了虚构他者戏剧性处境的方式,这些他者有的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有的则是西方经典人文作品中的形象,集中起来有《楚王梦雨》《刺客之歌》及《历史与欲望》组诗中的《梁山泊与祝英台》《罗蜜欧与朱丽叶》《吴刚的哀怨》《丽达与天鹅》《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一个德国间谍的爱与死》《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卡夫卡致菲丽丝》《海底被囚的魔王》。寻找不同的他者戏剧性处境,除了表达形态各异的生命悖论,更能激发语言的再生力,如钟鸣所言,“每一首诗,都该有一套自己的术语,而且,只对本文有效”[5]。张枣的诸多戏剧化诗篇近年被他的好友们揭开了其中的诗歌信仰、海外孤独等主题,但诗中如何借他人处境表达自我,各个戏剧化处境怎样推动诗意想象和语气节奏,值得细品慢研。
现代诗中的“戏剧化独白”不同于古代诗歌中的代拟写作。古典闺怨、相思情境趋向类型化,如李白的《长干行》《自代内赠》,都是女性思远的口吻模拟。现代戏剧化独白诗中的不同角色处于具体情境,其命运、心理自有殊异,同时又不是诗剧,因既不发展情节,也不呈现激烈外部冲突。西方近现代经典的戏剧独白诗形成了一个延续,如勃朗宁的《戏剧性抒情诗》集、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叶芝的“疯简”系列等。中国现代时期的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穆旦曾作过尝试。当代不少诗人也在这个技艺角度小试牛刀,如西渡的《少女之歌》《菩萨之歌》,臧棣的《相手师的独白》。在后一文本中,“相手师”所处的位置是“街角”,诗人抓住这一线索展开想象,处理“街角”向“历史的不易察觉的拐弯处”的转喻,完成由客观地理向人文语境的过渡,然后借“相手师”的视点、语吻进行延伸、变形,深入历史和时代中的阴影部分,都是诗人戴着“相手师”的“面具”进行的观察和判断。
张枣的戏剧化独白还是服务于元诗诗学。从角色选取角度看,他早期尝试的《楚王梦雨》戏剧独白既暗示了他自己的“楚文化”情结,又融合了“梦”的氛围,楚王几乎就是诗人自我的“面具”,典故中的巫山云雨、人神相通只是表面依托,最终变形为诗人的诗学理想。张枣借拟了楚地的幻想、巫术文化气息,用轻呼、祈祷的语吻虚构着楚王渴望与神相通的焦灼,表达的是张枣自己对传统诗意、空白美学的吟唱。比较他以前的作品,以及后来的同主题诗篇,《楚王梦雨》因为有了楚王这个戏剧化角色,抒情更加急切,语气更亲昵,叹词“呢”依性使用。开篇“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比张枣的非戏剧化独白诗来得直截了当,和传统神会,衔接古典的感性和唯美,是他写诗的总体志向。“我的心儿要跳得同样迷乱”“还燃烧她的耳朵,烧成灰烟/绝不叫她偷听我心的饥饿”,有了戏剧角色,语气分外热情。诗中借楚王的戏剧处境衍生想象:“宫殿春叶般生,酒沫鱼样跃”,这是关于写诗结构、语词的灵感隐喻;“枯木上的灵芝,水腰系上绢帛”,楚地的草木和华服正好解救诗的语言;“佩玉”“竹子”“荷叶”同样是张枣对戏剧处境的因地制宜;而“澌澌潮湿”“湫隘的人”之类的古语也是最恰切的传统激活。可见,戏剧化独白带来了不同的细节、语气和辞藻。当然,熟悉诗人执念的读者,注目的还是缭绕诗篇的“那个一直轻呼我名字的人”“叫人狐疑的空址”“空白的梦中之梦”这些写者心理的言说。
到了国外,张枣诗中的戏剧化角色处理大变,《刺客之歌》增加了场景动态细节和人物关系,并在角色和自我之间制造了间离感。荆轲刺秦为国捐躯,张枣赴德国则为借外语更新汉诗写作。对这首诗,柏桦读出的是诗人在异国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4](P25),钟鸣更细化了诗中反讽、解嘲的语调以及刺客唱词的松弛感,并提醒研究者思考诗人和刺客互涉的理由[5]。荆轲的历史本事充满了牺牲、危险,但诗中反复回荡“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暗示张枣不只是承受孤独和离开母语的牺牲。“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后果”,荆轲无谓地冒险,而“我”去德国终归寻到了些丰富汉诗的新器。在虚构的戏剧处境中,荡漾着威仪的“英俊的太子”是“我少年的朋友”,可能隐喻诗人的某位诗友。诗篇最后回到“我”的写者处境,“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似乎是对离开母语的无奈,但跳出内容细节看全诗,《刺客之歌》罕见地一韵到底,显示了张枣并未“抹杀另一地”的努力和抗争,颇耐人咀嚼。
有意味的是,“刺客”这一主题又在张枣的《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一个德国间谍的爱与死》《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注:后文分别简称《间谍》《士兵》)中得到延续,且都是戏剧化形式。《间谍》中是德国人在夜莺歌唱的土地历经战争、失去生命和爱情,《士兵》是懂俄语的德国人被判死刑,都和张枣远赴异乡的命运相似,但比起1986年的《刺客之歌》,更多了悲剧性和速朽感。也就是说,张枣在这两首戏剧独白诗中流露了当时的低落心境。生活困难等于诗歌困难,张枣在两首诗中进一步发挥了元诗书写个性。比起《士兵》的不断加速音高走向临终,《间谍》组诗中设计了复调,有“夜莺婉转”的背景,“醉汉的歌唱”,也有“我”和“她”隐隐约约的对话,还有“我”的祈祷……这些复调增加了全诗的含混,但根据张枣在诗中的音型建构,大概可以划分出几种基调。夜莺婉转和醉汉歌,是失意、痛苦之绪。“我”和“她”的对话则围绕情感、时间:“一个古老的/传说,我总是不能遗忘”,这是女性对爱情的信仰;“我正代替另一个人活着”,这是生死相继相成的时间循环观,和博尔赫斯的“别人将是(而且正是)你在人世的永生”[18]异曲同工。对话还穿插“她去井边汲水,/把凉水洒向汗晶晶的发额和颈脖”片段,将中国古典的感性细节移接给西人。“我”的轻呼祈祷型诉说则关涉元诗:“主啊,你看看/我们的新玩意:小巧的步话机/像你的夜莺”。“步话机”隐喻张枣的对话诗学,诗人把它和主的妙音联系起来,把对话观自觉地崇高化,接着是呼请诗神降临:“主啊/调遣你的王牌军”、调遣“你可怕的鸽子”,语气热切诚恳。可见,《间谍》戏剧化独白组诗容纳了张枣当时的多重复杂心音。
《历史与欲望》组诗的写作是从中西经典传说、故事中更新诗意,它们属同类题材,也关乎爱和死,但诗人为每一对爱侣虚构不同的具体情境,在情境中孕生诗人对语言的拯救和突围。《罗密欧和朱丽叶》以情侣的死别发明“来世是一块风水宝地”“死永霸了她娇美的呼吸”“像白天疑惑地听了听夜晚”“杀掉死踅进生的真实里”这些幻美的主题和修辞,产生语言现实的来世般极乐感。《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结局被诗人发挥为新的美学:“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她感到他像图画/镶在来世中”“这是蝴蝶腾空了自己的存在/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他们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蝴蝶成了器皿、装置,情侣亦如同诗人写者自我对读者自我的震撼,爱就是美,美即爱。《吴刚的哀怨》借吴刚对嫦娥的思念,表达“未完成的,重复着未完成”,是对理想诗歌、理性爱情难以企及的遥叹,以及“诅咒时间崩成碎末”的无力感。
在张枣的戏剧化诗篇中,《卡夫卡致菲丽丝》的戏剧化独白与其他不同,既非纯虚构的形象,也不是神话、故事中的角色,而是洞察历史现实的深刻作家,它的音势不可能甜美,张枣但也不直接靠着卡夫卡的批判性。钟鸣对这一文本中的潜对话、笼子、孤独的阅读者、内心自由、俄耳甫斯声音作了精彩分析[5]。贯穿该诗的还有空白诗学、自我猎取观。借卡夫卡的处境,张枣悲惋地唱着“菲丽丝,我的鸟/我永远接不到你,鲜花已枯焦/因为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鸟,也是张枣心中最高的诗,但也是未来的空白和虚幻。“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道出了张枣一直在因地制宜的作诗意图。在寻找自我的迷途中,张枣和卡夫卡是相通的:“而我,总是难将自己够着”。至于被神性化的写作,诗人直诉“太薄弱,太苦,太局限”,光明的诗(菩提树喻指)则“太远,太深,太特殊”,戴上卡夫卡的面具,张枣表达了写者的精神危机。
三、变换琳琅的戏剧化人称
张枣的多样戏剧化兴致在早期成名时就为人共睹。比如将诗艺虚构为舞台展演,上述《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即为证;比如把身边诗友来往看作一个交互的戏剧场面,反复在心中演绎各人的动作、表情、个性,再发明个人化修辞描绘诗界面孔,如《秋天的戏剧》。最具技术难度的戏剧化技巧是他的人称调遣,许多诗中的“你”“我”“她”“我们”穿来插去,夹杂在身份名词间,让读者迷失在戏剧化面孔中。柏桦曾表示,“人称变换技巧”是张枣主要诗歌技艺[4](P16-18)。
人称技术一般在小说、戏剧中微妙运用,抒情诗的典型常是“我”对某个具体的“你”或代表时代、国族的集体“你”说话,人称指涉简单易懂。但偏好诗意隐藏、丰富的一些现代诗人在增加诗歌的戏剧化、故事化因素同时,把自己化身别人,在自我之间、说话者和听者之间、自我和他者之间制造交互、差异、跳跃和省略,人称指涉就显得复杂了。如卞之琳《音尘》中的绿衣人、远人、“我”“他”以及之外的“你”,《候鸟问题》中的“你”“你们”,都需要读者小心分辨。张枣堪称当代这方面的佼佼者,钟鸣是最了解张枣的学者,他给张枣个性的定义包含“聪慧、狡黠、好戏谑”,创作喜好“自窥与转换”[19]。可以说,读张枣的诗,弄清人称所指是急要。
张枣的一类元诗书写敢于越轨,他把现实中的诗界情形纳入诗的图案,诗友的脾性、诗品,诗友和他或融或冲的关系,隐约呈现在他的笔下。但他不具体点名,都用“你”“你们”“他”“他们”“我”等代词进行隐蔽化,且诗歌行为事理和生活事理等同,读者难以捕捉背后的微讽真意。《秋天的戏剧》前三节总体抒发“我”对诗坛不同面孔的依恋、怜悯、苛求、无奈感觉以及赋形动作,从第四节开始,各色人物出场,“使我的敌人倾倒”的“她”,“把我逼近令她心碎的角隅”的“他”,“我病中的水果”的“你”,“夜半星星的密谈者”的“你”,等等。诗人取名“戏剧”,或许隐喻着人间关系的戏剧、想象和修辞的戏剧、人称代词的戏剧,颇为琳琅满目。张枣把诗生活搬进文本,能对号入座的只有代词后面的当事人或知情人。而《桃花园》中,他把不融洽的诗者统称“他们”,赋予他们戏剧化动作:“每天来一些讥讽的光,点缀道路。/怪兽般的称上,地主骑驴,拎八哥,/我看见他们被花蚊叮住,咬破了耳朵,/遍地吐一些捕风捉影的唾沫”。这些高度隐晦的修辞表达了张枣对诗坛美学异见者的疏离和笑侃,他们装模作样、互相搬袭。
更隐晦的是张枣将人物身份和人称设计并纳,置入一个看上去具体其实空幻的情境,如《镜中》《姨》《十月之水》等。《镜中》无需再经典长谈,《姨》作为吸引众多研究者解谜的神秘诗,迷障勘察还未突破。该篇短短的十几行,有“他”“我们”“她”“姨”“我”“你”“妈妈”诸多指称,这些指称的关系还被叠加、交叉,犹如多个镜面一起折射几个面孔,幻化出幽深玄异的场景。从人称之间的戏剧化关系看,“他”有着“我”“多年后的额头”,属于主体在时间中的关系,即当下写作的“我”退回过去某个时刻坐着的“我”去想象未来看望姨的“我”(即“他”),“我多年后的额头”是后退式回忆;“我每天都盼望你”是未来式畅想。而姨是谁呢?是“他”看望的人,“她”也眺望“他”,但又是“镜子的妹妹”。由此不妨大胆假设,“姨”就是时间本身,张枣探索的是时间镜像中的人和时间本身的形象,诗篇复杂戏剧化人称中似乎包含这样的美学逻辑:第一层面,“妈妈”照着镜子,在镜中看到的既是自己的影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是“姨”,但人照镜看到的更是时间,而时间也如镜般空幻,因而,时间“她”(即“姨”)也是镜子的妹妹;第二层面,“我”思量时间,也就是看望“姨”,“她”也眺望“我”的未来样子“他”;当时间“姨”被“我”或“他”看望、研究时,她也就有了“羞惭”的情态和呼吸;第三层,在时间面前,人只能充满“忧伤”。如此解读,戏剧化人称关系和情理逻辑似还通畅,况且张枣的主要诗歌主题是元诗和时间。短诗用这般繁复的戏剧化人称表现时间,几乎凝聚了人与时间的主要交集形态和情感模式,形式和精神皆令人叹服。
换个角度看,张枣能巧妙利用戏剧化人称,并非只源于技巧实践,而是他对“自我”的反复寻找、研究和创造,时间中的“我”,写作中的“我”,人际关系中的“我”,是他创作动力重点所在。《镜中》是张枣早期对写者“我”的镜像戏剧化,后来他又再度试笔,写下《看不见的鸦片战争》,用“皇帝”角色引领、呈现戏剧化现场,增加了故事化的生动性。
在抒情诗中,故事化是佯装的,戏剧情境中的角色和人称不为增添外部事件的冲突矛盾,而是为虚构抒情的新情境和新言说。《看不见的鸦片战争》组诗虽然只完成一首,但张枣显然意在创新元诗技艺。开篇“皇上”亮相,与《镜中》《十月之水》《星辰般的时刻》中的皇帝、国王呼应,只是本诗戏剧性情境戏仿了更具体的历史细节,用“后庭宫苑”“太监耳语”“武将”“龙椅”支撑着“皇上”角色的经验真实,加上对话的场面,戏剧片段感很强。有趣的是“鸦片战争”题名,如果说开篇皇上问话太监南疆炮台情形有点历史主旨,但下文的场景和对话全偏离了“战争”经验,故诗人用“看不见”限定“战争”,确保万无一失。诗中“战争”的内景是什么呢?是张枣内心对写作、虚构的权衡,对时间的抵抗。诗篇主要在“太监”和“皇上”以及不同人称变化的戏剧化关系中展开。“他”忽而是太监,忽而是皇上;“你”忽而是“皇上”的说话对象,忽而是虚构者的说话对象,还夹杂一个耸肩女人连声称“我”。绕过戏剧化人称来看,在这个后宫,太监“用漂亮的句法谈没有的事”、谈“小雀儿”,显然属元诗拟象,“小鸟”“小雀儿”,是张枣对诗歌的常见昵称;太监裤兜里的“玉环”,光洁、圆润,隐喻诗歌理想的样子。太监时刻观察皇上,但看到的情景是皇上对小胖婴孩说“叫我一声亲爹,我就把闹钟给你”,诗篇跳跃性突兀,不妨联系张枣后来的发福来阐释,岁月无情地把帅气诗人变为中年胖叔,“把闹钟给你”实为张枣对时间的诅咒。由此,戏剧化人称中的角色关系显示出来了:太监和皇上都是张枣写者的化身,太监是“我”清醒、警觉的一部分;“皇上”是写者此时的样态,他发着福,也留意着各种诗歌“云朵”形态,灵感天空中的各种“异象”。“皇上”睡着时大地显示“图案”,是他留下的诗绪轮廓。诗篇中的戏剧化“战争”和人称变化,都指向写者对诗歌写作、对时间的内窥。
由此看来,张枣调动人称变化技巧,但诗篇仍符合他的核心诗观:“绝不会自外于自己”。绝大部分人称指涉都是张枣内心关于元诗、时间的镜像出演。如《狷狂的一杯水》中的“薄荷先生”,诗中用“他”这一人称带出系列动作和心理,但实际上,“薄荷先生”就是张枣自我的戏剧化形象,他的“绝不会自外于自己”就是张枣的写作自况,诗中那满满的一杯水“内溢四下”又外面般“欲言又止”“忍在杯口”,象征张枣自我内盈的书写姿态,对内心虚构就是一切的信奉。结尾处,张枣直接改用“我们”人称来表达“来世”诗学:“它伺者般端着我们/如杯子”。未来的诗,理想中的诗,以“少”胜“多”的诗,把诗人如杯子般稳稳举着,维持他和生活的平衡。
四、结语
技艺不是纯粹形式,它本质上属于诗歌精神的重要部分,具体到张枣处,它是美学崇高的彰显。戏剧化分身、戏剧性情境、戏剧化人称都需要想象力或虚构能力,想象力本身就是诗歌主要形象。张枣认同史蒂文斯的诗观,把想象力称为“崇高”事物,“想象力做主体,穿透万物,占据现实……使生命富有趣味,拓展主体真实”,想象力的力量,能“成为猛虎,可以杀人”[10]。本文所举戏剧化诗篇例子,都透出了张枣用想象力改变现实经验、诞生新的存在和审美秩序的妙处。在戏剧化技艺中,他表达的多是元诗诗学,因此顾彬曾建议,我们要学会“如何把他的‘我’解读成一个诗学面具”[20]。
张枣诗篇的难懂一直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事实,等待着我们进入文本内部。近年有关他的细读批评不断突破,当然,也陆续呈现了分歧和矛盾。在本文看来,如果细读不是拘囿于封闭的文本,而是联系张枣所有诗篇,以互文的视野参照彼此,再联系张枣的诗学观和批评实践,形成视界融合,或许能提供新的阐释可能。本文选取张枣的不少戏剧化诗篇,它们是戴着面具的抒情,产生过多元化解读,此番尝试互文解读和视界融合,亦是想探综张枣隐藏的诗意机制,当然谬处也难以避免。某种程度上,细读诗人也只是自己想要一个美学“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