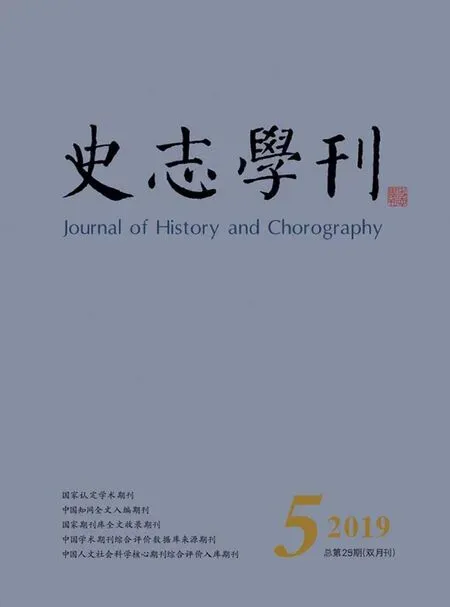《四库提要·洛阳伽蓝记》疏证
林丹妮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1)
一、《洛阳伽蓝记》的作者
《洛阳伽蓝记》属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撰者杨衒之,于正史无传,故究其个人情况,历来聚讼纷纭。如姓氏即有不同记载,一作“羊”,除唐刘知几《史通》、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外,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明高儒《百川书志》、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等亦同。二作“杨”,除《隋书·经籍志》外,还见于隋《历代三宝纪》、唐《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法苑珠林》、宋《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佛教史籍,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史书如《旧唐书》《通志》《宋史》等,明清以下更为众多。另有第三种,提要中未论及,作“阳”,见于《广弘明集》《新唐书》、元《河南志》等。以上三种记载中,“羊”通常被视为讹误,“杨”出现最多,亦是四库馆臣所采纳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此情况已言明[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衒之姓,诸书并作‘杨’,与隋志及本书合,惟广弘明集或作‘阳’,知史通作‘羊’者,不足据矣”.中华书局,1980.(P432)。也有主张“阳”者,认为衒之当属北平阳氏[2]该说似起于周延年(子美)、又有郑骞《洛阳伽蓝记丛谈》.景午丛编下集.燕台述学.台湾中华书局,1972.454-456.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文史哲,1956,(11):11-12.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19.,其名合于史载阳固家的排行次第,其人亦与北平阳氏文学显达的地位较为相符,情理甚通,但直接证据仍不够充足[3]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周氏之说固自有理,但各书多作杨,新唐书及元河南志之阳疑亦是杨字之譌(周氏所引广弘明集作阳,但查嘉兴藏本广弘明集亦作杨)。即或不误,孤证只字,究难碻信。因仍旧作杨,录周说以存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56.另,《广弘明集》与《续高僧传》同为道宣撰,而后者亦作“杨”,更使“阳”说成疑。,因此可备一说,难成定论。今提及衒之姓,多仍旧贯,以“杨”行。
衒之里贯,《广弘明集》卷第六《辨惑篇·列代王臣滞惑解》载其为“北平人”,并非如提要所言之“未详”。结合提要上文讨论衒之姓氏时对同样以《广弘明集》为据的“阳”姓说的忽略,可推测四库馆臣撰此提要时忽视了《广弘明集》对衒之的记载。至于“北平”的确切地点,据《魏书》卷一百六上《地形志》,名为“北平”之郡有二处,一为平州领郡,秦置;二为定州领郡,孝昌中分中山置,治北平城。衒之究竟是平州北平人还是定州北平人,难于论定,此争议与姓氏争议亦有所关联。“阳”乃平州大姓,若衒之姓阳氏,则为平州人的可能性较大;若姓“杨”则相对更难判断,时见从定州说者。但亦有学者提出平州北平沿自汉魏当属本名,而定州北平为后起,从而认为无论衒之姓杨或阳,平州可能性均大于定州[1]曹道衡.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3).(P30-31)。
至于衒之官职,各本《洛阳伽蓝记》所题撰者皆为“魏抚军府司马”,因此他在写作此书时为抚军司马并无疑问。但据书中所述,衒之却不止担任过抚军司马,此前他还有担任其它官职的经历。《洛阳伽蓝记》卷一载:“永安年中……衒之时为奉朝请……”证明衒之在永安年间曾任奉朝请。又有《历代三宝记》载“期城太守杨衒之”、《续高僧传》载“期城郡守杨衒之”、《法苑珠林》载“元魏邺都期城郡守杨衒之”,可见他又担任过期城郡的太守。此外《广弘明集》载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据《魏书》所载北魏官制,秘书监为三品,地位远在五品抚军府司马之上,若其属实[2]对《广弘明集》所载衒之曾任秘书监之事,亦有学者曾表示过怀疑,如曹道衡《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一文即从任职时间及衒之身份地位角度进行考证,认为其在魏末曾任秘书监一事不足信,可备一说。,当为衒之所任最高官职。
二、《洛阳伽蓝记》编纂背景及主要内容
《洛阳伽蓝记》开篇阐明杨衒之撰书背景及缘起。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佛法推崇备至,大量兴建佛寺。据《洛阳伽蓝记》所述结合《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记载,可知洛阳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18),至西晋末永嘉年间,城中寺庙为42所。晋室南渡之后,洛阳主要在北方少数民族控制下,历经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寺庙继续增加,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数量为500,及至《洛阳伽蓝记》所录的盛极之时,曾达1367所;然魏末永熙之乱,寺庙多数被毁,当由北魏分裂出的东魏政权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534),并弃洛阳而作都于邺时,洛阳余寺仅421所,区区16年竟骤减如此,可见期间所历变乱之巨,战火之深。武定五年(547),衒之重览洛阳,睹其破败情状而起麦秀黍离之悲,因此他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出发点是追叙旧日佛寺盛况以使其事传于后世,提要之言与衒之书序自述大意相同。但衒之撰书意图似未必仅止于此。《广弘明集》云:“(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衆庶也。”认为此书意在刺王公之骄奢,呼百姓之疾苦。后又载衒之曾经上书述称僧徒泛滥之弊,希求予以整治[3]《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列代王臣滞惑解》“……(衒之)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爲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啓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勅,知其真僞。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33.。由是观之,衒之撰书或亦包含针砭之意,《洛阳伽蓝记》满纸极言佛寺盛况并非全然出于怀念之褒扬[4]《景德传灯录》记载衒之慕佛,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盖僧徒造作诬词,以复其非毁佛法之雠,犹之谓韩文公屡参大颠耳,不足信也。”(P433),明为忆其辉煌,暗则斥其铺张,至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的现实批判目的。
《洛阳伽蓝记》在序中便介绍了洛阳城四面的基本情况,包括新旧名称演变等,作为总领,一目了然。提要此处似遗漏“西面”未提。全书五卷,先叙城内,再依序叙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确乎结构井然,体例明晰,对汉魏故城空间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勾勒复原。衒之的文才在书中亦颇有显现,其行文骈散结合,时而壮丽,时而清逸,语藻丰赡而纵敛自如,与另一部北朝名作、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时常并称。二者虽皆属地理类著作,皆写景叙史两相映,但风格仍有不同,《水经注》之自然山水气象尤妙,而《洛阳伽蓝记》则更以历史文化为侧重。
三、《洛阳伽蓝记》的历史意义
在史实记述方面,《洛阳伽蓝记》具有相当价值。关于尔朱荣等变乱,卷一城内首篇《永宁寺》所录最详,较完整地叙述了尔朱荣策划“河阴之变”的前情后果:明帝新崩,身为北魏权臣的尔朱荣以追查死因、帮扶朝政为由,勾结元天穆,以铸造铜像的方式选出长乐王元子攸为君,并与其商议联合攻洛阳;又发动河阴之变,借故将北魏王公卿士及诸朝臣集合至河阴屠杀殆尽,立元子攸为庄帝;但庄帝因不满尔朱荣专权,亲手杀之,而其后又被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绞死。这些记录与《魏书》《北史》等正史中尔朱荣等人的传记[1]魏书(卷七十四)·列传第六十二.北史(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足可相参。除却沉重的政治变乱,《洛阳伽蓝记》也关注“艺文古迹”,对伎乐歌舞、建筑景观等时常描摹细致;甚至还打开眼界,广纳异域风闻,例如卷五城北《闻义里》篇,“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其后历历细数惠生远赴西域所经诸国风物人情,采纳了丰富的奇观异闻。
《洛阳伽蓝记》的史料意义引起了后世史家的重视。提要中所举“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出自其刘知几《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所用的赵逸一条源于《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兴尼寺》。众所周知,《十六国春秋》《晋书》等史册中不乏有关苻生凶暴的记载,如其幼年时即为其祖苻洪所厌[2]苻洪云:“此儿狂悖勃,宜早除之,不然,长大必破人家”.十六国春秋(卷三十五)·前秦录三.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载记第十二.,嗣伪位后其下薛赞、权翼等亦对其有恶评[3]“(薛)赞、(权)翼说(苻)坚曰:‘主上(苻生)猜忍暴虐,中外离心’”.十六国春秋(卷三十五)·前秦录四.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载记第十二.,其曾经杀害过妻子樊氏、梁氏及毛贵、梁楞、梁安、雷弱儿、程肱、强平等众多大臣,且生活无度,沉湎酒色,常以种种残忍行径为乐,暴行几乎罄竹难书。而《景兴尼寺》篇中隐士赵逸却言道:“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君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认为苻生之凶暴是史官笔下的歪曲[4]此说后世仍有认同,如近人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亦认为苻生凶暴为史家诬陷。两晋南北朝史(第六章)·东晋中叶形势下·秦灭前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7.,此即刘知几所采之见。
《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之所以堪为史料,连不苟引据的刘知几亦采信其言,这与衒之的撰作态度是密不可分的。衒之自称“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在下笔时也的确致力于做到这一点,极重真实性。在卷二城东《明悬尼寺》篇中,衒之曾实地记录阳渠石桥桥墩上所刻的建造年代,由此纠正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里的错误,并对前人这种未经实地考察的落笔批判激烈,直言其“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其对待史实根据的严谨程度可见一斑。因此,《洛阳伽蓝记》中所载史实的信度可谓相对较高。衒之不仅考史,还善作解读,这在书中也不时穿插,如提要所言“解苗茨之碑”,出自卷一《景林寺》。永安年中庄帝于华林园骑射,随从百官皆来读魏文帝所立“苗茨之碑”,疑“苗”字有误,不得其解。时任奉朝请的衒之解释道:“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虽仅释一字,亦精审有见地。
至于提要指瑕一句,实则存误。余嘉锡、周祖谟、范祥雍等在辨证校释至此时皆有所论及[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433-434;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27-128;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187.。首先根据衒之原文,谈及“宅中之楼”的应是卷四《冲觉寺》中所记清河王怿宅,而非卷三《高阳王寺》里的高阳王雍宅;而“固于说诗”的批评,也并不准确,衒之原文为“西北有楼,出凌云台,俯临朝市,目极京师,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也。”是见“西北有楼”而引古诗句,表示正如古诗所云,并非认为诗句所言之楼即此楼。因此,“固于说诗”的并非衒之,反是提要自身。
衒之撰《洛阳伽蓝记》时,为做到内容丰富与行文明畅两相兼得,采取了正文与子注结合的方式,提要引《史通·补注》言此体例并无疑问,然而径称注文佚脱,却是又一谬误。《洛阳伽蓝记》的子注并非佚失,而是自宋以后在传抄中与正文连写混合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此即有所考证[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P434-435)。据刘知几此言,知《洛阳伽蓝记》至少在唐代仍以正文子注分列明晰的面貌存世。而《史通·补注》下文又云:“若萧(萧大圜)羊(羊衒之)之琐杂,王(王劭)宋(宋孝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余嘉锡由此认为刘知几“虽讥其琐杂,不能不服其该博也”,从而推断今《洛阳伽蓝记》中许多不涉及伽蓝的奇闻异事原本应当出于子注,即可知子注未佚,仅同顾广圻《思适斋集》所言,“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
清人吴若准评《洛阳伽蓝记》云:“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巨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2]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不仅如此,《洛阳伽蓝记》具备历史价值的同时,在中古文学、地理、佛学等多方面也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后世影响实为深远。关于其版本,就五卷本而言,明代主要有如隐堂刻本、吴琯刻古今逸史本、广汉魏丛书本、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等,至清代有嘉庆十年(1805)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嘉庆十六年璜川吴氏活字印真意堂丛书本。注释本自清人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始,“重为编次,厘定纲目,依据众刻,校其异同”,较早对分段及厘清正文与子注作出了尝试。吴若准之后有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民国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陈寅恪曾对以上校注本有所品评,言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唐本虽正文三倍于吴本,但分别正文子注的标准多由主观,未必符合杨书原意;而张本最晚出,合校矜慎[3]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6-158)。近人校注本中,以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及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最为通行。范本不别正文子注,内容丰富,材料详备;周本区分正文子注,校注精密,体例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