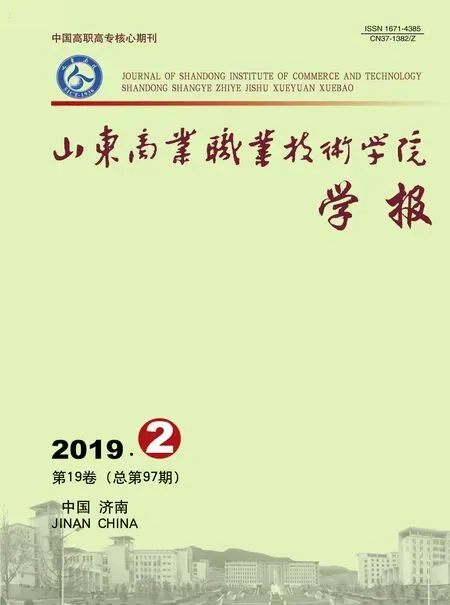在囚笼中挣扎的金丝雀
——试析曹禺剧作中的反抗女性形象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其代表作《雷雨》的问世正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曹禺对于女性人物的偏爱,恐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位作家能出其右。他创造了一大批生活在各个阶层的经典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对妇女的关怀、同情和理解。曹禺笔下的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封建帝制虽然结束了,但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依然根深蒂固,同时很多人又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思想与旧文化之间的冲突,编织着女性人物的命运,展开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这些女性形象如同囚笼中的金丝雀徒劳地挣扎,无力地反抗,最终都以悲剧的结尾收场。这也印证了那句哲理名言:“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梦醒了发现无路可走。”曹禺以其塑造的一个个悲剧形象引发人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唤醒人们心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推动时代的变革。
一、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纵观曹禺的戏剧作品,可以发现,他所创作的女性大都是弱者形象,都是被男人欺辱的对象,其中一些女性美丽、真挚、善良,具有良好的品德和人性。20世纪初期,虽然中国已经结束了封建帝制,但是封建伦理和纲常仍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即便这样,这些女性仍然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敢于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封建等级制度、男权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作斗争。[1]这些女性有的受过新思潮的洗礼,面对封建伦理和男权社会的天罗地网而选择奋起反抗,比如蘩漪、陈白露等,这些女性的反抗精神最为突出,也最有力量。此外还有在旧时代受凌辱和奴役的劳动妇女,这些女性虽然没有受过新教育,但是由于命运受到压迫,也奋起反抗,如待萍、四凤、翠喜、花金子等。以下就这两类女性形象展开具体的论述和分析:
(一)受到新思潮薰染的知识女性
曹禺的戏剧背景大都是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使妇女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随着西方妇女解放主义思潮的传入,中国也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秋瑾、葛健豪和唐群英等社会活动家发起了要求男女平权、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女权运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新女性,她们能够接受西式的教育,接触到西方的思潮,因此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向往。但是由于封建主义纲常伦理的枷锁十分强大,她们被囚禁在牢笼中,成为男人的玩物和精神奴隶。就是在这样的命运之下,她们展开了奋起反抗和挣扎。
《雷雨》中的蘩漪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人,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渴望自由和爱情,显然与周朴园所努力维护的封建传统下的“旧式家庭”是格格不入的。她与周朴园相差20岁,与他之间没有爱情可言。在嫁给周朴园之后,在周公馆生活的18年里仿佛坐监狱一般,在无爱的婚姻里逐渐被磨成一个石头一样的死人。周朴园极力维护封建伦理统治和宗法观念,要求蘩漪遵守妇道,不能有任何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这使得蘩漪心中感到苦闷和压抑。在最初的反抗中,蘩漪的表现还是极为克制,如“喝药”这一场戏中,周朴园要求蘩漪喝一碗苦药,而且是当着全家的面儿让她喝的。蘩漪苦苦哀求道:“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但是周朴园一再紧逼,于是蘩漪最后不得不屈从。第二次是周朴园要求蘩漪去看病,蘩漪发出“我没有病”的呼声,但最终还是屈从于周朴园的淫威。
直到周萍出现在她的生命当中,唤醒了她最原始的欲望,蘩漪内心又燃起了对爱情的冲动,无法遏止地与周萍展开了一段“乱伦关系”。她把希望寄托于周萍身上,渴望周萍来拯救自己,但是周萍自私懦弱,徘徊于蘩漪与四凤之间,甚至与父亲奉行同样的伦理道德,用封建妇道来约束蘩漪这个“半新不旧”的女性。蘩漪希望周萍来编织她作为资产阶级小姐“爱情至上”的梦。然而周萍又对这种乱伦关系感到愧疚,于是想结束与蘩漪之间的畸形关系。被始乱终弃之后,蘩漪开始了最后毁灭性的反抗,她当着众人的面揭穿了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乱伦关系。她的这种极端反抗并没有带给她想要的结果,四凤不堪羞辱,奔命而逃,不幸触电身亡;而周萍则开枪自杀。蘩漪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发了疯。
另一个典型的反抗女性形象是《日出》中的陈白露。与蘩漪不同的是,她斗争的对象不是一个封建大家庭,而是光怪陆离的黑暗社会。陈白露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五四新思潮”的熏陶,热情而富有幻想,她渴望拥有一个意中人和幸福的家庭。在遭遇家庭变故之后,她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只身来到北方洋城天津闯荡,成为名噪一时的高级交际花,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周旋于潘月亭、张乔治等巨商富贾中间。但是由于奇特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性格,陈白露对自己的处境充满了厌恶。每当奢华过后、夜深人静之时,她又感到一片空虚,找不到自己的归宿,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既热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当孤女小东西受到黑三的迫害时,她冒着风险去救小东西,当她知道小东西打过金八的时候,便连声自语:“打得好,打得好。”旧时恋人方达生的到来,激起了她内心的激荡,加剧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当维系她经济来源的潘月亭破产之后,陈白露的账单越积越厚,她不愿意再成为上流社会的玩物,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在日出之前服用安眠药自杀。陈白露的悲剧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罪恶的卖淫制度。她的抗争失败,是对中国当时金钱至上、男权主导的黑暗社会的极大控诉,也反映了曹禺对中国女性的关怀和同情。[2]
(二)旧中国受奴役和凌辱的劳动妇女
除了受过新思潮的女性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之外,曹禺剧作下的劳动妇女也蕴藏着与命运抗争的力量,只是不如知识女性的反抗更有力量。这类女性的反抗通常是出于无奈,是在面临极大的屈辱之时,处于人性层面考量的反抗,这正反衬出旧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伦理统治带给女性的极大压迫。这类女性的典型形象有《雷雨》中的鲁侍萍、《日出》中的翠喜和小东西、《原野》中的花金子。在封建道德秩序中,女性应该是逆来顺受的,但曹禺却赋予他们强烈的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再次体现出曹禺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关注。
鲁侍萍是旧式的劳动妇女,她正直、善良。鲁侍萍在三十年前与周家的少爷周朴园相爱,并为他生下两个儿子,这为她之后悲苦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三十年之后,当她来到天津,却发现自己的亲人却在为周家干活。在与周朴园见面之后,周朴园想要对侍萍进行救济,给她支票,却被侍萍当面撕毁。她坚决地想要带四凤逃离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重复自己走过的道路。这些都表现出侍萍对命运的抗争。
《日出》中也有这样的女性,翠喜和小东西的命运同样十分悲惨。翠喜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交际花,人老珠黄之后,为了谋生,不得不去下等妓院出卖自己的肉体,即便是这样,她心中的善良与正义仍然没有褪去。她的丈夫是一个瘸子,婆婆瘫痪在床,生出来的两个儿子还是瞎子,这都是妓女职业带给她的祸害。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她还对小金子无比关心,可见她并没有自甘堕落,而是在心中有一颗反抗的种子。小东西作为一个孤女,命运十分悲惨,不愿遭受凌辱,于是奋起抗争,打了金八。最后,小东西以一种极端的反抗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原野》中的花金子也是一位旧时代的妇女,但是她却勇于追求幸福和自由。她的性格错综复杂,时而乖巧嗔怪,时而泼辣坚强,将自己内心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她最后和仇虎在火车上卧轨自杀,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曹禺对女性人物的偏爱,与他的经历十分有关。曹禺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家庭,但是自幼能够体会到饥寒交迫者所处的困境,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他出生五天之后,生母就因病去世,对曹禺影响最大的两位女性是段妈和万家瑛。段妈是曹禺家的保姆,曹禺也是从她口中了解到农村妇女受剥削的情况的;而疼爱自己的姐姐万家瑛因不堪公婆和丈夫的虐待死去,对曹禺的打击十分大,这也坚定了曹禺要为女性的苦难生活和命运呐喊的志向。曹禺自幼跟着继母看戏,受到京剧、河北梆子等戏曲的耳濡目染,有了一定的戏剧基础。曹禺在中学时期,对演剧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并且出演《国民公敌》里面的娜拉。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曹禺广泛地涉猎西方戏剧,阅读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以及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人的剧作,这为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
二、“反抗女性”的审美特征
曹禺剧作中的“反抗女性”多以悲剧收场,无论是《雷雨》中的蘩漪,还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原野》中的花金子都无法逃脱黑暗社会的枷锁,成为封建伦理和黑暗社会的牺牲品。曹禺塑造的“反抗女性”具有十分高的审美价值。蘩漪、陈白露、花金子等反抗妇女的形象深入人们的内心,成为推动中国妇女解放的文化符号。
曹禺的剧作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日出》就是以“阮玲玉事件”而创作,曹禺以悲剧的形式呈现,对封建纲常伦理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一)曹禺对家庭至上文化的批判,揭示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
中国文化十分注重家族和家庭,提倡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成全家庭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难以实现。周朴园用家庭伦理来钳制蘩漪,还给她扣上“精神病”的帽子。曹禺目睹中国旧式家庭对人性的极端压抑,于是用这些“反抗女性”的毁灭来证明封建家庭伦理的可怕与罪恶。
(二)曹禺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进行了有力的颠覆
在中国古代,女性屈从于男性,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到了宋朝之后,甚至用“三纲五常”来约束女子,女子在丈夫死后也不能改嫁,要一直守节。女子不能选择离婚,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力。在《日出》中,曹禺将陈白露朝气蓬勃的性格刻画出来,而方达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怯懦、胆小,在情感上是被动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曹禺对妇女的不公待遇进行了有力控诉[4]。
(三)曹禺对封建卖淫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卖淫制度自春秋时期已经有之,而产生卖淫制度的根源是封建制度下女性权力地位的低下以及贫富差距的悬殊。为了创作《日出》这部戏剧,曹禺甚至去山西太原实地调查,在五台山目睹妓女的悲惨生活,这一切在曹禺内心形成了极大震撼。
曹禺在刻画这些“反抗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完全将她们作为控诉和鞭笞封建制度的工具,而是十分克制,让人物形象十分饱满。
曹禺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予以肯定。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人们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开始寻求在婚姻中人性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此外,曹禺的这些“反抗女性”性格也比较复杂,具有多样性。陈白露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女性,一面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面又在内心深处厌恶这种肮脏堕落的生活。在《北京人》中,曾思懿和曾文清的感情十分复杂,曾思懿极力维护自己的婚姻,甚至在出走的曾文清回来之后,一改往日对愫方的拒绝和排斥,甚至主张将愫方娶过来给自己的丈夫做妾,这显示出人性的复杂。
曹禺笔下这些反抗女性虽然所处社会阶层不同,但是都秉持着自己的纯真和善良,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望。封建伦理和旧社会的囚笼死死地将她们束缚住,大部分反抗女性的命运十分悲惨。《北京人》中的愫方也是一个典型的反抗女性,但是她摆脱压抑的生存困境的方法,是精神自救曹禺以此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摆脱困境,需要女性在精神上完成自我救赎,从根本上扭转自己的思想,用爱和坚强来应对这个黑暗的社会[5]。
结语
曹禺是近代中国戏剧的主要开创者,他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悲剧文化发扬光大,融合西方的悲剧艺术特征,创造出一部部经典的作品和一个个鲜明的戏剧人物。他借助这些“反抗女性”悲剧命运的塑造,既控诉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激发人们变革社会的力量,同时又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画廊,带给读者美的享受和深深的思索。
——玛格丽特和陈白露的死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