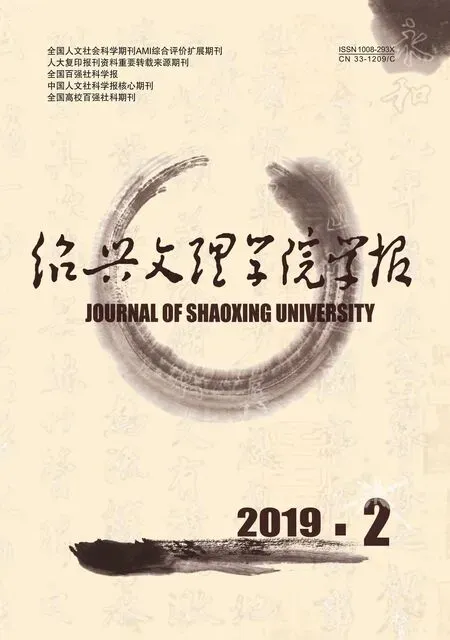六朝佛教造像文与唐代“墓志铭”
徐世民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学界关于“墓志铭”的研究论著较多,研究角度也很多,如墓志铭中的“义例”“词汇”“撰书人”“委婉语”“典故”等研究[1]1,然大多谈的是考古、历史、文物、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2]1。就笔者所见,专门从文体角度来谈的不多[注]如缐仲珊:《唐代墓志的文体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3年;李慧:《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马立军:《北朝墓志文体与北朝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部分谈及的也很少,且几乎都没有探讨“墓志铭”在唐代出现高潮之因,结合佛教造像文讨论的更未曾见。这是“墓志铭”研究中被普遍忽略的一个问题。
一、墓志铭的产生、发展及其在唐代的兴盛
关于墓志铭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从蔡邕的碑文开始,而“墓志的名称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则是在“南北朝时期”[3]3。由于人们对“墓志”的起源、概念和文体形式的理解存在很多差异,导致各书中所收录的墓志范围也不一样,如有些书中除了收录题目为“墓志”的篇章外,还有墓表、墓铭、墓记、椁铭等。因此,或许不好说某书具体收了多少篇墓志,但是依据“墓志的名称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的标准,大概的数量还是可以统计的。
就古代主要的传世经典而言,墓志铭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并不多见,如严可均辑录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唐前的墓志铭就屈指可数。当然,随着现代考古的进展,又陆续出土了不少墓志,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所辑录的墓志来看,总共有约650篇,其中汉魏约40篇。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新补的有119篇。另外还有如韩理洲所编《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隋文补遗》和《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也有一些收录。据上述这些今人辑录的文章来看,排除各书重收者,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这种墓志大概有近千篇。
然而笔者发现,这些墓志基本上都是北朝的,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南朝时期的墓志仅有11篇,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新补的119篇墓志也同样基本是北朝的,而韩理洲所编的几部书也都属于北朝。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南朝为主要代表,北朝为辅,但是在墓志的发展上却正好相反:北朝相对兴盛而南朝却显得极其弱势。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墓志铭的发展似乎与文学史不相一致。事实上,后人所发掘的墓志铭也大多是佚名之作,普遍缺乏文学性。就文学性的墓志铭而言,唐前的数量以严可均所辑录的墓志铭为标准更为合理。也就是说,唐前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墓志铭较为鲜见。
到了唐代,王朝一统,政治文化上不再有南北之分,墓志铭也就不再分南北,此时的墓志也更加发达,仅据周绍良所编《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来看,就约有5500篇[注]较早且相对较全的还有如毛汉光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版),其中收录大约有5000篇。,而后来吴刚所编《全唐文补遗》煌煌九大册,其中大部分是墓志铭,可见其兴盛之极。另据有关统计,唐代的墓志铭约有13000方[4]11-12,彭文峰也说“已经公布的唐代墓志总数量保守估计应在万方以上”[1]1,可见数量之巨。值得注意的是,陈尚君所编《全唐文补编》中除了卷150—156中大量佚名的墓志铭外,还有大量的文人墓志铭,其作者不乏著名文人。唐代的墓志铭不仅数量大增,单题目中带有“墓志铭”这种标准全称的篇章来说更是较前朝为多,而且很多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如吴讷《文章变体序说》中论“墓志”云:“古今作者,唯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5]53因此,从数量、体制及文学性来看,真正的墓志铭显然是在唐代才达到高潮的。尤其是在后世典籍中真正能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形式流行的墓志铭,更是非唐代的莫属。
二、墓志铭的含义、载体、内容及文体特征
“墓志铭”何以在唐代大兴?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墓志铭,它的载体、内容和文体形式是怎样的。徐师曾在《文章明辨序》中解释:“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日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至论其题,则有曰墓志铭,有志有铭者是也。曰墓志铭并序,有志有铭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志铭,而或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者,则别体也。曰墓志则有志而无铭,曰墓铭则有铭而无志,然亦有单去志而却有铭,单去铭而却有志者,有题云志而却是铭,题云铭而却是志者,皆别体也。”[6]148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墓志铭是刻在石头上的,载体是石碑;内容主要就是记述逝者世系、名字官爵、生卒年月、生前经历及其子嗣情况;功能主要就是为了“千载之后,陵谷变迁,欲后人有所闻知”[7]242;作墓志铭者或是逝者的亲人,或是逝者的好友,或是逝者的钦慕者,至少也是受逝者亲人所托者。因此,墓志铭的内容必然是对逝者的赞颂。也就是说,墓志铭的主要功能就是赞颂或美化逝者使其留下芳名,其重点在于“赞”。正如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所云:“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8]253曾巩认为墓志在记述逝者的生平上与史书类似,然也有区别。史书所记不择善恶,而墓志则只记逝者好的一面,对其不好的一面是不记的,即墓志的主要内容是对逝者的“赞扬”。关于这一点,甚至连耿直的韩愈都“未能免俗”[7]850。因此,就内容而言,墓志铭以“赞”为主;墓志铭的文体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有志有铭的为正体,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的属于“别体”,甚至有题目是“志”而内容是“铭”的,题目是“铭”而内容却为“志”的,这些也是别体。
我国古代墓志铭的主流是第一种类型,唐代的墓志铭也主要是这种类型,即完整的有志有铭的文章形式。下面选取韩愈所作的墓志铭《处士卢君墓志铭》来分析其特征:
卢处士,讳于陵,其先范阳人。父贻,为河南法曹参军。河南尹与人有仇,诬仇与贼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为是。廷争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法曹争尤强,遂并收法曹,竟奏杀仇,籍其家而释法曹。法曹出,径归卧家,念河南势弗可败,气愤弗食,呕血卒。东都人至今犹道之。
处士少而孤,母夫人怜之,读书学文,皆不待强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侧,油油翼翼不忍去。时岁母夫人既终,育幼弟与归宗之妹,经营勤甚,未暇进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岁,曰义;女九岁,曰孟;又有女生处士卒后,未名。于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浑以家有无,葬以车一乘于龙门山先人兆。愈于处士,妹婿也。为其志,且铭其后曰:贵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数兮。名兮寿兮如其人,岂无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独迎其凶。兹命也耶!兹命也耶!”[9]617
首先,这篇文章是刻在墓碑上的;其次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逝者世系、生平等的叙述,其实也就是赞语。如文中开头就对逝者的名讳、先祖、先父作了交代,所谓“卢处士,讳于陵,其先范阳人。父贻,为河南法曹参军”。接着叙述了逝者先父的事迹及逝者的一生经历,这部分是对逝者的赞扬。即使是叙述家人倾家所有为逝者安葬也同样是在表扬其教育有方。因此,第一部分是对逝者的赞扬之语,第二部分是铭文,两部分结合起来就是墓志铭典型的形式:有志有铭。这种类型的墓志铭在唐代非常多,兹不详举。
为何唐代这种有志有铭的被称为“正体”的墓志铭会大量出现?不可否认,这种墓志铭的基础是本土文化。无论是“志”还是“铭”,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都有,甚至二者结合的形式也有,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中的“赞曰”等都具有这个特征,甚至在蔡邕的碑文中也有这个特征。明谭浚在《谭氏集·源流》中论“墓志”云:“(墓志)源于蔡邕碑,流为墓志圹记。晋殷仲作《从弟墓志》。”[7]415就认为“墓志”起于蔡邕的碑文,可见蔡邕的碑文确实与后来的墓志铭非常相似。作者还举例说明晋代已经有“墓志”了。正如文中第一部分所论,汉魏墓志极少,南北朝墓志几乎都属于北朝,南朝正统文化中很少,这自然让人想到北朝大量的造像文。
六朝以来的佛教造像记、造像铭和造像碑与六朝隋唐墓志铭不仅在载体、内容、功能和文体上相同或相似,而且在发展趋势上也非常一致。
三、六朝佛教造像文与墓志铭的若干相同性或相似性
与墓志铭一样,造像记、造像碑、造像铭也是刻在石碑上的,二者载体一致,即使在文体形式和内容、功能上,二者也非常相似。如北魏阙名《齐郡王佑造像记》:
夫玄宗冲邈,迹远于鹿关;灵范崇虚,理绝于埃境,若不图色相以表光仪,寻声教以陈妙轨,将何以依希至象,仿佛神功者哉?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齐郡王,体荫宸仪,天纵淑茂,达成实之通途,识真假之高韵,精善恶(下当有“之”字,碑本脱)二门,明生灭之一理,资福有由,归道无碍。于是依云山之逸状,即林水之仙区,启神像于青山,镂禅形于玄石,缔庆想于幽津,结嘉应于冥运。乃作铭曰:
芒芒玄极,眇眇幽宗,灵风潜被,神化冥通。舟舆为本,广济为功,德由世重,道以人鸿。临观净境,□绝尘封,图形泉石,构至云松。□□□□□□□□福田有庆,嘉应无穷。熙平二年七月廿日造。[10]559
就文体形式而言,造像记的第一部分看似在议论,其实是对佛法的总结复述,也即“志”;第二部分是铭辞,即“铭”,也即有“志”有“铭”,与墓志铭的文体形式一样。就内容而言,虽然这篇造像记中“志”的部分是对佛法的记述,与墓志铭中“志”的部分对逝者的世系、生平及子嗣的具体记述不同,但二者的内容都是对所述对象的颂扬。造像记对佛法的赞颂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墓志铭对逝者的赞颂是为了让更多的后人记住逝者,二者的功能也一样,即都是为了使记述对象广为人知。唐代这种类型的造像记如阙名《弥勒造像记》[11]7034《景胜寺丁恩礼造像记》[11]7039《唐张公造像记》[12]551《唐造像记》[12]551等,非常之多。具体可参见《全隋文补遗》《全唐文》《全唐文拾遗》《全唐文续拾》《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这些造像记末尾或是铭曰,或是词曰,或是颂曰,亦或是赞曰,无论是其内容特征还是文体形式都与墓志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至于造像铭就更是这个特征了,如北齐阙名《比丘僧道略等造神像尊像铭》:
自梦影东翻,金人感帝,像法肇兴,鸠摩启悟……内安万练之僧,招精进之士,银炉鼓炎,百和腾烟,锡响赞声,定崩烦恼,有性厥灵,永登宝地,凡命含品,普升净土,藉斯功德,遍沾□劫。芳谣时歇,铭歌何穷。其词曰:
玄冲眇邈,正教终归,三明自达,六职云飞。浮虚兜极,扬影紫微,悬空游息,三界徘徊。地居胜土,寺绕花莲,周回风观,遍带流渊。上干浮汉,下际幽泉,方须玉棹,事籍金船。踵兹洪福,为海舟梁,发心何远,彼岸犹长。天人觉悟,超投太康,所愿阎浮,同登净乡。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九月十五日建。(碑拓本)[13]107
第一部分是祖述佛经佛法,第二部分是铭辞,有“志”有“铭”,与墓志铭非常相似,二者在用意上也都是对祖述对象的赞扬。此外还有如阙名《刘碑造像铭》[13]104、阙名《姜洪达造像铭》[13]106、阙名《洛阳合邑诸人造像铭颂》[13]103等都有此特征。这种造像铭自南北朝以来至隋唐时期,数量虽不能与造像记相比,但是也很可观[注]具体参见《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隋文补遗》《全唐文》《全唐文拾遗》《全唐文续拾》《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其形式与墓志铭最为相似。
不仅如此,就今天所流传下来的造像铭来看,它的文学水平要高于造像记。比如上文所举的这些阙名造像铭,就其内容而言,绝非普通百姓所写,显然是文人手笔。而造像记大部分都是内容简单,语言质朴,只要是识字者皆可胜任。因此,在这一点上,造像铭对墓志铭的影响要比造像记深刻一些,但并不是说造像记的影响就不大,因为从数量上来看,造像记远远大于造像铭,其对墓志铭的兴盛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况且,造像记中也有不少具有一定文学水平且文后带有铭辞的篇章,就形式而言,与造像铭本无分别,二者在很多时候可以通用,尤其是有铭辞的造像记,说它为造像铭同样可以。反之,很多造像铭完全可以用造像记做题目。因此,造像铭与造像记在墓志铭的发展过程中无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上述两类文章相似的是造像碑。从整体上讲,无论是造像记还是造像铭都是刻在石碑上的,因此都可称为碑文;从细节来说,很多题目为造像碑的文章,其实与造像记和造像铭基本一样,如北齐张宝洛《造像碑》:
大魏武定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使持节都督夏蔚二州诸军事、卫将军、夏蔚二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安武县开国伯,又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行晋州事,东雍州镇城,安武县开国侯张保洛;前使持节、都督东荆州诸军事、征西将军、东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东雍州镇城,永宁子刘袭;假节、督东雍州诸军事,新除右将军、东雍州刺史、当州都督、安熹子薛光炽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萨,藉此微功,仰愿先王、娄太妃、大将军令公兄弟等,亡者升天,托生西方无量寿佛国,现在眷属,四大康和,辅相魏朝,永隆不绝。复愿所生父母乃及七世,皆生佛土,体解至道,以至妻子,无病延年,长享福禄,在在处处,遇善知识。又使兵钾不兴,关陇自平,普天丰乐,灾害不起。乃至一切有形众生,蠢动之类,皆发菩提道心,一时成佛。[13]70
该文与本文第一部分所举的“纯记事性质的造像记”完全一样,除了在文尾都带有祈福发愿之语外,其余都是关于何时、何人、造何像的“记事之文”。不仅如此,还有不少造像碑也带有铭辞,如北齐阙名《临淮王造像碑》[注]由于原文篇幅较长,不便全录。:
窃以万川朝海,大海终自为陵;五云出山,名山久而为砺,谓天谓地,悉有时而崩毁……
使持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司空公、宁都县开国公、高城县开国公、昌国侯、临淮王娄公,孕彩中岳,摛精大水,龙章外动,豹气傍飞。妙质则若珠明,瑰姿则朗犹玉莹,负将相之奇器,怀社稷之高节。经文大德,纷纶而备九;佩武殊功,杂踏而兼七……故海岱之间,凡诸福地,罔不倾盖,悉展殷诚……遂于此所,爰营佛事……乃作铭曰……[13]112
该文分为三段,首段祖述佛法,次段记述造像主人的节行功德、造像缘由及经过,最后一段是铭辞,并有发愿。这篇文章不仅在形式上与“有志有铭”的墓志铭非常相似,其第一段对佛法的赞扬也与墓志铭对墓主的赞扬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从内容上来看,该文第二段对造像主人的很多赞扬之语与墓志铭主要以赞人为主的行文风格极为相似;从遣词造句上来看,这也是一篇颇具文学价值的文字。这种直接以“碑”为题的造像碑的数量也非常多。同样,到了唐代,这种类型的造像碑也不少。
综上所论,造像记、造像铭和造像碑在“有志有铭”类的造像类文章中没有分别,这些造像文不仅在文体形式上与墓志铭有很大相似性,二者在属于“志”的部分上也都是对所述对象的赞颂,且就文学性而言,造像文中也有不少具有一定文学水准的篇章。因此二者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是彼此的绝缘,它们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怎样的呢?这里就得考察南北朝佛教造像文与墓志铭数量的差异性了。
四、六朝佛教造像文与墓志铭数量之关系
由上文所举例子和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所辑录的墓志来看,南朝时期的墓志仅有10余篇,而北朝时期则有500余篇;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新补的119篇墓志也同样基本是北朝的。这样算来,两书所录北朝时期的墓志有600余篇。也就是说,北朝的墓志数量是南朝的60倍,这个差异大得异常。相对于北朝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南朝更重视文教,南朝人的整体文化水平要远高于北朝人。如果南北朝之前本土文化中的墓志或者说蔡邕等的碑文是南北朝时期产生大量墓志的主要原因,为何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南朝产生的墓志如此之少,而相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北朝则产生数量如此之多的墓志?作为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南朝人,对本土文化中的墓碑不感兴趣,而作为被中原人称为“夷狄”的野蛮民族反而对本土文化中的墓碑非常感兴趣,这显然很矛盾。况且,就“雅”“俗”而言,“碑”在本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所谓“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文心雕龙·诔碑》),绝非被视为小道的小说可比,南朝人也没有理由排斥。因此笔者认为,相较于南朝而言,北朝出现如此多的墓志虽然是借鉴了本土的文体形式,但其如此繁荣与本土文化中的墓志关系不是很大。相反,墓志铭的兴盛与北朝繁荣的佛教造像成正相关关系。
就现存我国六朝佛教造像而言,北朝佛教造像数量远远大于南朝,我国著名的佛教四大石窟也都在北方。马世长、丁明夷所著《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把我国的石窟分为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四个大的地区,其中有三个属于北方,只有一个指淮河以南的地区,而且“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14]20,并且大多为公元七世纪以后的造像,这也说明北方的石窟造像数量远远大于南方。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北朝的佛教造像数量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朝的佛教遗存数不胜数……南朝佛教造像实物比之北朝,却相当稀少”[15]3。
造像一般有造像记、造像铭或造像碑,尤其是对于北朝更是如此。对韩理洲先生所编《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隋文补遗》和《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进行统计,仅造像记而言,唐前的数量多达约1500篇,造像铭和造像碑数量也很可观。唐前的这些造像文基本都是北朝的。于是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关系:
北朝的佛教造像数量巨大,南朝的佛教造像数量较少;
北朝的造像文数量巨大,南朝的造像文数量较少;
北朝的墓志铭数量巨大,南朝的墓志铭数量较少;
北朝造像文数量远大于北朝的墓志铭数量。
这就是说,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佛教造像和造像文的数量与墓志铭的数量成正比关系,且北朝的造像文数量远大于墓志铭数量。如此来看,这不是一种巧合。尤其是结合上文所论造像文与墓志铭在载体、内容和文体形式上的相似性来看,北朝大量的造像文刺激了墓志铭的发展当是不成问题的。或者至少也可以说,在墓志铭的发展过程中,佛教造像文是有一定功劳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造像记大多是考古人员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这说明造像记很多是被埋在地下的,而早期的墓志铭也同样是被埋在地下的,如徐师曾《文章明辨序》中说:“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6]148宋人费衮在《梁溪漫志》卷六中亦说:“降及南朝,复有铭志,埋之墓中。”[16]397可见二者有着诸多相似性。如此一来,在南北朝佛教大兴、造像空前繁荣的背景下,人们在写作造像文祈福、发愿和赞叹佛、菩萨的同时,自然也会想到把歌颂的对象扩展到普通人身上,有希望得到佛陀保佑的意思,其影响到墓志铭的写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六朝佛教造像文对唐代墓志铭发展的推动
据今天所能见到的佛教造像而言,唐代的佛教造像是我国古代佛教造像继北朝之后的又一高峰。与北朝造像一致的是,唐代的佛教造像也以石窟为主,数量庞大,且也出现了大量的造像文。据统计,仅造像记而言,唐代约有700篇,再加上造像铭及造像碑,数量接近1000,然与北朝不同的是,唐代的佛教造像文数量与墓志铭数量差距甚大。如前文所言,就墓志铭而言,唐前约有六七百篇,唐代仅据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来看,就约有5500篇,再加上后来吴刚所编煌煌九大册《全唐文补遗》中大部分都是墓志铭,以及后来陈尚君辑录《全唐文补编》中大量署名的文人墓志铭和卷150—156中大量佚名的墓志铭,可以说,唐代墓志铭的兴盛远非南北朝可比。唐代造像文的数量基本与北朝持平甚至有所减少,但是墓志铭的数量几乎是南北朝的10倍。这恰恰反映了造像文对墓志铭影响的渐进过程。经过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造像文对墓志铭的影响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唐代造像文数量有所减少,但由于具有了六朝时期造像文对墓志铭产生影响的坚实基础,造像文的影响力依然不减。况且唐代的造像文数量也很可观。而且,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佛教造像记同时也本土化了,由祈求佛祖保佑过渡到了祈求祖先保佑,造像记的文体名称被墓志铭所取代。
综上所论,墓志铭虽然是受本土文化影响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六朝至隋唐时期繁荣的佛教造像及其附属物造像记、造像铭和造像碑的推动,这种文体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且在唐代数量陡然猛增。因此,唐代墓志铭的兴盛与佛教造像文的推动无疑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