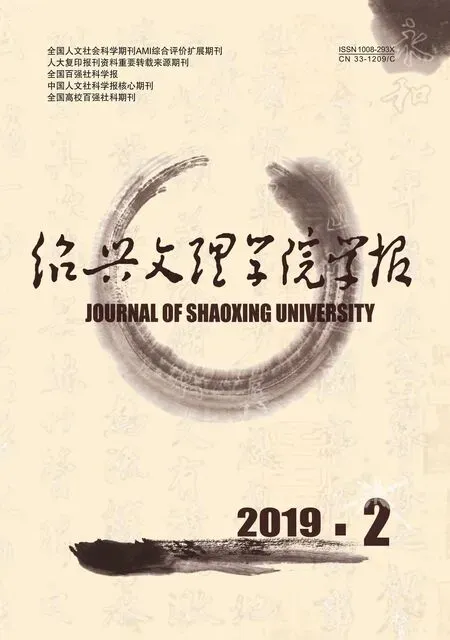唐顺之与越中文士交游考
曹诣珍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人,是明代继王阳明之后又一位文武兼资的通儒。他是南中王门的代表人物,以“天机说”为核心的心学思想自成体系,在阳明后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也是明中叶著名的散文大家,其洸洋纡折、理趣精深的古文创作及高扬主体精神的“本色”文论影响深远,被推为唐宋派的领袖。他博闻多识,“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1]5424。他还是一位抗倭名将,曾以兵部郎中督师江浙,率兵抵御倭乱,建立了壮烈功业。
唐顺之一生仕隐交错,交游广泛,上至台阁辅臣、文臣武将,下至布衣平民、医卜僧道,皆能切磋砥砺,互通声气,体现了“独学无友,则昔人所以深病于孤陋”[2]208的理念,其中,与越中文士群体的交谊相当引人注目,本文拟综述之。
一、与越中心学家的交游
明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心学迅速崛起,蓬勃发展,“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1]7222。唐顺之受心学思潮的浸润提出“天机说”,并成为南中王门的代表人物,主要得益于越中心学家王畿的启蒙及影响。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山阴人,嘉靖二年(1523)始受业于阳明,“亲炙阳明最久,习闻其过重之言”,是阳明生前最欣赏的弟子之一。阳明晚年门人益进,不能遍授,于是多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大旨,主讲书院,二人在当时有“教授师”之称[3]226。阳明逝后,王畿致力于传播师说,足迹遍及吴、楚、闽、越等东南各地,被视为浙中王门的创始人。
唐顺之与王畿初识于嘉靖十一年(1532)。是年,唐顺之官翰林编修,恰遇王畿寓京师赴廷对,借机发扬阳明心学:“是时缙绅之士以讲学会京师者数十人。其聪明解悟,能发挥师说者,则多推山阴王君汝中。”[2]624唐顺之由此得闻“良知”之说,遂有就道之念。李贽《续藏书·佥都御史唐公》记述:“壬辰(嘉靖十一年)……时则王龙溪以阳明先生高弟寓京师,公一见之,尽叩阳明之说,始得圣贤中庸之道矣。”[4]505《明史》在述及唐顺之思想渊源时也说:“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1]5424两人由此开启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交谊。王畿记述:
自辱交于兄,异形同心,往返离合者,余二十年,时唱而和,或仆而兴,情无拂戾而动无拘牵,或逍遥而徜徉,或偃仰而留连,或蹈惊波,或陟危巅,或潜幽室,或访名园,或试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或联袂而并出,或枕肱而交眠……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谓予论学颇有微长,得于宗教之传,每予启口,辄俯首而听、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尝戏谓予“独少北面四拜之礼”,予何敢当?[5]573
足见二人过从之密、交谊之笃,以及王畿对唐顺之的影响之深。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王畿主张一任自然,认为“夫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则便不得其正”(《答季彭山龙镜书》)[5]212,“君子之学贵于自然,无所澄而自不汩也,无所导而自不窒也”(《心泉说》)[5]504。他主张保持人心活泼之体,反对任何约束:“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华阳明伦堂会语》)[5]161唐顺之正是在继承王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他心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天机说”:
盖尝验得此心天机活物,其寂与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与之寂与之感,只自顺此天机而已,不障此天机而已。(《与聂双江司马》)[2]278
盖其酝酿流行无断无续,乃吾心天机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为。其所谓默识而存之者,则亦顺其天机自然之妙,而不容纤毫人力参乎其间也。(《明道语略序》)[2]435
认为“天机”作为人的本性,具有自然之妙,活泼之体,非人力可为,与王畿“以自然为宗”思想的承袭关系非常鲜明。故黄宗羲《明儒学案》亦云:“先生(唐顺之)之学,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3]599唐顺之与王畿不仅相互间切磋砥砺,还多次与其他学友聚讲。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春,罗洪先至毗陵访戚贤,唐顺之、王畿偕万表、陈九川、吕光洵等“复为旬日之聚”[5]615。三十二年(1553)夏四月,罗洪先、邹守益应胡宗宪之邀,会宿武林,唐顺之、王畿等又与其会于当湖,“相与论格物之指”[6]。
在唐顺之与王畿的诗文集中,留存了不少二人交往的信息。如唐顺之有《与王龙溪郎中》《答王龙溪郎中》书信两封,《书王龙溪致知议略》《跋自书康节诗送王龙溪后》二文,内容都是与王畿探讨世事学问。另有《与吕沃洲巡按》写道:“近龙溪相过,与之盘桓山中数日,别去已订他年之约。”[2]417《答林镇江巽峰》《与张本静》《与赵甬江司空》等文中也都提及王畿。而王畿有《与唐顺之》书二通,及《永庆寺次荆川韵》《秋杪偕唐荆川过钓台,登高峰,追惟往迹,有怀蔡可泉,短述见志》《万履庵偕其师荆川唐子南行,予送之兰溪,用荆川韵赠别》《送唐荆川赴召用韵》《祭唐荆川墓文》等诗文,记录了他与唐顺之的深厚交谊。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唐顺之与王畿之间实为“友直、友谅、友多闻”,不仅相互在学术上砥砺共进,且都能正视对方的不足并直言以责,然无损情谊,如唐顺之《与王龙溪郎中》一文中写道:
仆窃观于兄矣,惟兄笃于自信,是故不为形迹之防,以包荒为大,是故无净秽之择,以忠厚善世,不私其身,是故或与人同过而不求自异。此兄之所以生深信深慕于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于不相知者也。[2]187
在赞誉王畿自信、宽厚、忠善的同时,也对他未能把握好尺度分寸,以致“不为形迹之防”“无净秽之择”“与人同过而不求自异”提出真率的批评。而王畿对于唐顺之之不足,同样直言以告,如《送荆川赴召用韵》诗云:
与君卅载卧云林,忽报征书思不禁。学道固应来众笑,出山终是负初心。青春照眼行偏好,黄鸟求朋意独深。默默囊琴且归去,古来流水几知音?[5]540
认为唐顺之应朝廷征召出山有负学道初心,诗中所述,无论是“默默囊琴且归去”的动作,还是“古来流水几知音”的叹息,都难掩失望、责备之意。在《与唐荆川》中,王畿又直言:“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虚声耸动,只此便是道学障,便是应机欠神处,不可以不察也”“窃观吾兄近来举动,乍出乍没,倏往倏来,若神龙之变化,似欲使人不可测识,略出有意,却未免涉于轻躁,反使人情惝恍,不能快然。此是学问关系,非徒行迹加减而已也。”[5]265-266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唐顺之巡抚扬州,重病在身,王畿赴扬州与其相会,日夜护伴左右,顺之深感欣慰,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写道:“脾胀之病,非旬日所积,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牵牵,半死半活人也……龙溪兄已到此数日,议论可以代药。”[2]364即使是在两人相聚的最后时日,王畿依然不改真率本色,直陈顺之未能致得“真良知”的七种“病症”。顺之认可,怃然曰:“吾过矣!友道以直谅为益,非虚言也。”[5]7-8临终又不无遗憾地说:“吾死不恨,第山中尚少十年功夫耳。”[2]1088是年夏,唐顺之卒,王畿痛失诤友良朋,作《祭唐荆川墓文》:“舍我而游,孑然孤立,无与共究夫此学之全”“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梦,独所谓形骸者不可复作,已闭于夜台之重泉”[5]573,哀伤彻骨,感人肺腑。
除与王畿倾心相交外,唐顺之还与越中另外两位著名心学家季本、吕光洵有较密切的交往。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与王畿同为阳明直传弟子,但其学术宗旨与王畿异趣,倡“龙惕说”,主张以龙言心,主宰常在,时时警惕。唐顺之的“天机说”脱胎于王畿的“以自然为宗”,和季本学术分歧较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交谊。季本平生注重考索经传,著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等多种著述。唐顺之在《与季彭山》书中提到自己“自少亦尝有志于治经”,却不能得其要旨,“偶游会稽,获闻高论,则爽然自失”[2]283,对季本的治经成就甚为推崇。受心学思想影响,季本考索经传“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窃前人”[7]143,不拘一格,勇于破除旧说,唐顺之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先生之于经,关窍开解,掐擢肠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藏也。剖破传注专门之学,辞锋所向,决古人所未决之疑,而开今人所不敢开之口。
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提出“愿先生益深所养,使此心虚一而静,自所独然不必尽是也,众所共然不必尽非也,却意见以融真机”[2]283-284的客观意见。季本《春秋私考》书成,唐顺之为之作序,同样给予充分肯定。顺之逝世,季本作《祭唐太史文》,悲叹“哲人云亡,质疑何自。设奠陈词,潜为出涕。道义之思,曷其有既。灵如有知,鉴此微意”[8]902,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吕光洵(1508—1580),字信卿,号沃洲,新昌人,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徐渭《吕尚书行状》云:“(公)自结发为学,学靡不优,而中治新建旨,再后与余姚钱刑部德洪、吾乡王兵部畿、武进唐都院顺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12]652唐顺之的诗文集中保存了三封写给吕光洵的书信:《答吕沃州》探讨“养心”之道,并谓“居乡无朋友夹持,深惧堕落,得来教不觉悚然,甚幸甚慰”,期盼“何日得与兄共坐一室,日夜相与磨勘洗濯此心”[2]247-248;《与吕沃洲巡按》两篇,其一商讨赈灾事宜,另一叙离别之思,云:“同心之谊,怅然远别,以兄之不能忘情于仆,亦知仆之不能忘情于兄也”[2]416,足见情谊之深。吕光洵曾和唐顺之共同参加了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聚讲,还曾以唐顺之家藏宋刊旧本为底本,刊印宋人石墪所编《中庸辑略》二卷(唐顺之序),还共同校刻了宋人黄度所撰《尚书说》七卷(吕光洵序),二人在学术上的交流相当密切。
作为南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唐顺之与王畿、季本、吕光洵等越中心学家的交往,体现了南中王门与浙中王门的深厚渊源和紧密关联。
二、与越中文学家的交游
唐顺之的诗文创作自成一家,尤以古文著称,“洸洋纡折有大家风”[1]5424,“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7]1506。其文学理念也颇有独到之处,“本色论”倡导“直据胸臆,信手写出”[2]295,与“天机说”一脉相承,表现出崇尚主体、顺应自然的特点,在当时及后世均有重要影响。唐顺之与王畿既是道友,也是诗友,二人共研心学之余,还时常探讨诗文之法。王畿《祭唐荆川墓文》云:“兄为诗文,炜然名世,谓予可学,每启其钥而示之筌。”[5]573《〈击壤集〉序》又曰:“予友荆川唐子专志静养,工于诗,有意于别传者。谓康节之诗实兼二妙,尝为书《击壤集》若干首示予。”[5]344唐顺之《跋自书康节诗送王龙溪后》也写道:“龙溪王子盖有得乎诗传之意者,而亦未尝不深于诗法也,索予章草,余为举似《击壤集》数首。龙溪盖素以余论诗为然者也。”[2]769可知唐顺之经常向王畿传授创作诗文的方法,且二人的文学理念相近,都推崇以邵雍《击壤集》为代表的理趣诗。只是王畿的意趣终究以心学为主,于文学关注不多。在当时以诗文名世的越中文士中,与唐顺之交往的主要有沈炼、陈鹤和徐渭,三人皆名列“越中十子”,且都有一定的心学背景。
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又字子刚,号青霞,会稽人,年少时期便跟随王阳明游学,深受阳明赏识。王世贞《沈青霞墓志铭》记载:“始沈公少而读书有异质,从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与语,即奇之:‘生,千里才也。’”[9]《青霞集·年谱》《南雍志列传》中也都有类似记载。沈炼与唐顺之交往的时间地点,可从沈炼的《寄唐荆川书》推断:
忆畴昔辱游于阳羡之墅,省记微旨,教以挽弓……别后几二十年,末由一晤,而世路坎,不出公之所议。缅想英概,时时于梦中见之。顾仆出关以来,目睹世变,大有伤心者,恨不能会,并于数千里之外与兄握手倾此绪谈也。[10]
阳羡为宜兴旧称,可知二人相识的地点是唐顺之在宜兴的居所。唐顺之曾两次闲居宜兴:第一次是从嘉靖十四年(1535)至嘉靖十七年(1538),他因不附权臣张璁致仕返乡,期间客居宜兴。第二次是嘉靖二十年(1541)至三十六年(1557),他被再次罢官后归家,期间也多寓居宜兴山中。而沈炼于嘉靖三十年(1551)因上疏弹劾严嵩被谪塞外保安州,写此信时已在关外。从信中“别后几二十年”可以推断,沈炼应该是在唐顺之第一次闲居宜兴时与其相会。此次相会,二人曾一起探讨学问、武艺等。此后将近二十年间虽无缘再晤,却“时时于梦中见之”。沈炼在京期间,还与唐顺之的弟子莫如忠、吴维岳过从甚密,时常在一起论诗析文,显示了相近的文学旨趣。而在他被流放的第七年,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终被诬陷与白莲教阎浩等谋乱,惨遭杀害,未能实现与唐顺之“握手倾此绪谈”的夙愿。
陈鹤(1504—1560),字鸣野,一字九皋,号海樵山人,山阴人。陈鹤与王畿以叔侄相称,曾作《龙溪丈人歌》《送王龙溪表叔》《寄题王龙溪表叔池亭二首》等诗称赞王畿一心向道。其《龙溪丈人歌》中有“相携一见王夫子,乃知实重名为轻”[11]卷五之句,可知陈鹤曾在王畿的引见下亲自拜见过阳明,并且在思想上深受启迪。在陈鹤的《海樵先生全集》中,有多首诗歌记录了他与唐顺之的密切交往,如《唐荆川太史山居话旧》《唐荆川携酒过访》《过唐荆川太史隐居》《寄唐荆川太史》《仲春六日见雪,简唐荆川太史过村居一首》等,主要赞扬唐顺之闲居期间“心无时事累,家有古风存。已得川中乐,都忘河上言”(《过唐太史隐居》)[11]卷六的隐者风范。陈鹤早年弃官着山人服,一直居住于故乡山阴。嘉靖三十二年(1553)左右,因东南沿海倭患猖獗,他离乡避乱,曾奔走旅食于吴中,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寓居金陵。由此推断,他与唐顺之的交游也应集中于这段时间。而《悼唐荆川中丞》一诗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年唐顺之病逝于追击倭寇的海船上,陈鹤于金陵得此噩耗,作诗云:
学士何堪作武人,匡时靖难策空陈。占星未奏三吴捷,立帅先殂百战身。谩道街亭存马谡,徒闻淮海得张巡。千年名誉谁能似,开府诗篇句最新。[11]卷八
歌颂唐顺之文武双全的气概,痛惜其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命运。是年,陈鹤也卒于金陵。在诗文理念上,陈鹤中晚年越来越看重文章“玄雅”之风,表现出重道轻文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唐顺之的影响。他在《评俞是堂员外去楚诸集》中写道:
近惟唐荆川、陈后冈、高苏门、蔡白石、董浔阳、施武陵数子,各世之才,上古之学,而能超脱宏丽,独擅玄雅,后先起江南而海内响应……鹤不佞,然亦窃同数子之志。今复乐闲居,尚静理,日与方士道者游,音律之文渐成委弃,故自亦不知其何似也。[11](卷十七)
所举“数子”中,首列唐顺之,并明确表达了认同、追随之意。而在唐顺之的诗文集中,记录二人交游的主要有《赠山阴陈千户病卧毗陵三首》,题旁小注云:“陈故毗陵人也。”毗陵为常州地区的古称,据卢梦阳记载,陈鹤“其先武进人,六世祖以战功授绍兴卫百户,遂为绍兴人”[11],武进即属常州,则“山阴陈千户”当指陈鹤无疑,只是“千户”应为“百户”之误。诗云:
问子来何处,云从剡水阴。越吟多病客,吴语故乡心。尺牍人争羡,一言余所钦。由来绝弦意,今日为知音。[2]80
同样表达了与陈鹤的知音相赏之意。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阴人。徐渭先后师承季本、王畿,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对阳明极为敬仰:“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送王新建赴召序》)[12]531徐渭与唐顺之的交游始于嘉靖壬子(1552)。是年夏,倭患渐盛,唐顺之复有用世之意,途经会稽,与王畿、季本相会,徐渭也因此得以结识唐顺之,并写下《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诗,记录了这次聚会。诗前小序曰:“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射于越圃,而万总兵鹿园、谢御史狷斋、徐郎中龙川诸公与之偕西也,彭山、龙溪两老师为之地主。荆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所见渭文,因招渭,渭过从之始也。”可知唐顺之最初是在徐渭宗师薛应旂处得见其文,深为赏识,故借此机会相与论文。徐渭此诗云:
帆色乱蒹葭,舟行渺陂泽,昼日聚星精,湖水难为白。念此阳羡客,远从东海来,素书授黄石,朅使群公猜。引弓洞七札,矍圃风飕飕,白猿既坐啼,杨叶亦生愁。忽然弢白羽,招此文士游,转棹不可止,忽到津西头。柯亭锁烟雾,异响杳不流,独有赏音士,芳声垂千秋。[12]66
寄寓了对“阳羡客”唐顺之的仰慕之情。这次聚会给徐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曾多次提到,如《奉赠师季先生序》中有“武晋唐先生游会稽”[12]515,在《寿徐安宁公序》中也写到“当壬子夏,偶得见刑部君于荆川先生舟中”[12]956。
嘉靖三十六年(1557)冬,浙直总督胡宗宪招徐渭入幕。次年,唐顺之再度出山,十月,以兵部郎中的身份视师浙江,与胡宗宪协谋剿倭。在胡宗宪幕府中,徐、唐二人再次相聚。陶望龄的《徐文长传》生动记述了当时聚会论文的情景:
时都御史武进唐公顺之,以古文负重名。胡公尝袖出渭所代,谬之曰:“公谓予文若何?”唐公惊曰:“此文殆辈吾!”后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谓非公作,然其人谁耶?愿一见之。”公乃呼渭偕饮,唐公深奖叹,与结欢而去。[12]1339
这段描述充分说明了徐渭对唐顺之文风的追摹仿效,但也容易令人误会二人此时方才结识,其实他们早在嘉靖壬子即相识。应该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二人共赏冰灯,唐顺之作《元夕咏冰灯》一诗,徐渭与之相和,作《咏冰灯》诗,下注“荆川公韵二首”[12]782。在陶望龄的传文中,还记述:
归安茅副使坤时游于军府,素重唐公。尝大酒会,文士毕集,胡公又隐渭文语曰:“能识是为谁笔乎?”茅公读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谓渭:“茅公雅意师荆川,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惭愠面赤,勉卒读,谬曰:“惜后不逮耳。”[12]1339
进一步说明了徐渭与唐顺之文风之相似。徐渭在诗文创作上主张“天机自动,触物发声”(《奉师季先生书》)[12]458,在戏曲创作上强调“贱相色,贵本色”(《西厢序》)[12]1089,显然也都受到唐顺之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的影响。徐渭晚年自著《畸谱》,在“师类”和“纪知”中都列到唐顺之,并追忆:“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12]1334对唐顺之的知遇之恩始终报以感激之情。在《诗说序》中提及唐顺之,徐渭用了“子唐子”的敬称[12]522。徐渭晚年还作有一首《卌年》诗:“卌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下有小注云:“吾欲尽焚旧草,故作此诗,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12]375“卌”即“四十”,从时间上推算,彼时距二人初识四十年,则距唐顺之逝世已三十年有余,然知音不再的伤痛依旧弥漫于字里行间。
作为“越中十子”的核心人物,徐渭、陈鹤、沈炼都与唐顺之交游往来,体现了十子社和唐宋派的紧密联系。在共同服膺阳明心学的背景下,他们的文学观念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创作上遥相呼应,一起突破了“前七子”复古文学思潮的桎梏。
三、与越中历学家的交游
有明一代,传统天文、历法之学进入衰落蜕变期,尤其是明中后期,钦天监的天象预报时常不验,这一情形刺激了当时众多学者钻研历法,唐顺之就是其中一位。唐顺之是明代中期最早提出应研究《授时历》立法原理问题的学者,他在历学上的造诣颇受后代同行的推重,如梅文鼎说:“盖明之知回历者,莫精于唐荆川顺之,陈星川壤两公。”[13]而唐顺之的历学成就也与一位越中文士周述学密切相关。
周述学(约1500—约1572),字继志,号云渊子,山阴人。其人学养极博,著述宏富,黄宗羲对他极为推崇,云:“发前人所未发,凡千余卷,总名曰《神道大编》,盖博而能精,上下千余年,唯述学一人而已。”[14]562《明史·方伎》说他“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邃于历学”[1]7653。据黄宗羲《周云渊先生传》记载,唐顺之与周述学为“同学”,二人经常相与“论历”,在学问上相互促进[14]562。周述学《历宗通议题辞》也自述:“余与荆川唐公论历之余,乃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其讹舛,删其繁芜,凡诸儒之论历者入之。”[15]其《历宗通议》中收录了三封唐顺之论历的书信:《唐荆川与万斯节论历书》《唐荆川又与万斯节论历书》以及《唐荆川论张方斋历书》。周述学的另一部代表作《历宗中经》的创作也与唐顺之相关,黄宗羲云:“自西域回历入中国,始有经纬凌犯之说。然其立法度数与中国名度亦异。顺之欲创纬法以会通之,卒官不果。述学乃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以毕顺之之志。”[14]562周、唐二人在历学上的成就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影响,以致后世学者对他们的知识传承关系有不同见解。如黄宗羲云:“(顺之)与人论历,皆得之述学,而亦未尝言其所得之自。岂身任绝学不欲使人参之耶”[14]562,认为是唐顺之掩袭周述学;而梅文鼎却认为是周述学因袭了唐顺之:“唐荆川顺之论回历之语载王宇泰肯堂《笔尘》中,颇有发明,殊胜《历宗通议》。或反谓荆川历学得之云渊者,非定论也。唐荆川太史顺之亦深明西域之法而加之以论说,周云渊处士述学因之为《历宗通议》《历宗中经》。”[16]说法不一,各执一词,以致后世将《历宗通议》《历宗中经》或置于周述学一人名下,如《明史·历一》云:“唐顺之未有成书,其议论散见周述学之《历宗通议》《历宗中经》。”[1]544或又置于唐、周二人名下,如《四库全书总目》曰:“唐顺之、周述学所撰《历宗通议》《历宗中经》,皆旧西法也。”[7]901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顺之与周述学在历学上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他们合力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论述,从哲学、文学和科学多个领域勾勒了一代通儒唐顺之与越中文士交游的大致情状。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明一代吴越文化圈内在关联的紧密,尤其是在阳明心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南中王门与浙中王门渊源之深,唐宋派与“越中十子”关系之密。他们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推动了时代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