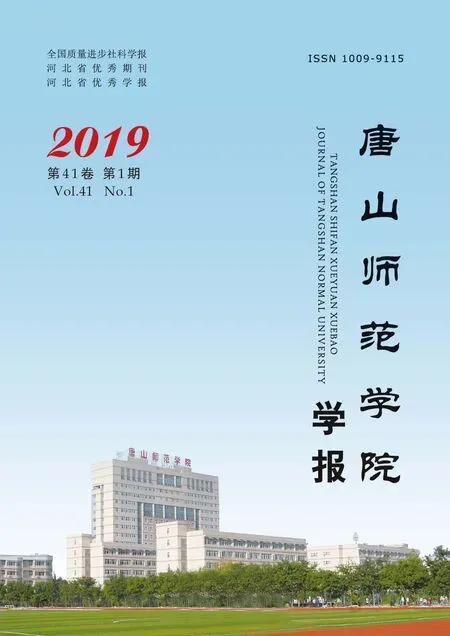论何振基《母亲河》的家族叙事伦理模式
王 平
论何振基《母亲河》的家族叙事伦理模式
王 平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母亲河》以高度的审美智慧与思想深刻性,将人民叙事伦理与自由叙事伦理完美结合,呈现出家族叙事伦理模式。用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的家国同构叙事模式,勾画历史背景中的家族。以“家”写“国”两条发展线索交织,扩大叙事的空间延展性与时间容量。文化血缘与家族血缘的彼此交融,形成家族史传的叙事模式。作者将敏锐的眼光投射在道德伦理的多元叙事模式之上,历史中道德的两极与家族中叛逆与回归,无一不是在此模式上对人性善恶悲悯的创造性挖掘。
《母亲河》;人民叙事伦理;自由叙事伦理;家族叙事伦理模式
刘小枫曾将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民伦理叙事,另外一种是自由伦理叙事。其中“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伦理学都有其教化作用,从这两种分类来看,每一种叙事伦理都有其瓶颈。“人民伦理叙事”以社会学方式来看待问题,以历史是非评判人性的善恶,将文本牢牢钉在政治历史形态之上,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本身的价值与真实人性的复杂,不利于促进人的自由与自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人性的觉醒与提高。而“自由的叙事伦理学”只强调“自己的道德自觉”,将文本与社会意识形态过度剥离,这样的伦理叙事苍白无力,没有根基,过分重视个性与特殊性,很难创造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只有将这两种叙事伦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优秀的文学作品。何振基先生在其长篇小说《母亲河》中,以其独特的叙事智慧,将这两种叙事伦理模式完美结合,并形成了特有的家族叙事伦理模式。
一、家国同构的叙事伦理模式
《母亲河》这部小说突破了仅局限于家族的叙事,在家族叙事伦理中钩沉出历史的沧桑与风云变幻,将人民叙事伦理与自由叙事伦理相结合,呈现出家国同构的叙事伦理模式。小说在时间跨度上纵贯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的前10年,展示了两代人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并将家族的小叙事伦理与国家大历史的叙事伦理相融合,使得家族与国家的发展史共同形成了全景动态的混合史。家族小说“既有家族的生命气质,亦有时代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这种将家族小历史编织进时代大历史的写法,堪称家族小说的经典叙事技法”[2,p5]。这种叙事技法极大地拓宽了小说叙事的深度与宽度,将历史叙述的厚重与家族叙事的轻灵结合于一处,既跳出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又能深入历史的根部,充分发掘家族与人的价值。其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实录精神与以“家”写“国”两个方面。
(一)实录精神
班固在《汉书》中对司马迁的实录写作原则曾作了如下总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实录精神最可贵之处是“不虚美,不隐恶”。纵观中国小说的起源,小说与传统的史传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代家族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史传小说中的编年体叙述结构的影响,其中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与历史还原的方法都体现着史传小说的实录精神。将实录精神运用于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还原,还要求作品对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处理要体现其叙事的智慧与技巧,既要切实体现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又要在其基础之上表达艺术的美感,将诗性智慧与诗意化的历史融入作品,使历史的空间性、延展性、启发性得以融合,打破叙事伦理的困境。
1. 小说历史时间的架构
总体来看,《母亲河》以时间发展为脉络,时代变迁统摄了全书的发展,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60年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其脉络以显性的时间或者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架构全文。全书38章,加上引子,共186小节,几乎每一节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将这些时间进行分类,可以归纳为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在此我们只关注历史时间。
《母亲河》中历史时间的描述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处于开头,一个是处于文中。仅仅是小节的开头便点明历史时间的大约有20次,占所有章节的百分之十一。其叙述模式有其规律性,比如以时间开头:“一九五七年。夏天还没走秋天就来了。”[4,p3]这是将历史时间与抒情性的语言相结合。“一九六六年秋,阳坝村的社教工作队刚一撤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熊熊燃烧起来。”[4,p25]不仅点出了历史时间,也点明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再如:“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是中国所有老百姓都不会忘记的日子。”[4,p72]不仅点明历史时间,并创造性扩大时间容量,将感情因素穿插于其中。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叙事结构的重复,作者巧妙地将时间嵌于文中,比如第二十七节,小节开头便叙述了庆生一觉醒来已经日暮迟迟,天黑下来。这是对生活时间的叙述,接下来,写庆生打开了周秀琴写给自己的信,其落款是:“周秀琴,1974年8月16日。”[4,p65]这就将小节开头未点明的历史时间极具匠心地穿插于文中。
2. 小说的历史事件的叙述
何振基先生在进行历史叙事的同时,对历史时间进行剪裁与详略处理,1950到1978年间的历史事件做简化描写,仅占整个叙述的四分之一,而将下笔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的32年中。
从作者略写的28年中,分别提到了“整风运动”“大锅饭”“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夺权运动”“知识青年下乡”“三线建设”“农村整组运动”“农村清理阶级队伍时的批斗”“七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农村整顿组织”和“1976年三大巨星离世”等历史事件。详写了“1978年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1981十一届六中全会”“80年代末北京学潮”“89年六四学潮”“90年代民营企业发展”“1993年反腐”“四川大地震”等历史事件。
这种详略处理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作家跳出了传统阶级斗争叙事的套路,不再以过多的笔墨探讨执政党过去的坎坷。其用力之处不单在追问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更迭的合理性、正义性,并且在历史的根部,找到了人的权力欲望和人性的自私、贪婪等恶念,由此呈现出社会万象。
小说实录地将人物命运与天下大势紧紧相连,其深刻性就在于将人物放于历史之中,不被观念性的历史所束缚,呈现出历史新的侧面。
(二)以“家”写“国”
《母亲河》主要采用自由叙事伦理模式对贺家两代人、赵家一代人的发展变迁进行了追根溯源,代与代之间以家族伦理进行维系,偏重于展示一个家族谱系的发展演变。与此同时,作者将自由叙事伦理放在人民叙事伦理之中进行阐释,以“家”写“国”,并将“国”之发展作为串起家族变迁的线索,作者既写出了历史自身的复杂性,又以家族的道德伦理注入历史叙述之中,赋予历史一种家族的道德伦理基础,历史不再是判断人性唯一的因素,家族的价值、人的价值得以彰显。小说以“家”写“国”主要表现在以“家”(或者是人物)的发展反映国共两党的历史因革,以及以家族的兴衰演变展现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发展变迁。
1. 以“家”(或者是人物)的发展反映国共两党的历史纠葛
何振基先生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与历史评价都进行了巧妙地处理,在文章中并没有太多的直接评价,而是在“家”或者人物命运中暗含了两党的历史因革,从而写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与人物命运的颠沛流离,这就在传统生硬说教的基础上,为两岸渴望统一注入了温情的一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下。
小说第十节便埋下伏笔,贺家户族之主老二梁生三子家的一个儿子“临在解放时被蒋经国招入青年师,随军逃往台湾成了国民党的团级军官。……几十年后突然从台湾回来认祖归宗,回到贺湾时已是满目疏离……感慨万千,只是两岸隔海、天涯肠断,只能在心里祈祷两岸的团圆”。这段文字写出了内战时期国民党撤离大陆,这场纷争导致了贺家子孙背井离乡,和贺家子孙相似命运期盼回归故土的又何止一人,这寄寓了作者渴望统一的深情。对于这种情感,作者还有直接表述“历史的悲剧往往以喜剧开头,而喜剧又常常以悲剧结尾。国共两党演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过去,未来或许以两岸统一、两党携手的喜剧终结,说不定我们还能看到那一天呢”[4,p200]作者借主人公贺庆生的口对国共两党的过去及未来进行了总结。
再如,小说叙述秦岚流落到了台湾,“秦岚竟是一无根二无家,而且被生活驱逐追赶,就像一个被放逐的囚犯,虽然身有自由但总感觉带着枷锁,像一片飘落的秋叶,不知明天会落向哪里。”这段文字描摹了秦岚漂泊的身世之感,她身在台湾,作者用了“流落”一词,事实上台湾也是流落之地,这就在情感上包含了两层意思,寄寓了盼望己身回归故土,台湾回归祖国的美好愿景。
小说比较巧妙地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进行勾连纵横,既避免了平铺直叙,又扩大了叙事的容量。秦岚滞留香港,勇探“禁区”,不仅引出了老兵“赵云儒”,即赵凌芬音讯全无的二哥,而且描述了1949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百万官兵的命运,以及在80年代掀起的“寻根”“祭祖”活动被蒋经国以“三不”政策所压制,终难回归故土的悲惨命运。
2. 以家族的兴衰演变展现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发展变迁
60余年的风云变幻,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随着国情的演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人物与家族命运兴衰与之起伏。贺文雍这个正直热血的青年干部被打成右派,屈死高原是政策的悲剧。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赵春月,以其过人的胆识,抓住历史机遇,从经营歌舞厅到承包钢厂,最后成为现代企业家,并荣选政协委员,“发生在赵春月身上的一系列故事,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国企改革的艰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进程”[4,p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滞后,又导致了社会腐败,草菅人命,官商勾结,在柯明与王志中的勾结中,赵春月卷入命案,企业发展几经起伏。小说看似在表面上勾画了人物命运与家族兴衰,但是其背后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无形力量推动其前行。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也是紧紧相连,小说中的人物刁雨晴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我知道,首长您一定会看轻我的,这是我的命。但是我们这代的命运就掌握在首长你们这代人手中,都掌握在这个社会手中啊!我的今天,正是同命运的一种抗争,也许我走了弯路,但我也在奋斗努力啊!我不明白,为什么社会就不能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梦呢?[4,p469]
这段文字直接阐发了作为底层小人物自我命运的抗争,人物命运始终与社会命运、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从小说的创作上来说,家国同构的叙事伦理模式将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两条线索明暗交替进行,是作家宏大叙事驾驭能力的生动体现。
二、家族史传的叙事伦理模式
家族史传叙事伦理模式的基本规律是重视家族成长变迁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命运的浮沉,即强调自由叙事伦理。“对一个家族的‘创世纪’历史本源进行追根溯源的叙事,……虽然这类叙事模式在展现个人生活成长史、家族史的时代变迁中并不一定会闪现出现宏阔的时代风云气势氛围,但仍然能够折射出当时的历史时代社会变迁的风云轨迹,从而引发各色人等对中华民族传统与当今现实社会的种种深入思考。”[5]这就阐明了家族叙事必然或多或少反映时代的风云,并在其中加入作者的独特道德伦理审美,进而对人性的复杂与社会关系进行反思。在这种叙事伦理模式之下,对社会历史的折射而形成的道德伦理准则思考,即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书写人民叙事伦理而形成的启发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家族史传的叙事伦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家族血缘与文化血缘的交织为线索,呈现不同人物的命运离合。
(一)家族血缘
家族血缘是家族史传叙事伦理模式的第一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有人认为‘人际’的一切事情自家庭始,‘孝’是人际中最主要的伦理,……由此,产生了家齐而及于国治的理念,国之本在家,统治者极为重视这种宗亲伦理,以作治国之本。”[6]这就点明了血缘关系是宗法制度的重要纽带,伦理型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家族伦理关系密切相关,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家族血缘的伦理要求甚至对治国的方略产生重要影响。家族史传的叙事伦理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以家族的血缘为纽带,从形象设置到情节选择,展现了家族中不同人物命运相互交错的历史图景。
以上是对《母亲河》中的主要人物关系进行的梳理,小说主要展示了赵、贺两大家族在现当代历史中的命运浮沉。

1. 五种形象选择
在贺、赵两个家族中,有商,有官,有农,有工人,有知识分子,作为五种力量进入历史。商人的代表是赵春月,官的代表是贺庆生,从血缘伦理上来讲,两人是表兄妹关系。从政治伦理上来说,两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商在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交往,两个人代表的血缘伦理使得关系必然亲密,而不同身份地位的政治伦理要求贺庆生抛下血缘伦理下的私心。因为庆生坚持操守不为春月大开方便之门,两人的关系一度僵化,直到庆生的母亲、也就是春月的姑姑去世才得以缓解。王蓬先生认为赵国强的发迹,“恰是一部当代中国农民涤荡改革开放的活剧”[7]。本来是农民的赵国强抓住改革开放的时机,最终挣脱出土地的限制,这种对农业进行淡化处理的方式,表明了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工商业。工人阶级的代表是赵界生,他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终于靠过硬的技术获得了幸福的生活。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两个,一个是贺玲,一个是秦岚,两人在文中的作用却不尽相同。贺玲身上带着某种哲学家的潜质,对人生、对情感、对婚姻都有一种彻悟式的见解,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理性传统。秦岚则是柔情与深情的代表,为生硬冰冷的家族叙述注入温情的底色,是知识分子感情的象征。
2. 四种情节设置
在描写家族血缘的重要性时,小说中主要设置了四种情节。第一种是整个家族的聚会。“贺家几族在外的人南北飘零各不相识,数年后终于在香港举办的贺氏宗谱聚会上,贺家的后人们才有了些相交相识。”[4,p24]本来各不相识的人并不存在什么感情基础,正是有了血缘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得以进一步发展。第二种是小说几次提到“上坟”。秦岚给父亲秦光明上坟,赵凌芬带着儿子和孙子给贺文雍上坟,这种行为本就是铭记家族血缘的仪式。第三种是子孙后代对先辈的崇拜模仿。以贺庆生最为典型,赵凌芬几次提到庆生与其父亲很像,这既包括了生理特征的类似还包含了人生选择的一致性。庆生的父亲平反后,母亲恢复工作,庆生继承父亲的遗志再上高原就是鲜明的体现。第四种情节设置就是流落他乡的人认祖归宗。这个和中国历史有关,国共两党的纷争,大陆与台湾海峡的分裂,出现了家族史传叙事伦理模式的特殊现象,老兵们的寻根祭祖,海交会上背井离乡之人渴望认祖归宗。
(三)文化血缘
文化血缘是家族史传叙事伦理模式的又一叙事伦理线索。“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8]这就肯定了家族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家族小文化就无以探求中国的大文化,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石。此外,关于家族文化与伦理的关系从李卓对家族文化的定义中可以略知一二:“家族文化主要包括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家族成员的家族观念及对自身、社会与家族关系的认识。”[9]这就凸显了家族文化的功能,尤其是对伦理关系调整上的重要作用。在《母亲河》这篇家族史传的叙事伦理模式中,作者叙述家族史,将小家族纳入到大的国家传统之中,在共同的文化血缘中,小说中人物既坚守了传统文化,又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找出出路。
1. 传统文化的坚守
小说中多次出现古文与诗词,这是坚守传统文化最直观的表现。贺玲一生都记得爸爸常常说的古人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死于安乐。”[4,p38]这是她下乡之时的自勉,更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旅居台北之时,适逢春雨,思乡之情难以抑制,贺玲念出了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以寄寓乡思。另外,贺庆生对古典文化十分热衷,曾化用曹操的《龟虽寿》[4,p454],背诵苏轼的词《定风波》[4,p519];周天佑在内地省亲时背诵杜牧的《山行》[4,p175];渴望回归故土的老兵将于右任的《望大陆》悬挂于墙上。每一首诗的出现,都和人物命运与心情息息相关,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展示了文化血缘之下,一个家族中个人命运的发展。
除此之外,作者关于酒桌“段子”呈批判态度,认为“这些‘段子’在起着‘蝼蚁之穴’的作用,在慢慢瓦解着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涣散人心的作用”[4,p182]。这就把贺庆生的价值观与批判态度进行了展示,同时揭示了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为了弥补精神文化资源的空缺,作者引出了《母亲河》的大型文化演唱会这一情节,褒扬了为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有识之士。
2. 中西文化的碰撞
贺庆生在读大学时,把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做了对比,总结出西方人的性格似海,而中国人的性格似山,并得出了“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西方文明也许并不亚于东方文明”[4,p486]的结论。他开始教书生涯,对文学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中国的伤痕文学,不仅是对产生那个时代的悲剧的深刻思考和揭露,亦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中千千万万悲苦灵魂的呐喊,是一次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是可以和中世纪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化史。”[4,p88]这就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放在一个大的学术史上进行了比较,主人公的思想进一步深入。贺庆生就《新时代与文化》这个主题进行演讲[4,p118],内容纵横古今中西,对西方文化的精髓进行吸纳总结,不仅仅是在知识上进行吸收,并着力于将中西文化与这个时代相契合,以走出更好的道路。
总之,家族血缘使得家族得以存在,而文化血缘使得家族得以发展,两条叙事伦理线索缺一不可。
三、道德叙事伦理的多元对立
《母亲河》这部小说跳出家族对立与阶级对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开展“多元对立”的叙事伦理模式。小说中没有家族之间因为权力、欲望而产生的矛盾,也没有不同阶级之间社会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以道德伦理作为维系小说的纽带,这就打破了传统家族叙事小说的藩篱,以家族叙事伦理模式展开叙述。而且,何振基先生通过不同人物之间道德的两极对立,展示对历史、对家族的道德伦理审美批判。
(一)道德的两极对比
何振基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人伦’在文革中被遗忘,对人伤害最重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有的是因为政治,有的是因为爱情,有的是因为仇恨。”[4,p477]贺庆生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道德的两极对比,主要是围绕他展开。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作家的人民叙事伦理,在官场上他的清廉公正,一心为民,勇于和黑暗势力作斗争,提供了可供参照的道德范本。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自由伦理叙事,在爱情与婚姻中,作者展示了主人公的生命感受与个体的道德境况,是主人公道德自觉的呈现。
1. 政治官场上的清廉与腐败
“古老的中国社会,政治的主体是由文人集团组成的,文人特有的伦理关怀与道德使命,塑造着中国特殊的政治伦理文化……故此,历来官场政治生活中,道德与政治的纠葛都难解难分。”[2,p74]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种政治伦理文化依旧适用,政治主体所提供的道德范式对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小康乃至社会风气都有巨大的影响。
小说主人公贺庆生在大学毕业之后,到高原上的石油基地调研,调解牧民矛盾,精神境界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历练,造福百姓的信念更加坚定。重返故乡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积极惩治贪污腐败现象。在烟草厂的上访中,将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稳妥处理好这次事件,使得官民关系进一步拉近。手握实权的贺庆生甚至不顾表姐赵春月的请求,以公正严明的态度处理企业招标的事项,致使赵春月很多年都不能释怀。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将这种反对以公谋私、刚正不阿的光辉共产党员形象树立得较为丰满。其政治对手柯明,在换届考察时,写匿名信件污蔑贺庆生的四大问题[4,p454],勾结王志中,利用钢厂凶杀案件,无事生非,步步设下陷阱,与贺庆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叙述对官场中的黑暗、对政治伦理文化的现状都是极有力的揭示。
2. 婚姻爱情中的克制与放纵
在如此宏大的叙事伦理中,婚姻和爱情的描写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制度的变革或多或少会影响人们思想的变化,婚恋观出现的新因素是作者着力之处。作者曾借贺玲之口说明那个时代婚姻的现状多数是出于报恩意识,或者是生存的需要,对特定时代的婚恋观做出了极为精辟的阐释。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随之开放,婚姻爱情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打破这个伦理困境需要作者的深刻思考与叙事智慧。
贺庆生与秦岚的感情可谓是柔肠百转:“庆生对秦岚感情上迟钝是有道理的,他们不是一母同胞,但却是异姓兄妹,兄妹情深是正常的,但是兄妹相恋确实是违背社会伦理的。”[4,p138]正是因为恪守社会伦理,出于对婚姻的负责,两个人彼此克制,贺庆生对妻子周秀琴始终如一。与之相反的是柯明与邹义相互勾结,对待男女关系肆意而妄为,与郝丽丽顺水推舟,对刁雨晴威逼利诱。同样是夫妻的赵国强与丁楠,先是丁楠不甘寂寞与马奎有了婚外情,致使国强遭受无妄之灾,之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居然纵容国强和雨晴的关系。这些都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婚姻爱情出现的变化,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进行了有力地揭示与抨击。
(二)精神的救赎与呼唤
对于一部小说的价值的评价,周保欣认为:“作家叙述到的事件、行为、生活现象、社会与人生现象是否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与自我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人性的提升。”[2,p8]《母亲河》对历史事实的曲折表述,对社会黑暗面的揭示,最终落脚点是对精神的救赎与呼唤。
1. 出走与回归
鲁迅曾提到“娜拉出走与回归”之问,《母亲河》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彻悟的人,每个人的精神都有一个不断成熟、不断演进的过程。文中主要有两条线索描写精神的出走与回归:一是秦岚的几次出走与回归,对故乡的感情纷繁复杂;二是秦岚与贺庆生对秦光明的感情变化从感性到理性。
首先,秦岚对故乡的心路历程,从不愿回到故乡到迫不及待地回归:
她不想回到故乡的少年的屈辱地,那里是魔鬼的天下,她甚至永远也不愿意回到故乡。[4,p77]
(秦岚)一旦决心回归,就一天也在台待不下去。……她决心回归大陆,是要与庆生做一个了断,是要回故土做一个了断,是要做一个落叶归根的了断![4,p454]
第一条是秦岚在云南求学时的心态,她迫不及待地逃离了故乡,甚至再也不愿意回去,这其中的感情侧重于“逃避”。经过几十年的沧桑,秦岚流落海外,其回归的心变得迫不及待,对故乡的认识更加深刻,不再逃避,而是采取直面现实的态度,这是她对故乡认识与感情的发展历程,最终的回归使之内心安宁。
其次,秦岚与贺庆生对秦光明的感情变化。秦岚漂泊在外,只有两次主动看望父亲。她赴云南师大求学,在这三年期间对父亲的联系只有五六封信[4,p77]。秦光明去探望秦岚[4,p95],秦岚也并未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秦岚第一次主动看望是凌芬去世时,在周南见到垂老但依旧贪婪的父亲[4,p239]。第二次是在阳坝见父亲,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4,p281]。第一次的感情态度带有些许厌恶,到了第二次,面对秦光明的忏悔,秦岚终于原谅了良心未泯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放过了自己,对后母的愧疚终于得以缓解。
贺庆生为了报仇,打了秦光明,“但是这一巴掌,却使一个年轻的心灵欠下了永恒的债,忏悔了一生一世”[4,p47]。作者塑造了贺庆生正直光辉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他曾经年少冲动,使得人物形象在渐进中丰满,思想在实践中逐渐成熟。他后来在秦光明坟前拜祭忏悔,其精神的反叛最终回归理性:
继父,我们曾经相互仇恨过,请你原谅我那时的无知和鲁莽!当历史的烟云过去,我们或许应该互相原谅。人生苦海,悲欢离合,都得走下去,我们无法选择,但我们终会谅解。[4,p549]
书写家庭伦理中的反叛与回归,反叛的是家庭伦理中不合理的部分,精神的回归之处则在于理性的安宁。经过历史的沧桑演变,人的精神也得到历练,从鲁莽无知到放下仇恨,是理性的回归,也是家庭伦理的回归。
2. 沉沦或奋起
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要拷问社会,拷问人性。从沉沦还是奋起的选择中呼唤精神,其选择必是艰难的,但正是这种纠结与挣扎才能更多地暴露出人性中的罪恶,才能更好地凸显高尚伦理价值精神的可贵。《母亲河》中有很多对社会现象的论述,对这些现象,作者忧虑并试图建立道德伦理基础以探索其出路。
飞速发展的社会展示着万花筒般的奇妙,就像高空的烟火,辉煌灿烂而又迷迷蒙蒙;就像大海的漩涡,深藏于汹涌的波涛下面不知深浅。知识不再被看重,大胆也可以发财;贞操已经不重要,情色开始泛滥;诚信受到嘲讽,陷阱越来越多;权柄备受青睐,官风民风日衰;社会欲望弥漫,气象雾霭重重。你如果不仔细看,那河里似乎漂流的全是肮脏和污秽。[4,p148]
几个人沉思了一会儿,好像都在想:人富起来了,现在缺少啥?[4,p156]
作者以尖锐的笔触谈及社会财富无限积累的同时,揭示了人伦关系败坏、诚信缺失、情色泛滥等社会现象。“你如果不仔细看,那河里似乎漂流的全是肮脏和污秽。”“仔细看”就是要求努力探究污秽背后的原因,以提出解决的办法。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扭曲的价值观涌入,社会陷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对等的困境,国家意愿与民众执行出现了不对接的状态,何振基先生此时塑造出贺庆生这样的人物,无疑是一场呼唤道德伦理的精神支援。
综上所述,《母亲河》以家族叙事伦理模式,创造性地将人民叙事伦理与自由叙事伦理相结合,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在文学体式上,小说打破了传统家族小说中“二元对立”的叙事伦理局限,融合两种叙事伦理模式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这对于文学体式与时代的切合有着创化意义。此外,小说的深刻性还在于既写出了历史自身的复杂性,同时又以自己的历史与伦理道德理性,赋予历史叙述以一种道德伦理基础。
[1]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香港:华夏出版社,2004:10.
[2] 周保欣.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953.
[4] 何振基.母亲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5] 李永东.颓败的家族: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1:43-44.
[6] 王贵民.先秦文化史[M].上海:上海书店,2013:155.
[7] 王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读何振基长篇小说《母亲河》[N].光明日报,2016-11-29(3).
[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1.
[9]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
On Family Narrative Ethics Model of He Zhen-ji’s “
WANG 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The novel “” perfectly combines the narrative ethics and free narrative ethics freedom to show a family ethical narrative model with high aesthetic wisdom and profound thought. Firstly, in the family narrative model which is combined family narrative with historical narrative, it delineates the family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y writing “country” with “family”, it intertwines two developing clues of family and country in order to expand the narrative space scalability and time capacity. Secondly, the cultural consanguinity and family blood mingle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the narrative model of family history transmission. Finally, the author reflected keenly on the multiple narrative modes of moral ethics. Both the poles of morals in history and rebellion and return of families are deep creative cultivations of human nature of compassion based on this mode.
people’s narrative ethics; free narrative ethics; family narrative ethical mode
I206.7
A
1009-9115(2019)01-0044-08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10
西北大学研究生质量提升工程项目(自主创新资助型)(YZZ17025)
2018-04-25
2018-11-01
王平(1990-),女,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