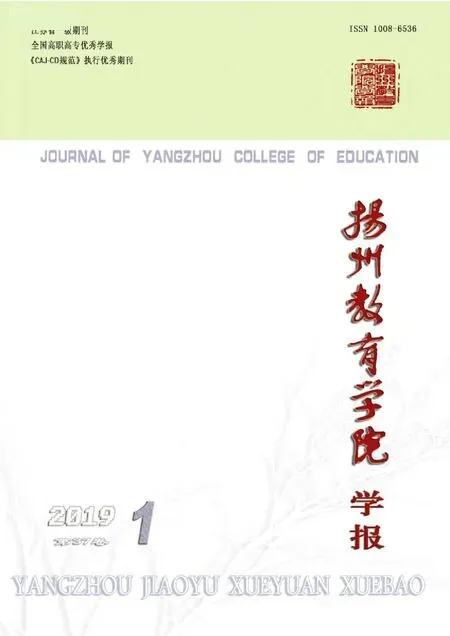伍 子 胥 与 邗 沟
——唐《伍相神庙记》考述
张 永 娟
(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 江苏 扬州 225008)
邗沟是我国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人工运河,也是大运河的前身之一。说起邗沟,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吴王夫差,现在扬州邗沟之畔的大王庙里仍供奉着吴王夫差的雕像。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那就是谋划开凿邗沟的伍子胥。近读唐代卢恕《楚州新修吴太宰伍相神庙记》(以下简称《伍相神庙记》),所述伍子胥与邗沟等相关史事较详,颇可补其他典籍之未载,具有较高的价值,故而略加考述如下。
一、郑漳与《伍相神庙记》
卢恕《伍相神庙记》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见载于《文苑英华》与《全唐文》,两者文辞略有差异。其文曰:
舍人事而介福,专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为也。苟不以仁惠爱民,而止以堕怠理道,持甘酌芳饎以交神,神在聪明正直,岂许之乎?若忧勤焦思,访接无怠,于贤人且不遗,况贤神乎!所以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也。
楚州淮壖涘太宰伍相庙,置在吴时,临邗沟。当伐越时,为馈运所开,太宰经画。及因谗而没,其神凭大波,雄愤无所泄,蓄为猛飙骇众。吴人恐之,故相与立祠邗沟上。历代皆崇其祠,椎牛酾酒,小民有至破产者。比齐清河王励刺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渎非神之意,其风稍革。国朝龙朔中,为狂人郭行真所焚。乾封初准敕重建。
大中十岁四月十八日,上以山阳荐灾,当宁忧轸,曰:“非朝之显德清望有材者,不可分吾忧子众姓。”于是诏兵部郎中荣阳公守郡,立政行道,得民之心。每两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请之,灵贶立答。连岁丰穰,岂非神之阴赞耶!旧庙菆隘浅迫,前横岸道,尘坌玷亵。公默图将显大之,且俟诚化更广,即增张神宇。俄有州人蒋容者启公,请合财葺之。殆天启乎,何冥契如是耶?于是开其前,伸其后,重肖神像及仪从等毕。新庙之成也,面河距淮,岩然崇堂,蜿然修廊。像设新而英姿益明,旗旓新而灵卫愈严。庭可以长布武,阶可以劳拾级。管箫朝奏,一何和神也;风月夕清,一何宜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林谷川泽,民所财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山谷。彼青骨而邀食于民者,岂得同日而语。
洎诏徵公为左谏议大夫,释符之日,恕蒙公付以留务。行及祠前,顾谓恕曰:“有事或诚存太宰,其应也如响。今去,能无感焉!君为我编其修建之由。”恕谨奉教,一无伪饰。公之始至也,承菑沴之后,庐井残矣,廪藏空矣,道既僵殍,牢亦充塞。及公之布德也,四时洽畅,千里醉歌,帑廥皆溢,庭无讼人。乡县郭邑,致十倍之繁富;廓宇亭肆,兴万堵之宏丽。休祥表见,仁声流扬,传车云归,耆少遮道,竟夕不得前。虽古之良二千石,实有惭色。素负谦损不先之道,至于理功,皆不欲人言。恕亲吏也,其可隐而不书?巨唐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记。[1]
《全唐文》云卢恕“大中时官苏州府掾”,未知何据。检索史籍,未能查知卢恕的家世、宦迹。
新修楚州伍相神庙之主事者,郁贤皓据《伍相神庙记》中“荣阳公”(当是“荥阳公”之误),推测姓郑,名讳则不知,称作“郑某”[2]。根据其他史料,其人或是郑漳。《东观奏记》记载:“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郓王已下侍读。”[3]《因话录》又载:“郑又自说,早承相国武都公知奖。当时为大理司直,常叹滞淹。会张謩欲除太常博士,李公云:‘郑司直久屈,必请举自代。’旋遇萧儹服阕,且要与官,诸坐遂以萧为博士。前此有大云寺僧宝锐者,知人休咎。因问之,锐曰:‘司直朝官终得,中间且合为数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历作河阳、浙西、淮南,累至检校郎中,方除比部员外郎。”[4]此条之前“大中九年”条后有“侍读谏议漳说”,岑仲勉[5]、陶敏[6]皆认为“郑”“侍读谏议漳”都指的是郑漳。其说甚是,可为定论。楚州为淮南道所辖一州,如此,则郑漳姓氏、曾为淮南道某州(楚州)刺史、大中十二年为左谏议大夫,皆与《伍相神庙记》相契合。
大中九年(855),江淮数道受水旱灾害,唐宣宗于七月颁下《赈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云:“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为人父母,宁不震悼!……应扬、润、庐、寿、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其间或贞元以来旧欠逃移后,阙额钱物,均摊见在人户,频年灾荒,无可征纳,宜特放三年。”[7]此次大灾,楚州亦在其列,所以大中十年“上以山阳荐灾”,任郑漳为楚州刺史。郑漳多次至伍相庙祷祠,常获灵验,遂扩大其规模,重修新庙。《伍相神庙记》正是卢恕为记录其事、夸耀郑漳政绩而作。
二、伍子胥与邗沟、伍相庙
《伍相神庙记》记载了楚州伍相庙自春秋至唐代的变迁过程,其先云:“楚州淮壖涘太宰伍相庙,置在吴时,临邗沟。当伐越时,为馈运所开,太宰经画。”太宰伍相即伍子胥,原为楚人,父兄受谗被杀,遂奔吴,时在吴王僚五年(前522)。在吴国晚期历史上,伍子胥是一个重要人物,受吴王长期重用,西击楚国、北上争霸、修筑姑苏古城、开掘胥溪等等,都可见其谋划参与的身影。按《伍相神庙记》所言,邗沟亦为伍子胥所主持开凿。
《左传》载鲁哀公九年(前486):“秋,吴城邗,沟通江淮。”[8]开凿邗沟、修筑邗城,是吴王夫差为北伐齐国、争做霸主所作的准备。楚州位于邗沟与淮河相交处,在当时应是较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吴王夫差即位之初,对伍子胥甚为信任,曾欲分吴国予之,后却听信太宰嚭的谗言,赐死了伍子胥。《史记》记载伍子胥临死之际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吴王闻之大怒,取其尸浮于江中。吴人怜之,为伍子胥立祠于江上[9]。司马迁所载,是吴人怜惜伍子胥受谗而死,为之立祠。《伍相神庙记》则说是伍子胥死后魂魄“雄愤无所泄,蓄为猛飙骇众。吴人恐之”,立祠地点也与《史记》不同,是邗沟沿线各地皆有。《水经注·淮水》载:“县有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县城临江,……县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旧江水道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10]则至迟在汉代时,广陵江水、邗沟交汇处亦有伍相庙,与楚州相同。
除了邗沟沿线,吴国故地还有多处伍相庙。东汉王充《论衡·书虚篇》云:“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恚恨驱水为涛者,虚也。”[11]大量伍相庙的出现,是伍子胥信仰的具体表现。
三、伍相庙与早期伍子胥信仰
由于吴王夫差投伍子胥尸体于江,又由于古代江潮汹涌、江阔难渡,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认为江水猛涛乃是伍子胥死后恚恨难平所为,甚至将其奉为“水仙”“江神”。《越绝书》载:“胥死之后,吴王闻,甚咎子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12]左思《吴都赋》刘渊林注:“昔吴王杀子胥于江,沈其尸于江,后为神,江海之间莫不尊畏子胥。将济者皆敬祠其灵,以为性命。”[13]《后汉书·张禹传》载:“建初中,拜杨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14]可见吴越之地都认为江中有伍子胥之神,这与先秦时期的多神崇拜、神灵世俗化以及秦汉时期造神运动、民间崇拜扩张的社会信仰变迁是息息相关的。为了求不起风涛、平安渡江,百姓多向伍子胥庙祷告祭祠。
这种关于伍子胥的朴素信仰在其死后就已经开始,延至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江于江都,……皆使者持节侍祠。”[15]前引《水经注·淮水》载:“县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祭祀四渎五岳是“祈为天下丰年”的国家行为,伍子胥得以配食于江水祠,实际上是被纳入了国家祭祀、信仰体系之中。到了南朝,梁元帝(552-554在位)甚至亲自祭祀伍相庙(此伍相庙应在都城建康),并作有《祀伍相庙诗》[16]。这些都说明伍子胥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民间信奉祭祀伍子胥,也带来一些问题。《隋书》记载:开皇初年,高劢“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17]。此即《伍相神庙记》中所说的“历代皆崇其祠,椎牛酾酒,小民有至破产者。比齐清河王励刺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渎非神之意,其风稍革”。信仰伍子胥这类地方祠祀及其带来的问题,受到道教的持续批判,楚州伍相庙“国朝龙朔中,为狂人郭行真所焚”,即是其具体表现之一。郭行真是唐高宗、武后时期十分得宠的道士,出入禁中,并代高宗武后至泰山造像立碑,是当时宗教界的领袖人物。龙朔年间(661-663)焚毁伍相庙等等地方祠庙,可能正是为了树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权威。不过,龙朔三年郭行真因罪被流放[18],大约因此之故,乾封(666-668)初又“准敕重建”了楚州伍相庙。
从整体上看,伍子胥信仰逐渐被政府认可,这从汉代伍子胥配食于江水祠即可见一斑。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拜冬官侍郎、持节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杰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而已”[19],也说明伍子胥庙是官方许可的民间信仰,不在淫祠之列。所以,虽有郭行真焚毁楚州伍相庙这样的极端事件,但并非社会的主流。绝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还是默许这类信仰的存在,甚至在遇到水旱灾害时,亲自去祭拜这些祠庙,并为其重修、增筑,以彰显自己亲民爱民的仁德之政[20]。郑漳请卢恕为新修伍相神庙撰写记文,自然是将此作为自己的政绩之一。卢恕《伍相神庙记》中“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云云,也为郑漳修庙行为提供了绝佳的理论依据,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吻合的。
四、结语
伍子胥谋划开凿邗沟、受谗而死后,民间百姓惧之、怜之,认为其化为水仙、江神,在各地为其立祠,邗沟沿线也多有之,楚州伍相庙即其中之一。卢恕《伍相神庙记》记载了伍子胥开凿邗沟和伍相庙的变迁过程,对于了解大运河早期历史和沿线民间信仰都大有裨益,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