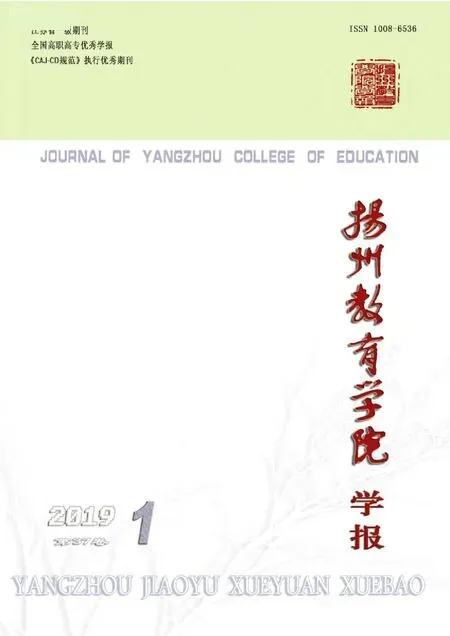《我的天才女友》的女性主义解读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我的天才女友》是意大利匿名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于201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她“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小说的首部,中文译本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两个女孩子——叙述者“我”和“我”的天才女友莉拉的童年、青春期经历为线索,展示了二战结束后50、60年代意大利那不勒斯一个破败小社区的风土人情。在这个充溢着血腥、暴力、资本、欲望的小地方,底层民众为了生存与贫穷抗争,一部分觉醒的女性为了自由解放与父权制对抗,阶级、性别冲突互相交织,压迫与反抗同频共振。
巴巴拉·艾伦瑞奇认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看待世界时都持批判视角,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的“合谋”,追求性别平等或阶级平等。故事发生的背景,恰逢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美国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种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女性主义受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启发,将生产、再生产、劳动、价值、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与女性主义相结合,通过性/性别结构、阶级关系揭示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重视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产生并发展。《我的天才女友》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觉醒和反抗的“史诗”。成长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埃莱娜和莉拉,逐步看清家庭与社会的权力格局,认识到想获得自由,就必须通过反抗争取独立的经济地位。
一、女性成长:两生花般的“姐妹情谊”
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埃莱娜与女友莉拉错综复杂、充满张力的友谊。也许读者自始至终都无法确定这两个女孩到底谁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作为叙述者“我”的埃莱娜,还是“我”浓墨重彩塑造的女友莉拉?或许,两个女孩就像并生一枝的两生花,性格迥异,既相互扶持又暗中竞争,既是统一战线又处在对立的两极,相反相成地生长着。同时,两朵花又在彼此的身上照见自我,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对方的影响和对彼此的依赖。并蒂而开、力量卑微的她们相依而生,最终得以在险恶纷乱的世界上绽放出光芒。
小说中“我”和莉拉童年生活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贫穷和暴力仍旧存在的那不勒斯。“我”是市政府门房的女儿,过着相对稳定和按部就班的生活。作为大人眼中伶俐懂事的乖孩子,“我”按照长辈设定的成长轨迹,一路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而莉拉作为鞋匠的女儿,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教育之路止步于小学毕业。然而在“我”看来,她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天才,考试第一名对她来说简直稀松平常,她能看书写作,又能自学拉丁语。这个看上去又瘦又脏、嘴巴刻薄的姑娘常常受人厌弃,但她身上与生俱来的“野气”和抗争意识令“我”既敬畏羡慕,又无比嫉妒。莉拉过着一种“我”求之不得的生活,她激发出“我”内心蠢蠢欲动的独立意识。因此,我本能地靠近她,追随她,与她分享自己的悲伤和喜悦。在学业上,两人相互攀比、暗中较量、彼此激励,生活中,莉拉带“我”逃学去看海,向暴躁粗鲁的阿奇勒索要自己的布娃娃……莉拉是“我”被压抑的另一面生命,对莉拉的追随体现出“我”对自由和独立人生的向往。
同时,“我”也构成了莉拉的另一面人生。莉拉小学毕业后就被信奉读书无用论的父亲禁止继续求学,反映出那个时代男权、父权思想对处在附庸地位的女性个人价值的压抑。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作坊中,如同本斯顿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描述的,女性处于交换和市场之外,她们的工作不具有交换价值,也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莉拉对“我”是羡慕的,虽然通过大量阅读和自学,莉拉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果让“我”不禁汗颜,但好强的她在心底里向往学校生活,故而难以释怀、深深自卑。小说的最后,即将出嫁的莉拉对埃莱娜说:“但你不一样,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要厉害,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1]305读者不禁感到惊讶,原来“天才女友”不仅是埃莱娜对天生伶俐的好友莉拉的赞美和指称,在要强好胜的莉拉心目中,埃莱娜代表着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女性通过受教育走向独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埃莱娜和莉拉在对彼此的观照中看见自己隐秘的另一面,她们冲突对立,又互相扶持、启发,共同成长。这对姐妹花与社区其他女孩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们接受了知识的启蒙,获得了改变自我和世界的勇气和信心。莉拉的辍学没有使她停止阅读和写作,小说提到两个女孩废寝忘食阅读《小妇人》和《爱的教育》的情节,侧面反映出教育对女性启蒙的重要性。莉拉与“我”虽然也继承了一些陈旧的观念,但并没有成年女性那样根深蒂固,也没有像马尔切洛和斯特凡诺的妹妹等同龄人那样,精神空洞、循规蹈矩地谈着恋爱。她们在外表、个性上或许存在不同,但骨子里却都受到了知识的浸染,被激发出强烈的自由意识和反叛精神。
20世纪60年代,参与西方激进组织运动的妇女逐渐发现自己在组织中的“失声”,她们发现同一阶级的男性仍然存在性别歧视,意识到唯有成立独立的妇女组织,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于是,她们以“姐妹情谊”为口号,强调妇女应当联合起来,相互鼓励、一同抗争,提高女性地位。但是,由于妇女群体内部构成的复杂性,不同民族国家、社会阶级、利益诉求使她们几乎不可能形成纯粹的、理想化的“姐妹情谊”。或许最真实的状态是,不同出身、背景的女性因追求解放和自由的共同理想走向联合,在共赴目标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帮扶,形成难解难分的情谊。《我的天才女友》中的“姐妹情谊”融入了排斥甚至对抗的“杂质”,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它恰恰摆脱了“姐妹情谊”中超现实、笼统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形成一种看似异乎寻常,实则最合情合理的姐妹情谊。
二、精神觉醒:母亲作为“隐喻”
小说围绕女性共同的心理与生理体验展开,记录二战后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新时期下,以“我”和莉拉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身体与心灵的成长路径。在女性生命中,母亲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母亲往往影响着她们是否形成,以及形成怎样的女性意识。《我的天才女友》存在着关于母亲的“隐喻”,通过“我”对作为血缘意义上的生身母亲农齐亚的厌恶、疏离,对精神意义上的母亲,“我”和莉拉的小学女教师奥利维耶罗的认同、归属,表达对女性成长过程中精神觉醒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西方社会,经典的母亲形象是作为家的天使存在的。她们被要求具备以下美德:精心抚育孩子,全心全意支持丈夫,有爱心懂奉献,温柔博爱。这背后体现的,仍旧是作为主导的男权思想对女性的规范和制约。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贾格尔在《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中提到了女性作为母亲被异化的问题,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妇女无权决定自己生几个孩子,妻子的生育权掌握在丈夫手中。小说一开篇,就提到“我”和生身母亲农齐亚的关系“不怎么样”,不仅因为“她走路一瘸一拐”,在“我”看来是一种丑态,还因为“在她的生命中,我是多余的”,反映出性别压迫中男性对女性肉体的占有。母亲农齐亚在“我”眼中是父权、男权制度的受害人和同谋者,“我”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学校念书,恰恰源于父亲的决定和母亲对父亲决定的绝对服从。青春期身体发育中的“我”,一度害怕自己变得像母亲一样。她残缺的、不完美的身体,象征着传统女性被压抑和被损害的生存状态,她们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般内心麻木、主动认同地践行男权价值观。小说中多次出现母亲农齐亚的银镯子这一意象,青春期的“我”用它在莉拉面前炫耀,满足生理本能的爱美和虚荣心。这一极具女性阴柔气质的装饰品,或许是“我”能从生身母亲那里得到的唯一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帮助“我”和莉拉摆脱蒙昧之境,走上精神觉醒和反抗之路的,是小学女老师奥利维耶罗。小学时候的莉拉不被喜欢,无人靠近,她首先发现了这个姑娘聪慧的头脑和过人的天赋,并表现出赞许和赏识;“我”每一次升学机会的获得,与她不厌其烦的家访、对父母的劝说直接相关;她对莉拉的辍学深表惋惜,并一直关注着莉拉的学习和生活。可以说,奥利维耶罗老师是两个女孩的精神之母,她代表着女性的启蒙和被解放。在奥利维耶罗老师强大的气场和坚决的态度下,父亲对于她的每一次家访都紧张万分,并不得不执行她近乎命令式的建议。她是执着而可爱的,关心自己女学生的成长和教育,也深刻认识到教育对女性的重要意义。教育不仅关乎知识和技能,以此获得谋生能力,更帮助女性开阔视野、完善心智,成为精神上高度自足,不依赖于男性存在的独立生命体。
小说故意隐去了奥利维耶罗老师的婚姻和生育状况,透过埃莱娜的表述,自己的这位小学老师更有可能是终生未婚的。当她得知自己曾经的得意门生莉拉年纪轻轻就要踏入婚姻,失望、惋惜甚至愤怒,拒绝前来拜访的莉拉踏入自己的家门。“就好像她是我母亲,而我的亲生母亲——那个腿脚有毛病、斜眼的女人是一个次品,并不需要获得她的认可。”[1]195在作者笔下,这个倔强甚至专断的女性,作为精神启蒙之母的奥利维耶罗老师,显然比血缘上的母亲农齐亚形象更加光辉和高大。这个或多或少带有居高临下甚至颐指气使姿态的人物形象,常常让两个女孩感受到压力和不自在,但透过“我”父亲对奥利维耶罗老师几乎无条件的服从甚至敬畏,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在反抗性别压迫,争取女性教育权和人格独立所做的努力,透露着女性解放的希望之光。
三、独立之路:反抗与依赖之间
在故事发生的那不勒斯,充斥着贫穷、暴乱、血腥的争斗。暴力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家庭中,男人欺凌女人,女人“比男人斗得更凶”,她们互相伤害,也对自己的孩子拳打脚踢。除此之外,还有哮喘、破伤风、毒气、废墟、工作、肺结核……它们不仅构成了“我”童年的阴影,这些创伤性体验更成为生命中永恒的伤疤。在伍尔夫所言“总是男人的价值占优势”的时代,莉拉通过自己的力量冲破家庭作坊和父权制的束缚,进入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争取和行使妇女追求财富的权利。
“女权主义者认为,对于经济因素的重视是女权主义从马克思主义那儿得到的恩惠。”[2]不论是西蒙·波伏娃,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经济独立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在小说中,不乏走出家庭劳动的私人领地,投入到资本市场中谋生的女性,例如堂·阿奇勒的妻子,因为丈夫被谋杀而开始经营肉食店来养活儿女,又如恩佐母子因家庭男主人离世,走上街头卖菜谋生。然而,这些女性并非真正从思想和身体上走向了自由和解放,而是通过模仿男性进入社会,为生计所迫,不得已从事男性的工作。当她们的儿子可以独当一面时,这些母亲又退回到家庭生活中,继续传统妇女的家务劳动。
莉拉作为真正受到意大利经济复兴、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受益于学校教育飞速发展的新一代女性,做出了迥异于母辈的选择。辍学后,虽然被父亲安排在家里的修鞋铺劳动,可她深知金钱就像是水泥,“可以加固我的生命”。追求财富成为她反抗父亲专制的方式,她始终有着开鞋厂的梦想,自己设计鞋子向富人区出售。然而鞋子的销量并不尽如人意,此时她又决定嫁给事业有成、家境富裕的斯特凡诺,提高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通过拥有财富获得安全感。
莉拉的所作所为不应被简单定义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拜金。对于以莉拉为代表的早期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觉醒后的她们反抗原生家庭中父权制对自我的禁锢,但男权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政治大环境对逃出家庭的女性来说,仍旧充满歧视、压抑和不平等,她们追求财富道路上的阻力远大于男性。莉拉是勇敢的,她大胆反抗父权;莉拉又是悲壮的,为了更好地与父权决裂,她旋即落入夫权掌控的深渊。婚礼上,面对新婚丈夫的背叛,她一下子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小说在此戛然而止。
读者或许对莉拉有充分的“自信”,相信她绝不可能接受丈夫的背叛而丝毫不反抗,而接下来“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二部的开头,也确实写到了莉拉毅然决然向斯特凡诺提出离婚。然而,莉拉的经历无法不令人叹惋,她通过缔结婚姻追求财富的选择体现出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出嫁前,她希望自己的天才女友——“我”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这“不一样”,或许代表着一种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女性生活状态:不必依附任何男性而存在,更精神自足、经济自由、不卑不亢。婚姻爱情都不必是融入功利考量的雪中送炭,而是自尊自立新女性的锦上之花。
20世纪50-60年代的那不勒斯,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开始认识到自我的被压迫状态,一部分人觉醒和反抗。但总体而言,妇女依然处于“失声”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3]作为新女性代表的莉拉,通过嫁给有钱的男性逃离父权制的“魔掌”,却因为欠缺谋生能力和谋生机会,短暂自由后又迎来作为性别压迫另一种形态的夫权。在作者看来,追求独立的女性既是勇敢的,又是悲壮的,既充满抗争精神,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对女性的排斥,对男性依赖和妥协。小说中女性的反抗,归根结底是通过模仿男性完成的,女性获得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男性的“施舍”和“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