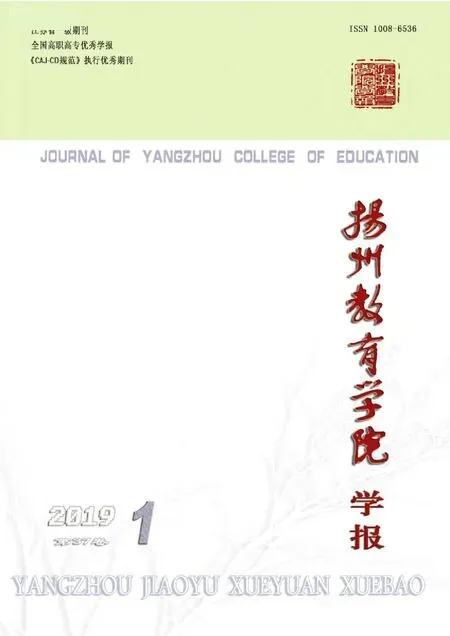布鲁克战争颂歌《安全》和《士兵》背后的死本能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鲁波特·布鲁克(1887—1915),剑桥才子,被称赞为“英格兰最英俊的男人”“阿波罗诗人”。他在一战中猝然早逝,被当时的一代人所崇拜、追忆,甚至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为其亲撰悼词,盛赞他为:英国最高贵之子的理想形象。在布鲁克逝世后,“他立即被英国的朋友塑造成为国家英雄——为众多英国年轻人树立参战的爱国榜样”[1]54。他的诗作,尤其是其代表作《1914》,更是被许多论者认为是对于战争的美化与歌颂。“布鲁克将战争认为是一个净化和升华的机会”[2]。那么,为何在其诗作中所描述的不是战争胜利时的场景,而是士兵的死亡意象?他的诗作是否只是对于战争单纯的歌颂?是否如众多论者所认为的是基于空想爱国情怀而创作?本文以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来分析布鲁克代表作《1914》中的《安全》和《士兵》,并与诗人相关的历史传记相结合,以证明战争颂歌背后所暗含的并非是爱国情怀,而是诗人自身的死亡本能。
一、死本能的弥漫
布鲁克的代表作《1914》包含了五首战争题材的意大利十四行诗,但这五首诗作从未描绘任何胜利的场景,它们所共有的一大主题其实是不断的死亡。其中更有两首诗名直接为死亡(The Dead)。“在心理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的重复动作,它超越了快乐原则”[3]17,实质上是死亡本能的体现。《安全》和《士兵》分别是诗集中的第二首和第五首。在这两首诗中,布鲁克皆描述了与死亡相关联的意象。
在第二首诗《安全》中,叙述者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夙愿——“安全是我的追寻”,而这是由他帮助我们“寻着此隐藏之地,容我们匿身之人;让我们可凭此抵御世界汹涌的暗潮;听吧,‘何人能如我们般安全?’”此时,叙述者已经找到了永恒的安全之地,不再担心人世间任何的暗潮涌动。叙述者内心渴望着能够到达这个永恒的安全之地。这个永恒之地是由他帮助我们找到的,而这大写的他是否正是对于上帝的影射?那么,这个他帮叙述者所找到的安全之地是哪里?是否是战争胜利后给人民所带来的平静?如果他确指上帝,那么这永恒之地自然是形容人死后才能到达的天堂或者地狱。诗人也在接下来的诗行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安全位于人们倒下之地”。“人们倒下之地”才是安全所存的地方,而不是人们平定战争后。而在战时,“倒下”所影射的自然是士兵中枪后的场景。安全只有在人们受伤死后才能获得,可见在这个世界、这个维度中,人们无法真正获得安全。而诗人所说的愿望,自然也只能够在死后才能获得。“假如我死了……在心里获得安宁”以及“这些残破躯体一死,便是最为永安”更是直接说出了死亡与安宁之间的关系,只有死亡才能够带来永安。布鲁克所歌颂的似乎并非战争,尤其不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胜利喜悦,而是战争致死后所带来的永久的安全。弗洛伊德指出作家们进行创作的原动力正是在生活中被压抑的本能,“这些愿望我们又必须对自己隐瞒,所以它们受到压抑,被压入潜意识之中。这种受压抑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得以一种极其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3]62。正如在诗作中,布鲁克的死亡本能被无意识不断地表现和书写。 叔本华认为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死亡本能正是人们所追寻的回到一种无生命的原初状态。“所有有机体的活动与人类心智的活动都指向消除紧张进入死寂状态……涅槃原则,其目标在于趋向死寂,趋向安息或睡眠,而安息或睡眠却不过是死亡的孪生兄弟”[4]。第五首诗的的诗名便是《士兵》,这一次诗人依然没有描述任何胜利的意象,而是在诗的首行便利用“如果我死了”将诗歌的情景预设为士兵去世之后。虽然在诗行之中可以看见诗人的爱国情怀。诸如,叙述者认为他死后“所躺的角落将永远都是英国的国土”。但是就战争本身而言,叙述者的态度则不那么乐观和肯定。叙述者怀念的依然是当时他在英国没有受到战争摧残的时光,他希望达到的是永恒的平和。而且,在这一首诗中,叙述者仍然提到在最后他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但这个平静依然是依托于他去世后这一大前提之下。《安全》和《士兵》两首诗中都体现了布鲁克对于死亡的追求,并且他深信通过死亡,人们方能获得平静。
死亡一直是布鲁克病态般痴迷的主题。布鲁克一生中最为挚爱的人物是永远长不大的彼特·潘,他害怕甚至是厌恶长大,认为“人一旦过了三十便不值得交谈”[5]。而从某种意义上,唯一能让人停止变老的方式便是死亡。布鲁克乐于拥抱死亡, 认为它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我坐在这,有着十九世纪最纯洁的宏观思考,关于人类的归宿,命运的必然,国家的毁灭。其实,死亡在前面等着我们所有人,前进吧”[6]491。在写给友人本·吉林的信件中,布鲁克邀请道“来,一起奔向死亡吧!这肯定会很好玩”[6]655。正如他所最爱的彼特·潘所认为的一般,死亡是一个巨大的冒险经历。布鲁克其实从未害怕过死亡,他似乎将死亡认为是他期许回归的家园,他渴望着早日到达预定的终点。“生命的目标必定是事物的一种古老的状态,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生物体在某一时期已经离开了这种状态,并且它正在竭力通过一条自身所沿循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挣扎着回复到这种状态中去”[7]41。也许这正是他对于死亡的态度,又或许是他内心的本能促使他在参战之前就像是预测到了自己死亡的结局一样,而把自己所有的信件、稿件和相关事务都一一安排好。他甚至嘱咐华德将他与另外两名女性的交往信件销毁以维护自己身后的名声,并称要“让(公众)知道真相”[6]671。正如第五首诗歌《士兵》一样,叙述者认为自己将死于国外,但是埋葬他的土地将永远属于英国。整篇诗歌虽赞扬了英国,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却更像是一封遗书。而布鲁克本人确实是在参与地中海远征军行动时死于前往希腊斯基罗斯岛的船舱中。在这两首诗歌当中,诗人本人都利用叙述者描绘了他死于战争时的场景,这正是由于他自己即将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于自己未来的假想,又或者说是他内心本能的驱使。
“战争不再蛮横”是两首诗中唯一一次直接提到战争的诗行。诗人认为上帝帮他们找到了安宁之地,自然战争也不再蛮横。此时,“蛮横”一词很难让人认为布鲁克对于战争有着歌颂的态度,甚至他应该对于战争的威力感到恐惧。不仅如此,一战作为当时波及力最大的事件,布鲁克在和友人的信件中,更是多次提到了这次战争。“我突然觉得,从我两岁开始,我人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军事远征去君士坦丁堡”[7]662。因此,有许多论者据此认为布鲁克渴望战争、热爱国家,希望建功立业。然而,在下文布鲁克便又说道“这都是胡说”[6]663。不仅如此,他对于现代战争感到恐惧,他看到“安特卫普荒芜、燃烧、破碎。一个夜晚,房屋成灰,人们死去,牲畜倒地……整个天与地被由汽油燃烧的河流和湖泊所燃亮。这就如同地狱,一个但丁式的地狱,可怕。但是,之后,就在这,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成百上千的难民”[8]。既然,布鲁克并不同许多论者所想的一般,他反而认为战争似乎是无意义的;而且,他对待现代战争还有着恐惧与害怕。那么,布鲁克为何自愿参加战争,这个极有可能致死的活动?究其本源,或许是他诗歌中所显露出的死亡本能。死亡本能“有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转向外部世界”[7]205,也就是施虐倾向。这种“攻击倾向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3]269。这也是为何布鲁克无法抵御自身本能的冲动。直至最后,布鲁克由于在行军过程中感染败血症,甚至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战争便离世了。至此,他的死亡本能已经促使他恢复了无生命体征的原始状态。
二、生本能的消散
《安全》与《士兵》中,诗人与叙述者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两者都是即将要参加一战的英国士兵。叙述者应该是诗人自己的投射。那么,在第五首诗歌当中“在英国出生、成长,变得有思想,曾给鲜花让她恋爱,给她道路随其漫游”。诗人为何用女性的“她”来指称自己?特别是对于一个即将“战死沙场”的人来说,他不可能是一位女性。
在《会饮篇》里,阿里斯托芬在谈到人的起源时称,最初的人是球形的,有着圆圆的背和两侧,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圆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圆圆的头,两张脸分别朝着前后不同的方向,还有四个耳朵,一对生殖器,其他身体各组成部分的数目也都加倍[9]。他们能够直立行走,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但可以任意向前或向后行走,等到要快跑的时候他们就象车轮一样向前翻滚,所以他们的力量也是现在人类的几倍。后来宙斯畏惧人类的力量,将人全部劈成了两半从而创造了现在形态的人类。由此可见人类的原始状态其实是男女、女女、男男同体的。而布鲁克用“她”来指称自己,所暗指的也许正是人类的原始形态之一——男女同体。诗人所渴望回到的就是生命的本初状态即男女同体,这其实也是作者自身死亡本能的体现。“本能是有机生命体中固有的一种恢复事物早先状态的冲动。而这些状态是生物体在外界干扰力的逼迫下早已不得不抛弃的东西”[7]39。与死本能相对,生本能“重新产生了生物的原始状态,但是,它们千方百计奋力以求的目的,是将两种特别分化的生殖细胞统一起来”[3]34。如果说死本能是将生命拉入消亡的本能,那生本能便是将生命进行延续的力量。同时,“曾给她鲜花让她恋爱”更是生本能中爱、力比多的体现。但是,诗行中用“曾”也就是过去时,也就意味着诗人的力比多曾经得到了满足而现在却已经消亡。布鲁克曾先后与三位女性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恋爱关系,考克斯在他的心中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考克斯和布鲁克好友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情感破裂。在1914年,“他意识到自己受到性冲动的驱动,迫切地想要结婚”[10]。但是与此同时,布鲁克转变了自己观点,认为只有在婚姻存续内,才能有性行为。而且,在他之后与自己的心理医生的交流中提到自己性方面的问题。虽然生本能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两性之间的力比多,或是爱欲。但是,在所有爱的形式中,两性之间的爱应该是最为重要且根本的。诗人在此方面的困扰也许正是由于自身生本能的消退。
在《士兵》开篇,布鲁克便预设在叙述者死后,“在异国他乡田野上的某个角落……一粒更富饶的尘埃在肥沃的土壤里埋葬。”他将自己比作尘埃,自然没有任何的衍生作用。此时,生本能也消失殆尽,死本能已经发挥其作用。尘埃这一意象取自上帝的诅咒“你本是尘埃,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17)[11],也就是最终人类的死亡。这与弗洛伊德的观念有着无形的契合。他的生死观并不是断裂的,而是相互连接的。即使叙述者在其死后已经化作尘埃,但是他生前却有着生本能的冲动。正如尘埃与人之间的互相转换。诗歌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诗人所言,诗人所不言说的也暗含其深意。生死两种本能之间本就相互对立,死本能的显现自然也就意味着生本能的消弥。这两首诗都将死亡当做核心,这也意味着两首诗少有关于生的意象以及诗人自身生本能的消散。诗中提到一次爱也使用了过去时。而在《安全》中,上帝帮我们“寻着此隐藏之地,容我们匿身之人/让我们可凭此抵御世界汹涌的暗潮。”隐藏和暗奠定的诗篇主基调便是与死亡相关。之后,便是和永生之物相伴,此时虽有“鸟儿歌唱”却也是在“深夜”。此时,鸟儿的歌唱似乎也与早晨万物苏醒的歌唱相对,使人易有另外一种解读,即死亡之歌。“安睡、自由、大地上渐浓的秋意”这些意象更是与死亡密切相连,“安睡”也似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渐浓的秋意”本身也使人联想到生命的逝去,万物凋零萧瑟。诗人不仅仅将主题立于死亡,其诗行之间更是体现了生的凋谢。人自一出生便有着自我保护本能,但是同时却也存在着死亡本能。人类的自身的发展便是一直存在于两者之间所不停歇的矛盾和协调当中。而在布鲁克的诗行当中,我们却难以找寻到生本能的踪迹,而死本能却成为了诗人病态般痴迷的主题。或许正是由于他两种本能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尤其是死本能的过于强大以及其对于生命本能的抑制,才促使诗人撰写出这般的诗行以及有了他自身的参战行为。
三、结语
布鲁克的诗歌中确有很多与一战有关的死亡意象,并把死亡看做是最后的安全之地。其本身正是死亡本能中强迫重复和涅槃原则的体现。诗作背后所暗含的也许并不是他对战争的歌颂亦或是对牺牲的美化,而是诗人无意识的心理动机表现而书写的死亡,是诗人死本能与生本能的此消彼长。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虽一直未被证实,然而在布鲁克的诗作中,我们似乎能一直窥视到死亡本能的弥漫以及其中生命本能的消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