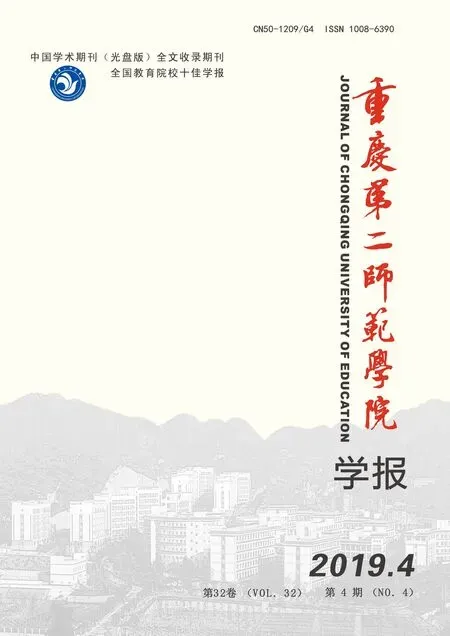“邯郸学步”抑或“青出于蓝”?
——试论清词的复古之路
高 媛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 新疆 喀什 844000)
清词中兴这一论断,在现代词学界已成共识。刘毓盘在总结词的发展历程时指出:“词者诗之余,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1]词体于宋亡之后400余年一直处于中衰不振的状态,直至明末清初始复兴起。从历史维度出发,清词在数量、规模上确实达到了可与宋词媲美的境地。然而从清词自身的价值角度来考量,质疑之声一直存在。清词是对宋词的复古还是超越,这一话题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已有论争。自从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并明确提到“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后世学者多受其影响。胡适即认为有清一代虽然出了不少全力作词的优秀词人,但词的极盛时代已然成为过去,“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潮流已去,不可复返,这不过是一点之回波,一点之浪花飞沫而已”[3]。与胡适观点相同,胡云翼虽然在《中国词史略》中承认清词在词史上是词的复兴时期,但对清词的评价却极低,他指出:“大多数的清词家,不是模拟南宋,便是模拟北宋,有的拟五代,也有的拟晚唐。总之,无论他们怎样跳来跳去,总不曾跳出古人的圈套,清人的词,因此便堕落了,走上古典主义的死路去了。”[4]胡适和胡云翼的说法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也指出了清词所处的尴尬境地:首先,宋词已经完成了词的独创性与开创性,清词要想在词体上有所创新,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次,宋词的经典化程度在清代已达至顶峰,清词想要提升自身的品格和地位,不得不以宋词为典范,以复古为旗号。因此,探讨清词的复古理念对于正确认识清词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词的复古之路:继承为主,纵横开掘
严迪昌论及清词“中兴”的实质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同时指出“‘中兴’不是消极的程式的恢复,不是沿原有轨迹或渠道的回归”,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宋词作为清词的衡量标尺,而应当将清词作为特定历史时空的一种抒情文体[5]。严迪昌从清词与其特定生存土壤之间的依存关系上,确立了清词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严迪昌的论断意在提高清词的地位,虽然有割裂清词与宋词之嫌,但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正确思路,即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创变绝不可能仅从对前代成果的回归和模仿中实现。这一认知常被历代倡导“复古”的文学家所忽略,文学史上众所熟知的论断“文必两汉,诗必盛唐”观即是一例,清代词人亦有此弊端。被清末词学家谭献称为“直接唐人,为天才”的云间词派领袖陈子龙曾指出:“诗与乐府同源,而其既也,每迭为盛衰;艳词丽曲,莫盛于梁、陈之季,而古诗遂亡;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又提出“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5]13。这种“迭为盛衰”的观点机械地将文体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中截断,认为任何一种文体发展到极盛之后,必然会走向衰落并被另一文体取代。因此,陈子龙主张作词当以南唐北宋为楷模,令“小道”之词向妍婉雅正的规范靠拢。这种复古理念极大地限制了词人的创造性和词作为抒情文学的生命力,同时否定了创作与所处时空的特定联系。不同文体之间的承传关系,绝不是完全此消彼长的交替序列,而每一种文体在极盛之后的新变也并非都意味着衰退。
清代词人的复古理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以唐宋词为楷模,机械地走向了回归与模仿的复古旧辙,上述陈子龙即这一类的代表。另一类以复古为手段,在复古的外衣庇护下实现其多元目的,或为了提高词的地位,或为了提升词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格调,或为了对词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进行规范。这一类复古理念在清代词人中拥有广泛的群体,虽然他们所属流派不同,树立的典范、所推崇的创作方法、词体风格等亦有差异,但皆对词体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初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提出词“存经存史”的功能即是对苏轼诗化理论的延伸,其所致力于词体表现疆域的开拓、主体性情的抒发以及词风由婉媚向雄豪的改革皆是对苏轼、辛弃疾一派词人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继承和深化。顺康熙盛世而生的浙西词派以南宋姜夔、张炎为宗,力主作词当以“淳雅”为本,同时将咏物词的题材抉发到极致,书画、烟草、猫等各种动植物以及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时下盛行的某些现象,无所不可入词。晚起于清后期的常州词派,进一步确立了词的尊体观,周济提出的“词史”①说,将词与诗歌比肩而论。常州词派还将诗歌中的“比兴寄托”手法作为词体创作和鉴赏的理论指导,对词体的思想深度和格调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把清词对题材选择、表现疆域的拓展称之为横向延伸,则其对词的内容、格调及创作手法的深化规范则是纵向开掘。
在探究清代词人的复古理念时,需要特别关注诗教传统的融入和运用。由于诗与词之间密切的联系,诗歌创作及理论又早于词体成熟并臻于完善,因此宋代词人在论词时常将诗论引入词论之中,在创作中亦有“以诗为词”(苏轼)、“以文入词”(辛弃疾)的实践。清代词人在继承唐宋词人词学理念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前代诗论的借鉴,尤其是对诗教传统的吸收利用,其程度之深在词史上前所未有。“应该指出,儒学诗教理论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有过巨大作用。所以诗教理论一旦进入清初词坛,对尊词体和词创作的发展,都起过良好影响。”[6]崛起于清代中后期的常州词派的复古理念即以诗教传统为基石,论词时首先着眼于文学与政教相通的社会功能。谭献提出词是“风诗之遗”,因此作词必须蕴含风诗以理节情、“温柔敦厚”之精神,他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引入词中,以求发挥词针砭时弊、反映忧生念乱的社会功能。撇开常州词派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迂腐说教,将诗教传统融入词中,在推动清词向前发展的历程中无疑是一大助力。宋词成就虽然登峰造极,但大多仍未脱“小道”观念,所表达的多囿于一己私情,就题材的选择范围来看,前有苏轼开辟道路,但表现疆域仍不够开阔,后有辛弃疾将边塞山水、田园风光写入词中,但更多还是个人自我形象的展示,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远不如清词之广阔。特别是道咸年间涌现出大量直接反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和沿海问题等堪称为“词史”的词作,一方面强化了词的抒情功能和与时代环境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印证了常州词派“词史”说的理论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讲,其对诗教传统的复古实则是对词体内部的发掘与更新。
任何复古都是为了实现时下的需求,但若把握不好度,使之陷入思维的死胡同,则容易把词引入褊狭的道路。阳羡词派“豪放”过甚而流于粗率;浙西词派因过于追求词作格调的“清空”、音律的标准和学问的熟练运用,忽视了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本末倒置,导致创作出诸多“巧构形似之言”[7],堆砌典故而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常州词派为纠浙派之偏,指出词应当有所寄托,但矫枉过正,其创始人张惠言以经学家身份援引儒家诗教入词,牵强比附,走上了一条偏执而迂腐的解词之路;周济虽在理论上提出词当与广泛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奈何理论与创作实践脱节,且常州派词人眼光比较狭窄,生活土壤不丰厚,又过分强调比兴寄托的技巧而逐渐丧失了词的真趣和活力,最后不得不以模仿为能,极大地折损了作品的美感。
总体而言,清词的“复古”之路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其潜在空间、不断向更深更广领域的拓展。
二、复古之集大成:“体”“用”内涵的丰富延伸
“体”和“用”源自先秦古典哲学领域,唐代经学家崔憬解释:“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8]词人将其引入词学领域,赋予其丰富的含义。关于词之“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词体这种文学样式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本质特征;二是指词的情感内容、内在品格。词之“用”主要体现为包括艺术手法、风格特征在内的词的外在形式。词之“体”为本,词之“用”为形,在清代词论,尤其是常州派词论中,二者往往是交融糅合、相辅相成的。
关于词之“体”的第一种含义,实际上探究的是词的本质属性问题。自苏轼“以诗为词”及李清照针锋相对的“别是一家”本色理论出现之后,清代词人沿袭这两条路线不断对词的特性进行延伸阐释。清代前期对其探讨多处于朦胧状态,陈维崧指出了词与近体诗相比在表现深沉复杂的历史感方面的优势:“谁能郁郁,长束缚于七言四韵之间?对此茫茫,姑放浪于减字偷声之下。”[9]陈维崧之言基于创作体验,并未上升到系统理论,但他所提到的词在抒情上比诗更具有曲折的表现空间为后继词论家多所借鉴。田同之进一步阐释:“且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旨益远。”[9]244焦循亦有言:“人禀阴阳之气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气寓之,有时感发,每不可遇。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劲之气长流存于诗、古文。”[9]249虽然“难言之情”与“柔委之气”并不对等,焦循“词为泄阴柔之气”的论断也有失公正,但二人都指出了词言情且更适合抒发曲折委婉之情的特质。
真正为词之“体”“用”注入新鲜血液并使之不断丰富完善,进而将词这一文学形式推尊到与诗比肩地位的是崛起于清代后期的常州词派。张惠言用儒家思想来阐释词:“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10]此处对词之“体”“用”皆有论述:其一,界定了词的概念,即“意内言外”;其二,确定了词的思想内容,须是抒发“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其三,规范了词的艺术风格,要“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到底什么是“意内言外”,“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又是怎样的感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又当如何在具体操作中实现,张惠言进一步解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10]“变《风》之义”指的是诗教传统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规范,“骚人之歌”指的是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这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其所言“意”和“情”就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而要做到“意内言外”且“低徊要眇”,就需要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张惠言通过向诗教传统的回归而努力将词的社会功能扩大,使之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政治感,这对于赢得主流社会的认同、提高词体地位的确提供了很大助力,但从词本身的文学特性出发,当词的精神主旨和诗的实际功用基本一致的时候,必然会模糊诗词的界限。为了避免使词成为“长短句之诗”,常州词派在向儒家精神靠拢之时,也注意到了保留词体区别于诗歌的独特成分。张惠言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要求“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已之情”要以“低徊要眇”的方式表达出来,一是保留了词独特的审美要求,“低徊”指情感的回旋往复,“要眇”指情感的微妙精致,以“低徊要眇”论词,就是强调词要传达自身所特有的缠绵往复、微妙细致的美感特质;二是为了做到“体”“用”的结合,即这种含蓄委婉欲露还隐的情感与词的美感特质正相契合。
常州词派后继词人继续对张惠言所论进行补充和延伸。谭献从体、用兼顾的角度对张惠言“意内言外谓之词”进行了发挥。其《复堂词录叙》云:“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9]315又《箧中词叙》云:“昔人之论赋曰:‘惩一而劝百’,又曰:‘曲终而奏雅’,丽淫丽则,辨于用心;无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词亦有然矣!”[9]315这里指出词由于与诗的文体特质不同,因此词不必像诗一样直接展示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庄语”),而是可以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侧出”“旁通”“触类”),借用同赋体一样的绮丽情思来表达重大深远的意义。对于词的“体”“用”认识进一步深化开拓的是陈廷焯,他从词的音乐特征出发,总结出词具有“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11]的词学观。以思想情感之“温厚”为本,又指向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张惠言等人并无差别。他的贡献在于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特色引入作词当中,对词的外在形式的表现形态作出了具体说明。
无论是张惠言的“低徊要眇”,还是陈廷焯所提出作词法“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都体现了中国古典传统“尚虚而弃实”的审美倾向。清代号称词学之集大成,常州词派功不可没。从宏观角度看,清代词论在不断深化词的“体”“用”过程中,集中于对情感内容和创作技巧的探索,而忽视了词创始之初的重要因素——声律与音韵。虽然周济在《词辨自序》里曾对词的声乐特质加以描绘,“后世之乐去诗远矣,词最近之。是故入人为深,感人为速,往往流连反复,有平矜释躁、惩忿窒欲、敦薄宽鄙之功”,指出了词因其入乐的特性而具有感人肺腑、平缓情绪之效,但他所基于的视角仍是词的教化作用。
三、复古的缺失
清词的复古之路看似硕果累累,深入探究便会发现与复古之成效相伴相生的是极大的缺失,同时也是导致清词的价值至今尚未得到彻底发掘与认知的重要原因。
其一,体现在对“雅”的极度追求导致了词之文学活力的丧失。词创生之初是为歌姬配乐演唱的佐欢之具,后由文人加工而逐渐走上雅化的道路,经历了南宋姜夔、张炎、吴文英、周密等词人的雕琢,词越来越远离最初侑觞佐欢、应歌应社的主要功能,至清代,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词已基本割裂了与音乐的关系,成为纯粹的文人词。因而在清代“雅”与“俗”已经不再成为论词的主要议题,“以雅为尚”成为清代词人的共同追求。可以直接印证这一点的就是清人编辑的众多宋代词选本、词话总集中收录的大多是文人雅词,而大量诸如宴饮、赠妓、谐谑等俗词并未被纳入其中。周济及其以后的词人虽然将俗词圣手柳永与周邦彦同誉,但其目的是为推周,而在选取柳永的词作时也仅仅对其描写羁旅行役、抒发个人情志的“雅作”予以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大多数清词选本即便对所标榜词人的作品也要剔除其俗俚之词。可见,在宋代占据半壁江山的俗词是被排斥在清代词人的话语体系之外的。清代词人对俗词全盘否定的态度,体现了他们对传统雅正文学思想回归的愿望。当然词体创作趋向于雅化与其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的崛起迅速占据了俗文化领域,而俗词到了清代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当词不再作为酒筵欢宴供佳人歌唱的“艳科”,而完全成为文人学士的“案头”之词时,其雅化已是必然趋势,这对词的原生态活力的破坏亦无可避免。
其二,体现在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节。吴熊和曾说:“词盛于宋,词学之盛,却不在宋而在清。”[12]清代词学家通过对唐宋词的整理与点评,在词学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清代词学对解词颇多心得,实际上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即使散发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词史”说,也因为过分强调寄托婉讽而难以在词作中真正体现出时代精神。常州派词人虽然在理论上也提到重视真情的流露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随即却又戛然而止,引回到思想品格重归忠厚雅正的诗教道路上去了。他们强调的若隐若现、一波三折的比兴手法,才力不足者就会变为看似深奥,实则主旨不明、不知所云。这种带有极强的宗派色彩的论词标准和按图索骥似的创作方法,使词人们在一条偏执而狭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也是复古主义者必然面临的困窘。在清词尊体的路上,宗派林立,教旨愈严,尤其是清后期,词作中个人一己私情的抒发被斥为不“厚”,而必须加上重大的与政治社会相关的思想内容且必须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才算得上是“佳作”。词人身上的负担越重,其思维束缚越深,而词之文学活力越衰。因此,通过对清词创作质量的整体考察,会发现清初词尚未取得尊体时,创作却十分繁荣,陈维崧、纳兰性德、顾贞观等词人颇多真性情之作,而清中后期,浙西词派专注于描摹咏物,歌咏太平,词作趋向浅滑无实,而常州词派终于以向诗教传统靠拢的方式尊体成功,却拘束过甚,创作下滑,反倒是那些不受宗派制约的词人如蒋春霖、龚自珍等多有佳作。且理论与创作本身就具备不对等性,创作高峰与理论高峰往往是交错而成的,历来某一新文体始出,常见的是创作先行,理论滞后,而理论在前的往往难出佳作。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理论束缚了思维,捆绑了手脚,或是由于佳作诞生之时往往是文体新生时期,活力旺盛,创作空间开阔,其个中缘由尚需探究。
其三,体现在清代词人有过于逢迎时代和不合时宜的双重性。前者主要体现在浙西词派的词旨词宗上。康熙中期,政局稳固,统治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文化肃清活动。康熙帝“钦命”编纂《历代诗余》和《词谱》并为之作序,表明了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词体文学也被纳入肃清范围。诞生于此时的浙西词派,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为旨而奉迎统治者的喜好,以适应盛世气氛。远离政治,以描摹盛世、拟形咏物为主,一方面退回了词创生之初的“小道”观念,一方面切断了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限制了词人性灵的抒发。后者主要体现在清代末期,尤其是近代中国在遭受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生死攸关之际,受常州词派影响的大批词人仍旧固守比兴婉讽的词旨,显然与动荡的时局背道而驰。不管是为了迎合盛世而歌咏太平还是不合时宜的故步自封,都会损伤词作为文学体裁所特有的美感,而缺乏真情,又无法表现出时代的性灵,势必会导致词的衰微。
四、结语
当词这种文体的规范已然成形时,同时也意味着词的创作走向了自我封闭。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固守已不符合时代特征的陈腐窠臼,一味向前代回溯以探求复古之路是不可能促进词体甚至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前进的。此时,如果后继词人不能摆脱创作的藩篱,终将使词失去生命活力,最终走向衰颓。然而将目光放长远,并非彻底否认甚至推翻前人所创造的成果,而是要看到只有改造传统并使之与时代相契合,才能充分激发传统的生命活力。清代词人在向宋词经典回首之路上,纵横开掘,在词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开拓延展,终成清代词学集大成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清词的价值始终未得到充分肯定,清词的流传度亦远逊于宋词,而今人对清词的体认也大多集中在陈维崧、纳兰性德等几位作家之间。由此观之,清词的研究还具有极大的空间和潜力,由于学识有限,本文仅从宏观角度对清词复古之路的概况及其得失进行粗略探讨,更细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学者的不断耕耘。
注释:
①“词史”有两种含义,一种指词作为文体的发展史,属于文学史的一部分。这里的“词史”是从杜甫“诗史”演化而来,专指反映当时历史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