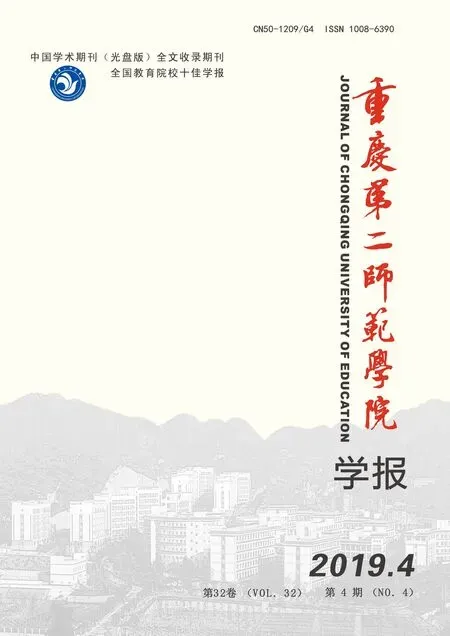郝敬《尚书辨解》对前说的辨订及其价值
江鎏渤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郝敬(1558—1639),字仲舆,号楚望,安陆京山(今湖北京山)人,世称京山先生,晚明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敬少有天资,出言机敏。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历知缙云、永嘉。万历三十二年(1604)因忤要人,仕途无望,遂挂冠归乡,潜心修学。崇祯十二年(1639)属纩而绝,享寿八十有二。郝敬为学淹贯群经,万历三十三年(1605)始著《九经解》,历九年(1614)而成秩。其《九经解》总结了明代以前学界对经典的讨论成果,力图统合经典与时代、修养与实践等问题,为晚明经学的代表著作。《尚书辨解》作为郝敬《九经解》之一,集中探讨了《尚书》所记载的先王之道,是其建构经学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其治学的典型范例。《尚书辨解》通过辨订《孔书》体例和前儒误说重新确认《书》教的意义,融合了时代精神,赋予了《尚书》新的内涵。郝敬采取这种注经方式,与晚明思想界的治学特点、思想倾向息息相关,从侧面映射出了明清之际治学特征转变的端倪。
一、辨订《孔书》体例
元明两代,《尚书》学著作多为科举而作,其讨论多围绕《蔡传》展开,而少有怀疑《尚书》文本之编排体例者。稍有眼光的学者,也只是把关注经义的范围扩大到《尚书》古义,如刘三吾等《书传会选》、王樵《尚书日记》。郝敬发现《孔书》的体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孔书》篇目割裂旧章,导致古意全失;二是《孔书》编订混今古文为一炉,真伪混杂。
(一)分合篇目
就《尚书辨解》对《孔书》篇目的分合而言,郝敬认为《孔书》割裂了《尚书》原本的篇目分合,并进一步导致了《尚书》核心内涵的缺失。“古史官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成为郝敬辨订《孔书》篇目分合的主要依据。这种“古史官精神”存在于《今文尚书》中,表现为《尚书》记载者(古史官)对圣贤的一种精神体认,体例上体现为《尚书》篇章不同于后世史书“一人一传”的形式。郝敬合并《孔书》之《尧典》和《舜典》、《皋陶谟》和《益稷谟》为一,指出如此才能体现“二帝并典”[1]120下栏、“五臣同心”[1]120下栏,即言《尧典》《皋陶谟》之文体与后世有异,其篇章内部寄寓了“并典”“同心”等“古史官精神”,而“一帝一纪,一臣一传”未能表达出这一层含义。在立论过程中,郝敬以《易经》之乾坤、六子分别比作《尧典》之尧舜、五臣(契先卒,故为五),把易卦之内容当成“古史官精神”存在于《易经》的证据,与《尧典》《皋陶谟》中的“古史官精神”互证。又解《顾命》云:“三代顾命多矣,独录成王者……本一篇,《孔书》分‘王出在应门之内’下别为《康王之诰》,与分《舜典》同陋。千余年来,无敢正之者,可怪也。”[1]242下栏“同陋”,意即《孔书》从《顾命》析出《康王之诰》与《孔书》分《尧典》《皋陶谟》导致的结果相同,亦违背了“古史官精神”。郝敬在具体行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孔书》自此以上断为《顾命》,下别为《康王之诰》,一时事断为两章,非也。”[1]242下栏郝敬认为《顾命》记载成王终、康王即位为“一时事”,《孔书》以“一人一传”的形式割裂了“一时事”,破坏了记载的完整性,故《孔书》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违背了古史官精神。
(二)分注今古文
分注今古文,即分注《今文尚书》(《伏书》)与《古文尚书》(《孔书》)。有关今古文的差异,历代少有说《书》家指出,朱、蔡尽管发现了这种差异,但仅于《尚书》篇名后注今文、古文之有无,没有进一步对其进行分注。此后元明两代能超越朱、蔡观念的仅有赵孟頫、许谦、吴澄等人。郝敬《尚书辨解》正是元明两代为数不多的分注今古文《尚书》的注本之一,该书一反《孔书》熔今古文为一炉的篇章编排方式,在注经实践中分别注释今古文,在辨伪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今古文。郝敬认为《今文尚书》才是真篇,《古文尚书》实为后儒所补葺,“始末悠谬”[1]259下栏,指出“夫子删定之季,周室东迁已久,典籍散亡。计当日所定,四代《书》亦应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缺两字)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书》辞深奥,故伏生所记止此。假如二十五篇者,虽多可不至于遗忘,亦真与伪之别也”[1]119上栏,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尚书》编订、流传的过程,直接点明《孔书》窜多二十五篇之伪。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郝敬观察到了《孔书》与今文尚书文辞上的差别,进一步下定了分注今古文的决心,其《读书》云:“《孔书》诸篇,辞意皆浮泛……古史典要,决无此病。若真古文如《大诰》诸篇,任说得纵横舒展,真赝功沽,天地悬隔。”[1]118下栏-119上栏郝敬通过分析《孔书》的文辞与篇章意脉证明《孔书》与《今文尚书》的差别,指出《孔书》辞义的浮泛与《今文尚书》之辞“纵横舒展”在格局上存在天壤之别。大量同类表述存在于郝敬解读《大禹谟》《仲虺之诰》《君牙》等《孔书》篇目里,足见他分注今古文的思考之多。
二、辨订前儒“误说”
在《尚书辨解》中,郝敬运用晚明时期的新思想,对汉以来的前儒经说展开了详细辨订,其辨订的类型可以分为辨订名物、制度,史实和义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终都归结到义理的阐发上。郝敬以儒家伦理实践为主要指向,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辨订为《尚书》赋予了时代内涵。
(一)辨订名物、制度
《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历史,其经文涉及四代的名物、制度。这些名物、制度作为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容,是了解先王、先贤治政的利器。后代对这些名物、制度众说纷纭,给学习者带来了很大障碍。《尚书辨解》对《尚书》记载的名物、制度进行辨订,企图归为一说,从而为厘清《尚书》中的义理提供了张本。
1.辨订名物
郝敬解《禹贡》“九江”云:“九江,或谓浔阳,或谓洞庭,世远迹湮,茫茫不可考。诸家所述巴陵之九水,浔阳之九江,皆未敢信其然也。大抵天下之水莫大于江与河,故河有九河,江有九江,皆其疏沦之支流。九河导河入海,九江导众流入江。古人于凡数之聚者多言九,后人因数撰名,转相附会耳。”[1]147上栏郝敬认为,《禹贡》所记之“九江”并不是“九条江”,《尚书》的语言习惯言“九”,意为数量多,而非一个确指的数字。他指出,因《禹贡》记载世代遥远,“九江”下属诸江其名已不可考,暗示这是造成后人议论纷纷、强以为说的原因之一。“五色土”是地方向中央进贡的重要物品,郝敬解《禹贡》“五色土”云:“五色土可用为涂饰,或云‘王者以五色土为社’。大抵方物当贡,不必尽凿求所用也。”[1]145郝敬指出,“五色土”作为贡品,不必尽“凿求所用”,它象征着天下大同,若言“王以五色土为社”,就违背了圣人制作本意。以“五色土”为君主分封立社用品的观点最早由《逸周书·作雒》提出,《韩诗外传》《史记》都本于《逸周书》,郝敬显然不认同此说。
2.辨订制度
《皋陶谟》之“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关于服制的最早记载。郑玄曾据以对照《周礼》之“五冕”(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划分此文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云“作服者,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卿大夫自‘粉米’以下”[3]170。郑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作解,联系“五色”“五采”“五服”,划此文为五服、十二章以配五冕。郝敬训《皋陶谟》云:“郑康成解服色执此章为据,按经文非专指服色也。”[1]138下栏他指出,郑玄的划分以服色为解,有以偏概全之嫌,大胆怀疑郑玄的阐释。郝敬又云:“制器尚象,而日月七者皆象也。正服辨色,而藻火六者皆色也。今附会《周礼》‘五冕’,皆以为服色,未然……世有古今,制有沿革,即使周冕有五,衣裳有九,果取诸山、龙、黼黻,虞时未尝尽以为服,而强虞从周亦非也。况《周礼》后世之书,未可尽据。”[1]138下栏以历史为主要视角对郑说展开逐条辨订,揭示世有古今、制有沿革,《周礼》为后世之书,所论之制异于《皋陶谟》。如郝敬训“华虫”云:“夫华之为花也,虫之为虫蛾也,甚明,何据鷩冕而定指为雉?”[1]138下栏不认可郑玄以“华”“虫”比附“鷩冕”,认为“山”“龙”与“鷩冕”之雉不同。他指出,郑玄没有考虑到“古人尚象”的实际,“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皆为象,郑划分五服不合“尚书”的古礼。对此,郝敬解《顾命》进一步指出“《周礼》‘衮冕’衣裳九章,裳四章……后儒纷纷讼议,唯《诗》《书》足据”,引用《尚书》《诗经》中的相关记述作为自己的立论点。
(二)辨订史实
知其人必论其世,史实是了解对象生命轨迹并展开论述的依据,也是义理阐释的重要基础。郝敬把《尚书》统合于《九经解》阐释的理论脉络之下,对“大禹治水”与“周公居洛”等史实进行了辨订,其说对理解《尚书》文本、体认圣贤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曰“作十有三载,乃同”。对此有两说:一是马融、《孔疏》、伪《孔传》等的解说,尽管小有异同,但都将“十三”释为治水总年;二是把“同”释为州内治水同,认为“十三载”专指兖州而言,郑玄、林之奇等持此说。对于此种争论,郝敬认同前者,其释《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云:“或疑十三载与孟子云‘八年’殊,孟子谓不入家门者八年,非谓治水止八年也。”[1]144上栏试图弥合《禹贡》与《孟子》记述的差别,以具体文本分析作为辨订异见的根据。他指出,《孟子》所言之“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意为禹“不入家门八年”,大禹治水为十三年。
又如解《洛诰》“周公居洛”云:“王命在十有二月,即戊辰王至之日也。诰成公留,则明年也。公留洛,即王烝之新岁,惟七年也。不云留洛而云诞保文武受命者,因于王留公之辞也。说者谓公居洛七年乃薨,然则诰作于成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之册,又何册邪?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东。三年至五年,公东征。六年春,公营洛。是年东十二月,洛工成。王与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治洛。经文编次甚明,纷纷诸说不足据也。”[1]221下栏郝敬认为,后儒对“惟七年”的“误读”导致了对《洛诰》成篇年代的误判。他申述“惟七年”不应释为“公居洛七年而死”,而应直接解读为“成王七年公留洛”。若解读为“公居洛七年而死”,则意为作诰于成王十四年,一事不容有重复诰命,此与经文中“逸诰,在十有二月”之作诰时间相冲突。
(三)辨订义理
《尚书辨解》辨订前儒义理,企图为统治者提供治理经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关注君臣大义和批驳灾异之说。前说对三代禅让的错误想象,潜伏着危及君臣纲常的危机;汉儒对“灾异”的解读也显得荒诞不经、贻误后人。这两个方面的辨订体现了郝敬对政治的敏锐思考,也可窥知他隐居之后依旧不忘国家的情怀。
1.关注君臣大义
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君主具有核心地位,赋予臣子权力,而臣子则要忠于君主。君臣关系一直是经典解读所讨论的重要话题。郝敬以君臣大义审视辨订前说,其对“耄期倦勤”和“侯伯专征伐”的辨订最为典型。
尧、舜、禹作为明君贤臣的代表,塑造了中国政治的理想模式,他们之间关系的处理成为后世君臣参照的典范。可是,《大禹谟》中却有“舜耄倦勤”的说法,里面潜藏着臣子威胁君主的危机,为强臣僭主提供了依据。郝敬企图从经典内部澄清此种错误说法,在解《尧典》时论述“尧老舜摄”与“舜耄倦勤”云:“按:孟子谓尧老舜摄,尧在,舜未尝为天子。然祀天觐后,皆行天子事,何也?祖庙受终,尧固以天下与舜。廷臣、师锡,天下固以天子望舜矣。其即位改元,虽在尧崩之后,而其行天子事则自受终时始矣,岂其非天子而敢为天子之事乎?自古惟尧之于舜为然,故孔子赞其荡荡则天。史臣以《舜典》从尧,明始终一体之义。若夫舜耄倦勤,则《孔书》因袭附会之说耳。”[1]127上—下栏郝敬通过解释“尧老舜摄”,并声明其特殊性来证明“舜耄倦勤”为《大禹谟》附会。他指出,尧晚年以国家大事嘱托给舜而未禅位于舜,舜仅代行天子之权而无天子之实。郝敬解《大禹谟》进一步指出:“尧老舜摄,舜受尧终,以天下之大与匹夫,宰相行天子事二十有八年,从古希有……史臣以《舜典》从尧,二圣一体,古今不容有两,谓禹复然,是后人之附会耳。岂舜不若尧,禹不若舜乎?事不可常,虽圣人不相袭也。”[1]268下-269上栏郝敬认为,尧和舜之间的君臣遭际特殊,舜禹之间的君臣关系不似尧舜之间,以君臣大义为标尺考量“耄期倦勤”为后世之说。
郝敬阐发《文侯之命》也颇为用心,集中辨证诸侯“专征伐”之说。此说为春秋五霸“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治理方式提供了依据,在春秋时期成为晋、楚、吴等大国讨伐政敌的借口。郝敬云:“按:诸侯有武功,则王赐弓矢以表之。《诗》咏彤弓,《书》命文侯,皆未有使专征伐之语。后儒因《西伯戡黎》‘伐崇密’,齐桓、晋文为侯伯,搂诸侯相伐,遂臆度为古礼”[1]255下栏,指明《诗》《书》等儒家原始典籍并无记载“侯伯专征伐”之语,“《诗》咏彤弓”“《书》命文侯”并非天子赋予诸侯“专征伐”之权的表现。他指出,“专征伐”实起于后儒解释《西伯戡黎》中“伐崇密”之“伐”为征伐的“臆度之说”,为后世儒者逢迎霸者之辞。
2.批驳灾异之说
汉儒的图谶之说以灾异与经典相结合,建构起了一套规范人君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也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即灾异之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容易找到征象。汉儒为了弥合此缺陷,常牵强以说之。郝敬承续义理一派对汉儒灾异之说进行了批评,他以《高宗肜日》《洪范》为依托对前儒灾异之说予以辨订。其《高宗肜日》解题云:“高宗肜日,有雉升鼎耳鸣,祖已正其事以训王,史臣即事命篇。今绎其辞,观象论理以明天变当畏,不深求附合而凛然使人深思,可信斯善言天矣。后儒言天牵强以求必中,一不中而百皆妄……理贵有余,言贵不尽,凡事皆然,而况天道?”[1]168上栏郝敬指明《高宗肜日》的意义在于“观象论理”,汉儒“牵强必中”每言灾异必以现实征之,无妄之极。刘起釪所言“殷代统治者在他们的宗教迷信思想笼罩之下……对于一向视为神鸟的雉鸟的鸣叫,是非常敏感的……《高宗肜日》篇就是这件事的实录”[2]1041,指明雉鸣与灾异无关,可与郝敬之说相印证。郝敬通过对《高宗肜日》的阐释表明他执义理而黜象数的立场,可谓得解。又郝敬解《洪范》云:“刘向父子作《传》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牵强补凑,殊乖自然,大抵圣人观象玩数以示参伍用中之义而已。”[1]167上栏刘向父子作为以灾异衍《范》的代表,分作《洪范五行传论》《五行传说》,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洪范》的态度。郝敬指出,《洪范》文本的意义在其义理方面的“参伍用中”之义,即贵数字五的意义、执中之道,而刘向父子把金木水火土、貌言视听思与现实表征联系起来,割配《洪范》经文,无疑是对《洪范》的误读。
三、郝敬辨订前说述评
经学发展到明代中晚期已呈现式微之势,不仅儒学内部危机重重,佛老之学也对儒学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历代解经众说纷纭,初学者阅读儒家经典往往不知所从,而简易明白的佛老之学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知识分子有的固守章句、陈陈相因,有的逃禅归老、脱离社会,儒学阵营面临不断缩减的危机,这对于有志儒学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思想困局。明代中晚期的知识分子亟待内部反思者的出现,以重新巩固儒学的权威地位。郝敬是明代中晚期对此展开反思的代表人物之一,《尚书辨解》即其反思的重要著作,体现为辨订前说。《尚书辨解》辨订前说分为辨订《孔书》体例和前儒误说两大方面。其中,辨订《孔书》体例可分为分注篇目以及分合今古文两个小方面,辨订前儒误说按类型可分为辨订名物、制度,辨订史实,辨订义理。这五个方面形成了自足的脉络,为郝敬更好地阐发义理、探寻“先王”之道奠定了基础,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郝敬辨订《孔书》体例采取了文本编纂的策略,他以“古史官精神”为依据对《孔书》分合篇目进行辨订,主要从文本精神内涵的层面得出结论,观点新颖,可备一说。其辨订结果早已被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乾嘉学者用严谨的考据之学再次证实。郝敬通过关注史官书写的道德性来辨订《孔书》分合篇目,丰富了《尧典》《皋陶谟》等篇目的内涵。分注今古文则体现了郝敬深邃的洞察力,他通过分注今古文以期明辨《尚书》真伪,用不同的方式对《尚书》今文、古文部分展开研究。郝敬采取分注今古文的方式与分合篇目一道,在体例上否定了传承久远的《孔书》,由此展开并进一步触及《尚书》辨伪问题,拓宽了清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具有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
就名物、制度层面看,郝敬讲求“九江”“五色土”“服制”在诸经典记述中的依据,启示着考据的出现,透露出经世之意。关于“九江”,《尚书校译释论》总结历代“九江”之说为四类,并认为“关于‘九江’也不必说确是九条水”[2]656。《尚书辨解》“九”不谓确数的看法与之不谋而合,符合真实的历史状况。关于“五色土”,郝敬的观点不够贴切文本原意,但其解读旨在约束人君的聚敛,指向明代晚期繁苛的捐税,从中可窥见其淑世情怀。关于“服制”,刘起釪说:“经师们详谈了这些衣服上图案使用时的详分等级,其具体划分,不足深考。”[2]499足见郝敬与郑玄谁对谁错不用深究。郝敬对服制的讨论不苟郑说,回归到原典文本中寻找新的阐释路径,他所重视的“礼之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策略上返本开新,启发了礼学走向义理本身,在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就史实层面来说,郝敬辨订前儒对大禹治水、周公居洛的看法反映了他对历史进行祛魅的意图。《禹贡》“十三”非指禹治水十三年而专指治兖十三年,王樵、胡渭等均持此说,刘起釪亦认同治水十三年之说,“把传说中禹治水的年数作信史来推求,是不足信的”[2]567。郝敬的观点承自马融,或许没有郑玄一派有说服力,但自有其意义。郝敬以《尚书》《孟子》为基础申述大禹治水为“十三年”,从侧面反映了郝敬贯通诸经的意图,为更深入的义理阐释、建构他的经学体系开路。关于“周公居洛”,郝敬的说法与现代考古学成果相符,《尚书校译释论》释“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一条:“近年今文发达,见《艅尊》铭‘惟王来正人方,惟王廿又五祀’,始知古代有将大事写于年岁上的习惯……然后确定了本文所记的烝祭和诰周公是当成王在位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的事情。”[2]1509“周公居洛”的年份涉及周初一系列史实,对其史实理解偏差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周书》经文的义理阐释造成影响。郝敬这种说法与为其阐发“周公不杀兄”“周公不谓商士为顽民”“周公无归志”等众多观点提供了基础。
就价值层面看,郝敬对君臣大义的关注和对灾异之说的批驳均与明代的政治情况息息相关,表现出明代士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舜耄倦勤”,刘起釪通过详细梳理承认了尧在世禅位于舜的事实,在史实上消解了郝敬的立论依据,但是这并不妨碍郝敬结论的正确。清代学者已经证实“舜耄倦勤”为伪古文之说,证实了郝敬的观点。郝敬通过辨订“舜耄倦勤”表达对朝政的关注,对明代中叶以来皇帝无心朝政而专断震主的内阁首辅展开隐晦的批评。至于“诸侯专征伐”之说,陈乔枞、皮锡瑞等人皆认为史有此事,与郝敬相异。较之两者,郝敬之说更具价值。考量古代政治,若天子的权力能够渗透到地方,诸侯则不必要有“专征伐”之权,诸侯有“专征伐”之权会开启乱端,唐末藩镇割据就是例子。郝敬对《文侯之命》的论述亦有重要价值,他从天子对诸侯的表彰形式出发,切入君臣大义的讨论,目的在于维护政治稳定。关于“批驳灾异”之说,郝敬解读《高宗肜日》《洪范》主要针对明代笼罩社会的崇佛、崇道风气,具有唯物立场,旨在更好地把经典作用于社会,其意义自不待言。
四、结语
郝敬以价值取舍为准绳,对前儒误说进行梳理,判断其正误,在晚明儒学阵营中具有权威的地位。其意义在于,它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士人建构自身人格的努力以及以经书阐释为依托的“内圣外王”实践路径,在此过程中又融入时代思想,为经世致用提供了坚固的思想阵地。综上观之,郝敬的《尚书辨解》无疑具有管窥晚明儒学内部思想交融的意义。郝敬解经好发议论,清儒称之为“好为议论,轻诋先儒”[5]189中栏,这已经成为学界对郝敬的基本认识。若深入研读《尚书辨解》,可以发现清儒所言之“好为议论”的确存在,但是这种议论并非如清儒所说的“千虑一得”[5]189下栏。若全盘否定《尚书辨解》的价值,恐也不能服众。《尚书辨解》尤其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于客观分析人的道德性问题,其论述统摄在重塑儒学经世精神的脉络之内。要言之,《尚书辨解》的《书》学诠释作为郝敬《九经解》的代表,反映了明清之际学界思想、方法上的新动向,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亟待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