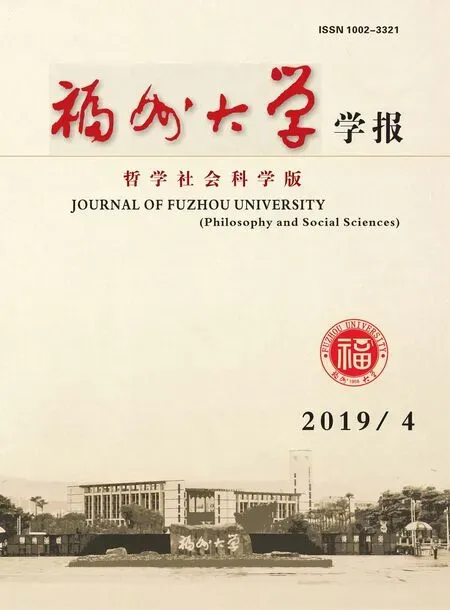患者自主决定权之困境及其法治化路径
钟三宇 林 云
(1. 福建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122; 2. 福州大学法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6)
引言
患者自主决定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法律问题,时常被提起,又总是被遗忘,导致相关法律规定的滞后,由此引发的医疗事件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早在2008年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案”,经审理认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的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朝阳医院不构成侵权,在朝阳医院同意补偿10万元的情况下,判决朝阳医院支付孕妇家属10万元。[1]2017年,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8·31榆林产妇跳楼事件”[2],更是在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在这些案例中,医务人员由于没有取得患者家属的签字同意而放弃手术治疗,造成“一尸两命”的后果。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是否是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导致的?为何家属享有如此权利,可以去决定患者能否进行手术?而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反而被忽视?在患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能否对诊疗措施享有自主决定权;或者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能否对将采取的诊疗措施进行预先指示?2018年10月1日施行了《医疗纠纷防范和处理条例》首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人文关怀。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应有之意,有必要以患者自主决定权切入,探讨“以患者为中心”的法律实现机制。对于患者自主决定权,诸多学界翘楚从手术签字权、知情同意权、医学伦理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3],提出相当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但在制度完善层面却收效甚微,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所谓“正本清源”,唯有从权利本源出发,从患者享有人格权,对自己身体、生命有关事项享有最高处分权的角度出发,以法治化路径作为破解患者自主决定权困境之道。
一、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理论诠释
(一) 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内涵解析
患者自主决定权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就与自己的身体、生命有关的健康、安全相关的事项自己做决定的权利。[4]概言之,患者有权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具有侵袭性医疗行为的可行与否。此概念肇始于美国纽约州,1914年卡多佐法官在一起医疗上诉案件中指出,每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均有对自己身体作医疗处置决定的权利,医方进行手术前应当取得患者同意,如果未取得患者同意即进行医疗活动,会构成故意伤害罪,需对患者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5]就患者自主决定权而言,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未明确规定患者自主决定权,在医疗实践中,通常是医务人员针对患者特殊病情为患者提供多个医疗方案,由患者自主选择最终实施的医疗方案。[6]
从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权利内涵上看,患者自主决定权是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源于德国刑法理论的法益概念[7],在引入我国法学研究领域后,经过法哲学理论的改造和提升,已然成为卫生法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衍生的正当生命法益理念,要求在对待个人生存权、健康权、生育权等基本权利保障时,应当给予更大的尊重,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自主决定权。
(二)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正当性基础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规定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表明我国从根本法的层面肯定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民法总则》第130条规定 :“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确定了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一种对世权,权利人有权主张自己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在医疗机构施行手术时,患者所享有的自主决定权,是他人无法剥夺、阻碍的权利。《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第33条[8]规定医疗机构进行诊疗行为前,需要同时取得患者及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第62条[9]规定,在患者精神状况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应向患者告知其医疗情况,有不宜告知患者的情况,也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侵权责任法》第55条[10]明晰了患者及其近亲属的同意权,其规则是保障患者知情权,并在患者知情的前提下,由患者自行行使同意权,但又规定了“不宜向患者说明的”由患者近亲属代为行使同意权。这些法律法规规定导致的后果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为了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免于或减轻法律责任,往往在诊疗中要求患者和近亲属同时“同意”才实施诊疗行为。当近亲属拒绝签署“同意书”时,即便有患者的“同意书”,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会拒绝进行重大诊疗行为,导致侵害患者自主决定权现象的发生。[11]现代医疗,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已从父权医疗模式向现代民主医疗模式转变。[12]在现代民主医疗模式中,强调患者自主决定权,其目的不仅在于尊重人的尊严,更在于关注患者的自由意志价值观判断的权利。[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018年10月1日施行的《医疗纠纷防范和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人文关怀”,这无疑为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制度实现提供最强的支撑和制度正当性。
(三) 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必要性基础
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必要性源于其在医疗实践中的双重功能 :第一,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采取诊疗行为需征得患者同意,从患者角度而言,这有利于保障患者的权益,患者有权通过了解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法,确保患者自主性;第二,医疗活动系复杂性与风险性并存,若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需承担侵犯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的法律风险。[14]医疗机构如实告知患者诊疗方案及可能的风险,由患者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该诊疗行为,如出现告知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可免于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保障与落实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既是对患者权益的保护,亦是对医疗机构权益的保障,实践中要求医生对有关诊疗信息的权利说明到位,能从实质上减少医患之间的不均衡状态。
侵袭性是医疗活动最明显的特性,医务人员告知患者可能存在的后果,患者清楚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进行侵袭会有何种后果,并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医务人员的该医疗活动。[15]在一定程度上,当医疗机构与患者就相关后果如实交换意见后,医疗机构充分告知患者诊疗结果、方案与风险等信息,患者如果知情不同意,亦是在履行自主权,在厘定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时,无需承担侵犯患者权益的法律责任。在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未就诊疗行为的规范性和技术性进行充分沟通,患者缺乏对自身病情、手术风险、以及其他相关诊疗信息,难以做出合理又正确的决定,消极地影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影响患者的健康情况,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因此,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必要性基础需着眼于患者利益最大化,医患双方需加强沟通,患者配合治疗,医方保障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减少医疗纠纷。
二、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现实窘境
(一)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冲突
《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活动须取得患者同意的同时还应取得患者的近亲属的同意并签字。但《条例》第33条立法初心却与《民法总则》第130条的立法精神相违背,《条例》第33条更强调的是近亲属的书面意见,而《民法总则》第130条强化的则是人作为个体所应享有的民事权利,不受干扰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侵权责任法》第55条也是将患者的意见放在首位,而后才考虑近亲属的意见,显然,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左的情况。首先,《条例》在《民法总则》与《侵权责任法》产生之前就制定了,从法律适用考量,新法优于旧法,在患者自主决定权的行使过程中,理应优先考量《民法总则》与《侵权责任法》;其次,《条例》是行政法规,国家的基本法已经对此作了相应的新的明确规定,国家的行政法规作为下位法就应当及时作出修改,以保证国家的下位法和上位法的一致性。
(二)患者自主决定权、患者近亲属代为同意权与医疗干涉权之间的冲突
首先,缺乏对权利本源的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与患者近亲属代为同意权之间按照法律上代理的逻辑,代理人的代为同意权来自于被代理人,代为同意权不应当大于本权,代为同意权从属于本权。榆林产妇事件中,孕妇入院之初书面授权其丈夫全权负责相关文书的签署,丈夫作为产妇的代理人,有代为同意权,但医院以未取得代理人的书面同意为由没有进行剖腹产手术,医院忽视了意识清醒着的产妇本人的意见,是悲剧产生的根源。当患者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足够的辨别能力时,首先需要尊重和保护的是患者的表意,其具有优先价值。然而,医疗实践中,医疗机构却更加看重患者的代理人意见,没有代理人的书面签字,即便患者强烈要求治疗也难以得到医疗机构的同意。
其次,医疗干涉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的两权冲突。医疗干涉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矛盾冲突源于二者博弈过程中的相互限制,医疗干涉权是医务人员在出现特殊情况下无需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对患者采取医疗行为,医疗干涉权是医务人员的专属特殊权利,医务人员对该权利的行使,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患者自主决定权。[16]医疗干涉权以医务人员为主导,为患者决定最有利于患者权益的医疗活动,患者让与了自己的决定权,把本应由自己决定的事情转由医务人员代替做决定。这种关系建立在医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但在医患关系紧张情况下,医院的公益性不足,盈利性有余,医患之间不信任程度滋生,医生的防御性医疗行为、过度医疗行为又加剧矛盾的程度,影响了医疗干涉权正当性基础。[17]此外,我国立法对医疗干涉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规定的滞后,使得两者各自的边界不明晰,我国尚未有系统的医事法,遑论涉及患者自主决定权的详尽规定。如何保障医疗机构在行使医疗干涉权时是合法的,如何防止患者自主决定权的不断扩张,如何让权利的行使有益于患者的切身利益,成为医疗干涉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冲突的焦点。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如何分配医疗干涉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所带来的责任[18],造成二者之间的医疗与伦理的矛盾深化,寻求解决方案已是医疗实践与司法审判化解矛盾的重要关注点。
(三)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疗紧急救治权的冲突
2010年12月,广州华侨医院产妇事件,使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疗紧急救治权的矛盾冲突彰显出来。[19]该事件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拥有优先决定权的清醒着的孕妇不同意剖腹产手术,即患者的“知情不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取得患者家属的同意签字,行使了紧急救治权实施了手术,救下了产妇的性命。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医学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然而,医疗活动具有复杂性,常常遇有紧急状况,需引入医疗紧急救治权,因此,便引发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疗紧急救治权冲突的窘境。
从医疗实践中看,在手术治疗之前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同意源自于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手术治疗的结果密切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患者或其近亲属有权知晓并行使决定权,医务人员有义务告知情况。这一程序性设置,一方面是为了预防医疗纠纷发生,同时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均有主张的依据;另一方面,是为防止出现手术治疗之后的医疗费用无人负担的困境,因而近亲属的意见也往往变得重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行使民事权利,患者不同意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实施手术行为,是患者对自己生命权与健康权的一种处分。[20]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的紧急救治权受到了阻碍,诚然,患者有知情权与自主决定权,但对于危重患者的抢救是医德伦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权属可以通过事后采取医疗解释等行为补救,但错过紧急救治的后果则异常严重。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是紧急救治措施的目的,紧急救治行为中亦夹杂着医务人员的职业伦理、法律规定和当前社会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强烈碰撞。
从法律上看,《侵权责任法》第56条[21]《执业医师法》第24条[22]与《条例》第31条[23]均鼓励医务人员实施医疗紧急救治权;《条例》第33条第1款免除了医务人员因紧急救治而造成的后果的责任。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规定相对缺乏,没有明确的边界来定义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更无法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来阐述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医疗紧急救治权相冲突而导致的侵害类型、法律后果等,导致我国出现患者近亲属的签字同意权越过患者自主决定权,比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更为有效。因而会出现“不签字、不手术”的情况与医务人员的紧急救治权之间相背离,让处于人道主义的医疗紧急救治权缺乏可靠依据。因此,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疗紧急救治权的冲突有待相关法律进行厘清。
三、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法治化路径
(一)确定患者自主决定权行使之原则
1. “充分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原则
身体健康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必要基础,患者自主决定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其行使主体为本人,且不可替代、不能让与,患者有权自主决定实施在自己身上的医疗活动的可行性与否。[24]确立“充分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原则,一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有辨别能力的患者坚持拒绝治疗时,医疗机构就应当行使医疗干涉权,以“生命优先”的原则对患者进行紧急救助。[25]二是患者因宗教信仰或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明确拒绝相关诊疗时,医疗机构要尊重患者的选择。
2. “最有利于患者”原则
“最有利于患者”是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一般原则,当近亲属代为同意权、医疗干涉权与医疗紧急救治权之间出现冲突时的处理指导原则。[26]医务人员的本职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当其在履行本职工作时,以“最有利于患者”原则为患者利益考虑,当以“充分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原则为指导,有可能使患者因未得到救治而失去生命的情况发生时,生命的无上地位和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冲突碰撞,此时因时间的紧迫与道德的召唤,以“最有利于患者”原则对患者进行救治,那么则不能再要求其承担后果。[127]
(二) 完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功能
最初我国医疗机构引入医学伦理委员会,是为了核验临床试验方案及附件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并为公众提供保证,确保受试者的健康、安全和权益受到保护。[28]后因医患矛盾的升级而使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功能进一步升级,我国法律制度尚缺乏关于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性质及其衡量标准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完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功能亟待学界探讨。患者自主决定权时常涉及道德伦理,因此,可以在现有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度的基础上增设评估体系,以完善患者自主决定权行使的合理性。评估体系由专家组成认定会成员,专家认定会从属于医学伦理委员会,由专家组成员依照程序对医疗情况是否属于“特殊情形”、患者的自主决定能力是否正常等情况进行认定,采取程序公开透明的方式,以增加患者的安全感,降低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
(三)建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
预先医疗指示又被称为生前预嘱,是指患者在尚有完整的辨别能力时提前对将来如果丧失决定能力时要接受何种治疗方式所做的预决定。[29]我国对于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的相关问题还未进行系统立法,从法理层面上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彰显了价值位阶原则的人性面,每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其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决定应当得到尊重;从社会学角度上看,推动建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且急切的[30];从立法形势中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的构建,是现今中国老龄化日益凸显的社会背景下,患者自主决定权制度需求的直接反映。首先,患者行使预先指示权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指示他人在自己丧失决定能力时替代自己行使决定权,二是患者直接事先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诊疗风险做出选择,这体现了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其次,患者在行使预先指示权时,不仅要求患者本人具有辨别能力,而且代理人也要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建立预先医疗指示制度能有效限制权利的滥用或怠于行使权利,患者通过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所选择的治疗计划或方案,由代理人应当按照有利于患者利益的原则,选择最佳方案或者最接近患者本意的诊疗方案。但若患者滥用医疗指示制度,相关的预先医疗指示内容违反法律或医疗职业道德,医疗机构在必要时可以进行干预。
(四)适当扩大“紧急情况”医疗干涉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
《侵权责任法》第5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了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紧急情况医疗干涉权的行使。该制度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出现“紧急情况”,但仅列举“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一种紧急情况;二是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三是行使医疗干涉权的主体限于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或授权负责人。在出现法律规定的“紧急情况”,医疗机构怠于实施相应医疗措施导致患者损害的,患者有权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当患者无法行使自主决定权时,医疗机构就应予启动医疗干涉权预案,主动联系患者近亲属并征求其意见,但不管患者近亲属意见如何,其“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先行对患者实施相应医疗措施。但是,我国对患者“紧急情况”的解释过于单一,且医疗干涉权的行使主体规定过于笼统。因此,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完善医疗干涉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 :一是对“紧急情况”进一步进行列举,以确保在具体的医疗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情况可以采取类推的方式作出启动或者不启动医疗干涉权的决定[31];二是考虑患者及其近亲属的意见时,对一些显然不利于患者的不符合常理的选择决定则可予以排除,防止家属为了互相推脱逃避责任而对患者本人的生命作出极其不负责任的决定;三是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责任人在行使医疗干涉权时,应当首先征求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意见,由医学伦理委员会对行使医疗干涉权是否符合“紧急情况”、是否侵害“患者自主决定权”、是否符合“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等方面进行判断,作为医疗机构负责人决定是否行使医疗干涉权的伦理支撑。
四、结语
社会医疗水平在进步,但悲剧却在不断重复,榆林产妇的悲剧无疑是继肖志军拒签案事件之后,为法制建设敲响的又一大警钟。当前对于患者自主决定权的保护,不管是在法律制度层面还是在权利的救济保障层面,都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2006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布《医疗上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对预前指示适用的种种状况进行论述,分析预前指示的有关建议,从而强化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法律依据。2016年,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成为亚洲地区第一部明确病人自主决定权的法律,其中明晰了紧急救治权、预先医疗权,实现了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保障,其立法目的在于推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化,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作为借鉴,国内的相关制度应当进行相应调适和变革,适宜以正当生命法益理念作为制度重构的逻辑起点,在对待个人生存权、健康权、生育权等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着重强调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尊重,从患者本身利益出发,加强确认和保护患者自主决定权。首先,通过完善现有法律,界定患者自主决定权,修正现有模糊状态,并对患者自主决定权与近亲属代为同意权、医疗紧急救治权以及医疗干涉权之间的权利界限进行厘清。其次,加快关于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立法步伐。依据《民法总则》第130条的概括性规定,患者自主决定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背景中,人格权是重要的权利属性,将患者自主决定权引入人格权的立法进程,为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单独立法提供法律依据。希望能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和人们的法律意识的增强,逐步完善关于患者自主决定权的问题探讨,让悲剧不再继续,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增强人民的幸福感。
注释 :
[1] 北京朝阳一产妇李丽云被丈夫肖志军送到医院,医生在诊疗时发现其因为难产引发多种并发症,其中包括心肺衰竭,要求产妇立即进行手术,但其丈夫却坚决不同意签署手术同意书,并在手术通知单上写道 :“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产手术,后果自负。”在场医务人员在历时3个小时的抢救过程中,一边试图联系孕妇的其他家属,一边向上级领导报告,但得到的却是“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指示。于是,在几位医生的轮番心肺复苏下,22岁的产妇最终还是抢救无效,离开人世。详见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8)朝民初字第06072号民事判决。
[2] 2017年8月31日,陕西省榆林市一孕妇从医院妇产科5楼跳楼身亡,事后医院声明,是因为家属拒绝剖腹产才跳楼身亡,但产妇的丈夫却否认了医院的说法,称其曾先后两次同意剖腹产,而医院则说“快要生了,不用剖腹产”,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双方各执一词,事件成“罗生门”。
[3] 孙慕义 :《医法大法学》,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4] 杨立新、刘召成 :《论作为抽象人格权的自我决定权》,《学海》2010年第5期。
[5] Sherwin S,“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Autonomy in Health Care”,in S.Sherwin ( ed.) ,ThePoliticsofWomen’sHealth:ExploringAgencyandAutonomy,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47.
[6] 乔 荣 :《从榆林产妇跳楼事件看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中国卫生法制》2018年第6期。
[7] Onora O’Neill :《知情同意 :从纽伦堡到赫尔辛基》,《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11期。
[8]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及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生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9]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10] 《侵权责任法》第 55 条规定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11] 鄢 超、尹 口 :《医院履行术前告知义务的几点启示》,《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1年第4期。
[12] 杜政治 :《医学伦理学探新》,郑州: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213页。
[13] 张 娟 :《患者自主权 :内涵、困境及突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页。
[14] 熊静文 :《患者自主决定权实现中的情感预测——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中国卫生法制》2019年第1期。
[15] 周 瑶、何旭昭 :《患者自主权行使及其限制》,《理论观察》2015年第3期。
[16] 汪丽清 :《医疗干涉权的法理分析》,《中国卫生法制》2012年第2期。
[17] 张维帅、尹 梅 :《论医疗干涉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年第5期。
[18] 张 雪、孙福川 :《生命权、知情同意权和特殊医疗干涉权的冲突及衡平》,《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年第2期。
[19] 2010年12月,一名产妇在广州华侨医院被医生症断为 :胎盘早剥症状,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分娩,产妇的丈夫在听取医生描述孕妇的状况和个中利害后,同意签署手术同意书,但产妇却不同意签署,坚决要顺产。最终,医生经过特殊批准对产妇进行手术,保住了产妇的性命。
[20] 刘召成 :《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人格权权利地位的法理证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
[21] 《侵权责任法》第 56条规定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22] 《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 :“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23]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 :“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
[24] 陈树鹏、石庆红 :《关于患者人格权保护的几点思考》,《医学与法学》2018年第3期。
[25] 刘子平 :《术前签字制度的法律思考》,《群文天地》2012年第14期。
[26] 毛梦丹 :《浅析患者的医疗同意签字权》,《中医药管理杂志》2012年第5期。
[27] 阿依加马丽·苏皮、阿克白·加米力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医学与哲学》2015年第13期。
[28] 李志光、梁宁霞、张馥敏、赵 俊 :《医学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特点及思考》,《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11年第4期。
[29] ACT Health,Mental Health Policy Unit,OptionsPaper:ReviewoftheAustralianCapitalTerritoryMentalHealth(TreatmentandCare)Act1994. Canberra : ACT Health,Mental Health Policy Unit,2007,p. 20.
[30] 金心蕊、姜栢生 :《院前公众紧急救助免责问题的立法进展与完善研究》,《医学与哲学》2018年第6期。
[31] 黄 戈 :《对手术签字的法律思考》,《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