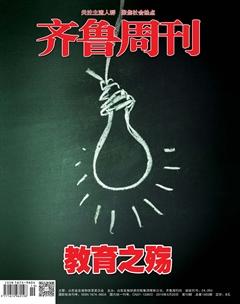教育进化与我们的时代
海欣
人为什么要受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永恒的问题。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在亚当的堕落中我们大家都有罪”
“教育”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人为什么要受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一些没有標准答案的永恒的问题。
1892年,美国名噪一时的《论坛》(The Forum)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教育现状的重磅报告。报告的写作者约瑟夫·梅耶·赖斯(Joseph Mayer Rice)原本是纽约市的年轻儿科医师。基于对教育的浓厚兴趣,他到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花费了整整三年时间研究教育学。
从欧洲回来后,这个33岁的年轻人开始在媒体上宣扬一些教育新观点。他的尖锐言辞受到了《论坛》的关注。主编佩琦(Walter Hines Page)建议赖斯代表杂志准备一份有关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手评估材料。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从纽约到圣路易斯,赖斯到教室听课,同教师谈话,出席地方教育董事会会议,访问家长。1892年,他调查访问了36个城市。基于这次调查所发布的报告成了刺向美国教育的一把匕首。
赖斯激烈地抨击说,在美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教育正在毁灭。教学往往是草率的,教师们认为“教低年级的孩子不费心”。所有的课堂都弥漫着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息。未经培训的教师对着老掉牙的课本照本宣科,而孩子们的学习就是死记硬背他们的课本。每节课花费10~15分钟在背诵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教学模式。
赖斯所处的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现代教育革命。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为了对涌入城市的贫民区儿童进行教育,同时对大量移民进行“美国化”,以1852年马萨诸塞州的《义务教育法》为发端,19世纪下半叶,美国各州相应建立起公立教育制度,普及中小学教育。至19世纪末,美国的初等教育制度基本定型。
从本质上,灌输式的教育是由教育中的权力结构决定的。近现代教育产生之前,教会是教育的核心机构。以神启知识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促进了灌输式教育的形成。人的认识只能局限在教义所规定的思想范围内,对教会所确认的事物和结论不能有任何怀疑。而在教育内容上,人们自然也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几百年来,灌输式的教育从未受到动摇。它被应用在各种层次的教育中,儿童教育并不例外。
在中世纪及其以前的时代,人们并没有把儿童看作儿童的观念。在中世纪社会里,孩童一旦到了可以摆脱父母、保姆或其他人经常性的关照,能够独自行动的年龄,他就从属于成人社会。人们只认可他们在生理上与成人存在差异。于是儿童参与成年人的各种活动,穿着与成人一样的服装,他们与成人世界混杂在一起,被当作“缩小版的成人”。
既然无所谓“儿童”,也就更无所谓针对儿童制定的教育方法。甚至,儿童受到的教育可能更为严苛。拯救这些灵魂的任务最初是由家长与教会联合完成的。
当正式教育逐渐发展并且兴盛之后,学校机构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16世纪的学校里,儿童穿着大人般的衣服,维持大人般的姿态,而且只要稍有不顺从,就会换来钳制与体罚。
在中世纪,剑桥大学的学生想要成为一名文法学学校教师就必须通过这样的考试:在主考官面前展示自己用木棍体罚一个儿童的能力。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小学的主要教科书里,在教孩子认识第一个字母时,课本上依然写着:A——在亚当的堕落中我们大家都有罪。
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什么是最好的教育?不仅在美国,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在上个世纪经过了激烈的反思、实践,不断在不同的教育模式之中进行取舍。
20世纪初,杜威、克伯屈、帕克等进步主义教育学家先后访问了四大洲近20个国家。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大批留学生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其中一部分直接受过杜威、克伯屈等人的教导,程度不同地受他们思想的影响。杜威的著作先后被译成中文、日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等36种文字。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和实验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指导了各国的教育改革和实践。
在英国,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以传统课程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课程占据主导地位;60年代,注重儿童发展的课程最终成为主流。70年代以后,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又促使教育回归保守。1980年和1988年的改革都体现了撒切尔主义,推行新保守主义的文化右翼纲领,即强调教育中的标准、传统、秩序、权威、等级制度等。《1988年教育改革法》按年龄重新划分了学段,并为每个学段制定了成绩目标和教学大纲。在20世纪英国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为课程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成绩目标和教学大纲。
事实上,所有这些教育改革均围绕着一个国家的核心议题,即加强英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对于教育的评价标准总随着时代议题的变迁而变化,在社会需求和个人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保守也一直是美国教育的主流。2002年,小布什政府签署了半个世纪来最重要的教育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重点是对全国所有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设定发展目标,加强标准化考试,对不合格学校进行惩罚。
尽管如此,美国教育已经打上了进步主义的诸多深刻烙印:学校从8年小学和4年中学的体制变成了6年小学、3年初中和3年高中的体制。这是对发育期儿童的特殊需求的更大重视。所有年级都继续扩大和重新组织了课程。学校增加了课外活动,学生俱乐部以及各种活动成了美国学校的一个显著特征。
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学校组织多样化和更灵活的学生小组。教室特点的变化非常明显,特别是小学教室,与作为曾经的课堂教学的教室有了很大不同。课本变得丰富有趣,越来越多利用一些补充材料,比如幻灯片、电影,不计其数的资料,从植物、动物到制造业产品,都进入了课堂教学。校舍进行了改革。体育馆、游泳池、运动场、实验室、商店、小型的桌子和椅子,可以移动的家居和隔板都说明教学计划和管理发生了变化。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它变得更加灵活、积极、不拘于形式。
在学校管理上,行政管理人员放弃了部分权力,教师在课程制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家长可以通过家长协会或家长和教师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全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的学校教育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
我们时代的“自由教育”
按说,教育没有那么复杂。
人之初,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3.75亿年前,泥盆纪海洋强者如林,弱肉强食,某一只盾皮鱼某一天做了一个天大的冒险:把卵生变为胎生!就此一刻,命运突变,盾皮鱼分娩出强壮后代,彻底超拔出鱼吃鱼的残酷现实,挺起了进化的脊梁,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祖先。
在随后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中,依然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人类智力还是获得了高质量发展,终于成为世界主宰。后来我们之所以有了学校和教育,应该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期获得更高质量的智力提升,以确保我们拥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
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正如《大学的理念》的作者约翰·亨利·纽曼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
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2005年,美国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华莱士是在西方有卓越影响力的作家,被誉为“近20年来最有创造力的作家”。
演讲的开头,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两条年轻的鱼遇到一条老鱼。老鱼打招呼道:早上好,孩子们。这水怎么样?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终于,其中一条忍不住问另外一条:什么是‘水?”
演講中提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需要早早起床,赶赴办公室,应付8-10个小时充满挑战的工作。然后去超市、做饭,放松一会就得早早上床。因为,第二天又得周而复始,再来一遍。
人很容易在这样的生活里,形成无意识的惯性:无意识地翻手机、给生活加速、陷入琐碎的柴米油盐、忽略身边的人和事、冷漠、愤怒、抱怨,而不自知。
就像开头的故事一样,生活在“水”中太长时间,已经不知道水是什么。
实际上,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不是“我”被杂乱、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而是生活由“我”掌控。
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