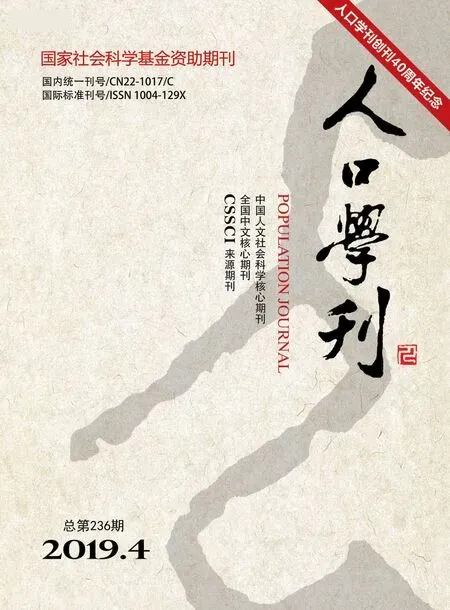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陈 璐,谢文婷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天津 300350)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亿,占总人口的17.3%。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如何实现“健康老龄”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外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数达2.45亿,占总人口的17.7%,其中农民工人口数量庞大,接近1.6亿人。成年子女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由此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留守农村的老年人群体。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社区照护机构和专门老年护理机构发展滞后,老年父母的赡养和生活照料依然是由家庭来承担,主要是由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一旦子女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父母所获得的各种照料和支持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可能增加留守父母照料孙辈的负担,从而对其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而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不仅可能影响外出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同时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成为家庭、社会和政府广泛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旨在科学系统地评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为今后我国相关老龄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研究和决策依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1997-2015年的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考察农村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同时考虑在中国农村地区,“孝道”对不同性别的子女而言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检验对于留守父亲或母亲以及不同性别子女外出务工产生影响的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结论并不一致。绝大部分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无论是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心理健康状况都有负面影响。Antman使用墨西哥2001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增大了父母身体和心理健康恶化的可能性。[1]Falkingham等人使用印度2011年的截面数据,通过二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家庭中有在国内或国际流动的子女,老人罹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概率更大。[2]Adhikari使用泰国2007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有在国内流动子女的老人更容易呈现较差的心理健康。[3]连玉君等采用CHNS数据,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使得父母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下降。[4]杜鹏等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2004年在安徽省寿县、河北省承德县和河南省浚县等地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孤独感加重。[5]江克忠、陈友华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简称CLHLS)2008年数据,发现空巢老人心理健康受到负面影响。[6]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有积极影响。宋月萍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子女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支持能显著增进老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水平。[7]Kuhn使用来自摩尔多瓦2011年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子女流动带来的收入提高能为留守父母提供更好的饮食和更闲适的时间分配,这些积极作用能补偿老年人与子女社会联系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8]Böhme使用来自印度尼西亚1997至2000年的家庭生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后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给父母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超过了消极影响。[9]
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的选择不是随机发生的,可能会受到可观测和不可观测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克服这一问题带来的影响,才能得到无偏的回归结果。在现有文献中,有的学者采用截面数据的Logit回归方法或对数线性模型方法;[10-11]有的学者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4][12]也有的学者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截面数据的倾向值匹配方法解决自选择问题。[6][13]虽然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外出务工的自主选择问题,但是如果选择外出务工的子女在不可观测因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不同,那么固定效应模型无法解决这种自选择效应带来的影响。此外,Gibson在对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以及工具变量方法的比较研究中,发现PSM方法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效果优于其他两种方法。[14]
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使用了CHNS七次纵向调查数据,从1997年问卷中第一次调查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情况,到2015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数据跨度19年,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第二,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来控制自选择效应可能带来的影响,由此得到的回归结果也更加科学可靠;第三,本文进一步基于性别角度,分别对不同性别的留守父母以及不同性别的外出务工子女进行回归分析,使研究更加深入。
三、数据和变量
1.数据
本文使用CHNS数据,该项调查具有全国性、大规模、多层次和开放性的特点。调查涵盖全国12个省份(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北京、上海和重庆)约7 200个家庭,共约3万人。这些省份遍布全国并且在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等诸多特征上有所不同。因此,作为一项以家庭为基础的纵向调查,CHNS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15]本文使用跨度19年的七轮调查数据(1997、2000、2004、2006、2009、2011和2015年),将样本限定为农村地区,在剔除了未养育子女的个体和缺失值后,有效样本量为23 830个,其中7 817个样本为有子女外出务工的父母,占总样本的33%。
2.变量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个体的健康水平,如何科学地度量健康自然成为关键问题。健康是个体的体格、精神与社会适应的整体状态,是一个包含生理和心理指标的多维度概念(WHO,2015)。因此,本文选择三个不同维度来测度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过去四周是否患病”变量衡量短期身体健康,该变量来自问卷中受访者对过去四周生理健康状态的客观判断;“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变量(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衡量长期身体健康状况,由于对于IADL的调查仅针对55岁及以上人群,所以对于该变量的研究我们仅针对55岁以上受访者样本;“生活满意度”衡量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由于CHNS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从2006年才开始,因此对于该变量的研究我们仅使用2006、2009和2011年的数据①由于2015年公布的CHNS数据中没有“生活满意度”指标的数据,所以对于该变量的回归我们仅用了3年的数据。。
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是否为留守父母”,CHNS问卷通过“该家庭成员是否住在家中?”询问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居住状况,我们把选择回答子女“外出打工”定义为至少有一个同户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父母,即“留守父母”;而“非留守父母”则定义为没有同户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父母。在本研究中,留守父母占总样本的3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CHNS问卷中只对与父母同户的外出务工子女做出上述提问。因此,我们的研究没有涉及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考虑在一般情况下,同户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实质性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性支持,与父母的互动也最密切,因此在所有成年子女中,同户成年子女的外出对父母的影响最大。
此外,本文控制了留守父母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拥有医疗保险(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家庭人口构成包括家庭中是否有多个成年子女以及是否照料6岁及以下的儿童。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家庭资产指标(是否有摩托车、拖拉机、汽车等)①CHNS问卷中调查了家庭中某些耐用品的拥有情况,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构建代表家庭财富的综合指数,该指数基于家庭对普通耐用品的拥有状况,而拥有这些耐用品代表着相对现代和舒适的生活。。研究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1。
四、计量方法
研究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产生的影响,一定要解决外出务工的自我选择对于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基本思想是从没有子女外出务工的控制组中根据倾向得分选取某些个体,与有子女外出务工的处理组进行匹配,进而可以求得配对个体间的结果变量的差异,以实现对干预效应的无偏估计。[16-17]
以Treatment=1表示有子女外出务工,即处理组;Treatment=0表示没有子女外出务工,即控制组。则平均处理效应可以表示为: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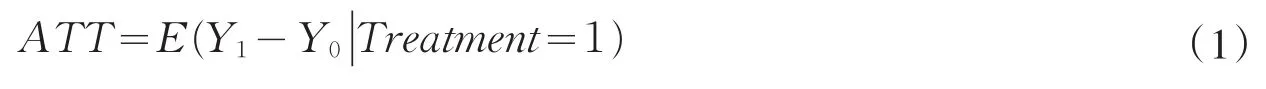
其中,Y1和Y0分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健康变量。
为了选取与处理组个体在可观测的基本特征上一致的控制组个体,本文利用Logit模型获得倾向得分,即Logit模型的预测值,模型如式(2):

其中,Ind表示留守父母的个体特征,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劳动及是否有医疗保险等;HS表示家庭的人口构成,包括家庭内是否有多个成年子女以及是否照料6岁及以下的儿童;HE表示家庭的经济状况。

图1 匹配后核密度函数图
五、实证分析结果
1.样本匹配质量
表2呈现了可观测变量匹配前和匹配后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的t检验结果①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仅呈现四周患病率指标匹配质量的t检验结果。没有呈现生活满意度、IADL和自评健康指标的匹配质量的t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劳动、家庭人口构成、家庭资产状况等方面均有比较显著的差异,而在匹配后,控制组中根据倾向得分选取的样本组与处理组在可观测变量方面的差异均有所减小,说明选取的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能够保持一致性,具有较好的匹配质量。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见图1,两组变量的特征在匹配后是相似的。表3是我们进一步呈现了匹配后的数据整体平衡条件的检验结果。

表2 匹配质量的t检验结果(四周患病率)
2.回归结果
表4呈现了基于PSM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结果。我们采用近邻匹配(Nearest-Neighbor Matching)方法下的1对2匹配作为主要结果进行呈现(见表4第1列),此外将近邻匹配中1对1匹配、1对4匹配以及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作为稳健性检验(见表4第2-5列)。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匹配方法下,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和符号与主要结果保持一致。此外表4还呈现了每种匹配方法下不满足假设的样本数目,即不满足共同支撑要求的观测值,这些观测值与总体数量相比,数量非常小,可以认为共同支撑要求未对样本总体产生较大影响。
表4第1列中,匹配之后四周患病率与生活满意度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等于0,相对于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导致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增加2.7个百分点,显著降低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回归结果表明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对留守父母在短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外出务工时,家庭的照料方式会遭到破坏,而缺少子女照料后产生的孤独、焦虑以及压力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3][18]此外子女外出务工显著减少了留守父母得到的日常生活上的实质性支持,增加了父母在农活和家务上花费的时间。[19-20]与此同时,子女外出后与留守父母的情感交流的减少也会对父母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7]

表3 匹配质量的整体检验结果

表4 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是保持一致的。Ao等人使用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n 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2009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增加了父母健康恶化的可能性。[12]Huang等人使用CHNS 1997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3]Antman使用来自墨西哥2001年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增大了父母身体和心理健康恶化的可能性。[1]国内相关研究中,舒玢玢、同钰莹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2012年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长期两地分离而导致家庭照顾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减少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21]连玉君等使用CHNS 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使得父母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下降。[4]
从表4中我们发现IADL指标在匹配后的ATT值并不显著。那么这是否说明子女外出务工对于父母长期健康因素不产生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考察不同年龄分组的留守父母数据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在表5中,对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匹配后的ATT值均显著不为0,相比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而不能完成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的概率增加6.1个百分点。这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留守父母的长期身体健康状况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我们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相比较年轻的留守父母,老年的留守父母对子女照料的依赖程度更高,从而受到子女外出务工这一行为的影响也更显著。这一结果与国际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Ao等人研究发现子女移民对60岁及以下的留守父母的自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增加60岁以上的留守父母有较差自评健康概率17.8个百分点。[12]

表5 区分年龄段考察子女外出务工对于留守父母IADL指标的影响
3.基于自评健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在主要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用自评健康这一综合性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卫生经济研究中自评健康被认为是一项较为稳定的度量健康状况的指标。[22]由于自评健康变量仅在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问卷中进行询问,因此本部分稳健性检验采用1997-2006年的数据样本。表6显示在以自评健康作为关键被解释变量时,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不为0,相比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而增加自评健康较差的概率6.4个百分点。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的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6 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自评健康的影响
4.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检验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状况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分别对两类子样本进行了匹配回归。
表7中Panel A是对留守父亲和母亲进行分组,呈现了匹配后的ATT值。我们发现留守父亲会因为子女外出务工增加患病概率3.6个百分点,而留守母亲则会增加患病概率2.3个百分点。对生活满意度指标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对留守父亲产生的消极影响要略大于留守母亲。表7中Panel B是对外出务工的儿子和女儿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较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会因为儿子外出务工而增加患病概率3.7个百分点,因为女儿外出务工而增加患病概率2.9个百分点。对生活满意度指标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儿子外出比女儿外出给留守父母带来的健康冲击更大。针对这一结果,我们分析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地区是父权制体系,农村儿女所承担照护老人的角色不同。[20]儿子在经济和日常照料上承担主要责任,[23]而女儿的照料责任通常出于亲情而非社会期望。[24]根据2009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与女儿外出相比,外出儿子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在外出前后的降低效果更明显。[20]因此,儿子的外出更有可能破坏家庭原有的模式,并对父母健康造成影响。

表7 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六、主要结论
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是由城市化推动的独特的人口迁移活动。在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我国农村地区,子女外出对留守父母健康产生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研究发现有成年外出务工子女的留守父母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比没有外出务工子女的父母要差,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对父亲更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家庭破坏理论模型保持一致,强调了父母与承担其照料责任的成年子女异地分离的破坏性影响。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成年儿子的外出对父母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基于以上结论,为了弥补以家庭支持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和建设,以期弥补由于子女外出,照料缺失给父母带来的健康影响。
由于CHNS问卷变量的局限,我们承认本文存在两点研究不足,这也是今后可以拓展研究的方向。第一,虽然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第二,子女外出务工时间长短对于留守父母的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在程度上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