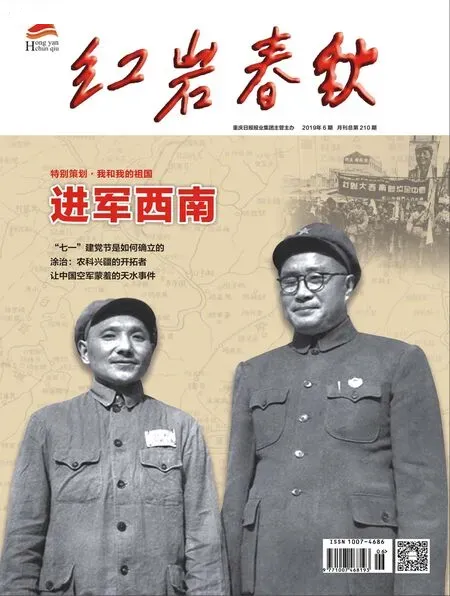消失的合汤
■陶 灵
四五岁时,一天,我走了很远的山路,跟姑妈去白水滩窑罐厂买瓦缸。挑了很久,姑妈却选了一口带凹瘪痕迹的瓦缸,我十分不解。
瓦缸横绑在背篓上,姑妈背着,然后牵着我的手回家。路过毛坝供销社的一个食店时,早过了午饭时间,姑妈进店给我买了一碗包面(抄手),她自己则吃随身携带的苞谷粑。这时,食店服务员端来一碗清汤,姑妈吃一口苞谷粑,喝一口汤。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姑妈为了省下钱给我买包面,才买了那口相对便宜的凹瘪瓦缸。服务员端给她的那碗汤也不要钱,称“合汤”。
合汤是什么汤?我又是许多年后才明白。那时候的食店烧煤炭土灶,用烟囱抽煤烟,往往灶堂的火力也跟着往外扯,打灶的师傅便在灶台靠烟囱的位置嵌入一只铁鼎罐。厨师利用余热在鼎罐里烧一罐白开水,煮汤和炒菜时勾卤汁水都用得上。他们还时不时把剔下的骨头和需要焯水的肉,放进鼎罐熬煮,白水因此有了肉鲜味,煮汤、勾卤汁水就可以增鲜了。这就是合汤,相当于现在烹饪时熬制的高汤。
以往年月贫穷的人多,来食店吃饭大多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不点汤。服务员则会在鼎罐里舀一碗合汤,撒上葱花,免费送给客人。这是那时候食店的普遍规矩,客人们称其为“欢迎汤”。
我第一次喝合汤是在30多年前,云阳南溪乡场上一家小食店里。当时我点了份豆干炒回锅肉,正开吃的时候,老板端来一碗淡乳色的清汤,上面飘着绿绿的葱花,淡淡肉香夹杂葱的辛味,扑鼻而来。这是初冬,我赶紧端起这碗热汤,喝了一口。这碗汤没放盐,腻而清淡,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老板本来在汤碗里放了一只调羹,我没用,而是直接端起碗喝,这样才配!
姑妈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曾经在云阳县城人民饮食店当服务员。有一天,店里来了一对农村人打扮的年轻夫妇,他们手里提着一串叠捆的中药纸包。两个人只买了一碗米饭,没要任何菜。丈夫说自己不饿,让妻子先吃,妻子把饭碗推给丈夫,说“我吃不下”。表姐见状,又拿了一个空碗,把米饭分成两份给他们。然后用土海碗舀了一大碗合汤,还特别舀了一调羹酱油在汤里,端给这对夫妇。他俩不停地点头,谦卑地叫着“劳慰了!劳慰了!”表姐说:“合汤不要钱,来的都是客!”表姐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却说了这么一句人情味的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到云阳一个偏僻山区采风,喝过另一种合汤,更是有滋有味。这时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小食店多数由私人开设,食店老板兼任厨师。炒菜之后,不论荤素,厨师会在锅里稍留一点汤汁,我们称“卤汁水”。他们在留下卤汁水的锅中,会再加一两勺清水,放入姜粒,烧开为汤,然后撒上葱花端给客人。这种汤融入了炒菜的调料、作料,有盐有油有味,大方点的老板还会在汤里放些菜叶。陪我采风的当地乡村文人马老头,给这汤取名“神仙汤”。
为什么叫合汤?我至今没弄明白。因为赚不了钱,现在食店、餐馆早没了合汤的踪影,连米饭都不再单卖。合汤不再有,“神仙汤”倒是自己可以在家里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