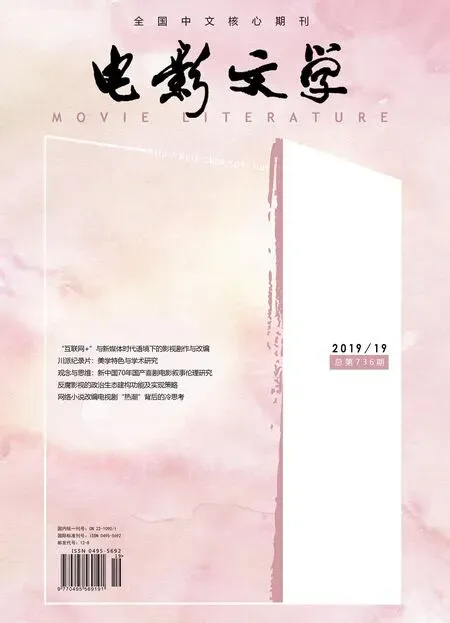观念与思维:新中国70年国产喜剧电影叙事伦理研究
邵君立 吴登容
(1.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创作室,四川 成都 611331)
一、绪 论
何为喜剧片?有论者如此定义:“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在总体上有完整的喜剧性构思,创造出喜剧性的人物和背景。主要艺术手段是发掘生活中的可笑现象,做夸张的处理,达到真实和夸张的统一。其目的是通过笑来颂扬美好、进步的事物或理想,讽刺或嘲笑落后现象,在笑声中娱乐和教育观众。矛盾的解决通常是正面力量战胜邪恶力量,影片的结局比较轻松愉快。”[1]
判断喜剧片的第一要素:是否能够产生笑的效果。生活的日常要在共通的规则下,通过心理作用的效果,治疗“疾病”。喜剧的笑就是寻找这些相对恒定的概念,寻找普世价值中的异类。生活当中,好玩的人或者逗比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异类。异类就是在相对恒定的社会契约中,“夸张处理”的人。所有的社会契约、普世价值,有他的合法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于是那些人群中的异类,夸张的言行,怪诞的举止,这中间的对抗,就是法理中间的对抗——法理引起人的异化。“在笑声中娱乐和教育观众”是商业电影在当今政治形态中的生产规则,一定要合乎相关法律法规,否则生产就会变成无效生产。“矛盾——轻松愉快”喜剧模式生产是当下生产的高峰期,喜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社会的焦虑,而焦虑背后是人类生存的撕裂和慌乱。
古希腊以来的喜剧都有一种充满民间性的幽默。而所谓对喜剧研究的“民间性”的观察视点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言说。
首先是一种“礼乐道德之下:空戏滑稽,德音大坏”的批判。回看人类的整体喜剧史,第一个高峰是古希腊,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崩溃的时候。喜剧寻找的是一个制度的崩溃或者是荒谬的某种反思。喜剧的民间性说的是喜剧的话语体系,有一个所谓的“主流话语之外”的说法,那就是主流话语之外的喜剧话语的描述。这是传统道德对于喜剧性、对于民间话语的非常严肃的批评[2]。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有着强烈的对抗,有一个例子:东三省地区有著名的传统曲艺,特别好看,那就是“二人转”。但在普世价值观里,原味儿“二人转”因其俗与“黄”难登大雅之堂。国外也存在类似的形态——性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就是借鉴了性喜剧,反映的是国人的性焦虑。这种话语体系,呈现出“主流之外”的民间的声音,是其在民间生存非常重要的根源,国外也是这样,《十日谈》也是在民间话语体系当中,对纲常法理的控诉。
由于具体的生产者加入了民间的声音,中国传统文人作品中加入了喜剧的创作,喜剧要做生产就一定要考虑传播的速率。李渔的作品就特别符合我国的喜剧生产环境。他见识和经历过明末清初的文字狱时期,作者选择了一种现实的生存哲学态度:娱乐主义。这无疑是在告诉后世的作者们,在各自的社会形态下,哪些东西绝对不能碰,不能调侃,不能沾边。2016年初上映的网络大电影《喜气洋洋小金莲》里描写虚假新闻、伪劣药品等桥段形成了对现实的某种揭示,但作者要放在北宋写。某种程度上,文人在黑暗时代的角落里向丑恶现象发出的怒吼,就是喜剧的创作来源。
民间性带来了喜剧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反抗性。伦理纲常不一定是法律法规,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喜剧的反抗性究其根源,就是人对于生的渴望。喜剧片为什么要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是消费者希望看到生活的希望,这是喜剧反抗性最终的落点。再生产当中,将喜剧的生产偏离了落点,这种喜剧的生产都很危险。如同民间性是在千百年的发展中产生,反抗性也在千百年演变,那都是历史。
二、道德规范与制度驱离
(一)中国喜剧电影创作的道德化倾向
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一直被宏大政治环境影响,这种外部变化给国产喜剧电影形态植入了一种“强生产”的背景。国产喜剧电影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度陷入迷茫的危机。如果说工业化意味着生产的持续性,便可以供养具体而微的人、支撑众多的家庭,因为在经济指标层面一个社会的有效性运转与每个社会个体收入之间的关联显得十分密切。电影的生产是在货币的支撑下进行的,由于战争的日益迫近,包括喜剧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生产的停顿从1949年的春天持续到1950年的春天,从而引起当时的中国电影主管领导夏衍专门在上海召开关于民营电影业重振的会议。社会动荡造成经济的停滞,这种伤害不仅是喜剧电影生产的停止,还包括所有电影的生产——瞬间电影的供给端消失了。
伴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败退,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战后经济尚未彻底恢复,原有的市民阶层消费能力严重下降了。那些没有跟随国民党政权撤退而留下来的人在新政权的序列中主动放弃了作为旧市民阶层的日常娱乐,同时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管制(1)这个场景在陈凯歌作品《霸王别姬》中有清晰描述,其故事背景虽然是北京,但是依然呈现了原有文化消费者走向“市民—公民”的转变。。如果“看电影”的本质是一种社交(成群结队的、搭伙的行为),1949年之后市民化的消遣方式被新的社会共同事务所取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集会使闲散的生命个体有了新的事情要做。市民阶级的消遣方式可以通过铿锵有力的政治运动消解内心的郁闷:结盟和排斥异己都成为一种新的社交。电影类型化的根源是人群在社交活动当中永远是党同伐异的。通过多次的社会改造运动,这时的电影观众不再是“消遣的市民”,而是政治的发烧友。而国有电影大厂的建立是伴随一次次军事上的胜利而立刻进行的对文化的建设和控制。
(二)媾和:作者的主动
1949年之后中国喜剧电影创作自动地到了规范化的生产中,这与彼时的政治时代状况息息相关。此时我们所处的时代风貌显现出与1949年形成一种互文本的倾向。民族、政治分裂化向一个统一化的叙事发展。政治层面下文艺生产中是民国末期开放式的讽刺喜剧到1949年以后道德规范化叙事发展,人们的价值规范被自动地归于同一个信仰中。
伴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作为生产者,对于大的文化语境中的叙事选择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放弃。分裂走向统一是如何实现的?1949年之后,我们对英美电影的胶片进行过一次清洗,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一律禁映甚至销毁,清洗了党内的异己分子。民国初年的默片时代也是碎片化的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从比较干瘪的市民喜剧和闹剧、滑稽剧之类类型单一的喜剧模式走向了体量庞大、叙事不再仅仅指向具体而微的个人、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走向了更大的叙事,表达时代中人物对国家命运的诉求,是基于民主和自由的立场对于黑暗社会的讽刺(《三毛流浪记》)。1949年之后,(《新局长到来之前》)喜剧内容不再有“革命性”的反抗(但是有对抗)。这就是所谓当中国喜剧电影进入1949年之后,有意无意地在叙事倾向里对于过去的割裂的对照。制度的驱离使得中国喜剧电影在1949年到1955年有6年的静默期,把不同立场不同利益的诉求掩盖了。喜剧的自由表达和规范性叙事通过新的话语体系进行构建。
这时候出现的“温和喜剧”酝酿了一套政治规训下的叙事法则:不对根本性叙事质疑,只在共通的价值体系下做出细微的调整。决定性胜利是指从政治秩序、经济运行都按照共产主义安排。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要说——这是所谓的温和——而不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用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来说。于是以下四种法则成为支撑国产喜剧电影的法宝:
第一是误会与巧合。高度的戏剧化情境(“境”上要更加像物理意义上的真实,情境被压缩得越狠,戏剧的张力越大。误会和巧合是被高度人为设定的)。
第二是去我化。取消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强烈冲突(“我”和社会的概念之间的冲突程度,在政治边界,是去我化的)。
第三是人物诉求简单化。没有生存之虞(人物诉求涉及生命主体的欲望)。
第四是人物关系的对立序列组合(人物关系的组合方法是不同的)。
(1)从民国喜剧电影中的善恶对立到1949年后国产喜剧电影中人物之间只有对错对比(“文革”电影无小事,全是阶级立场的问题)。
(2)1949年后中国喜剧电影中人物之间具有共同利益(终极诉求的一致化)。
(三)放逐:制度的驱离
1959年《今天我休息》出现的时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喜剧电影进入到了温和喜剧的阶段。那时的电影充满了温和桥段的编织,是对当时的政治秩序的再造,通过包装,包装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个体生命的情感诉求都进入到更加统一化的情感叙事里面。“文革”时期进行政治叙事的时候是将政治秩序通俗化一体。此时此刻设计剧本产品,编织进此时此刻的怎样的喜剧元素,在当今的产业里,如何实现票房,如何实现商业化诉求。通过历史的方法去回顾在不同时代中的消费热点。《三毛流浪记》反映的是当时上海民意的集中表现——体现了非官方的民间声音:反政府、“我活得不爽”,这种不爽,凝聚了民间气质——以泼皮无赖的方式进行讽刺。今天我们处于安稳的政治环境,因之,今天的物质化成为我们的时代命题。我们在一个物质化时代里面,可以达成一致的幸福畅想。而在民国末期社会状态是民不聊生、食不果腹,那怎么办?当物质化不是普世的时候,就会产生民间的声音,就会产生三毛那样的泼皮无赖,对时代进行讽刺甚至是反抗——然而我们不是。我们“时代的鸦片”是——“小时代”小妞电影。这些“时代的鸦片”是建立在普世的物质化时代上的——是打在时代审美的心态里面。20世纪50年代末期则是“普世的政治化”。社会的诉求在共同的政治里得到实现的。
每个生命所处的共识是在政治化语境中的,在这里构建的是“慈祥的父权”和“顽童”,是浮现了那个时代关于国家和家庭伦理的秩序。如果在原有的体系中,很难得到沟通和对话的可能时,就要编织出新的话语体系。所有的焦虑和欲望是要被释放的。一个新的政权对一个国家的规定、欲望释放的方法是在一个集体中,使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体得到欲望的合法性。刺客、特务的下场很惨,是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这个政权里释放欲望的方式。资本主义国家相信私有制才能保证人民幸福的根源,作为一个新的权力体系如何让人们认同?此时此刻,我们生活中的剩男剩女都是要被清除的——剩男剩女是向传统的家庭伦理进行挑战。家庭伦理的秩序是性秩序的衍生产品。当政治话语要传播一套权力话语体系,就建立在你我比较熟悉的生态里面(“慈祥的父权”)。在《今天我休息》中,建立的两个对话的序列(“慈祥的父权”与“顽童”),是具体意见的分歧,而不是终极利益的冲突。而“温和喜剧”的叙事存在巨大的逻辑缺失:
一是戏剧对抗的缺失(不要脱离时代,政治化的审美:在这样的政治序列里找到了自我所在的点)。
二是人物性格的无力感(生命在普世的价值中编织,自我的诉求就不再重要)。
但是所有的伪和都不能长久地维持,都会被击破。1966年,我们进入了整体撕裂时代——“文化大革命”。“父权”衰落,“顽童”都变成毁灭和谐的贡献者。伪和最终一定会被击破——这也是中国喜剧发展的局势。
三、神话与欲望:喜剧生产的两形态
(一)政治神话的瓦解
1976年,中国喜剧电影跟随中国社会与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历史在喜剧电影中的作用是很强大的。政治神话的瓦解导致了表述主题、社会心理、观众诉求(价值体系)的变化。
1.生产的角度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说的”东西总是变化的,片子的形态总是变化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才能看到统一假想消失的征兆。政党政治会带来全民的幸福感(政治话语),与政党政治相对应的是民主政治。在政治神话瓦解之前,国产喜剧电影里所描述的幸福感是政党政治带来的幸福感,所有的异类都是对政党政治统一性的怀疑。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休息》还能看到反派角色,后期便看不到反派角色,所有的喜剧逻辑不是建立在矛盾双方的对抗上,是建立在好人与好人的误会上——我们深刻地受着苏联喜剧电影的影响。在政党政治的环境中,是假设社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只有共通的任务。民主社会中,承认在社会问题中是存在彼此利益差异性的,可以有无数种解决方式。1949年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意味着我们消灭了资产阶级,再往后,我们有了“私”的意识。是承认人民有“私”的追求。“造反有理”是因为造反满足了人民的“私欲”。公社化运动收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便只有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内一度不承认公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这就是对财产的“私”的否定。正因如此,在政治神话瓦解之前,就在想象人民可以从中获得幸福。
从政党政治走向民主幸福。通过假想一个超级政治权力使得大家在假想中获得幸福。《瞧这一家子》解决的是年轻人与上一代的矛盾,由此看到,表述主题从政党政治幸福感走向了民主政治的幸福感。
2.社会心理
我们的幸福感是源于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党政治的正确性。《新局长到来之前》《今天我休息》,展现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喜剧电影中社会心理是在认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同政治制度毫无疑问的优越性。从《新局长到来之前》到《今天我休息》社会心态发生了变化。影片中的女性从没有选择性到了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女人选择配偶,两代人之间对抗的和解,点都落在“科技”上。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掌握了科技的才是最可靠的。只有“科学技术”能让我们幸福。这是社会时代变化下的社会心理变化。对于年轻人,学习科技文化,追求进步,就可以有资格成立家庭——这呈现的是当时社会的心理焦点。
3.政治规范演变下的叙事走向
政治神话瓦解之后,观众的诉求变了,和第二点息息相关。观众再也不要求看政治神话,在其中找不到快感。政治神话的体系观众不再信奉,于是观众的诉求发生变化。诉求从抽象的假想到了具体的对欲望的直视。欲望和欲望之间是要相互“撕”的——这就是民主。而政党政治,是不允许直视欲望甚至产生欲望的。欲望的价值体系在政治神话的时代被压制,到了新时代开始慢慢复苏,于是产生新的喜剧格局——家庭形象的构建。
家庭的前提是“父、母、子”。不同于社会关系、公共关系、非血缘关系,家庭是血缘关系,私人关系。当家庭形象构建时,是要有大大的“撕”构建出来的,这与政治神话的瓦解是有关的。统一公共的假想消失后,生命的假想回到“撕”的部分,个体的欲望开始需要消解。
到了新时期,农村喜剧也崛起了。农村社会生活图景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从假想的期望的虚构的丰收快乐的人民公社制度走向了实实在在的土地承包制度。经济领域的变革极大地撼动了农村原有的经济体系——由共同到私有。
(二)新时代之“旧”与旧家庭之“新”
所谓乡村生活的部分,生活的区间、成长空间是在一个大家族的序列当中的。当作为一个家族的共同体,可以共同承担家庭的义务,共同承担家庭的痛苦。家庭是小的“私”,家族是被放大的“私”。当1977年之后,中国的大家族未消失,仍持续到今天。对于今天更多的生命个体来说,家族生活是疲累的,但也是有所收获的。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国家庭中,无法摆脱旧有的传统序列,但幸福感不仅是家族想象带来的,是货币。个体价值的评判不仅在家族想象,还在于货币(个体价值的体系)。这些都是新时期农村喜剧所呈现的。每个生存在农村中的个体,就是在这样的藩篱和缝隙中生存的。
影片《喜盈门》中呈现的农村生活基于家庭的矛盾是多于城市的。影片中喜剧与未来神话的构建突出表现在:
(1)统一的时代命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反映。
(2)危机的反向写作——家族融合:直视分歧和冲突。
片子上映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电影强烈地触摸到当时的社会现象。乡村生活在当时是主流,城乡生活差距不大。观众可以普遍消费。当时的社会脉搏是:当经济改革发生,如何处理经济利益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再回看古老的喜剧电影,给我们的触发是,我们也应关注当下的社会利益。
(三)欲望的快感
而从观众学的角度考虑生产主题,“三毛”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威权政治秩序已经丧失,市民阶级不再信奉政治的权威,从而反抗;市民阶级要求欢乐——这样的一个群体,我把他们描述为“自动观众”。现在的观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众是“规定型观众”,他们的审美更多地受到了社会主流价值的影响。
新政权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快速包装”了新的运转模式,那样的时代的社会体系和价值体系都是指向政党的,观众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个人的私欲是不可以被宣泄的,当表现出真实的私欲时,是要被消灭的。不同于今时今日,个人的私欲是可以被宣泄的,比如出现了直播、炫富等。于是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真实的喜剧电影的,时代是不允许有“个体生命”的。在描述这些部分的时候,我们喜剧电影发展的路径和研究的路径,史的部分比较少,论的东西比较多,这时在我们创作的时候,要发挥充分的思考——在生产的语境里,如何实操。
创作的时候,进行一定的社会学研究,看看它的形态是什么样子。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研究喜剧电影,社会图景包括那个时代的空间、人类发展的样貌,对于中国整体叙事的描绘的角度。回看“文革”之后的40年,20世纪80年代或许是最开放的时代,是最多元的时代。现在都是政治化的价值观,趋于统一的价值观。社会图景的多元化反过来就是中国喜剧电影已经匮乏。中国喜剧电影,尤其是农村喜剧电影的匮乏。今天的中国电影观众和电视剧观众,谁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中坚部分?社会图景在不断变化,影像展示出来的社会图景和真实社会图景的契合度都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时候一些避不开的名词。《喜盈门》从观众学的角度上,讲述了“私”的部分,影片中有关于养老的问题——这是规定型观众。
四、躁动的探寻
(一)国产城市喜剧电影
城市喜剧发展比农村喜剧发展晚的原因是城市并未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而快速发展,仍处于相当一部分时期的共同生命体的意识。1984年的城市改革,带来城市发展的变革,才使得城市的生命个体的意识。《今天我休息》中的马天明没有生命个体的价值,高度的城市生活的计划、秩序开始松动。松动的程度(改革)表现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城市中政企不分、平均主义城市国企还是老的体制,影响企业自主权。
1984年的政治背景是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2)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这个提法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做了铺垫。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作为一个虚拟主体,他掌握着所有的生产资料。1984年之前我们是不敢提商品经济的口号的,今天要么谈市场经济,要么说商品经济是有碍于生产的发展的。那个时代我们必须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是从一步一步的规定选择秩序走到了自动选择秩序。当超级的政治权威消失的时候,每个生命个体就不彷徨了吗?这些问题都准确地被80年代的作者捕获,因为那个时代产生了新的观影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生命焦虑——新生群体:待业青年(3)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高中毕业的国有企业子弟不再分配工作,大批不能继续接受教育的中学毕业生等待分配就业。。
经济的改革,社会价值认同的多元。70年代末期的农村,1984年的城市,错误经济模式的结束。对于经济状态的认知在极端的大一统当中游荡。民国时期30年代的货币改革到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崩溃都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分裂的经济体必然带来政治统一体的大崩溃。70年代末期,经过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整合的统一经济体日渐暴露出生命的衰弱性:50年代的公私合营到国营公立的统一性问题,经济上的分裂承认经济个体在政治层面的合法性。
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经济的活力,进入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庞大的私营经济个体成为新的话语体系的话语权的描述:由新生权贵进入政治权贵。80年代的文化热(4)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思想基调有两个,一是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二是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第一个基调突出的不是单纯承接“五四”传统,也不是激进主义思潮发作,而是借用当时中共高层认可的“肃清封建专制流毒”的定向。和新的社会价值多元相互碰撞,产生了许多作品,讲的是城市边缘人,讲的是统一体中的游子。每一个人都牢牢成为经济的序列基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到价值认同到文化走向的大讨论。
90年代初的中国喜剧电影伴随着大解构的进程。1989年之后的13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在中国电影的生产中出现了两大倾向:
一是意识形态的重建需要复习国家的苦难史,才能消灭分歧,在苦难史中营造共同的美好回忆,这时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的红色作品(5)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周恩来》《焦裕禄》等作品。。
二是世俗的自我放逐: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社会成员实现“政治人”到“经济人”的转变。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不再是传统的高度计划、统一配额,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竞价的意识)、合拍片的胜利(6)这一阶段票房大卖的作品有:《新龙门客栈》(1992)、《新少林五祖》(1994)等。、电视喜剧的兴起(7)90年代出现了《我爱我家》等大型电视情境喜剧。等都深刻影响了国产喜剧的形态。
(二)“我”的时代:国产喜剧电影的“作者化”
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是民主意识觉醒的前史,而“前史的前史”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社会实践运动的失败以及对外关系的解冻。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有着思想文化的交流。所有的共同体想象都是建筑于社会、思想意识的防火墙之内的。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带来的是思想文化、艺术的探讨。比如传统戏剧(如话剧)走向了“无场次话剧”,这些变化意味着志士被解体,在表达形式上,不再是线性的现实主义。线性的现实主义被击破,意味着更加复杂的象征主义的探讨。
作者化时代意味着创作中越来越看重生命体的价值。1949年《三毛流浪记》呈现的是造反有理,所有的安逸生活都是可耻的。20世纪90年代的《三毛从军记》故事借用的是抗战史,描述抗战史的时候与之前所有抗战影片描绘的抗战英雄是不一样的,是意义的解构。在统一体想象时期,在创作的“去作者化”时期,讲述的都是意义的建构。在解构时期,当作者产生,所有的宏大意义是消失的。宏大历史是大家的共同想象,是大家试图找到一个体系去找到生命的放置。所有的情感和价值追求都是古典主义的方式。关于意义的价值,通过破坏获得幸福。在宏大历史想象中生命个体的消失是很可怕的。这是所谓作者化时代进入喜剧创作的非常沉重的状态。
(三)中国喜剧电影的娱乐化回归
在自我消解中的娱乐:娱乐是喜剧电影的共通法宝。进入到作者化时代的娱乐性和之前的差别是:70年代的“去我化”,80年代的“自我化”,90年代自我被消解、被解构。对当下的否定、将生命的意义建立在对于彼岸的畅想。一旦进入作者化时代,作者想要告诉我们当下的东西一定不是最好的东西,唤起观众对彼岸的畅想。走出政治神话,开始具体而微的社会实践。90年代的自我消解与90年代末期的大的社会危机有关:1995年经济衰败,1997年政府换届,在全国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减员增效”,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位数可观的下岗人员,整个经济大环境伴随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同步发生衰减。
在原有的经济体之下对其依附的人群,在经济结构日趋低效和崩溃的时候,人们找不到自身的位置,开始用娱乐的方式消解。《甲方乙方》有着作者清晰的“草根意识”,情感非常明确地向底层倾斜。作品呈现了小品化的叙事倾向:几个故事、段子的罗列,不再是经典喜剧的固定模式了。《三毛从军记》也是游戏化的累计、游戏拼贴。
社会的阶层对抗日益明显,我们看到了中国喜剧电影创作中的新元素:对欲望的消费。作者化时代统一体消失后进入到的肉身快感。肉身快感是一种关于肉身的强烈的消费,所有肉身之外的原来的大一统政治想象已经变成了一片虚无,肉身之外皆为虚无。只有肉身内部基于具体的消费格式,只有消费是可以被数量化的,是我们在宏大概念消失后,还能使用货币来换取快乐。欲望总是要被释放的,当欲望被具体消费时,关于爱情的消费,进入到肉身的消费,变成了可以进行任意的选择。消费欲望可以被进行数量化的计算,当情感可以数量化的时候,人们的人生都进入到了游戏模式。
这时的国产喜剧电影还呈现了“人生游戏”:高度假定性——对于肉身的消费是阶段性的,人生进入游戏模式的时候,充满了高度的假定性。对于欲望的本质,是今天的喜剧叙事的手段。这是作者时代喜剧的表现形式,今日的喜剧都是关于肉身快感的想象。对于爱情的捕捉变成假定性的梳理,男孩对于爱情的渴望也变成了基于肉身快感的想象。内地喜剧电影2007年才拍出《爱情呼叫转移》这样肉身快感消费的电影。
五、结 语
关于中国喜剧电影创作更大的解构方式是将武侠电影和悬疑元素融合起来的大杂烩,比如周星驰开始大量地学习和使用这样的方法。整个中国喜剧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今天做电影的那些可能性中,任何创作手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有大的发展阶段和大的统一路径,背后是需要关注观众群体的社会心理,以及具体而微的生命个体在各自时代的生命焦虑。周星驰的虚拟化的手法让我们感到很快乐,外部世界的生存方法造成我们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是润物细无声的。
如今,信息不再仅仅通过纸媒、广播、电视台传播了,任何一条信息都有可能崩溃一个体系。对于信息的解读是实现共通文化的想象,一种理念一统天下的时代不再了,便注定引起“江湖混乱”。今天的信息不再是大一统的信息,信息的传播也不再是大一统的方式,当价值观多元的时候,如何产生共识。此时此刻的政治命运时代,文化倾向的多元、信息爆炸化,宏大的经典叙事是要被消解的,碎片化的短小叙事是要被建立的——这是我们当下喜剧的倾向。
碎片化的叙事中将人物的种种欲望肢解,未来VR技术作用到人类的叙事手段当中,这为我们继续电影创作制造了一个新的命题,完全会是一个难以预见的新的时代,我们不应贸然反对任何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