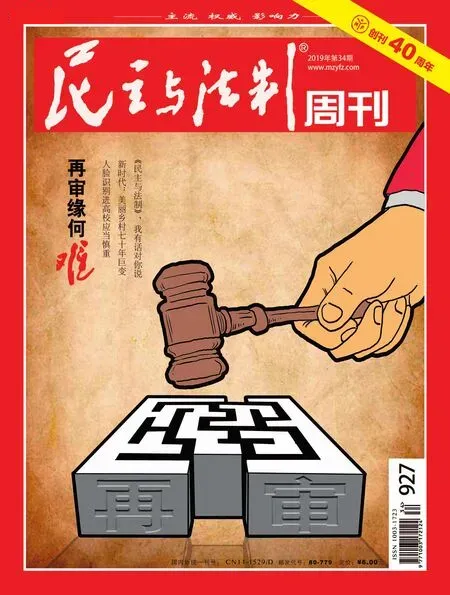冤案平反:再审缘何步履维艰
本社记者 李蒙
十八大以后中国平反了不少冤错案,每一个冤错案件的平反都很艰难。但之前更多难在启动再审程序,亦即从当事人角度而言的“申诉难”。
像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都是如此,申诉往往持续了十年二十年,而只要启动了再审程序,“再审即平反”,接下来的审理和判决并不难,时间也不会太长。
的确,从2013年张辉张高平案平反开始,直到2016年聂树斌被宣判无罪,虽有个别案件严重超审限,但大多数案件还是可以在6个月审理期限内审理完毕,作出判决。
2017年之后,突破审限延期审理的案件越来越多,能够在6个月内审结的反而成了少数。直到出现李玉前案这样延期审理了三年法院却意欲中止审理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担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指出了导致再审难的一些制度缺陷和人为因素。
判决稳定性需求和审理难度大等客观因素
张建伟教授指出,再审难有其诉讼机制原因。诉讼案件一旦形成确定判决,就形成既判力。裁判一旦作出并且生效,应当保持稳定,不容许随意改变。诉讼本为某一社会关系发生紊乱而发生,裁判则具有以和平形式稳定业已发生紊乱的社会关系的作用。要达到这一目的,裁判生效后须具有稳定性,否则会使已经稳定了的社会关系重新陷入不稳定状态。裁判的这种稳定性具有程序正义的性质,没有这种稳定性,权利就失去了切实的保障。
不过,判决的稳定性不能绝对化,裁判有可能是错误的,对于错误的裁判,不能仅为了判决的稳定性而维持其不公正,如果是这样的话,权利同样不能切实得到保障。许多国家设置了对错误裁判的补救程序,其本意在此。
徐昕教授认为,再审案件很多高度疑难复杂,6个月的审限确实时间紧迫。而平反一起案件牵涉极大,法院必然慎之又慎。以聂树斌案为例,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再审中做了如下工作:合议庭审查了本案原审卷宗、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卷宗;赴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察看了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班路线、原审被告人聂树斌被抓获地点及其所供偷衣地点,询问了部分原办案人员和相关证人;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的审查判断咨询了刑侦技术专家,就有关程序问题征求了法学专家意见;先后5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依法保障其诉讼权利;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等等。
在一些案件中,法院还需要安抚被害人家属,依托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处理利益部门的博弈等。客观地讲,对于李玉前案一类的重大疑难案件,再审的工作量十分巨大,6个月内查清事实做出判决,确实是对法院的考验。此外,法院还面临审判监督人手不足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法院一般在启动再审前就经过了漫长的申诉复查阶段,又有原审阶段以及申诉阶段各方对案件提出的各类意见,案件的疑点、争议点早已明确,再审法院在再审程序中更多要做的是对相关意见的核查,对疑证的判断,对疑罪是否从无的取舍。就案论案,坚持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不应人为地扩大再审范围。
无罪标准被一再拔高,“疑罪从无”举步维艰
陈永生教授认为,重大冤错案件再审难,难在再审证明标准被无限拔高。其具体表现为:1.当事人申诉再审的条件被拔高为法院、检察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条件。
本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诉启动再审的条件与法院、检察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的条件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法院、检察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的条件较高,必须发现生效裁判在实体上“确有错误”;而当事人申诉启动再审的条件较低,大多并不要求达到证明原审裁判在实体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确有错误”的程度。
这样的不同标准之所以定出,是因为法院、检察院享有广泛的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和人、财、物力做支持,因而有能力在查清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再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而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能力非常有限,人、财、物资源也往往严重不足,如果要求当事人申诉启动再审也必须达到证明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程度,必然导致当事人申诉很难达到法定的标准,很难启动再审,严重影响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
然而,在我国实践中,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诉的案件,法院、检察院在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时,往往也要求当事人提出申诉的理由必须达到证明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程度,才启动再审;反之,即便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申诉达到了法定的申诉再审条件,但如果没有达到证明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程度,就拒不启动再审,以致当事人申诉很难启动再审。
2.法院改判无罪的证明标准从“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拔高为被告人确实无罪。
在刑事诉讼中,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因此,如果法院经再审,认定原审裁判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度,也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应当改判被告人无罪。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经过再审,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经过再审查清了案件事实,被告人确实无罪;二是经过再审,仍然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既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
本来,按照刑事诉讼法理以及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这两种情况下,法院都应当改判被告人无罪。然而,在我国实践中,法院往往仅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即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时才改判被告人无罪,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充分时,往往不愿改判被告人无罪。也即对疑罪,往往不愿按照疑罪从无规则,改判被告人无罪。在十八大召开以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只有“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才可能改判被告人无罪,因原审裁判认定有罪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极为罕见,原因即在于此。在十八大后,因原审裁判认定有罪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逐渐增加,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案件都经历了漫长的、艰辛的申诉,甚至抗争过程,也表明法院、检察院对疑罪案件普遍不愿启动再审改判无罪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
3.法院改判无罪的证明标准“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甚至被拔高为案件事实完全查清,乃至“真凶出现”“亡者归来”。
实践中,不仅对疑罪案件法院普遍不愿改判无罪,对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实无罪的案件,如果该案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只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不是被告人所为,那么不少法院还经常要求能够查清犯罪事实到底是谁所为,也即查明真凶,否则,他们也不愿改判被告人无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犯罪确已发生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改判原案被告人无罪,而又没有查明真凶,将面临来自被害人以及社会公众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如果是“命案”,由于公安系统有“命案必破”的要求,法院、检察院还可能受到来自公安机关的压力。
徐昕教授指出,我国刑事诉讼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始终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究其本质,实事求是就是追求绝对的实体公正,这对再审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影响深远,导致疑罪从无理念的缺失。十八大之后的很多冤错案件都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而改判无罪,说明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已然彰显。但不少案件再审艰难,刘忠林案审了6年,开完庭两年未宣判,吉林高院在纠结、犹豫什么呢?自然是担心错放,担心万一刘忠林是真凶怎么办?贵州高院同样是在担心李玉前是真凶怎么办?这种担心自然会拔高改判标准。
审限缺失刚性约束 应当立法回避自错自纠
所有久拖不决的再审案件,都严重超审限。如张志超案,已经6次延期,长达两年多,还不知道要延期多久。像廖海军案、刘忠林案、徐辉案这样延期长达9年、6年的案件,都表明最高法院同意省级法院延长审限基本上是无限期的,只要申请就会批准。如此一来,6个月的审限设置实际上形同虚设,可以无限延长。如果不进行一定的刚性约束,不建立起法院系统有关审限的奖惩机制,再审案件久拖不决就会成为常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律师指出,我国平反冤错案的制度安排有问题,对申诉、再审的审查制度安排有问题。我们基本上是两种模式启动再审:一是法院决定再审,二是上级检察院启动抗诉。基本上自错自纠,体制上肯定有问题,因为原审的公检法办案人员和案件本身产生了很强的利益关联,按照法理的规定,应该全部回避。而现在,要求他们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难度可想而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异地审查、异地审理,聂树斌案件开了头,但缺少法律依据。
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春丽指出,当初的案件承办人有的可能是刑讯逼供者、滥用职权者、枉法裁判者,一旦开庭再审,当年办案过程中的违法甚或犯罪行为便会昭然于天下。尽管时隔多年,然迄今有的领导还在位(至少影响力还在),有的承办人员也已经晋升为领导了,身居高位要职的更是不乏其人,各方面带来的压力都非常大。掌权者、在位者,都会利用手中权力和影响力穷尽一切手段阻挠再审。理由很简单,谁都不愿为冤错案件担责,更害怕被追责。如果制度设计上一定要由原审法院来启动再审程序,就很难避免冤案制造者对再审的干扰。所以,急需建立脱离原审法院系统的冤案复查审理机制。
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认识分歧
张建伟教授指出,对于案件生效裁判是否确实存在错误,不同的司法机关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大体有两种情况较为常见:一是上级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对于案件的认识与上级法院存在分歧,案件审判工作就可能延宕下来,其中包含下级向上级请示与上级法院研究决定,都可能使案件节奏放缓乃至久拖不决;二是由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案件因此迟迟不能开庭审理,有的开庭之后法院迟迟不作出判决,或者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检察院再度抗诉,案件在法院维持原判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拉锯战中久拖不决。
在十八大以后相当多平反的冤错案中,如果是检察机关抗诉或者提出再审建议的,平反起来相对就比较容易。反之,如果检察机关对平反这个案件不太积极,法院的压力就比较大,往往会“耐心”等待检察机关的态度转变。比如,同样是吉林高院平反的刘吉强案和刘忠林案,检察机关对刘吉强案态度明确,再审就比较顺畅。对刘忠林案态度不太鲜明,法院就一直拖延审理,一拖就是六年。
再比如张志超案,最初是由山东省检察院启动复查的,无疑检察机关对平反此案应该是比较积极的。后来不知何故,久拖不决,移交给最高法院审查。最高法院指令山东再审后,山东高院态度比较积极,山东检察院反而一直“没有准备好”,导致该案迟迟难以开庭。
而贵州唐昌华案又是一个反例。据唐昌华的申诉代理律师周立新介绍,2017年2月,贵州省检察院告知该案代理律师,他们已经向贵州省高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并告知律师,经省检一年来所作的复查取得的证据,比律师提交的证据更充分、更有说服力。2017年12月上旬,代理律师到贵州省高级法院联系,本案承办人和立案庭负责人告知,该案将在2017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作出结论,会给律师一个惊喜。
但贵州高院一直拖延到2018年11月才作出审查决定,竟然是代理律师没有想到的“不立案再审决定”,给律师的不是“惊喜”而是“惊讶”。之后,贵州省检察院告知该案代理律师:本院经向贵州省高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在贵州省高级法院经复查作出“不立案再审决定”后,本院的申诉复查程序已经终结,如果不服,请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
害怕追责导致的官僚主义和司法腐败
张建伟教授指出,再审意味着原来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相关政法系统及其原参与办案的人员的形象和仕途前程可能大受影响,原来造成错案的责任人员可能要被追责,因此出于讳疾忌医、上下包庇的考虑,为再审的审判添加阻力。此外,案件相关人员出于种种考虑,提供伪证、错误鉴定等等,为再审改判增加了变数和阴影,导致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从而使案件的审判延宕下来。
张建伟指出,司法机关的官僚主义恶习本身就有办事效率低的特性,表现为推诿扯皮。在官场,“拖”字诀有许多妙用,因此,在一些场合工作效率不高是常见现象,司法机关也不例外。
杨学林律师代理的广东“黄立怡票据诈骗案”,2004年开始代理申诉,2005年广东高院就决定再审了,可是一直拖到2010年才开庭,从决定再审到开庭经过了五年时间。在杨学林与主办法官数不清的电话联系中,拖延庭审的理由有如下这些:一是调卷;二是法官被借调;三是换了书记员;四是黄立怡被送往新疆监狱,法官无法提审;五是北京开奥运会,啥也不能干;六是发回到广州中院重审;七是在哪儿开庭要交涉。每件事情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光调卷就调了一年。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和律师都心急如焚,也只能熬着。
王春丽副教授指出,既往刑事司法的实践和经验证明,几十年来,中国的不少刑事法官习惯了庭审走过场,习惯了先定案后审判,或曰先判后审;习惯了拿到案件事先掂量掂量,习惯了去考量案内案外所涉的人和事、各种所谓错综复杂的关系或影响因素,而习惯性忽略对事实的认真探查和证据规则的审慎运用;甚至习惯了不把被告人当回事,不把被告人事实上的罪与非罪乃至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回事,侦查人员侦查的、检察官公诉的甚或法官办理的,只不过是案件而已!
尽管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已经实施数年,但在司法人员的思维调整和理念更新层面更需深化,司法文化的建设明显滞后,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模式亟待优化和提升。尤其是所谓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始终实质性地潜伏于司法中枢系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使得权责本就不清的权力运行惯性与司法责任制的理性要求总是呈悖论式存在,正式法律制度建构起来的司法决策系统功能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或许才是造成再审难的根本原因。
(张建伟、陈永生、徐昕均对本文有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