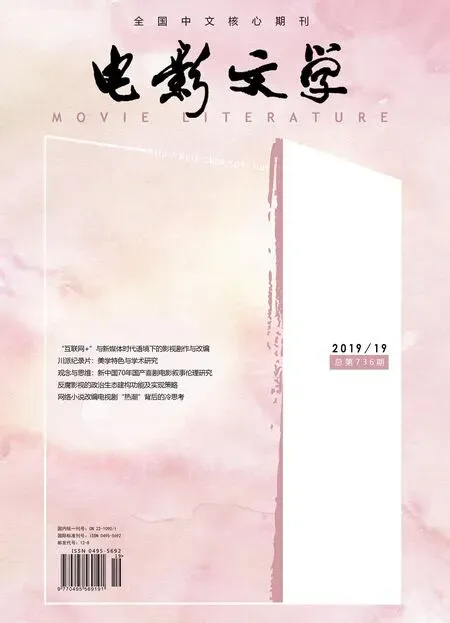80年代王朔电影叙事伦理批评
赵文国
(山西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1988年在电影史上被称为“王朔电影年”。是年,王朔的三部小说被搬上了银幕,分别是黄建新的《轮回》(王朔小说《浮出水面》改编)、米家山的《顽主》(王朔小说《顽主》改编)、叶大鹰的《大喘气》(王朔小说《橡皮人》改编)。
1989年,夏钢将王朔的小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也搬上了银幕。关于王朔电影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本文尝试从叙事伦理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王朔电影进行评析。
一、亵神的幽默(1)“亵神的幽默”语出刘小枫。刘小枫在论述米兰·昆德拉时,称其小说继承了拉伯雷小说的幽默叙事,通过“幽默叙事吊销了道德归罪的法权”。详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178.
中国社会曾经走过一段特殊的历程:一个人的脑袋控制着十几亿人的脑袋和身体、目标只有一个(解放全人类)、事业仅有一项(革命)、书籍只有几本、电影仅有几部、衣服只有两套(中山装与军装)、话语仅有一种(革命)、越穷越光荣……当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被欺骗、被利用而青春已逝时,心中的错愕、恼怒、怨恨、绝望可想而知。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在处理这些关系,如血泪控诉的伤痕电影、“娘亲错打孩子”的谢晋政治伦理电影、忘记过去向前看的改革电影、向往现代深入传统的农村电影等。这些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将电影从作为政治工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修复抑或遮盖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但正如戴锦华女士所说:“他们(第四代导演)的生活与历史充塞着社会生活的大事件,他们的个性无法消除整齐划一的社会构形,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时代规定,他们的遭遇只能是历史的遭遇。他们渴望讲述自己,结果都只是讲述了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们希望去记述独特而畸变的个人命运,却只能记述一段独特而畸变的历史。……这也是一次逃脱中的落网。”[1]简单讲,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电影依然难以表达独特的个人命运。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表达个人成为可能,但如何表达是个问题。王朔以“亵神”的方式适逢其时地出场了,这里的“神”泛指一切僵化的、抽象的价值观念。在影片《顽主》中,这种“亵神”通过情节设计、语言对白、影像展示多层次进行表达。
于观、杨重、马青三人(《顽主》主人公)经营一家3T公司,公司承办的业务是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影片中,三人主要承办了三件事情:一是替肛肠科大夫与女朋友谈恋爱;二是给沽名钓誉的作家宝康发奖;三是替病人家属照顾生病老人。肛肠科大夫没时间和女朋友约会时,杨重出场了:遵守“替人排忧不动感情”的职业道德,讲哲学、谈弗洛伊德;肛肠科大夫想要甩掉女友时,于观出场了:买酸奶、逗乐子、安慰情绪,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当病人家属不愿照顾生病老人时,于观、杨重、马青三人轮流值班,精心照料,不料老人去世,三人反遭老人家属起诉以致公司停业整顿。更荒唐的是,作家宝康希望获奖,3T公司积极筹办,租用了豪华的颁奖场所,购置“大号”奖杯,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参会,请来表演团体助兴,然后,冒牌领导讲话,冒牌作家代表发言,宝康发表声泪俱下的获奖感言;发奖大会中场,表演团队上场助兴:京剧演员、时装模特、地主老财、变脸演员、革命青年、农民、红卫兵、解放军战士、霹雳舞演员、国民党败兵、比基尼、军阀……在闪烁的灯光下相互致意、嬉戏调情,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在重金属的摇滚音乐中顷刻失去了重量。特别是葛优扮演的领导在颁奖会上的讲话,既深沉庄重又言之无物,既拿腔捏调又恰到好处,使得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距离消失、身份互换以致互渗,讽刺效果极佳。
顽主们“亵神”的另一有力武器是通过语言的反讽、戏仿、类比等,将高雅的事情“俗”着说,将庸俗的事情“雅”着说,“一点儿正经没有”。试举几例:
杨重给一个手淫患者治疗,说道:“不要过早上床,熬不住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鳄鱼。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
马青:“我也觉得特空虚,结婚特没劲,找来找去不是找来自己爹就是自己妈。哪像人家外国啊,谁跟谁都能睡觉。人家也方便都有房子,你自个儿有房子吗?家里老有人吧。我就特佩服人家外国女的,睡完就完,而且无论怎么睡也不扭着男的胳膊买这买那。”
侯耀文饰演的侃爷:“你对目前世界上这情况可能不大了解,无产阶级队伍人民少,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这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吗?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你看外国人那肚子。”
……
在这些忍俊不禁的台词对白中,所有曾经神圣的、崇高的、理想的、政治的、禁忌的词语都在顽主们一泻千里的调侃中被解构。正如王蒙所说:“他(王朔)把各种语言——严肃的与调侃的,优雅的与粗鄙的,悲伤的与喜悦的——拉到同一水平线上。”[2]从而实现对旧有僵化价值的戏谑、嘲弄与消解。
在影像展示上,《顽主》也极具意味。影片一开始就展示了一个混杂的现代世界。拥挤的车流、不断建设的高楼、农民的脸庞、交警的指挥手势、文身的青年、劳务市场的广告、老外、穿文化衫的青年……加上毛主席纪念堂前不断播放“要求身份证工作证单位介绍信”的声音与黄土高坡歌声的嘶吼,“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秩序与混乱、农民与老外、拥挤与闲适、革命与欲望、崇高与卑微、世俗与神圣在镜头的快速组合中被搅和在一起,分不清也道不明。
《顽主》正是通过情节设计、语言戏谑、影像展示等方面不断消解着旧有的价值与理想。毫无疑问,王朔的顽主们是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下人与人,特别是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体户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就是这种关系变化的反映。当摆脱国家、集体对个人的束缚后,个人急需寻找新的价值与意义,而囿于自身的学识、社会经济地位、游移不定的身份、市民社会不发达等原因,这种意义的寻求遂成为“意义的焦虑”,进而沦落为对一切意义与价值的虚无——游戏人生,玩世不恭,顽主们就是这种个人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僵化价值观念“腐而不朽”,虽落后、保守与虚伪的面貌已然显露,然余威犹存,顽主们戏谑式的“亵神”实际上是一种虽显无奈但最少危险性的话语策略。
二、要求平庸(非崇高)的权利
赵尧舜:“你们平常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马青:“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玩玩牌,要不然就睡觉。”
赵尧舜:“找些书看看吧。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啊。”
马青:“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
赵尧舜:“烦恼太多不是什么好事,可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好,不成了白痴了嘛。不看书就多交几个朋友,不要老局限在你们那个小圈子里头,有的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使人获益匪浅。”
这是《顽主》中德育教授赵尧舜教育于观三人时的一段对话。马青的话真实地表达了顽主们的想法。
如果马青只是“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玩玩牌,要不然就睡觉”的话,石岜(《轮回》男主)、张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男主)则更庸俗,且真诚地承认自己的庸俗。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张明平时通过假冒警察敲诈嫖客挣点钱,然后就是搭讪女孩、吃喝玩乐。在公园里偶遇大学生吴迪,搭讪、言语挑逗、自轻自贱。看看张明的自报家门:“我和一百多个女人睡过觉。我是个劳改犯。我要是你男朋友啊,我就敢和你睡觉。我贪财、好色、道德沦丧。”在家中张明对吴迪唱:“最大的人民币是一百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人民群众热爱的。”张明将吴迪追求到手后,又想法甩掉,这导致了吴迪的沉沦以致最后自杀。后来因敲诈嫖客,张明被公安人员逮捕,刑满释放后,良心发现,悔恨难止。一次外出散心时,张明在海边偶遇胡亦,尽管胡亦各种投怀送抱,但张明不为心动,并教训了欺侮胡亦的两个流氓作家。
《轮回》一开始就是石岜百无聊赖地在商场步梯上上下滑动,然后无所目的挤上地铁,盯上美丽的舞蹈演员于晶,偶然相识之后,插科打诨,油嘴滑舌。石岜通过关系(私盖公章)搞点钱,然后就是各种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后来,石岜遭到黑社会的敲诈,并被对方用电钻“钻”断一条腿。伤残后的石岜因为自尊,不愿再与于晶来往,通过各种方式打发于晶,但于晶始终无法放弃石岜,两人结婚。婚后的生活琐碎、平淡、争吵,终于在一个晚上,石岜跳楼自杀。不久,于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石小岜,影片结束。
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邵牧君先生直呼其为“痞子”,并认为其有四个特征:“一、文化水平低;二、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三、游戏人生,享乐至上;四、蔑视既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3]
然而无论是《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还是《轮回》,都通过叙事赋予这些“痞子”一种价值。
《顽主》通过真/假的二元对立,将于观们置于“真人”一端,而将道貌岸然的德育教授赵尧舜、薄情寡义的“屁眼养护专家”王明水、沽名钓誉的作家宝康,还有不尽孝道的知识分子等置于“假”的一端,在真与假的二元对立中,于观们被赋予了“真诚”价值。《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则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不断通过画外音表达张明的心理感受,从而影响观众对其伦理判断;在情节设计上,影片将张明与吴迪的相遇,同张明与胡亦的相遇进行对比:大致相同的相遇环境,大致相同的对话,但因张明的心境不同,结果不同。吴迪因张明的玩弄而沉沦以至于自杀,但胡亦因张明的守护而得以自我拯救。也就是说,影片后半段张明的忏悔使得前半段的“犯罪”变得可以接受,而且通过叙事时间的安排,将叙事的价值落在了张明的忏悔上,从而赋予其“人”的价值。《轮回》通过淡化情节的叙事试图进入石岜的内心世界,前半段石岜想要钱便得到钱,后半段想要于晶则得于晶,然而,当拥有了一切的时候,石岜却自杀了。影片中两次出现石岜粉刷房子的情景,一次是准备同于晶结婚时,一次是自杀前,通过红与黑的颜色变化,隐喻石岜的精神变化。石岜的自杀源自精神的不满与虚空,这种不满与虚空是现代人特有的:一边是“得到”之后的短暂兴奋,一边却是“失去”之后的漫漫长夜;一边是生存欲望的满足,一边却是理想的放逐。当物质(性)的满足使得精神虚空显得更为刺眼时,石岜的纵深一跃就获得了超出“痞子”行状的精神意义。
王朔电影文本本身赋予“痞子”们一种价值,其时的社会语境也为“痞子”们的价值提供了土壤。对于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走出“神话国”(2)“神话国”语出刘大任,主要指“政治弥赛亚”:以“创造完美社会、创造新人类为最终目的”的“极权主义”。这种政治弥赛亚高举一套乌托邦式的人类完美境界为鹄的,以狂热的理想主义为号召,以“历史的巨流”作为证据,以动员、组织、控制为手段,要求的对象,则是渴望投身到一种强烈的信仰中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救赎需要的群众。详见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景里的政治伦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8.之后,人们很难迅速建立一套坚固的信仰、价值与理想系统,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的激烈争锋正是理想放逐之后价值迷茫的表现。激情与焦虑同生,迷茫与真诚共进,虽“生气淋漓”,但“众生喧哗、泥沙俱下”(陈平原语),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大潮奔涌而至,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原子化的个人开始显现,而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并没有为这种原子化的个人提供更多的价值依据,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痞子”的出现自然能够得到部分认同。
王朔的“痞子”们试图表达一种个人价值,这种价值无关崇高、理想、信念、信仰、忠诚,只关个人“幸福”。换句话说,王朔电影将电影从事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转移到事关个人“幸福”的小叙事,将过去对电影教化功能的过分强调转移到电影的娱乐功能上来。
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在论述大众时代的特征时说过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4]套用奥尔特加的话来说,王朔电影的“痞子”们就是要求平庸(非崇高)的权利。用王朔更为激进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三、过度浪漫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价值观、一种对“人”的解释与设定,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按照英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的说法,个人主义至少包含以下基本观念: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抽象的个人、政治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在这些基本概念和学说存在着“有趣的和复杂的逻辑或概念关系”,其中“上述个人主义的前四个单元观念——人的尊严、自主、隐私和自我发展——是平等和自由思想中的基本要素”[5]115。王朔电影的“痞子”们试图建立一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电影叙事中通过人物身份设计、对白等进行表达。
王朔电影中的“痞子”几乎都是脱离家庭、社会网络的个人,无论是《顽主》中的于观、杨重、马青,还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以及《轮回》中的石岜、《大喘气》中的丁健,都是如此。如下表所列:
上表中,除于观外,其余人物在故事中均无父母(或无交代),而于观的父亲在影片中恰恰是作为儿子反叛的对象出现的;除石岜外,其余人物均无配偶,而石岜的妻子于晶恰恰是导致石岜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工作单位与职业,按当时的社会语境,影片中所有的人物都可看作无正当职业、自谋发展自谋出路的个体户或待业青年。
影片设置这群痞子脱离“伦理本位”(梁漱溟语),意义有二:其一,“痞子”们对固有价值观念的戏谑与消解,不会引起观众“恶”的伦理判断。在观众眼里,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群不学无术、东游西逛、喜欢享乐的社会青年。学者陈垦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不是社会的宠儿,但也绝不是渣滓。他们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丰腴的物质财富,但他们更没有这方面的奢求。崇高的理想对他们没有诱惑力,正统的道德规范对他们也没有约束力。在失控而且变形的世界里,色彩怪谲,气氛荒诞,地平线倾斜,向心力紊乱,他们自以为把握了生活的真谛,凭着本能与冲动,放浪形骸,游戏人生,活得荒唐而且充实。”[6]其二,脱离伦理位置的“痞子”们,极有可能表达一套个人主义的话语。影片《顽主》中,于观与父亲有一段对话:
父亲:坐下,我要给你谈谈……严肃点!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于观:吃、喝、说话、睡觉,跟你一样,偶尔拿拿大顶。
父亲:不许你用无赖腔跟老子说话,我很为你担心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想想将来了,该想想怎么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于观:……我怎么就那么不顺您的眼哪,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没上街游行去,您说我乖乖的招谁惹谁了?非得绑一块,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哪?累不累啊?我就不庸俗点嘛!
父亲的严肃形象在于观的戏谑调侃中变得迂腐可笑起来。明显地,于观的个人主义表达挑战了父亲所代表的旧有价值观念。
如果说于观的表达还显迂回的话,石岜则直接多了。石岜对于晶说:“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整天用嘴侃大山不止,现在这世道,只能自个顾自个,可是我不自私,你们也看到了,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那些不危及公共秩序的私事。”于晶问道:“什么事能跟大家一点关系也没有?”石岜:“比如说,我上床洗不洗脚,吃不吃羊肉,再严重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对吴迪也有几近相同的说法:“都认得字,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管得着人家吗?”
无论个人主义有多少条理路与诉求,尊重人的自主选择、隐私与自我发展都是个人主义的核心要件。于观、张明等人的戏谑戳中了个人主义的核心,即“不受‘公众’干预的最低限度的‘私人’领域是自由理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118。
然而,个人主义的表达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胜利。影片一方面通过人物伦理身份设置、台词对白表达着个人主义的信念,一方面在情节安排、结尾设计中消解着这种个人主义表达。首先,在王朔电影中,几乎都有一个纯情女孩的形象,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轮回》中的于晶、《大喘气》中的张露等,这些纯情女孩都承担着拯救者的角色,换句话说,以往电影中由革命者、老干部承担的角色在王朔电影中被纯情女孩所替代,“痞子”们只有在纯情女孩的拯救中才能拥有现代个人意识。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为例,影片前半段以张明偶遇吴迪始,以吴迪自杀终;后半段是几近相同的安排:以张明胡亦偶遇始,以胡亦被拯救终。如果说前半段的张明是一个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蔑视法纪、嘲讽一切的个人主义者,后半段的张明则是在忏悔中回归的个人,至于这种个人能走多远,影片没有交代,只是让张明教训了两个欺侮胡亦的流氓作家而结束。也就是说,纯情女孩吴迪的死造成了张明对曾经“个人主义”的怀疑与忏悔,从而使其重新选择人生价值与方向,当然,最有可能的选择就是回归社会规定的轨道上来。其他三部影片都有几乎相同的结构。
其次,四部王朔影片闭锁式的结构也不断消解着影片个人主义的表达。《顽主》以于观、杨重、马青三人坑蒙拐骗、嬉戏玩闹始,以诚实守信、沉重无奈终:3T公司被病人家属起诉停业整顿,面对无理取闹的病人家属,于观三人诚实守信;面对公司门前排起的顾客长龙,于观三人再也没有“痞子”的潇洒,反倒沉重无奈起来。《大喘气》中当丁健知道李白玲等人对他的欺骗与利用后,所有当初“痞子”样的潇洒都变成了一块伤疤,贴在了李白玲与他自己的身上,最后,无法面对“橡皮人”的丁健骑着摩托车从楼顶飞出去了。《轮回》中的石岜,通过倒卖政府公文挣了钱,又得到了美丽漂亮的舞蹈演员于晶,当一切似乎趋于正常的时候,石岜却从楼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详见下表:
很明显,王朔电影的结构不断消解着人物的个人主义表达。一边是嘲讽一切、蔑视权威、玩世不恭、享乐人生,一边却是自救忏悔、想要回归、沉重无力、消解个人,这是一种过于浪漫的个人主义,王一川教授称之为“王朔主义”;“所谓王朔主义,是指通过王朔的作品和其他媒介行为呈现出来的以调侃去想象的反叛又缅怀权威、破坏规矩又自我扯平、标举又消解个人主义的精神。”[7]造成这种过度浪漫个人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众多论者所说的“王朔失落的大院子弟身份”“新旧文化之间的断裂”等,但笔者更愿意强调的是,“痞子”们的个人主义一开始就找错了靶子——价值权威主义。正如前文所说,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伦理诉求,它还要求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支持、个人伦理自觉。“痞子”们认为只要消解了旧有价值观念就会实现个人主义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过于浪漫了,更要紧的是,消解旧有价值观念之后呢?“痞子”们从来未曾想过,因而陷入更大的惶恐与焦虑中。
四、结 语
20世纪80年代的王朔电影通过语言反讽、影像展示、痞子形象塑造等方式表达个人主义的伦理诉求,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情节上纯情女孩拯救者形象、闭合式的故事结局设计使得王朔电影陷入叙事价值的冲突:一方面是嘲讽一切价值,消解一切意义,一方面却在寻找新的权威;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彰显,一方面却是个人主义的彻底失败。这种分裂的个人主义叙事在表达启蒙的同时也消解着启蒙,在言说个人的同时也遮蔽个人,最终陷入价值混乱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