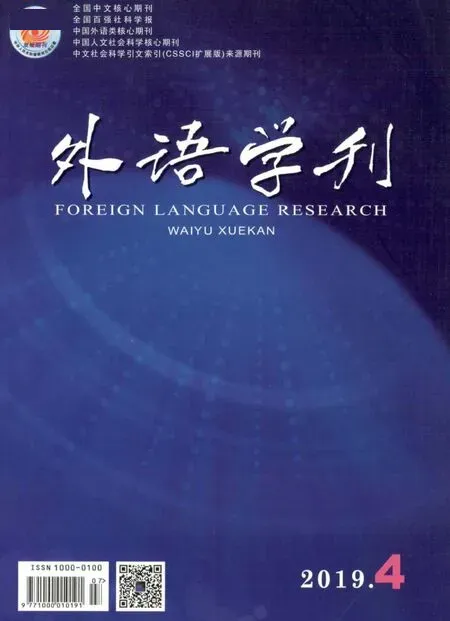译介学中的“译”与“介”∗
周 彦
(广西民族大学,南宁 530006)
提 要:译介学以相对独立的面貌出现在学界已有20年,译介学原本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与翻译研究也有天然的渊源。随着译介学的发展壮大,其自身的特点也愈加凸显。译介学的核心术语“译介”不仅是对比较文学译介学中最初概念的发展、扩充和超越,也是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相关概念的超越。对这个中心术语的剖析可明晰译介学自身独特的研究特点、对象、范畴等,更可以牢固地树立译介学自身的独特形象。
1 引言
译介学原本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一个分支的分支,是影响研究媒介学中的一个分支,是比较文学中一个“没有比较”的研究领域(谢天振1991:95)。查明建认为,“‘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术语是中国学者的发明”(查明建2005:41),自20世纪80年代始,“译介学”一词便出现在比较文学学者的著述中,如孙景尧、乐黛云、卢康华、陈惇、刘象愚、谢天振等都在各自的比较文学著述中对译介学的定义、实质、研究方法等有专门的界定,或专题或专章论述(卢康华 孙景尧1984,乐黛云1988,陈惇 孙景尧 谢天振1997)。不过,在上述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著述中,译介学大多只是定义界定,都是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被界说、被辗转研究。直到80年代末,随着谢天振的一系列论文和《译介学》专著的问世,译介学才开始在比较文学领域独辟一块领地,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
译介学从比较文学这个“娘胎”里一出世,便得到翻译界的青睐,这并不奇怪,因为译介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翻译,只是与传统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传统翻译研究关注的翻译主要是语言层面的转换问题,其出发点、研究重心和归宿点都是翻译,而在比较文学译介学中,翻译最初只是媒介,其目的是探讨两种不同文学文化的关系。比较文学译介学在翻译研究领域也激起涟漪,这正说明译介学的跨学科特点,而恰恰是这样的跨学科特点才能促成比较文学译介学的独立面貌,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地。这样的独立面貌是伴随着《译介学》(1999)一书的出版而形成的。在该书出版之前,“译介学”一词虽在卢康华、孙景尧、刘象愚等学者的比较文学权威著述中提及过,但它只是偏居一隅,未成大势,可以说这些前辈学者们都走到译介学的门口,甚至叩响大门,但未把译介学推上显身的学术舞台。衍生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因其兼具翻译研究领域的某些特点,才逐渐在学界拥有相对独立的立足之地。译介学得以诞生和立足主要有这两个领域的根基和土壤,而译介学的创立者同样也须具备这两方面的学养背景。
许多学者从译介学的视域去探讨翻译、探讨翻译与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文化对作为媒介的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等的介入和操控,等等。然而,译介学以独立的面貌现世以来,在理论研究上还未有深入的进展,虽然关于译介学的定义、本质、范围、重要概念、研究方法等的讨论一度较为热烈,但也大多围绕或局限在《译介学》一书所框定的范围内,或支持、欢迎其学说,或反对、质疑其观点,或对谢天振译介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或理论进行辨析、探讨与补充(费小平2002,查明建2005)。有一些学者混淆译介学中的“译介”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翻译”,认为“如果从规范性角度对译介学进行界定的话的确很困难”,即便对其界定“也是名不副实”,“译介学的研究范围与传统翻译研究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并指出,“‘译’与‘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不可能把二者很明确地区分开来”(朱安博朱凌云2008:5)。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出发,探析译介学中最核心的概念“译”与“介”在比较文学领域中意义的延伸、变异和超越,并解析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译介的关系,尝试说明译介学中的“译”与“介”或“译介”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既能“分”也能“合”。
2 比较文学中的“译”与“介”
在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著作《比较文学导论》中,译介学一词出现在影响研究媒介学中的文字媒介部分,该书虽然只是概略地指出译介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译本研究的方法等,虽然并未对此概念做深入的阐释,但明确地使用译介学这一术语:“译本的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我们统称为译介学”(卢康华 孙景尧 1984:165)。其中的“译”和“介”实则有不同的含义,且“介”是放在译之前被界说的,并主要出现在“媒介”和“评介”之中,这两个词都以“介”为词根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意义。具体而言,“媒介”一词范围更大,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产生影响的“中介”、传播的“途径”,虽也包含“译”,但其范围远远超出“译”,它可以是个人媒介中的“媒介人”,也可以是环境媒介中的“团体或社会环境”(同上:160),也可以是文字,即文字媒介。“评介”一词则主要局限在文字媒介中,是文字媒介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字媒介“主要是评介文字和译本”(同上:165)。由此可知,此处的“介”与“译”是分离的,“介”是指“评介文字”,主要是刊物著述中“评介外国人和外国作品的文字”,而“译”主要指“译本”。显然,此处的“介”还不完全专属于译介学中的“介”,而是比较文学媒介学中的“介”,“译”则已然具有比较文学译介学中“译”的一些含义,它不仅指译本(研究),还包括与之相关的译者、文学翻译与文学作品的借鉴、翻译理论和翻译史(同上)。
在西方的比较文学著作中,还没有与译介学“相对应的词”(查明建2005:61),较早谈及比较文学中翻译研究的著述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该书第二部分关于比较文学媒介研究的第七章谈到译本与翻译者,该部分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译”:译本、翻译者、译本的完整性、准确性、译本之比较(梵·第根 1937:193-200),“介”一词只出现在“媒介”中,显然指作为中介、途径和方法的比较文学研究手段。
须指出的是,在最初的比较文学译介学或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中,“介”实则是中心、核心,是其全部的起点和终点,“介”贯穿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或译介学的开始、过程及结束,是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或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实质,而“译”则是其表象及研究路径。
3 译介学中的“译”与“介”
3.1 译介学中的“译”
“译”虽然在比较文学媒介学中及在最初的比较文学译介学中有所论述,但对这一概念的扩充、丰富、发展甚而超越是从谢天振的《译介学》开始。该书中“译”的内涵和外延都与上述中外比较文学著述中的界定有所不同,比之前者更明晰、丰富、深厚。从谢天振对译介学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比较文学专门著述中“译”的内涵与外延,“译”的概念部分已经不只是比较文学中文学翻译的译本、译者等,而是扩展到翻译的过程。他明确并具体地指出,译介学中“译”的研究对象包括两种语言转换(翻译)中 “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还把译介学中“译”(翻译)提升到对翻译在人类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探讨。不仅如此,在“译”的研究范畴方面,谢天振的《译介学》还把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误译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把与“译”相关的翻译文学研究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作为译介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所有这些都是对渊源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中“译”的充实、提升甚至超越,因此增强了译介学自身“译”的独特性。
译介学的第二部专著《翻译研究新视野》(谢天振2003)是《译介学》的“更新版”和“增补版”(谢天振2015:10),对“译”阐释和探讨的分量有所增加,且注入新的内容,尝试从理论层面上构建译介学的框架,并主张用与“介”相关联的理论范畴①来审视“译”的行为、活动和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比较文学视野中关于翻译研究的内容,也极大地提升了“译”的译介学独特性。
在《译介学导论》(2007)中,谢天振厘清了译介学中的翻译与传统意义上翻译的区别,并重申译介学自身领域中翻译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同上2007:6-16)。在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他明确指出,译介学研究的另一个缘起即是翻译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我的译介学研究的缘起”(同上 2011:111)。可见,译介学已不再仅仅是比较文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它也同样渊源于翻译研究领域。换言之,“译介”这一概念中“译”的成分增加了,它不仅源于比较文学媒介学中的译本和作者研究等,也源于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本身出发对翻译的探讨。在《隐身与现身》一书中,译介学被阐释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交汇和接壤”(同上2014:20),这样的命题更加凸显译介学的独立研究领域,译介学自身的“译”与“介”也更明晰,“译”拥有与“介”分庭抗争的独立领地:“所谓‘译介学’,它既有对‘译’即‘翻译’的研究,更有对‘介’即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和接受等问题的研究”(同上:21)。译介学“思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怎么译’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译’、为什么‘译这个国家、这个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个国家、那个作家的作品’……”(同上)。
译介学中的“译”与比较文学中最初的“译”已经不完全是同一个“译”了,那么传统翻译理论中的“译”是否与译介学的“译”有等同的意义呢?其实,在译介学(或比较文学)中的“译”诞生之时,此“译”就非彼“译”。前者关注的是语言间的转换本身,而后者关心的是语言间的转换结果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透过语言转换中的现象(失落、变形、增添等)去探讨“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的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同上 1999:1)。“译”即“翻译”的研究(同上2014:21),这里的翻译是加了引号的,它“不是简单的‘怎么译’”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译,为什么译这个而不译那个,为什么有些译作成为了经典而有些则不能……(同上)。换言之,普通意义上的“译”或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译”关心的是翻译过程、翻译技巧、方法和原则、翻译中语言转换的成败等,而译介学中的“译”聚焦的则是译者和译品及其翻译行为的缘起、传播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简言之,译介学中的“译”(翻译)侧重的是文化对翻译的操控。正因如此,在传统译论中被排斥的、不可取的“误译”,在译介学中则是一个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切点之一,也正因如此,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在译介学中极具研究价值,成为其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
笔者认为,译介学中的“译”有其相对独立的含义,它是比较文学中的“译本、译者”等意义的延伸和发展,与传统译论中的“翻译”有所不同。当然,译介学中的“译”也并非比较文学与传统译论中关于“翻译”定义的简单合成,正如谢天振所说,它是两个领域的交汇和接壤。不仅如此,它是两者交汇、接壤后产生的第三空间,有自己区别于比较文学和传统翻译研究领域新的、独立的领地。
3.2 译介学中的“介”
“介”在比较文学名目下有重要的意义,其地位超过“译”,那么在译介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里,“介”是否有自身的内涵呢?
关于“译介学”相关定义中的“介”,谢天振指出,“Medio⁃translatology这个词的前半部分意为‘媒介’‘中介’,英语中的‘媒介学’一词即为Me⁃diology”(谢天振 1999:2)。在译介学创立之初,脱胎于比较文学媒介学的“介”还主要依附于比较文学媒介学中的“媒介”“中介”的意义,谢天振本人对使用英文词缀“medio⁃”也并不是很满意,认为只是“勉强可以表达译介学的意思”(同上)。
比较文学媒介学中广泛意义的“媒介”或“中介”远不能涵盖译介学中“介”的涵义。译介学中的“介”虽然渊源于比较文学的“媒介”,但其内涵不止于此,它还是对翻译文学及媒介成果进行的研究,即考介翻译产品的影响和接受等,并把这样的现象呈现介绍给学者和读者,以此介说翻译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译介学不仅有“对‘译’即‘翻译’的研究,更有对‘介’即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和接受等问题的研究”(同上2014:21),这样的“介”已然明确地延伸并超越了比较文学的“介”,它不局限于比较文学媒介学中传播的媒介手段和途径,也不仅仅是对具体的国外作品和作家简单的评价、介绍,而是上升到“文学文化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和接受等问题”的层面,“介”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厘清译介学中的“介”与比较文学中的“介”的关联与不同,那么,译介学中的“介”是否与其另一个渊源即传统翻译研究领域有牵涉呢?从表面上看,笔者认为几乎无关联,并且笔者还未在传统译论或当代译学中查阅到“介”的专门释义,也没找到翻译概念中与“介”的直接关联。不过,确如一些学者所说,翻译研究中“译”的概念其实包含“介”(朱安博 朱凌云 2008:5),隐藏着“介”,因为翻译行为本身就是对外来语言文化的介绍。虽然“介”在翻译研究领域并没有单独的界说和释义,但它与翻译领域中的“译”并非毫无关联,只是不像比较文学中的“介”,从字面上到意义上都与译介学中的“介”关系密切。但是,即便翻译研究中隐含着“介”,也只是暗含着语言的交换或文化的传递,仅此而已;相反,译介学中的“介”则不同,它是翻译过程中的媒介、翻译作品的评介、译者的介绍、评说,甚至可以是原作者及原语文化的引入、引介,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原语诗学与译语诗学的跨界及碰撞等,其内涵与外延的广度和深度绝不是传统翻译研究中那个戴着面纱的“介”所能界定、介说的。
总之,译介学中的“介”已经不止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或“评介”,更非传统翻译研究领域中隐身的“介”,作为译介学中重要的概念,“介”在译介学中有自身独特的意蕴。“介”是对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研究,“介”也是对异质语言文学文化的介绍和引入,更是对通过翻译而引入的异质语言文学文化与本土语言文学文化交汇、交融的探析,进而从中窥探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这样一种跨文化活动对于人类文化传承的意义。
4 “译”与“介”的交融
本文对译介学的核心术语“译介”分而析之,目的是为明晰“译介”这一概念在译介学领域中具有的独特意义。在译介学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虽然“译”与“介”研究时有侧重,但“译介”也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于分割,而这也正是译介学中“译介”一词的独特性。
“翻译”从译介学的视角可定义为“翻译即跨文化交际”,这体现出译介学中翻译研究的特征,也正好说明“译”与“介”的交融(谢天振 2014:21)。从译介学的角度看,“翻译”即“译”,而“跨文化交际”则为“介”,因为“跨”和“介”都有处于两者之间的意义③,此处的“跨文化交际”可理解为“介”的具体内容,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间实现交流的目的,从这样的角度定义、探讨、研究翻译,就把“译”和“介”衔接、组合起来,进而使两者有所融合、交汇,构成“译介学”中“译介”一词的特征之一。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早就有译介学性质的、介于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之间的著述。譬如,被视为中国翻译理论之发轫的“文质之争”,不仅探究佛经翻译还谈及用以指导佛经翻译的哲学思想,用中国的孔子和老子之言来为其翻译思想做辩护,这就是译介的交融;再如,在《辨正论》中,隋彦琮不仅剖析道安翻译之得失(“五失本、三不易”),还纵论译者之“八备”,要求译者做到“不坠彼学”,“不眛此文”,要做好翻译中跨文化交际的准备,其所论翻译已包含译介融合的特色。又如,美国20世纪的作家及汉学家魏莎(G.Wimsatt)关于薛涛诗歌翻译和介绍的著作《芳水井》(A Well of Fragrant Waters,1945)很难归类于比较文学或是翻译研究领域,因为该书既有对薛涛生平的介绍,也有对薛涛诗歌的翻译,在每首译诗前还有对该译诗写作背景的介绍说明,此外还有对薛涛所处时代诗学和历史文化的挖掘。从该书的特点看,应归属于今天的译介学的范畴,且是“译”与“介”融于一书的典型例证;倘若有学者把此书作为研究对象,从译介学角度来探讨,就更是译介研究的交融,既要探讨诗歌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丢失、增补,文化意象的扭曲变形、误译的原因等“译”的方面,又要探讨该书作者是怎样去翻译介绍薛涛、书写中国文化等“介”的方面,而这“译介”两方面又常常是不可分的,因为书中的“译”是为了“介”,而“介”则促成魏莎对薛涛独特的“译”(翻译)。还如,一些汉学家对中国典籍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翻译,对原文的字字句句及其隐含意义都详尽地说明介绍④,这样的翻译方式其实已经是“译介”,是译介学译介方式的交融。
5 结束语
运用译介学自成一体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已有的或将有的介于比较文学和翻译领域之间的著述进行研究,可以拥有新的学术视域,取得新的学术成果,从而有助于从新的侧面探讨翻译和文学,探讨文学与文化,探讨“译介”或“译”“介”,等等。笔者认为,译介学有自身相对独特的领域,我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已为译介学的独立研究范式搭建起基本的理论框架,“完成了对译介学理论的基本建构”(谢天振2014:21),目前须要进一步明晰译介学的基本术语、概念、研究方法等,以丰富译介学框架中的各种理论,使其在理论构建上更加坚实、完善。
注释
①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角度,运用阐释学、结构主义和多元系统理论等对翻译进行审视,可以看成是对翻译的介说、对译本的阐释,属于“介”方面的内容。
②这里的“翻译”并非比较文学译介学中的“翻译”,而是与比较文学平行的翻译研究学科中的翻译。
③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的、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90页。
④例如,美国当代学者大卫·席勒(D.Schiller)翻译的《论语》(2015)长达1500多页,对每个词语都做解释、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