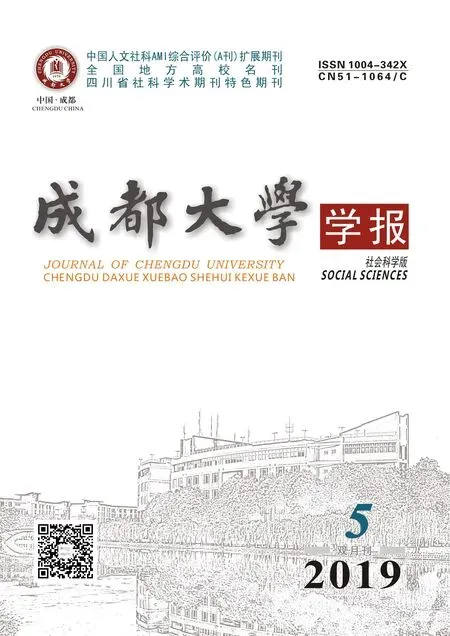论贺贻孙的诗学主张与审美理想*
蓝 青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东 珠海 519082)
贺贻孙(1605—1688),字子翼,号孚尹,又号水田居士,江西永新人,明诸生。崇祯间,曾与万茂先、徐世溥、陈宏绪等人结豫章文社。明亡后,隐居不出,以著述自娱。贺贻孙系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与诗学家,其《诗筏》一卷是清初重要的诗学论著。学界大多将贺贻孙诗学视作竟陵派的继承者,实际上贺贻孙在取鉴包括竟陵派在内的明代诸派诗学的同时,对其流弊有着清晰的认识,弃其所短,合其所长,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本文即从贺贻孙对明代诸派诗学的反思入手,探讨贺贻孙诗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审美理想所在。
一、贺贻孙对明代诸派诗学的反思
明清易代对士人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与冲击,亦激发了社会思潮及学术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无论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公安三袁为首的公安派,抑或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皆受到清代诗学家的普遍质疑,而“专以依傍临摹为事”[1]的复古派首当其冲。实际上,明人已对拟古之弊有所警觉批判,如王世贞即宣称“剽窃模拟,诗之大病”[2];屠隆亦对赝古弊病甚为不满,称“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3]第1册,368,并期待“有大匠起,则此鳞次栉比者咸无当,一扫除矣”[3]第8册,352。入清后,复古派的模仿形似、优孟衣冠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受到猛烈抨击,如钱谦益称:“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4]567,“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4]311,批评复古派尺尺寸寸的机械摹拟,窒息了诗坛的生气。贺贻孙对于复古派的赝古之弊亦深恶痛绝,对其痛加笔伐:“凡诗文可盗者,非盗者之罪,而诲盗者之罪。若彭泽诗、诸葛《出师》文,宁可盗乎?李、杜、韩、欧集中, 亦难作贼。间有盗者,雅俗杂出,如茅屋补以铜雀瓦,破衲缀以葡萄锦,赃物现露,易于捉败。先明七才子诸集,递相剽劫,乃盗窝耳。”[5]10385抨击前后七子之模仿形似、优孟衣冠,直斥之为“盗窝”,可见其态度之鄙夷。
贺贻孙论诗尤重“本色”,反对因刻意模仿而汩没性情。《诗筏》曰:“释皎然尝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以效韦苏州,韦大不喜。明日献其旧作,乃大称赏,云:‘何不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即此可见作诗当自写性灵,摹仿剽窃,非徒无益,而又害之。”[5]10431又曰:“余谓作诗未论气象,先看本色,若赀郎效士大夫举止,暴富儿效贵公子衣冠,纵气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虽无唐人气象,犹不失宋人本色,若近时人,气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远矣。”[5]10432贺贻孙主张要真实自然地表现个性、情感,在提倡性灵这一点上,贺贻孙明显继承了公安派的主张,但对其诗学亦有指摘:
作者之意,宁有时而伤庄重,宁有时而伤浑雅,宁不珍大家,宁不为汉魏晋唐,宁为七才子之徒摈弃唾骂,而必不肯一语一字蹈袭古人,掩其性灵,缚其才思,窘其兴趣,亦近代诗中豪杰也。初学若先从汉、魏、晋、唐诗涵濡有得,然后看公安诗,见其洒洒落落,亦善学古人之一助也。若学古而无所得,切勿读公安诗,读之即不能为公安诗,即有真俳真纤真佻之魔,冒公安之似,入我手腕,沦隳恶道,虽真公安复生,有口不能自白矣。[6]卷5,555袁中郎才情超忽,如千里神骏,但防泛驾啮膝而已。[5]10438
公安派有力地冲击了诗坛上的拟古风气,但存在俚俗纤佻、轻率芜杂的缺点,贺贻孙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对其弊病亦有所防范。贺贻孙虽提倡性灵,但他所偏爱的还是含蓄蕴藉的汉、唐风范,而不是肆口而出、轻率浅直。如他评价徐渭诗曰:“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七言律虽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惟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蕴藉。集中诙语俊语,学之每能误人,此其所病。”[5]10437此语虽针对徐渭诗,但其对“诙语俊语”的批评,亦可移作评价“戏谑嘲笑,间杂俚语”[7]的公安派。
明亡后,竟陵派因“孤峭奥僻、势尖径仄”,往往被视为亡国之音,备受攻伐。其中尤以钱谦益之论最为代表:
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4]571
钱谦益将诗歌与国运相连,讥弹竟陵诗之凄声寒魄、深幽孤峭,并斥其为败坏国运的“诗妖”。王夫之更是将竟陵派目为“灭裂风雅”的“戎首”[8]113,斥“钟以宣城门下蚁附之末品,背公死党,既专心竭力与千古忠孝人为仇雠。谭则浪子游客,炙手权门,又不知性情为何物”[8]69。竟陵派的“凄清幽独”在明亡后成为诗坛的矛头所向,受到猛烈抨击,大有人人喊打之势。而贺贻孙却对竟陵诗学多有肯定,这在清初实属少数。蒋寅在《清代诗学史》中指出:“在清初,除了王夫之提到的沈雨若、张草臣、朱隗、周伯孔,朱东润指出的闽中蔡复一,吴门张泽、华淑,以及钱钟书提到的张岱、林古度、徐波与傅山,公开表示服膺钟、谭并发挥其诗学的,我只见有贺贻孙。”[9]需要指出的是,贺贻孙虽对竟陵派多有取鉴,但对其弊病并没有回护。如《诗筏》云:
今人贬剥《诗归》,寻毛锻骨,不遗余力。以余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惟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学诗者诵之勃然乌可已,又能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但未免专任己见,强以木子换人眼睛,增长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然瑕瑜功过,自不相掩,何至如时论之苛也。[5]10437
明代复古派一味追求声调宛亮、气势雄壮。《诗归》有意与李攀龙《唐诗选》背道而驰,“以纤诡幽渺为宗”[10],对复古派奉为经典的诗作予以删黜,独选表现幽独孤峭的“真诗”,另辟蹊径,颇具见识胆魄,但亦将诗学引向了势尖径仄。贺贻孙充分肯定竟陵派在廓清复古派弊病上的贡献,但对于竟陵派立论之偏、取材之狭多有不满,尤其是竟陵派的“尖新割剥”,与贺贻孙深婉浑融的的审美旨趣相违背。
流派纷争是明代诗学的一大特色。明人好立门户,争讼不息,理论的提出往往并非源自艺术理想,而是为标新而故意立异,不免陷入片面化的泥潭。对此,贺贻孙有着清醒的认识:
两汉、唐、宋诗人文人,前唱后和,异代名家递为师承,同时作者互相激扬,有相长之益,无相倾之习,何其盛也。近世不然,何、李两人,既已矛盾,而应德、遵岩诸公,复与元美、于鳞门户角立。其后公安、竟陵出,扫前贤而空之。虞山继起,欲掩公安、竟陵之胜,弹射诋呵,更无虚日。当其拔帜树帜,辄令学者从风而靡。既而风会递变,议论迭新,人情厌常,各矜创获,彼帜方立,此帜已夺。……才非兼长,学无条贯,各以其长攻人所短,其弹射前人愈巧,其不及前人愈甚。譬之一音成响,难谐众器;一味独赏,遂废八珍。岂知钧天之乐,贲鼓维镛,无嫌笙磬;大官之庖,甘酸辛咸,并滋淳熬也哉。可慨也矣![6]卷5,558
贺贻孙认为明代种种文学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门户之争,明人缺乏谦虚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尤好分门立户,党同伐异,以排挤、标榜为事,自以为是、互相攻击代替了冷静的思考,因此往往走入极端,矫枉过正。贺贻孙严厉抨击明人“高自标榜,互相屈辱”[5]10438,提倡开放、包容的学习态度,并将其贯彻到诗歌批评中,前引对公安派、竟陵派的评语即为证明。即使面对他所反对的复古派,亦未一味抹煞,《诗筏》曰:“自钟、谭集出,而王、李集覆瓿矣。记余曾与同辈赋《爱妾换马》诗,都无警句。有示以钟伯敬诗云:‘功名伏骥足,志节略蛾眉。不贵此时意,难于无后思。封疆方有事,闺阁亦何为?君向承平日,明珠买侍儿。’慧舌灵腕,叹为绝唱。复有以王元美诗相示者,觉才思更迈。王诗云:‘只解驰驱易,宁言离别难。兰膏啼玉箸,桃雨汗金鞍。物喜酬新主,人悲恋故欢。横行渡辽海,那问翦刀寒。’遂以此二诗,糊名邮送万茂先定其甲乙。茂先尝进钟、谭,退王、李,见此竟以王第一。乃知前辈各有得力,不可随人轩轾也。”[5]10438又曰:“明代如李献吉、王元美诸公,非无佳诗,若得明眼人删削,尤可传世。”[5]10438在清初对复古派与竟陵派的声讨浪潮中,贺贻孙的评价颇为客观、公允,尤为难得。
二、贺贻孙的诗学主张
贺贻孙盘点明代诸派诗学流弊,称:“舍性灵而趋声响,学王、李之过也。舍气格而事口角者,学袁、徐之过也。舍章法而求字句者,学钟、谭之过也。”[5]10437他左绌复古派模仿形似、优孟衣冠,右叱公安派空疏无学与竟陵派尖新僻涩,目的就在于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诗学理论。贺贻孙云:
诗至中晚,递变递衰,非独气运使然也。开元、天宝诸公,诗中灵气发泄无余矣,中唐才子,思欲尽脱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无长吉、东野、退之、乐天辈一番别调。然变至此,无复可变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觉成晚唐苦涩一派。愈变愈妙,愈妙愈衰,其必欲胜前辈者,乃其所以不及前辈耳。且非独此也,每一才子出,即有一班庸人从风而靡,舍我性灵,随人脚根,家家工部,人人右丞,李白有李赤敌手,乐天即乐地前身,互相沿袭,令人掩鼻。于是出类之才,欲极力剿除,自谓起衰救弊,为前辈功臣。即此起衰救弊一念,遂有无限诗魔,入其胸中,使之为中为晚而不自知也。……嗟夫!由吾前说推之,则为凌驾前辈者所误;由吾后说推之,又为羽翼前辈者所误。彼前辈之诗,凌驾而羽翼之,尚不能无误,乃区区从而刻画摹仿之,吾不知其所终也!嗟夫!此岂独唐诗哉?又岂独诗哉?[5]10387-10388盖作诗贵在悟门,悟门不在他求,日取《三百篇》及汉、唐人佳诗,反覆吟咏,自能悟入。
若无悟门,但于古诗及汉魏晋唐人诗内声容字句,摹拟描画,如在琉璃屏外拍美人肩,虽表里洞见,然所拍者终是琉璃,不是美人。若舍《三百篇》汉魏晋唐而别寻悟门,如涉江海者,本无神通,漫学折芦浮杯,损弃舟航,凌空飞渡。此两种病,近代名家往往有之。然悟门不能遽开,积累时日,庶几一朝遇之。[6]卷5,554
就明代诗学而言,复古派提倡诗学汉魏盛唐,但往往流于法度格调的刻意规模,仅在形式上与古人相似,既缺乏真实的思想情感,又不具备独特的艺术风格。虽标榜学习古人,实际上并未学到古人的神髓,反而走上了字剽句窃的歧途。公安派与竟陵派欲起衰救弊,别寻法门,或空疏无学而流于率意浅俚,或另辟蹊径走上孤峭奥僻。正如诗至中晚,几经变化,非但未能超越盛唐,反而愈变愈劣。有鉴于此,贺贻孙主张折中复古派与反复古派,既要抒写性灵,又要师法汉、唐,合其两长,从而避免弃情求法和舍法言情所产生的弊端。
贺贻孙提倡直抒胸怀,《诗筏》称“今日学诗者,亦须抛向水中洗濯,露出天然本色,方可言诗人”[5]10437,反对各种人为约束和“模仿形似”。贺贻孙曾评曹景宗《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诗》“风韵洒落,翻觉杨素、高骈胸中多却数卷书”,又评《敕勒歌》“天然豪迈,翻觉得曹景宗目中多却数行字”,“以此推之,作诗贵在本色”[5]10411,似乎并不注重学力。然而,贺贻孙实际上非常重视学古,他认为作诗“固由才情,亦关学力”[5]10384,并提出要借鉴古人的形式风格,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
古人诗文所以胜我者,不过能言吾意之所欲言耳。吾所矜为创获者,古人皆已先言之。以吾之意,出古人手,较吾言倍为亲切。试取古人意,出吾手,格格不甚畅快,始愧吾短。[5]10383
贺贻孙认为,诗歌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在体格音调上已经达到了完备状态,后人再怎么创新也无法超越前人,与其在形式风格上别求新异,不如借用古人的体格来书写己意。在师法古人这一点上,贺贻孙显然继承了明代复古派的主张,但他又不同于复古派的尺寸古法,而是提倡学习古人的神思:
拟古诗须仿佛古人神思所在,庶几近之。陆士衡拟古,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讫,句句蹈袭,然去古人神思远矣。[5]10397
明代复古派学习古人重在声貌,往往沦为徒具形貌的空壳,正如《诗筏》所言,“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之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5]10385。为了不重蹈前后七子的覆辙,贺贻孙强调要发掘古人的精神内涵,以开启今人心窍,从而达到内外兼美的境界。
贺贻孙还提出熟参以求变之法,《诗筏》曰:
元微之作《杜子美墓志序》云:“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是矣。然余观子美诗,创而不沿,孤而无偶,竟不能指某篇某句出《风》、《雅》,出沈、宋,出苏、李,出曹、刘,出颜、谢,出徐、庾也。如蜂采百花以酿蜜,不能别蜜味为某花也。如秦人销天下兵器为金人十二,不能别金人之头面手足为某兵器也。合众体以成一子美,要亦得其自体而已。[5]10421
贺贻孙于诗不喜讲法,他更喜欢“熟参”以臻“妙悟”,强调在融汇古人的基础上抒写己意,这一点明显借鉴了谢榛的“酿蜜法”。谢榛《四溟诗话》曰:“予以奇古为骨,平和为体,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与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蕴。作诗有学酿蜜法者,要在想头别尔。”[11]所谓“酿蜜法”,就是在广泛借鉴前人的基础上熔铸变化,自成一格。熟参汉、魏、盛唐,获得诗家三昧,在此基础上虽自抒性情,然始终隐然古意。而“合众体以成一子美,要亦得其自体而已”,即强调既要兼收并蓄,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不仅限于随人脚跟,这就与刻意古范、“太似不嫌,反曰能书”[12]的明代复古派拉开了距离。

上官星雨一路听得连连点头,可是……真的不用去找宇晴师父吗?她长得那么好看,性格又那么温柔,她的眼睛里,好像藏着一个更深的落星湖,幽幽闪着波光,她的双手又是那么灵巧,好像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条藤蔓,被她的手指触碰一下,就会吐芽、生根、开花、结果,生机勃发。她用“点墨山河”的轻功在晴昼花海里奔跑的时候,就是一个仙女。
三、贺贻孙诗学的审美理想
明清之际,天崩地解,饱受战火摧残的士人重新思考诗歌的政教价值,普遍体现出回归传统儒家诗学的倾向。这里必然要涉及到风雅正变问题。清初不少诗人以凄戾之音书写亡国大哀,他们极力推崇变风变雅,黄宗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尝曰:“向令风雅而不变,则世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13]相较温厚和婉的正风正雅,黄宗羲无疑更看重变风变雅,这与其慷慨郁勃的激越情怀有着密切关系。贺贻孙亦持类似观点,《诗筏》曰:
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使其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乌以怒而飞,树以怒而生,风水交怒而相鼓荡,不平焉乃平也。[6]卷3,499
风人之感慨,即其优柔。感慨者其词,优柔者其旨。词不郁则旨不达,感慨不极,则优柔不深也。不观之风乎?使风之行也,仅能击芙蓉,猎蕙草,上玉堂,入洞房,泠泠洒洒,煦咻披拂以为常乎,则不过起于青苹,绕于华屋焉至矣。胡为乎蓬蓬然发东海而至南海,吹砂崩石,掣雷走电,鼓鲸奋蛟,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哮吼叫号,潜谤庵忽,栗焉糟焉,洞于心而骇于耳。使夫郁者疏,滞者解,百谷草木甲拆,而万汇以成。……太平之世,不鸣条,不毁瓦,优柔而已矣,是乌睹所谓雄风也乎?[6]卷3,468
贺贻孙认为太平之世的情感平易而肤浅,很难具有深度和力度,惟有身经丧乱、与惨烈现实激烈碰撞所迸发出的乱世之情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贺贻孙的诗歌创作亦是如此,他自称“丧乱之后,余诗多哀怨之旨”,“彼老父以歌为哭,吾以哭为歌”[6]卷5,562,“时值国变,三灾并起,百忧咸集,饥寒流离,逼出性灵,方能自立堂奥,永叔所谓穷而后工者在此时乎”[6]卷5,554。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均是习见的诗学话语,强调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正是不幸的遭际令文辞获得动心神魄的艺术魅力,而贺贻孙旧调重弹,其重心在于民族气节的坚守。贺贻孙所倡导的性灵,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故国之思,既不同于公安派带有叛逆精神与异端色彩,又区别于竟陵派的遁世精神。由此出发,贺贻孙对宋诗尤其是宋末诗歌的价值做出了全新估量:

身为遗民的贺贻孙对宋遗民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他反对明代复古派严格区分唐宋畛域,而是以忠孝为标准,充分肯定宋末诗的思想价值,并由此将宋诗纳入诗史视野,突破了“诗必盛唐”的狭隘观点。需要指出的是,贺贻孙虽对宋诗有所改观,但他所推崇的是唐诗框架中的宋诗,或者说他的审美理想典范仍是唐诗而不是宋诗。《诗筏》曰:“宋人诗佳者,殊不愧唐人,多看可助波澜,但须熟看唐人诗,方能辨宋诗苍白。盖宋之名手,皆从唐诗出,虽面目不甚似,而神情近之,如人儿孙十传以后,犹肖其鼻祖。昔萧颖士绝肖其远祖鄱阳忠烈王,非发冢破棺,亲见鄱阳王者,不能识也。但不可从宋入手,一从宋入手,便为习气所蔽,不能见鼻祖矣。”[5]10435贺贻孙虽提倡学习宋诗,但他对宋诗的“朴拙粗僻”[5]10420颇为不满,每每提醒士人勿走入歧途,宋诗之于贺氏,更多是开拓视野的作用,而不是审美理想所在。
从诗歌的政教意义出发,贺贻孙高度肯定怨刺精神与雄肆激越,但在审美上更侧重含蓄蕴藉。《诗筏》曰:“阮嗣宗越礼惊众,然以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文王称为至慎,盖晋人中极蕴藉者。其《咏怀》十七首,神韵澹荡,笔墨之外,俱含不尽之思,政以蕴藉胜人耳。然以《拟古十九首》,则浅薄甚矣。夫诗中之厚,皆从蕴藉而出。”[5]10401“诗以蕴藉为主,不得已溢为光怪尔。蕴藉极而光生,光极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诸大家,各有一种光怪,不独长吉称怪也。怪至长吉极矣,然何尝不从蕴藉中来。”[5]10381贺贻孙强调对感情的节制与范型,即使怪异如诗鬼李贺,亦从蕴藉中而来。蕴藉只是贺贻孙对诗歌审美的基本要求,他还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化境。《诗筏》云:
清空一气,搅之不碎,挥之不开,此化境也。[5]10382
贺贻孙将“化境”视为诗歌最高的美学境界,即内容与形式合为一片、浑融无间,段落无迹、离合无端、繁复无缝,非言语笔墨所能形容,给人无穷尽的审美享受。“化境”这一概念虽然抽象,但它并非是悬空的,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是诗歌的生成。《陶、邵、陈三先生诗选序》曰:
诗之有风,由来尚矣。十五国中,忠臣孝子,劳人思妇之所作,皆曰风人。风之感物,莫如天籁。天籁之发,非风非窍,无意而感,自然而乌可已者,天也。诗人之天亦如是已矣。今夫天之与我,岂有二哉?莫适为天,谁别为我?凡我诗人之聪明,皆天之似鼻似口者;凡我诗人之讽刺,皆天之叱吸叫嚎者也;凡我诗人之心思肺肠,啼笑寤歌,皆天之唱喁唱于刁刁调调者也;任天而发,吹万不同,听其自取,而真诗存焉。[6]卷3,467
贺贻孙认为诗歌由天生成,神授之,类似“天籁之发”,诗人的职责仿佛只是传达表述,而不能人为地设计与控制。贺贻孙非常注重创作动机的偶然性,《诗筏》称:“书家以偶然欲书为合,心遽体留为乖。作诗亦尔。”[5]10386“张谓侍郎七言律,多奇警之句,及死后见形,独爱人诵其‘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二语。晋谢康乐诗尤多警语,而独喜‘池塘生春草’五字,自谓神助,可见诗以偶然语写偶然景为得意,凡他人所谓得意者,非作者所谓得意也。”[5]10420张谓的“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之所以能够成为惊人句,是因为其乃诗人偶然之所见,不经意之所得,并无任何人工着意痕迹。贺贻孙强调妙手偶得、不假思致的创作模式,这就保证了诗歌创作的自发性,而不是人为地、刻意地进入创作状态,从而杜绝了复古派为文造情、矫揉伪饰的隐患。
其次是诗歌的构成。贺贻孙认为诗歌藉“神”构成,“神”是贺贻孙诗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神”是抽象的,隐行在字里行间,深藏不露,但贯通起整首诗歌,成为构成“化境”的重要因素之一。《诗筏》曰:
诗文有神,方可行远。神者,吾身之生气也。[5]10382
神者,灵变惝恍,妙万物而为言。读破万卷而胸无一字,则神来矣,一落滓秽,神已索然。[5]10382
贺贻孙自称“家世治《易》”[14],并著有《易触》七卷,可见其对《周易》浸染之深。“神”的概念显然借鉴了《周易》中有关“神”的论述。《周易》认为“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15]282,万物之运动变化系自造自发,不知所以然而然,而推动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即“神”。贺贻孙认为诗歌之所以前后一贯,富有生气,正是因为有内在的“神”,它将散乱的内容材料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若无“神”,断不成文。《周易》还认为神是深不可测的。正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15]235,“神”变化无常,很难像测物那样可以准确把握。贺贻孙认为神是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隐形”联系,它具有不可测性,如神龙不见首尾,变化无端,不可捉摸。《诗筏》曰:“乐府古诗佳境,每在转接无端,闪铄光怪,忽断忽续,不伦不次。如群峰相连,云断之,水势相属,缥缈间之。然使无云缥缈,则亦不见山连水属之妙矣。《孤儿行》从‘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后,忽接‘春气动,草萌芽’,《饮马长城窟》篇从‘展转不可见’,忽接‘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语意原不相承,然通篇精神脉络,不接而接,全在此处。末段‘客从远方来’,至‘下有长相忆’,突然而止,又似以他人起手作结语。通篇零零碎碎,无首无尾,断为数层,连如一绪,变化浑沦,无迹可寻,其神化所至耶!”[5]10395-10396“段落无迹,离合无端,单复无缝,此屈、宋之神也。惟《古诗十九首》仿佛有之。”[5]10382诗歌表面可能似断似续,忽碎忽整,但实际却浑然一体,妙合无垠,正是由于“神”的贯穿。若无“神”,断不成文。“神”不仅不可解,而且是自然生成的,不可迹求。《诗筏》曰:“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吾身之神,与神相通,吾神既来,如有神助,岂必湘灵鼓瑟,乃为神助乎?老杜之诗,所以传者,其神传也。田横谓汉使者云:‘斩吾头,驰四十里,吾神尚未变也。’后人摹杜,如印板水纸,全无生气,老杜之神已变,安能久存!”[5]10382前后七子强调法度格调,有形可见,可感可学,而贺贻孙所强调的“神”则排除了一切模式化的规则技巧,亦排除了尺寸蹈袭的可能。
最后是诗歌的艺术效果。既然“化境”系自然生成,藉“神”隐而贯之,那么它所呈现的艺术效果必然是浑然天成,难以句诠的。《诗筏》曰:
诗家化境,如风雨驰骤,鬼神出没,满眼空幻,满耳飘忽,突然而来,倏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迹相求。如岑参《归白阁草堂》起句云:‘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白阁云,半入紫阁松。’又《登慈恩寺》诗中间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不惟作者至此,奇气一往,即讽者亦把捉不住,安得刻舟求剑,认影作真乎?近见注诗者,将‘雨在八九’、‘云入紫阁’、‘秋从西来’、‘五陵’、‘万古’语,强为分解,何异痴人说梦。[5]10408
贺贻孙认为岑参的《因假归白阁草堂》和《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即臻“化境”,写景苍茫浩渺、涵浑空远,它给人的审美感受是浑然整体、不可分析的。对于这样的境界,只能涵咏领悟,而不能强为分解,拘泥字句。《诗筏》曰:“以声韵格律论诗,已近于学究矣。”[5]10421即批评宋元以降那些所谓的诗法诗格论著。贺贻孙最欣赏《古诗十九首》,赞其“不知何所起,不知何所止,一片灵气,恍惚而来”[5]10387,浑然化一、不可句摘。基于此,他特别强调诗歌的有机整体性:“写生家每从闲冷处传神,所谓‘颊上加三毛’也。然须从面目颧颊上先着精彩,然后三毛可加。近见诗家正意寥寥,专事闲语,譬如人无面目颧颊,但见三毛,不知果为何物!”[5]10383局部的价值就在于其对整体的贡献,没有整体,局部亦失去意义。贺贻孙论诗往往从整体出发,即使具体到字句层面,亦着眼于其是否能够形成很好的整体感:“炼字炼句,诗家小乘,然出自名手,皆臻化境。盖名手炼句如掷仗化龙,蜿蜒腾跃,一句之灵,能使全篇俱活。炼字如壁龙点睛,鳞甲飞动,一字之警,能使全句皆奇。若炼一句只是一句,炼一字只是一字,非诗人也。”[5]10386他认为诗歌应该在整体上下功夫,即使要炼字炼句,亦要注意整体的整合。由此出发,贺贻孙对晚唐诗歌颇有微词:
看盛唐诗,当从其气格浑老、神韵生动处赏之,字句之奇,特其余耳。如王维“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孟浩然“石镜山精怯,禅枝怖鸽楼”,张谓“野猿偷纸笔,山鸟污图书”,岑参“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此等语皆晚唐人所极意刻画者。然出王、孟、张、岑手,即是盛唐诗;若出晚唐人手,即是晚唐人诗。盖盛唐人一字一句之奇,皆从全首元气中苞孕而出,全首浑老生动,则句句浑老生动,故虽有奇句,不碍自然。若晚唐气卑格弱,神韵又促,即取盛唐人语入其集中,但见斧凿痕,无复前人浑老生动之妙矣。[5]10417
中、晚唐人诗律,所以不及盛唐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也。[5]10384
盛唐诗气格浑老、神韵生动,虽不乏脍炙人口的隽语,但能够和整首诗浑然无间。晚唐诗人偏爱字句的琢磨与锤炼,苦吟成癖,的确创造了不少佳句,但往往孤立地拘守字句,导致有句无篇,字句之奇警放到全诗的语境中显得颇为突兀,破坏了诗歌的浑融之气,故落入下乘。
综上,贺贻孙在反思明代各派诗学的基础上,运用折中思维,合其所长,去其所短,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其提倡师心与师古相结合、学古重在神思、熟参以求变均体现出为避免明代诗学弊端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对化境的追求,更是针对明代复古派之赝古、公安派之纤佻以及竟陵派之僻涩所提出的新的审美境界,彰显出卓越的审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