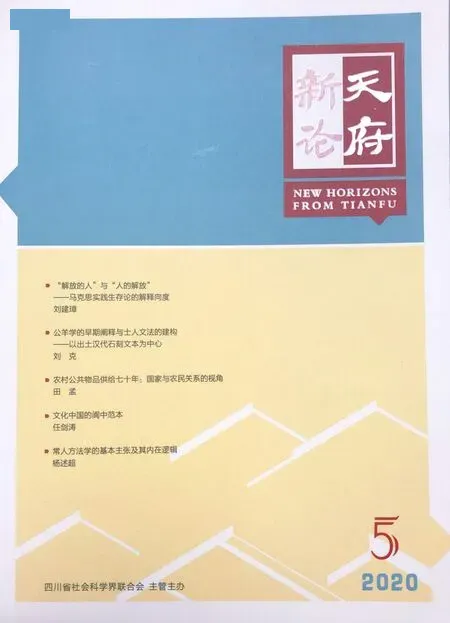爱的光华与苦难的承付
——《诗经·邶风·柏舟》的启示
李 静
在现代社会谈爱,看起来就是陈词滥调。充斥在我们周围的文艺影视作品,几乎无处不在谈爱,这些爱有的撕心裂肺,有的轻飘飘,撕心裂肺的以貌似深情的面貌在感染人,轻飘飘的又以浅尝辄止的“理智”在告诫人。无论是撕心裂肺还是轻飘飘,都不是真的深情或理智。前者把自我全部抛洒给一个不能接受自己的对象,看起来在贡献,其实却是自私,因为他既没有自爱,也没有爱他人;至于后者,连“小马过河”的勇气都没有,由始至终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我”里,从未爱过他人,也不可能在互爱中懂得自爱,更谈不上理智。自私的爱,离“厚德”的深情和“载物”的智慧,实在太遥远。
大爱无私,无私的爱最高级的形式乃是“厚德载物”。想要“载物”,需得“厚德”,要积累德性,就得与苦难并行。许多人沉浸在进步的神话里太久,趋利避害的思维太重,早已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忘了,爱的能力总是与承受苦难的能力相当。爱需要学习,需要磨练。对爱的学习和磨练时刻不离于我们的生活,不离于我们的当下,也时刻体现在对往昔经验的反复咀嚼之中。于是,在我们勇往直前时,也需要回头看看历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与旧总在携手同行。
一、时的变化:从葛藟到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127-128页。这是《柏舟》的开头,也是《邶风》的开头,甚至也可以说是“变风”的开头。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雌雄音声相和不同,《柏舟》以一叶孤舟开头。舟者“以济不通”,本是为着渡水到岸,但柏舟却没能“济不通”,它始终漂浮在水流之上,不得靠岸。是没有人掌舵,还是这一叶孤舟不够坚固?柳宗元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同样是孤舟,漂浮着的柏舟却更加孤独,它不但承载不了远离尘嚣的自得其乐,甚至也没有蓑笠翁与它心心相印。这一叶孤舟也不是不够坚固,因为它是“阳刚至坚”的柏木所造。柏舟阳刚至坚,却不能如其所愿到达彼岸,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亦汎其流”,柏舟“汎”,水流也在“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柏舟之所以不能渡水,原因恰恰在于水流的泛滥。水“居众人之所恶”,可以代表谦和不争,然而《柏舟》开篇的水流却不是“谦和不争”,而是涌动不休、泛滥流行。泛滥的水流好似人心里不断涌出的欲望,欲望不停歇,水流就不能安静,也就无法承载柏舟的志向。于是,浮在涌动水流之上的柏舟好似无所系赖,迫不得已只能“随波逐流”。虽是“随波逐流”,却没有同流合污,柏舟始终坚守着自己作为柏舟的品质,没有一刻想要去做泛滥的水流。“兴者,喻仁人不见用而与群小人并列”(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127页。,柏舟漂浮在泛滥水流之上,在周遭取利不取义的欲望社会中自强不息,在困境中坚守。仁而不遇,就是柏舟所喻之人的“殷忧”。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23页。松柏四季常青,“经冬不彫,蒙霜不变”。自古以来,松柏就被用来分别君子与小人。君子无论是身处治世还是乱世,始终都能洁身自好,坚守德性。而小人却不同,他们只能在治世的盛德教化之下不去做恶,而在乱世却无法坚守德性而变得肆无忌惮。唯有冬天的严寒,才能检验松柏的收束力量。《庄子·德充符》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4)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第106页。张文江先生解释“青”通“静”,静为“息争”,“青青”于是变得极有“生气”。(5)张文江:《〈庄子〉内七篇析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141页,第141页。《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与“止”有着密切的关联。静能止争,尤其能够停息心里各种相争之念,而要做到静,又须得先“知止”,须得时刻“止于至善”。“唯止能止众止”,正己而后能正人。只有自己先做到“知止”,才可能延伸出去引导他人向善。庄子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谈松柏。“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受命于地为坤二”(6)张文江:《〈庄子〉内七篇析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141页,第141页。,松柏喻君子,君子不仅有男子,也有女子。虽都是讲“仁而不遇”,但比起《毛传》 《郑笺》的贤人不遇明君,三家诗的贞女似更符合诗旨。松柏冬夏常青,原因在于“独也正”,之所以知道它内里“独也正”,恰恰是外显的“青青”生机。“正”即“止一”,止于一也就是止于至善。“青青”是外面显出来的光明,是“光大”,“止一”是内在的修养,是“含弘”。只有战战兢兢的收束力量积累得足够多,才可能“青青”、“光大”。青青的松柏处处是厚重的生气。柏木所造的柏舟能够在泛滥的流水中坚守,这就是“独也正”,是严冬里的挺拔。挺拔喻男子十分常见,但说女子“挺拔”,似乎并不符合习常的理解,因为在此之前, 《诗经》常常以“葛”、“藟”来喻女子。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这是诗经《葛覃》对女子生命历程的经典概括。在《葛覃》里,象征女子的“葛”不断延施,从父母之家蔓延到夫家,以劳动和生育的方式继续开枝散叶。从出生到死亡,女子总是在两端之间横向延展。倘若女子想要纵向延伸,光靠葛自身的力量很难做到,它得借助“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高木下曲,葛和藟紧紧缠绕,借力攀缘,向上延展出茂盛。高木挺拔,葛藟柔顺。《葛覃》里横向生长的葛,《樛木》里向上攀缘的葛藟,都不是严冬里的柏,它们在安静中蔓延,在欢喜中攀缘。只有治世才有安静和欢喜,严寒里多半都掺杂着“殷忧”。安静蔓延的葛有“服之无斁”的男子与她相依,欢喜攀缘的葛藟有主动弯腰低头的樛木与她相和。柏舟所喻的女子既无闲适安静,也无欢喜,她非但没机会遇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男子与她和鸣,甚至也没机会碰到同时代的一个君子成为知己。
《毛传》把国风分为正风与变风,“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二南”为国风“正经”,余下十三国风为“变风”。《郑笺》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7)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页。《诗经》的编排虽不见得一定依照历史的先后顺序,但“二南”与十三国风的治乱之象却十分明显。《周南》是治世之风,《葛覃》 《樛木》有圣人所化之象,处处彰显安静、欢喜,女子在这样的安宁中自然能够横向蔓延,纵向攀缘,外显她们柔顺的一面;而在乱世之中,没了“服之无斁”、主动“下曲”的男子支撑,女子就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向外蔓延、向上攀缘了,她们若想保持“独也正”的力量,只能如松柏般挺拔。“坤至柔而动也刚”,内直外方的女子静也顺正、动也顺正,这就是她的“刚”。
从柔顺的葛藟到刚强的柏舟,女子仿佛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柔顺隐去而刚直外露。当高木变得崟岑绝人,葛藟要么不得攀缘,要么那攀缘就变成了扫不去的“墙有茨”。葛藟若是还想保持直方大的品质,只能成为柏木。归根结底,从葛藟到柏舟,并没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女子还是那样的女子,内里的品质还是如初,只是时势变了。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圣人之为圣人,就是因为他能抓住“几微”,时刻根据时间、时势的变化而行动,君子同样如此。无论是葛藟还是柏舟,都只是取象,无论是柔顺还是刚直,也都是君子之一体,治世的柔顺与乱世的刚直走的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学习之路。当世风日下、小人成群,“止水”大都变成“流水”时,柏舟女子“耿耿不寐”,心怀深忧,不能遨游。不是不想像《葛覃》中的女子一样安静地采葛织衣,做好清洁欢欢喜喜回娘家,也不是不想像《樛木》中的女子一般欢喜地攀缘樛木,用“易简”帮助累积“高明”,(8)参见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4页。实在是泛滥的流水势头太过猛烈。时机需要我成为柏舟,那便做一艘柏舟。王先谦云:“贞女言今汎汎然而浮者,是彼阳刚至坚之柏木所为舟也,乃亦汎滥流行于水中,无所系赖乎?”(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127页。柏舟女子果真无所系赖么?
二、艰难的维持:“我心”的贞一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柏舟女子的“心”向来有所系赖。她心系什么,爱慕什么?镜子光洁,能反映人的外在,但柏舟女子却说镜子还不够,它虽能照物却不能明察内心,镜子照出来的物象不分美丑善恶,而“我心”却能分辨善恶美丑,容不得半点污秽。“我心”如此坚韧和刚强,定然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各种诱惑时能够不断提醒自己“匪”、“不可以”,定然是“持志如心痛”。一旦把“匪”、“不可以”坚守到了骨子里,那便成了一种本能,于是自然“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污然”(10)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2011年,第24页。。柏舟女子的所爱从来都是“皭皭”的德性。
然而,柏舟女子要成就自己的“皭皭”并不容易,她需要面对各种境况一次次保持贞定。《列女传·卫宣(应为寡)夫人传》讲了柏舟女子的身世。卫寡夫人本是齐侯之女,嫁去卫国时刚到城门口,卫侯就不幸去世,这时她的保母劝她“可以还矣”,夫人不听,仍旧嫁进卫国,为去世的卫侯守丧三年。(11)绿净:《古列女传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60页。这是柏舟女子成人后的第一次坚守。古代女子出嫁,三月庙见而成妇礼,卫寡夫人尚未嫁进卫国,原本有机会重新选择,但她却毅然决然走向做寡妇的“不归路”。在古代,女子的生命意义主要体现在生育的延施,卫寡夫人选择进入卫国,也就选择了没有延施的未来。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的未来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一定举步维艰。卫寡夫人明知有难而不避,这到底是为什么?
经历现代启蒙的我们,早就习惯了理性的筹划,习惯了用主体性的思维对待世界,自信地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卫寡夫人没有经过理性启蒙,她不觉得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她的所爱不是一时之“利”,而是长长久久的“义”。她不会认为嫁去卫国做寡妇是“弊”,转头回齐国重新嫁人就是“利”,因为恒久的“义”也一定是最大的利。她只知道随时尊礼而行:“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礼以时为大”,在每个时代,特定的礼法就意味着道义,而顺着道义、行在道上就是在回返自己的原初本性。这就是最大的自爱。卫寡夫人或许想过未来在卫国的日子不会好过,或许她根本没有去想。对君子而言,个人利益从来都不需自己去谋划,因为私智计算出来的利益一定不会是真的利益,真正的个体利益总在总体利益之中。相应地,人生的灾难也不是一次次利弊得失的计较。我们往往习惯于把灾难看作“人祸”,以为自己总有计算利弊的空间,但君子却不这么认为。天灾人祸,人祸从来都与“天”联系在一起。子路死,子曰“天祝予”,颜渊死,子曰“天丧予”,恰恰在灾难中,“天”凸显出来,同时“我”与“天”也更亲密地连结在了一起。《庄子·养生主》曰:“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12)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第30 页。人祸即天灾,“我”与“天”倘若总是能保持在融通状态,那么就不会把生活中的劫难单独剥离开来,用主体与对象的二元平面关系去思考、去计较。计较容易滋生怨愤。卫寡夫人断然回绝保母的建议,她大概从未想过去回避人生的劫难,她的反应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在理解“天与人不相胜”之下的顺命。一旦顺命,就谈不上“飞蛾扑火”,而是坦然面对,无论前路是安逸还是艰难,都只需“安时而处顺”。这就是柏舟女子的第一次贞定。
卫寡夫人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原本可以在夫死无子的困境中安静生活,然而她的苦难却远未结束。为夫守丧后,丈夫的弟弟继任卫侯,请求与她“同庖”联姻,她再一次拒绝。比起在城门口听闻丈夫去世后坚持出嫁的艰难,这次的拒绝显得容易得多。既然已经可以回返自己的天性,坚守礼法道义,那么任何想要打破这种“坚守”的威逼利诱,都不能再让人动心。这是柏舟女子的第二次贞定。
拒绝之后,新任卫君向她的齐国兄弟控诉,齐国兄弟支持新任卫君,令她改嫁,但卫寡夫人坚持不从,于是有诗“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古代女子有两种“归”,出嫁到夫家的“归”和出嫁后回娘家探亲的“归宁”。这是她们生活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女子的生存感觉有所不同,夫家是生活重心,而娘家却是时时依恋的源泉,尤其当女子在夫家遭遇委屈,就会更期待父母之家的温暖。如同葛的生长,无论葛的茎和叶延伸得多远,总不能离开根的滋养。可惜卫寡夫人的娘家非但不支持她,反而伙同夫家一起逼迫她。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接连两个“我心”强调心志,既是对夫家逼迫的回应,也是对齐国兄弟无礼“怒气”的回应,是可贵的义愤。义愤乃是向上的力量,如同《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鸟“怒而飞”。为什么柏舟女子的义愤爆发在这里?遭遇小叔的无礼要求尚且可以忍耐,因为还有父母之家可以依靠,但若父母之家也来逼迫,女子就失掉了“根”的滋养,成了无根的野草。到此,柏舟女子丧失了所有亲人的支持。石头已经够坚硬,然而坚如磐石还不能表达柏舟女子的心志,毕竟石头还可以被迫转动。君子说,石可转心不可转,席可卷心不可卷。“转”与“卷”都是动态,是随着外界事物变化的被动迎合,柏舟女子彻底否定了这种动态迎合,强调自己安静的贞定意志。这是她的第三次贞定,也是诗的高潮。从“不可以茹”到“不可转”、“不可卷”,柏舟女子的心志愈发坚定,即便没有父母之家的护佑,即便双双失掉夫家与父母之家的支持,也要保持自己的“贞一”。《坤》之彖辞曰:“元亨,利牝马之贞。”贞者正而固,“牝马之贞”即牝马之顺,“言如牝马之顺而不息则正”(13)来知德:《周易集注》,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古代女子无外事,所以女子的贞一首先表现为从一而终。从一而终表面上是针对一个人,内里却是在强调礼法背后自然正当的力量。一个时代的某些特定礼法是否适用于另一个时代,这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相比于作为对象物的礼法,活的礼法下鲜活的人的生活才更有讨论意义。柏舟女子显然没有把礼法当成僵硬之物,她的坚守也不是僵化,而是由礼法入道义。人的生活是类的生活,总需要中介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法或准则就是这样的中介。当一个人把礼法或准则不仅看成一种被动承受之物,而且看成自由意志的产物,他便可以由中介入道义,达到自由。只有获得这样的自由,才可能面对外事保持“贞定”。面对不相干的疏远之人能够保持贞定,尚且还算容易,如果面对至亲至爱之人能保持贞定,那才算是真正的“知止而后有定”。
“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面对亲人,一般人都有偏爱之心,很难持守道义之正。血缘的美好亲情,常常是一个人对天地有情的基础,一个人对亲人的感情有多浓,对天地的感情就可能有多深,相反,亲人的无情常常也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对天地的感情。但对君子而言,情况却有些不同。血亲的抱怨和无情对所有人都是难言的苦痛,即便虞舜也只能呼天。然而,君子虽忧痛却不沉溺,“知耻近乎勇”,苦痛的力量也可能变成“上出”的可贵勇气。“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14)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第4页。,有多少苦难,就可能有多少勇气。亲人越是无情,人对美好的渴望反而越强烈,就越能够明辨是非,守住道义,变得贞定。这样的否极泰来不是人为的筹划,而是命运的安排,没有人想去主动经历这样的苦痛。然而,虽是命运的安排,却也是主动的承付。只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主动炼狱,才可能把这些苦痛变成上达的志气。一旦柏舟女子能够明辨至亲至爱之人的恶,能面对亲人的逼迫坚守道义,她的洁身自爱便会“若肌肤、性命之不可易也”(15)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2011年,第22页。。一个人有了“若肌肤、性命之不可易”的自爱,自然也就能发出皭皭之光,于是就有了“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三、自然的光华:“威仪棣棣”
柏舟女子的“威仪”富不可量,多不胜数。什么样的威仪才是有形数字数不清的呢?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像谓之仪。”(16)刘勋:《左传精读》,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270页。威而可畏,不少人习惯把威看成“威慑”,只看到它背后的强力,强调它让人害怕的一面,然而强力所带来的威慑缺少真正的根基,它依靠的只是外在于人的物的力量。物与人不相沟通,物的力量就不会长久,只有贯通内外的力量才有生机。威仪之威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力的结果,有一种威叫“不怒而威”,它根源于自然的“威严”。《论语·述而》里记载孔子“威而不猛”,就是一种自然流露的中道。什么叫“有仪而可像(象)”呢?《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仪只是人身上的一张皮,只是外在的形式么?没有皮,人不成其为人,然而只有张外皮恐怕也不成其为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这就是只有外皮的样子。真正的仪一定“可像(象)”,那什么样的仪才可以作为万世之法供人学习呢?《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17)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793页。只有内寓至诚的工夫,才可能外显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有仪而可像”并不是只有形式的礼仪,它是内在威严自然外显的结果。有威之人不必有仪,刚猛过头就不成其为仪,有仪之人也未必有威,只有外在的形式礼仪谈不上有威;有威之人一定有仪,内有至德的威严,外在的容止一定中和,有仪之人一定有威,外有崇礼的好容仪,内里一定有敦敦厚重之力。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威仪便成了文质彬彬。
威仪之为威仪,既具体而微又形容广大。说它具体,是因为威仪总是某个具体之人的威仪,不是抽象的威仪,君有君的威仪,臣有臣的威仪,夫有夫的威仪,妇有妇的威仪,男有男的威仪,女有女的威仪。柏舟女子的威仪离不开她作为一个女子、一个守寡妇人、一个国君夫人的身份,她的威仪一定是契合这些“位”的威仪。所谓“富不可量、多不胜数”的威仪,若用一个长句来表达,就是“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像,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18)刘勋:《左传精读》,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271页。,若只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无体之礼”(19)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750页。。所谓“富”和“多”,可以比这个长句的形容还更多,实际上说不清有多少,因为那是“无体”。
“体”总括人身十二属,是身体看得见的部分,“无体”隐去了身体的有形部分,仿佛让人忘记了身体,看到了不属于肉体的东西。“无体”内里暗含着“吾丧我”(20)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第24页。。忘记这个特殊的身体,并不是全然忘记自己,而是忘记作为小我的这个自私个体,打开自己。打开自己,就让“我”通达了整体,通向了天地,把“我”变成了“吾”。所以《韩诗外传》言“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忘身”(21)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2011年,第19页,第16页。。内有充沛的志气,便可“破体”,“破体”不是不要身体,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养身”(养神)。“无体之礼”大抵就是在“破体”的基础上所展露出的“礼”。《礼运》曰:“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行于大道的礼总是上与天地自然合一,下达人伦日常的方方面面。《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2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249页。体(體)与礼(禮)形相通,老鼠尚且有身体之质,难道人却不能从有形之“体”上达“无体”之礼么?无体之礼,就是礼的最高境界。礼借由身体展露,却又不止于身体,它能把有形的身体与无形的精神连结,于是有形之体的行动便能生发出穿透身体的力量,如同柏木一般生机勃勃。柏舟女子的威仪所展露的就是这样的生生之气。
把威仪视作无体之礼,无体之礼又得通过身体展露,既然不是不要身体,那为什么不叫“有体之礼”呢?称“无体之礼”而非“有体之礼”,很可能内含忘却生死的勇气。《韩诗外传》曰:“此三子(王子比干、柳下惠、伯夷叔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故杀身以遂其行。”(23)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2011年,第19页,第16页。无独有偶,船山也认为柏舟女子与伯夷有“同情”之处。他说:“古之有道者,莫爱匪身。臣之于君委身焉,妇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己,荣辱自彼而生死与俱,成乎不可解、而即是以为命。然而情睽而道苦焉,哀恶从而遣、思恶从而为之度哉?”(24)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6页。要成就“无体之礼”的威仪,就得有“杀身成仁”的勇气,而要想避免“委身”于人的逼窄境地,就得“莫爱匪身”。爱身与杀身,表现虽不同,道理却相通,二者都是自爱的结果,都是循道的结果,时势不同,选择就不同。有了“威仪棣棣”,柏舟女子自然散发出“赫兮晅兮”的光明,这样的光明会给她足够的力量去抵御黑暗。
一阴一阳之谓道,柏舟女子的坚守有多贞定,她所受的侮辱就有多深厚。不仅夫家逼迫她,娘家也逼迫她,不仅亲人逼迫她,卫国的众多在位“君子”也逼迫她。“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就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逼窄境地。这样的穷境对于一般女子已经彻底绝望,然却成就了柏舟女子的第四次贞定。她是前国君夫人,她的选择不仅仅影响一个家庭,更会延及卫国甚至整个天下,如同那位待火而死的宋伯姬。对她而言,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是一次“如履薄冰”的检验,如同时刻行走在“刀锋”之上。在“群小”的逼迫下坚守道义,在泛滥流水中做一艘柏舟,柏舟女子有着万夫莫当的勇气。以一敌万,柏舟女子的贞一与“群小”在德性上的摇摆形成鲜明对比,她的“一”对峙小人的“多”,非但不逊色,反而能绽放出“赫兮晅兮”的耀眼光华。在亲人的逼迫下,在小人的包围中,柏舟女子看似已经无路可走。然而,无论是群小包围,还是觏闵受侮,君子总能绝处逢生。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求仁得仁的人,才会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才会“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有了不被知的觉悟,绝处才会变成生地,所以即便是“愠于群小”,即便是“觏闵受侮”,柏舟女子却仍能“静”,能“静言思之”。
不过,虽有“静言思之”的沉淀,柏舟女子却仍旧无法释怀。地上已经没有支持她的人,仰头望日月,日月也“迭而微”,于是她只能再言“心之忧”,坦言“不能奋飞”。全诗以“殷忧”、不能“遨游”开头,又以“心忧”、“不能奋飞”结尾,首尾一贯,都是“忧而不能解”之象,中间以“我心”和“威仪”明志,又是“忧而不困”之象。柏舟女子到底是忧不能解,还是忧而不困呢?船山曰:“谓伯夷之无怨者,伯夷之心也。父以其国而命诸弟,己去而大负释,北海之滨、乐融融也。传伯夷而为之怨者,亦伯夷之心也。君不惠而丧其天下,臣寻干戈于君而天下戴之,众不知非,而独衔其恤西山之下,恶得乐之陶陶也?”(25)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5页。柏舟女子与伯夷确有“同情”之处,她不怨,却有忧。“忧不能解”是她的深情,“忧而不困”是她的通达。深情与通达并至,才能达到自爱与爱他的中和。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页。《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天生具有爱的能力,但却不一定都能在生命中展开这种能力,爱的能力需得“率性”、“修道”,需要在苦难中学习。苦难是生命的特殊环节,它是磨炼人的利刃,既可能把人重新打回动物的禽兽状态,也可能刺激人去领悟存在的意义。柏舟女子用她的生命历程教会我们如何在苦难中保持贞定,如何保持自爱与爱他的通达,如何厚德而载物。只有达到自爱与爱他的通达,爱才能生发出光华,一种穿越时空的普遍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