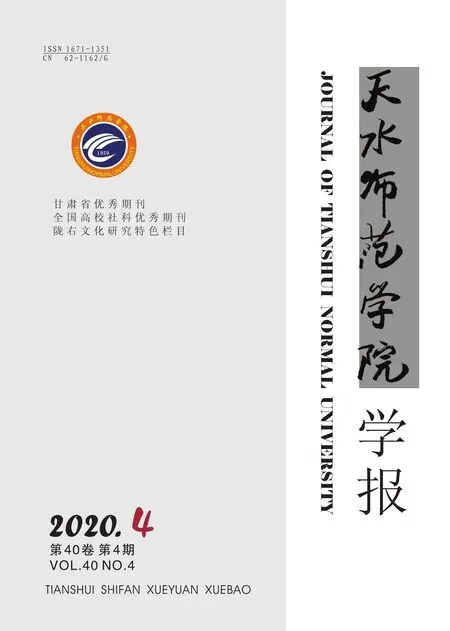《还乡》中的空间叙事与女性主体的生成
蒋贤萍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还乡》(1878)是其创作中期的重要著作,也是“威塞克斯农村社会悲剧的序曲”。[1]在这部小说中,哈代打破当时英国主流文化传统,构建起以女性为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塑造了一位极具现代意识的女性——尤斯塔西雅。对于《还乡》,传统的研究以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悲剧主题、自然意象等居多,而鲜有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就文学作品的空间批评而言,以往评论家往往过多地关注作品中地理环境同作者经历、作品主题之间的关系,将空间看作一种静态的、自然的场景。自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发表以来,空间问题逐步受到批评理论界的重视。空间批评打破文本中景观的传统研究方法,聚焦于空间及空间隐喻背后的文化、历史、身份、权力等问题,强调对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解读。
笔者以《还乡》为研究文本,以空间理论为依托,结合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的研究方法,揭示在维多利亚社会构筑的“纹理空间”中,女主人公尤斯塔西雅被他者化的悲剧性命运,同时再现其在“平滑空间”里的“逃逸”过程,进而阐释“第三空间”里女性主体的“生成”过程。通过追溯女主人公尤斯塔西雅试图冲破维多利亚社会樊篱,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心路历程,笔者意欲阐释小说中空间叙事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思想内涵,并在美学层面上建立空间叙事与女性主体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一、空间批评概述
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空间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客观现实,它还意味着文化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方位参照,还是一种价值反映;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还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并生产着叙事自身。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常常作为我们生活的环境而潜在于生活的背景之中。空间之维在社会理论中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学想象力。20世纪末,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的空间文化生产理论以及麦克·克朗、米歇尔·福柯、菲利普·瓦格纳等学者的文化地理学成就,极大地拓展了空间批评的视野。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被视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其著作《空间的生产》(1974)分析了三种“空间认识论”:可感知的、物质的第一空间,构想或想象的第二空间和无穷开放、不断解构与重构的第三空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中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已成为近年来后现代学术中的热门话题。后现代“空间”多元、开放、流变的特征,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及美学相契合。例如,德里达强调能指与所指关系中意义的“延异”;福柯倡导权力话语和档案研究,以系谱学和知识考古学追寻并还原历史的碎片。这些哲学家提出一些富于原创性的重要概念,如延异、生成、游牧、逃逸线、系谱学、知识考古等,大多与空间相关,为我们审视世界、思考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样的空间反思最终导致建筑、地理学、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诸学科呈现出交叉渗透的趋势。
在空间批评领域,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具有特殊而深远的影响。福柯曾预言,20世纪将会是“德勒兹世纪”,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把德勒兹称为“我们时代的康德”。
可以认为,吉尔·德勒兹是20世纪最重要的空间哲学家——他不仅贡献了极为丰富的关涉空间的新概念,而且空间也正是他从事哲学的方式。德勒兹曾言一切事物皆在内在性的平台上发生,他设想出一种巨大的荒漠般的空间,而概念则犹如游牧者一样在其间聚居流散。德勒兹空间化的哲学赋予我们以众多概念:平滑与纹理、游牧与定居、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褶子,以及其他许多使我们进行空间思维的概念。[2]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借用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关于“平滑空间”(smooth space)和“纹理空间”(striated space)的术语,阐发其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指出空间总是混杂着平滑与纹理的力量,这是地理哲学的完美表达。平滑空间既无高潮又无终点,处于不断变化和生成状态,而纹理空间则属于科层化的静态系统。与同质化的纹理空间不同,平滑空间是去中心化的、恒变的、开放的空间,其间充满强度,是新事物不断生成的空间,德勒兹将其定义为游牧空间。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之间既存在简单的对立,也存在复杂的差异,甚至还有双向的混合与转化:“这两种空间事实上只有以混合体的方式才能够存在:平滑空间不断地被转译、转换为纹理化空间;纹理化空间也不断地被逆转为、回复为一个平滑空间。”[3]68在这一双向运动中,平滑空间的纹理化是一个总体化过程的结果,列斐伏尔和哈维所描述的空间的资本化过程,正是它在现代政治经济领域的典型实例。不过,德勒兹更加关注相反的生成,即一个纹理化空间是否以及如何允许一个平滑空间得以展开。[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代的空间哲学与德勒兹的空间思想颇为契合。
此外,德勒兹还创造出“生成”“块茎”“逃逸线”和“游牧思维”等空间概念,以差异哲学对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进行批判。德勒兹强调“生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生成”过程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德勒兹认为,大千世界除了生成之外别无他物,一切存在只不过是生成生命的流动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而生成是异质性因素的运动过程。[5]块茎思维与西方文化传统的树状思维截然不同。块茎是不同于树的另一种植物形态,没有根基,没有逻辑的组织结构,只有自由的伸展与撒播,是流动的、离散的。块茎思维又称游牧思维。
20世纪的空间哲学与美学思想已成为当代人思考空间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更为我们解读维多利亚时期小说《还乡》中的空间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二、纹理空间中的他者
空间是哈代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对人物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还乡》中,埃顿荒原上的家宅、丘陵、山谷、荆棘等,这些空间意象都是纹理空间的象征性描写,是作家对维多利亚女性所处压抑环境的空间隐喻。
尤斯塔西雅的童年是在繁华的海滨城市蓓蕾口度过的,父母去世后,受生活所迫,她不得不随外公迁居埃顿荒原。外公很喜欢这个地方,而她觉得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又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者。“尤斯塔西雅·维伊天生就具有神的秉性,只要稍加准备,她就能在奥林匹斯诸神之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神”。[6]72尽管尤斯塔西雅是哈代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是“夜之女王”,但在威塞克斯空间里,她只是一个被排斥和边缘化的他者。在乡民眼里,她是异教徒的化身,具有黑夜的种种神秘。在古老的埃顿荒原,乡民们深受父权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性应该性情温和,遵循社会礼仪和传统道德。而尤斯塔西雅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渴望繁华都市的生活,渴望音乐、诗歌等令人激动的事物。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秩序,要求女性安分守己,而尤斯塔西雅独立不羁的性格与之形成激烈的冲突。
房舍是维多利亚小说中重要的空间景观,哈代的小说也不例外。哈代小说中的房舍也是纹理空间的典型表征。与尤斯塔西雅相关的房舍,首先是她与外公居住的房子:
外公由于在一次海难事故中断了三根肋骨,便在埃顿荒原这块空气清新的高地上定居下来,由于房子几乎用不着付什么钱,又由于站在家门口能看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的大山间露出的一线蓝色,人们一直相信那就是英吉利海峡,因而这地方能令他产生遐思。然而尤斯塔西雅却很恼恨搬到这地方来,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遭放逐的人,可她又不得不住在这儿。[6]75
外公喜欢荒原,喜欢这所房子,而对尤斯塔西雅来说,这里是她的“放逐”之地。与克莱姆订婚以后,克莱姆的母亲拒绝尤斯塔西雅进入她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尤斯塔西雅再次被剥夺拥有家的权利,再次被他者化。婚后,她和克莱姆租住在荒原边缘的房子里。本来,尤斯塔西雅想要通过跟克莱姆结婚,让他带她离开埃顿荒原,去巴黎生活,但克莱姆并无此意,他回到家乡正是因为他厌倦了喧嚣的城市生活。于是,这所房子依然成为尤斯塔西雅的囚禁之所。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空间的诗学》中,对“家宅”意象做了诗意的解读。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也是构成维多利亚小说空间景观的重要方面。在《还乡》中,房屋是威塞克斯乡民重要的避身之所,要保护其免受来自外部的侵扰。然而,对尤斯塔西雅来说,不管是先前和外公居住的房子,还是后来和克莱姆居住的房子,都不再是巴什拉意义上的安全家宅,而是囚禁之地,阻止她追求浪漫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作为浪漫的个体,尤斯塔西雅被维多利亚传统道德紧紧束缚。有形的房屋成为尤斯塔西雅难以逾越的物理障碍,而它所代表的传统道德成为其精神的枷锁。
尤斯塔西雅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逃离埃顿荒原。她告诉怀尔德夫:“这儿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耻辱,令我死亡!”[6]95
埃顿就是她的地狱,一来到这儿,她的内心就与之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它灰暗的基调中汲取了不少东西。她的外表正是最好不过地表现出了她内心郁结的心理:要与现状作一番抗争;而她的这般受压抑的美貌光彩正是她内心悲哀和被扼杀的热情的表现。她的额上真正显现出一种严峻的威严,这种威严绝非故意做作,或是受到逼迫装出来的,而是在这么些年月里养成的。[6]74
荒原上阴沉、悲凉的景色使尤斯塔西雅感到压抑与束缚,她一直梦想着能够离开荒原。然而,荒原阴郁的气质仿佛已渗透进她的血液,使她难以摆脱。她越是反抗命运,在命运设置的罗网中就陷得越深,离自己的毁灭也越近。尤斯塔西雅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更是因个体与空间(环境)冲突而造成的悲剧。
在《还乡》中,部分自然景观也构成静态的纹理空间,成为尤斯塔西雅生命旅程中的羁绊。埃顿荒原“从古道起便逐渐向荒原腹地上升。它包容着小丘、沟壑、山岭、斜坡,一个接一个向前延伸,直到被迟暮未尽的天际处一座突起的高山所遮挡”。[6]12夜幕降临之时,尤斯塔西雅就站在天际处孤寂的雨冢之上。当她夜间匆匆行走在荒原上的时候,“一丛黑莓挂住了她的裙子,使她不能再迈步前行……等她想到要脱身时,她就左右转动身子,这才挣脱了多刺的树枝”。[6]62在尤斯塔西雅准备逃离荒原的那个雨夜,“她绕过水塘,顺着通向雨冢的小路向前走去,不时会被盘根错节的荆树根、簇簇丛生的灯心草,抑或是漫山遍野都是的厚实的真菌绊一个踉跄”。[6]390
不管是绵延起伏的山丘、沟壑,还是遍布荒原的荆棘、石南,都象征着维多利亚纹理空间的严酷与冷漠。它们仅仅容忍那些默默遵循威塞克斯伦理道德、完全融入埃顿荒原的人,而对尤斯塔西雅这样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则充满敌意。文明之光仿佛无法照进埃顿这片蛮荒之地,尤斯塔西雅也无法挣脱纹理空间的层层束缚,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自然元素之间的“共谋”形成尤斯塔西雅必须面对并努力克服的障碍。[7]72这些自然元素象征着自然神圣不可动摇的威严,也象征着传统和秩序的力量。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握着尤斯塔西雅的命运,并适时给予惩罚。自然作为“命运”的工具而存在,被人格化的埃顿荒原是“命运”的代理人,作为他者的女性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在广阔的自然和宇宙体系中,人类显得如此卑微渺小,其追求主体性的企图被完全吞没。
长期以来男权意识将女性视为第二性、他者,摧毁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强制她们服从男权社会文化所定义的责任和义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男权社会价值体系当中,男人体现了超越性。对他来说,存在就是超越,就是实现自我。而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女人是男权社会中的“绝对他者”,是客体。“对大多数女人来说,超越的道路是封闭的,因为她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无法让自己成为任何一种人。男权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创造了女性绝对他者的神话”。[8]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女性受到重重压制,对感情与物质的欲望都难以得到满足,其意志与追求也无法实现。正是维多利亚传统道德所建构的纹理空间迫使尤斯塔西雅一步步走向悲剧的深渊。
三、平滑空间中的“逃逸”
在《还乡》中,哈代不仅勾勒出以维多利亚传统道德为根基的纹理空间,再现了女性被他者化的形象,而且描绘出与之相对的平滑空间,使女性得以实现想象性的逃逸,从而使读者得以见证纹理空间逐渐瓦解为平滑空间的动态过程。小说中的平滑空间主要表现为“荒原”和“黑夜”两种形态,而这两种空间常常相伴而生。
《还乡》尽管以威塞克斯这个具体的地理空间为背景,但文本所呈现的空间则是无限开放的,尤其强调天空的高远、大地的辽阔,构成小说中浪漫主义的质素,也是小说中平滑空间的最佳表征。小说开篇,哈代不惜笔墨,对古老的埃顿荒原进行了细致描写:
蒙住苍穹的是这片灰白的帐幕,遍布大地的是这片黑苍苍的石南植物,它们在天际处交接,呈现出一条清晰分明的界线。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下,这片荒原不等夜晚按天时自然降临,便早早蒙上了一层夜色……遥远的大地与天际的衔接处看来不仅仅是物质间的分界,而且也成了时间的分界。石南荒原黑苍苍的外貌使夜晚的降临提前了半小时;同样,它能推迟曙光的降临,使正午显得昏暗,使风暴还未降临,便提前显出它那副蹙额狰狞的面目,而在一个漆黑无月的午夜,它则使那片漆黑显得更其骇人。[6]3
在哈代看来,埃顿荒原自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变化,即使是一些“细微不规则的变化也不是因为鹤嘴锄、农耕和锹铲的挖掘所造成,而是因最近的地理变化的轻微触摸所造成”。[6]7这里几乎不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着,拒绝现代文明的压制与束缚,具有某种人类不可抗拒的威慑力,构成小说悲剧性的基调。同时,小说中悲剧性的埃顿荒原也成为拒绝纹理化的平滑空间的重要形式。
伴随荒原意象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尤斯塔西雅。她拥有非凡的美貌和独特的个性,是从“古老宗法制母体中经过长期的内部阵痛后分娩出来的第一个叛逆女性”。[9]小说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位尤斯塔西雅,展现其女神般的气质。虽然在美学意义上已经与荒原融为一体,是荒原“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6]13但实际上她并不属于荒原,而是一个受到现代文明浸染的外来人。尤斯塔西雅由于精神的压抑而感到痛苦不堪,只能靠外出散步来缓解忧郁的心情。“散步时她总是带着她外公的望远镜,还有她外婆的沙漏”,[6]79似乎要把周围的一切从时间和空间上统统克服。哈代将尤斯塔西雅与埃顿荒原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起女性主体与平滑空间之间的同构关系。
在哈代的小说中,外部环境与女性自我情感的表达密切相关。作为绝对他者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受到压抑,而“外部空间和自然与人类对自由的渴望相契合,伴以逃跑或到达地平线所勾勒出的遥远风景的浪漫欲望”。[7]156在《还乡》中,广袤而野性的埃顿荒原常常伴以狂风、暴雨等自然现象,从而构成一个自足的浪漫主义的平滑空间。尤斯塔西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户外的埃顿荒原上,而其中的雨冢是她经常去约会或漫步的地方。野性的自然空间构成小说中的对立于纹理空间的平滑空间,与主人公的内心空间相一致,是其逃离欲望的空间投射。
游牧思维是与平滑空间相对应的思维模式,也是哈代在《还乡》中赋予尤斯塔西雅的思维模式。尤斯塔西雅努力摆脱威塞克斯宗法制社会的纹理空间,常常漫游在解辖域化的埃顿荒原之上,无视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幻想有朝一日能够跨越威塞克斯的边界,从而摆脱维多利亚社会的樊篱,实现她的人生价值。尤斯塔西雅游牧式的“运动”进一步强化了荒原平滑空间的概念。尤斯塔西雅身上所具有的叛逆性,仿佛野性的自然侵入维多利亚式的纹理空间,扰乱且摧毁了维多利亚家宅的原型品格。
尤斯塔西雅在其抗争过程中,勇敢选择了背离传统的“逃逸”。劳伦斯认为尤斯塔西雅是现代女性的先驱,“与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艾米丽、塞得利小姐们作了戏剧性的最后决裂”。[10]《还乡》中多次出现“篝火”的意象,而且都是伴随尤斯塔西雅的出现而出现。明亮的篝火与阴郁的黑夜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突显出尤斯塔西雅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尤斯塔西雅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尽管受制于严格辖域化的纹理空间,但她有足够的勇气对其进行解辖域化。哈代在小说中建构的平滑空间就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表征空间。
尽管尤斯塔西雅的血液里早已渗透荒原忧郁的气质,但对于无法真正融入其中的她来说,开放的平滑空间在给予她逃逸可能性的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将其吞没。在那个暴雨肆虐的夜晚,尤斯塔西雅与怀尔德夫相约一起逃离埃顿荒原,最终却遭遇溺水身亡的悲惨结局,“大自然的一切似乎都披上了黑纱”。[6]389在此,作为女性主体的尤斯塔西雅降格为力求生存的无助个体,承受强大的非理性力量的控制。埃顿荒原是一个平滑的自足空间,消灭任何人类将其纹理化的意图,然而,生活在荒原上的女性不得不屈服于它,并任其摆布。
事实上,恰恰便是在这昏黄转入黑夜的时刻,埃顿荒原那独特而伟大的壮观才真正开始……当夜色降临之时,这块荒原的地形地貌和四周景色便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互相吸引,互相交融的趋势。这片忧郁凄冷的荒原上的圆阜和洼地似乎都挺起身来,真心诚意地迎接夜晚的朦朦昏暗,荒原吐出黑暗,天空倒下黑暗,两方的动作一样迅速。[6]3-4
埃顿荒原与黑夜的联姻共同构成一个广阔的平滑空间,但这个空间最终也被“封闭”起来,“紧密地连成了天地间的整整一片黑暗”,[6]4预示着荒原与黑夜共同编织的平滑空间最终将浪漫主义主人公吞噬的悲剧命运。哈代对平滑空间浓墨重彩的描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荒原上或在黑夜里活动的绝对自由。尽管哈代笔下以埃顿荒原为中心的地理空间都已最大化,但依然受到边界的限制。遥远的地平线作为难以逾越的边界线,成为尘世社会的纹理化之线。哈代小说聚焦于浪漫的意象,勾勒出人物在天空背景上的剪影形象,强调荒原平滑空间的广阔性。但深受纹理化空间束缚的女性最终依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逃逸,唯有构筑“第三空间”,以期女性主体的“生成”。
四、第三空间中女性主体的“生成”
第三空间是一个非实体性的结构,是无形的、抽象的、比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双方或多方相互混合而形成第三方。第三空间并不是一个闭合的、不变的空间,相反,它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吸收新的因素,永远处于变化之中。[11]在《还乡》中,具体有形的物质空间,如巴黎、蓓蕾口、大海等,被赋予象征意义,用来表达第三空间的思想。这些空间与人物身份相互作用,并不断变化,使得此处/彼处、里面/外面、中心/边缘等空间界线变得模糊不清,第三空间由此产生。
“巴黎”在小说中不断出现,但仅仅是作为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意象存在于埃顿荒原之外,是尤斯塔西雅一心向往的地方。然而,她只有通过克莱姆的描述,在想象中感受大都市的魅力。克莱姆向她讲起美丽的小特里阿农宫,那是法国凡尔赛宫花园内的皇家别墅,并告诉她可以乘着月光“在花园里散步”。[6]221他还向她“描绘了枫丹白露,圣克卢,大树林,以及许多巴黎人熟知的常去游逛的地方”。[6]222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都是威塞克斯边界之外的异空间,构成尤斯塔西雅暂居其间的第三空间。
离开蓓蕾口来到荒原生活的日子里,尤斯塔西雅时常回忆起曾经在蓓蕾口度过的美好时光,那里有着明媚的阳光,还有“草地上的浪漫回忆,军队的乐团,军官们”。[6]75尤斯塔西雅向往荒原之外的生活,她所崇拜的偶像是征服者威廉以及拿破仑式的英雄。但在残酷的现实中,她只有在陌生的第三空间里想象性地建构其主体性地位,获取心灵的慰藉。尤斯塔西雅虽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却具有20世纪现代女性的诸多品质,表现出超越时代的追求精神。
“大海”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意象,也是哈代所建构的第三空间的另一种样式,与尤斯塔西雅息息相关。尤斯塔西雅出生在海滨城市蓓蕾口;她的父亲来自希腊西北部伊奥尼亚海中的科弗岛;她的外公曾经是一位老船长,在海上服役多年;尤斯塔西雅从家门口就可以看见遥远的英吉利海峡;站在雨冢之上,她可以眺望“雨冢前的海湾,那片忧郁的克里斯海”。[6]218“大海”的意象同样承载着尤斯塔西雅逃离荒原的渴望,通过想象创造新的环境,挖掘自身的潜力。
爱德华·索亚指出,第三空间概念具有列斐伏尔赋予社会空间的多重含义,它既是一个区别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即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空间,又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12]80“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12]译序13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或可称为第三空间的微观或地方地理学:
可能在每一种文化里,在每一个文明里,还存在一些真实的地方——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在建构社会的进程中形成——它们类似于某种反地点,这是一种表现活跃的乌托邦。真实的地点,以及所有其他能够在文化中发现的真实的地点都同时在这里受到再现、争夺和颠倒。这样的地方外在于一切地方,即使能够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13]
异托邦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它使我们脱离自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历史,都在其中遭受腐蚀”。[12]18异托邦类似于贝伦所谓的“镜像空间”(mirror-space)①福柯在《不同的空间》一文中曾提到镜子异托邦的概念。参见Michael Foucault,Different Spaces:Aesthetics,Method and Epistemology,ed.James Faubion.New York:The New Press,1999.。
威塞克斯小说中的异托邦存在于地平线之外,这些空间具有陌生化及入侵性的现代元素,影响并渗透着埃顿荒原的微观空间结构。
小说中的巴黎、蓓蕾口、大海等这些亦真亦幻的意象,就是超越所有空间的空间。它们无所不在,但作者从未在空间上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只是人物在话语间偶尔会提到的地方。这些朦胧的空间意象是哈代在小说中想象性建构的产物,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对于作品中的人物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这些想象与真实并存的开放空间里,威塞克斯女性得以摆脱身份的困扰,“生成”女性主体。“生成”不是最终的或间歇性的产品,它是变化的原动力。[14]正如巴什拉所说:“一个家宅的梦想者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家宅。”[15]只有在想象与记忆中,在地平线以外的世界里,尤斯塔西雅才能够投递自己的梦想与渴望。
尤斯塔西雅像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她无视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义无反顾地追求浪漫的爱情与幸福的生活。她心目中的爱情表现出超越世俗的自然生命力,其反叛行为背离了人们对传统女性的期待,打破了父权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规范,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以及对自我主体性的坚决捍卫。在德勒兹的空间理论中,去疆域化既是一个创造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过程。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向未知的领域开拓,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去疆域化,这是构成德勒兹游牧思想的核心。对尤斯塔西雅来说,去疆域化就在于对第三空间的不断探索,对女性主体的孜孜以求。
尤斯塔西雅和传统的荒原女性完全不同。在和男性的关系中,她也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在这方面,尤斯塔西雅颠覆了男性在情感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差异性中重新诠释了身份的表演性①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提出表演性主体的概念,以此解释性别的建构过程,她的性别理论揭示出身份的表演性特征。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为女性突破身份界限开拓了新的空间,为建构女性主体提供了更多可能。关于表演性概念,详见Loxley,James.Performativ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身份需要不断重复的表演,这一重复同时也是对既定意义的重新演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份就是一种创造,一种想象性的建构”。[16]9为了接近克莱姆,她女扮男装代替查理去参加假面戏演出,扮演土耳其骑士的角色。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主题意义,是身份表演性的典型案例。
哈代在小说中对尤斯塔西雅身份的描写变幻莫测,从“夜之女王”,到奥林匹斯诸神之国的“女神”不等。“在周围沉沉一色的夜幕映衬下,她的脸部侧影显露出来;看上去就好像萨福和西登斯夫人的侧影复活,复合成一个既不像两个本人,却又能表明是这两个人的人”。[6]60萨福是古希腊女诗人,以美丽、诗才和情爱著称;西登斯夫人是英国著名悲剧演员,英国画家伦那尔兹曾为她作画,称之为“悲剧诗神”。这些描写无不揭示出尤斯塔西雅身份的表演性特征。
德勒兹强调“生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一种生成缺乏一个不同于其自身的主体;同样,它也不具有终项,因为它的终项只有在介入于另一种生成(它构成了此种生成的主体)之中时才能存在,而这另一种生成与前一种生成并存并形成了一个断块。按照这种原则,存在着一种生成所特有的真实性”。[13]335哈代主张主体的重新创造。他赋予尤斯塔西雅不同的身份,使她通过不断变换的重复,创造差异,从而揭示出自我无限的可能性,表明主体是一个永无休止的“生成”过程。这一“生成”是一个可持续的、创造性的过程,指向全新的未知领域,是一种模糊内部和外部之间界限的运动。
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空间是一个虚构的王国,而威塞克斯边界之外那个以巴黎为代表的世界,只是一个朦胧的意象,并未真正出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在尤斯塔西雅身上体现了女性追寻自我的内心诉求,但她溺水身亡的悲剧性结局表明,维多利亚女性实现自我的道路是封闭的。唯有在审美意义的第三空间,她才得以建构其主体性身份。《还乡》不仅揭示了平滑空间被纹理化的空间所捕获和包含的事实,而且演绎了平滑空间在纹理空间中得以展开的情景,同时建构了真实与想象并存的第三空间,见证了女性主体创造性的生成过程。哈代想象性地建构了威塞克斯这个古老的王国,揭示了地理景观的叙事功能,其中蕴含着作者独特的空间哲学思想,从而实现地理学与美学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