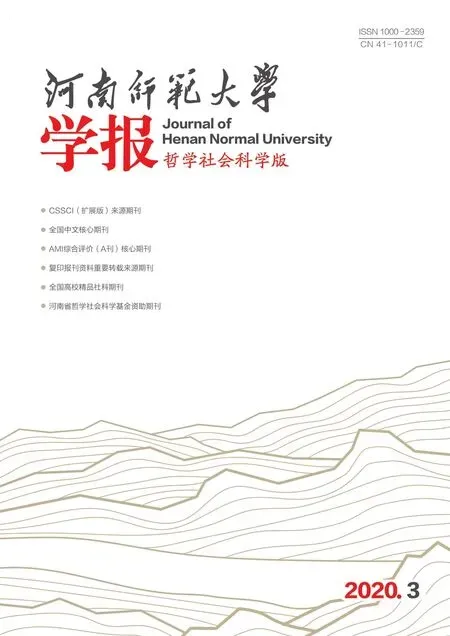补偿型经纪:村干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角色定位
——基于苏北B村资本下乡过程的分析
吴晓燕,朱浩阳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1)
乡村振兴是中央围绕“三农”问题而作出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总要求,诸多资本资源也趁此机会纷纷“下乡”。其中,社会资本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是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元素[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构建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388086885016282&wfr=spider&for=pc.。资本下乡的过程中涉及村民、村干部、基层政府、外来资本等多重治理主体,资本下乡促使城乡间要素流动不断加快,农村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因此,在农村社会分化以及村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的背景下,要处理好村干部承担的多重角色关系,厘清支配村干部行为逻辑的价值趋向。
一、村干部行为角色的研究进路
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架构中,村干部在衔接政府与农民关系,夯实农村群众自治以及分配社会公共资源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其行为角色的定位一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经纪理论”与“双重角色理论”。这两种理论均利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将研究置于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以及税费改革大背景之中,获得了对村干部这一基层行为主体的理论界定和经验认知。
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传统乡村是绅治的,“由村内家族中具有威信的人领导。而这些人一般都向村庄而不向国家官僚机构认同”[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4年,第254页。。在“国家-士绅-农民”这一框架下,杜赞奇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自晚清至民国村社精英经历了由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的蜕变。“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我称这种‘国家经纪’为赢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赢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是抢夺者)打交道”[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页。。因此,“经纪理论成为分析晚清至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经典框架,以至于一些学者在研究税费时期村干部的收入及其行为模式时,仍借用这一概念”[注]贺雪峰,阿古智子:《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在借鉴经纪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村治经验,形成了解释村干部行为模式的双重角色理论。徐勇在承接费孝通“双轨政治”[注]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8页。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村干部在贯彻政府行政事务和村民自治任务时摇摆于‘政府代理人’与‘村民当家人’之间”[注]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但这也极易造成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使其“陷入国家与农民夹缝中的结构性两难境地”[注]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页。,以致在实践中面临政府体制和农民社会的“双重边缘化”问题,“既为两者所需要,却又无法为两者真正接纳,只能在结构的夹缝之中讨生活、求利益”[注]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
近些年来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富人治村”现象在一些地方也越发普遍。围绕富人治村现象及其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形成了两种观点: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富人治村是对“传统乡绅治理的传承与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注]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对此表示质疑的学者认为富人治村“从长远看隐藏着较大的治理风险,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村庄和谐共治及村级‘四个民主’建设等重大治理主题会带来隐忧”[注]韩鹏云:《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4期。。另有学者根据农村分化程度的不同,“将富人治村的类型划分为阶层分化村庄的富人治村和去阶层分化村庄的富人治村”[注]刘磊:《农村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类型及其影响》,《人文杂志》,2016年第12期。,这两种类型的村庄在形成机制、形式特征以及治理效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年来,围绕富人治村的研究更为具体化以及类型化,一方面是不再仅仅将富人治村笼统归为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以及中西部资源禀赋型农村这两大分类,而是针对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比如有学者“根据国家权力在基层配置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资本主导、行政主导以及公共规则主导三种类型”[注]仇叶:《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1期。。另有研究将富人治村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注]陈柏峰:《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等类别。同时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个案研究的经验事实提取出诸如“悬浮型村庄治理”[注]朱战辉:《富人治村与悬浮型村级治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形式化民主”[注]冷波:《形式化民主: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再认识》,《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新的分析框架,不断丰富“富人治村”的理论内涵。
本研究在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融入资本因素,将村干部的行为分析与角色类型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并以苏北B村的资本下乡实践为考察对象,展现资本要素在介入村庄社会后的治理样态,以发掘处于上级行政压力与乡规民约之间的村干部在行为逻辑及功能特征上的不同面相。
二、资本下乡背景的村治逻辑与治理实态
资本下乡的结果主要落在两类项目上,首先是工商资本深度参与农村社区改造以获得节余建设用地的使用价值,最终落实到以“农民上楼”为主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其次是各类工商资本帮助基层政府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所涉及的惠农有关的各类项目[注]张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3期。。多类惠农项目的“落地”都要以当地村治生态为参照,在压力型体制架构中实现资本下乡的强农逻辑。
(一)“两族平衡”下B村的村治生态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村干部处于整个行政架构的末梢。科层结构的运行模式造成村干部处于刚性稳定与自主性发展这一张力之中,显然,这是韦伯式经典命题的理论延续过程[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4页。。在整个村庄治理生态中,村干部不仅要承接各类普惠性的惠农项目,而且还要负责各种项目资本的分配。村主任和村支书共同掌握权力资源分配的执行权和决定权,但二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B村表现得可谓明显。
B村[注]依照学术规范,本文所涉及的地名及人名(包括姓氏)均做了技术处理。位于苏北腹地,农民均以种地为生,打工潮的兴起导致村庄“空心化”现象愈发凸显。该村属于较为典型的“两族平衡村”——以张、金二姓为主,村治格局也融入了较强的宗族色彩。传统乡土社会沿袭一套伦理本位的内生性自治模式,这种内生性的模式主要依托宗族社会的调节机制和伦理教化途径实现村治生态的平衡。在B村的历次选举中,由于两族势力相当,竞选非常激烈,即便其中一方以微弱优势当选,也很难得到另一方的承认与合作,由此形成了金、张两姓“轮流坐庄”为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村治格局。
就B村而言,“村内宗族格局与宗族在选举上的影响力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宗族越是集中对垒的村,宗族对选举的影响越强。实力对比鲜明的宗族格局,容易形成边界分明的宗族关系,从而引发宗族矛盾,并强化宗族之间的自我意识和内聚力”[注]肖唐镖:《村民选举“宗族势力干扰论”可以休矣》,《人民论坛》,2011年第8期。。即正是在宗族势力集中对垒的村庄,更容易强化各自的宗族意识。因此,在项目下村的大背景下,村支书和村主任以“轮流坐庄”的合作方式给全村带来了现实的经济效益,却仍未改变宗族势力影响下的村治格局。
(二)压力型体制下村干部参与资本下乡的过程
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注]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而后,此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对各层级政府的运行绩效与行为逻辑的研究中。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任务,纷纷采用数量化分解和奖惩相结合的一套治理手段和管理方式,获取助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项目成为村干部开展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因此,唯有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密切配合”,才能争取到上级“规定”的各类项目资源,在压力型体制下提升项目运作的效率。
B村引入的W[注]W公司是其母公司H公司为涉足农业项域而专门注册的一家子公司,H公司的主业是房地产。公司主要经营农产品的深加工及销售。在资本下乡中,由于优质非农资源很难流向农村,因此带有附加条件性质的资本进入也为地方所默认。村支书和村主任深刻意识到“资本兴村”的重要性,他们力图通过土地流转,并对一些分散的宅基地进行了置换,以实现土地的连片经营。同时在充分比较周边区域的产业结构,以及做了大量市场调研和论证之后,将B村定位为药材种植基地,以期带动B村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但由于两委班子代表两个家族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并直接导致土地流转难以推进,导致最初项目计划被搁浅。最后在时任村支书张某自己出一部分资金与W公司合作推进B村药材种植项目后,并在时任镇党委委书记的亲自“过问”和协调下,才使这一农业合资经营协议达成,之前的合作僵局也得以成功化解。由于药材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基本解决土地流转之后村民的就业问题,以弥补之前因租金过低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因此这一项目最终落地,也基本实现了地方政府、下乡资本、村干部以及村民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均衡。
三、村干部权力实践中的“背景资本”及其行为逻辑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基层政府、村干部和资本资源共同结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来落实上级政府的强农意志。当前的乡土中国并非完全是一个抽象而统一的乡村,为了获取国家资源下乡的惠农资源,各类资本项目的发包和落实与各级干部各自的“背景资本”休戚相关,村干部同样被赋予了“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注]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但是,村干部会“主动”选择与政府有一定“背景”的项目,以期推动资本下乡的顺利开展。
(一)乡村振兴乡中的“背景资本”
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工商资本中的龙头企业来引领,以推进土地流转并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这类龙头企业大都由一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而来,由此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由于这类资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更容易获得主要领导的关照和相关政策优惠,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参与B村资本下乡的W公司就具有这类“背景资本”的基本特点。B公司是当地县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下属乡镇基本都与此企业有项目合作关系,涉及的资本扶持类型主要是农产品深加工和土地流转等多项惠农项目。B公司借助与政府及主要领导私人关系的桥接,在具体的资本实践中,通过相关领导的“打招呼”,从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被“庇护”[注]陈尧:《庇护关系:一种政治交换的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在政治生活中,庇护关系也是构成非正式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对于“庇护”和“庇护关系”,斯科特从人类学视野中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包含了工具性友谊的特殊双边联系,拥有较高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庇护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资源为地位较低者(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及恩惠,而被保护者则回报一般性支持与服侍。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当前的政商关系中,这样的庇护关系更符合施耐德(Aaron Schneider)对此的解释,他认为庇护关系必须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去探究,庇护关系根源于资源汲取和经济依附的关系,被庇护者不得不依赖庇护者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如土地、工作或基本服务。被庇护者不得不从庇护者那里获得好处,实际上加强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庇护者仅通过提供基本的庇护品,却能从被庇护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剩余。在政治上,庇护关系表现为庇护者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庇护者通过关闭公共渠道、排除竞争者和限制政治参与等,从而消除竞争性权威,达致统治公共生活的目的。。在资本下乡中,由于土地集体产权模糊,导致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新增利益的归属问题,也无法完全界定清楚。由此,收益的分配更取决于产权实施主体的力量强弱,能力强的主体则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制度性的模糊导致资本在与权力形成狭隘的共生利益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行为选择空间。
据B村的村支书回忆,W公司在获取政府农业补贴方面“很有办法”,同时他列举了下乡资本主要的非农化经营手段:一是“只圈不用”,利用可以预期的土地增值来赚取差价;二是利用自身优势和便利承担或转包村里的一些基建项目,如修路建桥、土地平整及大棚搭建等工程;三是获取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和其他直接补贴。如果没有这些营利手段,仅靠企业自身发展,大多是“走不长的”。由于一些涉农企业的目的主要并不是在农业生产领域获益,而是在非生产性的再分配与土地经营中获益,因而其农业经营与管理能力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就不是地方政府在推动资本下乡时考量的关键因素。
尽管B村的涉农系列工作都围绕着推动资本下乡而展开,但在与农民的接触及与村干部的协调中,资本却“隐没于流转土地的后台,成为一个使之影响于前台的重要后台力量”[注]冯小:《资本下乡的策略选择与资源动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化约为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隐形资本”,成为区别于普通资本的重要标签。在规范性的合同文本签订之前,它更倾向于采用非正式的交易规则推动自身目的的实现,而这是前台的正式规则和程序无法触及的。因此,前台所呈现的均是规范的法律文本、标准化的程序操作以及公开的流转过程,但其在乡村社会得以顺利运作的关键却是运用非正式规则建立与主要领导的关系,打通双方合作或结盟的利益点,以在政府主控的治理形态下获得政策关照。由于具有官方背景的资本更熟悉政府的运作体制与逻辑,更清楚政府的关注点,因而更容易抓住其要害而占用更多的财政资源。
(二)“背景资本”助推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
在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格局下,政治理性支配着资本下乡的行动路径。王海娟指出,“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在形式上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尤其是逐级淘汰的晋升制使地方政府有政治动力不计成本地投入财政资金推动资本下乡。这表明农业企业不是以经济优势进入到农村市场竞争中,而是以政治逻辑参与到政治锦标赛的竞争中”[注]王海娟:《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锦标赛体制作为中国特殊的政府治理模式,其内驱力是压力型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通过行政体系的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将上级政府界定的标准要求与下级官员的切身利益捆绑在一起,催生出官员特殊的激励模式与动力机制。上级党委政府为突出某一工作的重要性,就将其定性为“政治任务”,以督促下级政府高度重视,并通过目标责任制保证政策的落实和目标的达成。
B村所在的县、乡政府就将“大力推进农业示范区项目”确定为本地区的“政治任务”,试图将其打造为亮点工程,并通过科层体制分解任务,引导资源配置流向,实行“一票否决”,集中人力、财力动员资本下乡。由于资本可以有效整合高度分散的农民,其形成的规模效应更有利于对接政府的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因而容易得到上级青睐。上级越重视的任务,在政绩提升中所占的权重也越大。为了获得稀缺的晋升指标及向上争取项目资源,基层干部往往积极主动地配合土地流转,引导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以下乡资本为杠杆撬动经济发展。
由此,权力与资本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合作。市场主体通过积极响应地方主要官员提出的政治任务,并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实现对权力的依附或联合,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从形式上看,因纯农业收益不高,W公司的经营行为是违背经济理性的,但其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还是经济利益,以政治任务为出发点,以配合政府工程为基本路径,从而实现对经济理性的“杠杆化”,这也符合资本的逐利属性。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任务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资本的具体实践过程是通过地方权力来推动的。由于资本获得了正式权威的支持,并形成紧密相连的“权力—利益”网络,进而通过经济与政治力量重组村庄社会的治理结构。这样,整个村社生态就被动地卷入到围绕资本下乡而开展的一系列行动中,并接受多方主体的“洗礼”与再造。
政府与资本的利益衔接机制使其打通了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渠道,同时凭借某种“私人”关系或利益关联具备了吸纳正式权威的强大能力。H公司前期通过种种渠道很快与新来的市委领导“搭上线”,展现出资本在与政府沟通中的高度娴熟,并最终得到了主管领导对其项目的支持。由此,H公司如愿将新成立的W公司像“邮包”一样置于行政序列的“传送带”上,并借用政府的正式力量顺利实现无阻碍的自由传送。这样,在前期运作中,资本无须直接与农户接触,而是借助行政过程中的压力体制与村干部的正式权威,建立与农户沟通的桥梁,并利用农户的信息不对称与分散化特点,单方面确定流转价格与程序性规则。由于资本与权力的团体规模相对较小,更容易协调一致,进而达成集体行动。这样,资本通过与政府的非正式利益联盟,并借助压力体制分化村社力量,加速推进土地流转。
四、补偿型经纪:乡村振兴实践中村干部角色的尝试性解释
在一些“富人治村”的村庄,置身于压力型体制之中的外生型村干部并非仅仅处于“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二元角色之中,即在上级领导与村民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但在两者利益无法兼顾的情况下,村干部更倾向于服从上级利益,以此保全自己的利益,即出现向“赢利型经纪”角色转变的村干部基于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通过向村集体进行一定的资本输入,从而实现地方政府、下乡资本和村民间的利益均衡,由此“补偿型经纪”的村干部角色类型得以建构。
(一)置于资本与体制双重压力下的村干部
从B村的实践可以看出,在资本下乡中,政府的政治逻辑而非资本的商业逻辑在支配着村庄治理的具体形态。在压力型体制运转中,上级官员通过层层加压的形式将任务分解和细化,并通过科层体制的指令性计划实现压力传导。资本下乡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无形中也充当了压力传导的恰当“介质”,强化了压力体制的运转力度。与资本下乡相关的企业、各级干部都处于压力传导的不同链条中,维持着压力体制的运行。资本下乡是服务于压力型体制的,因为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是压力型体制的核心要旨,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锦标赛中官员们的政绩。由此也导致尽管一些下乡资本并没有带来实际效益,但各级干部出于政治考量仍不计成本地推动资本下乡。
在压力型体制形塑的基层政治场域中,村干部不仅在组织、动员农民同意土地流转等关键性工作中要围绕上级界定的政治任务而展开配合性行动,而且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由村干部凭借个人资源予以解决。村干部虽然并不隶属于正式的科层体制,但在村庄行政化日益强化的背景下,村干部具有承接、支持和协助上级交办的事项的行政职能,其行为也容易受体制性压力的影响,导致其在选择行为策略时并不将经济利益纳入首要的考量因素,而更多地遵循政治理性及对上级的义务。从B村的实践看,在与W公司合作的问题上,时任村支书张某所感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上级政府,并以上级主管领导透过“一定渠道”(而非通过科层体系以文件形式进行传达)“打招呼”实现了压力传导。虽然领导的“打招呼”并非正式文件,但其压力传导效力在一定程度上要超过“红头文件”。
(二)补偿型经纪——基于调和村资利益冲突[注]指村民或村庄与下乡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村资利益冲突”,后文“村资矛盾”的表述,亦指村民或村庄与下乡资本之间的矛盾。的尝试性解释
在杜赞奇的经纪理论框架中,“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所发生的蜕变,乃是在国家权力深入,战乱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联合作用下,迫使“传统的乡村领袖纷纷躲避公职”的结果。“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是造成乡绅‘退位’的主要原因”[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村干部受着压力体制与乡土规则的双重约束,习惯于采取“两头一致”的策略,即在上级领导与村民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但在两者利益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上级利益,以此保全自己的利益,即出现向“赢利型经纪”的角色转变。
B村作为“富人治村”的典型,一定程度上符合“保护型经纪”的基本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时任村支书张某以村社利益为重的行为逻辑上。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杜赞奇在提出“双重经纪”这一理论时,也附加了一定的时代背景,之所以导致“保护型经纪”的退出,其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持续推进以至于国家权力对村庄社会的不断渗透,从而打破了传统“皇权不下县”的“双轨政治”模式,由此以传统乡绅为代表的“保护型经纪”也自然失去了联结皇权与基层社会的媒介作用,破坏了村庄传统的文化网络。反观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既有格局,尤其是深植于“压力型体制”的背景之下,村庄社会自然难以独善其身,故而将经典的“保护型经纪”理论解释投射到当前的治理生态之中显然难以反映其真实样态,以此对照本个案也是如此。张某选择自己出资介入到村民与资本间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之中,并最终实现了地方权力、下乡资本、村干部以及村民的四方利益均衡,其特点既不为“保护型经纪”的解释所涵盖,更与“赢利型经纪”的基本特征相左,为此需要在此方面寻求一些新的理论解释。
本文提出“补偿型经纪”这一概念旨在解释个案中基于“压力型体制”背景下“富人治村”实践中外生型村干部的角色呈现。干部为村民服务的宗旨和制度要求不允许他们演化成“赢利型经纪”,村庄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和上级政府政治任务的压力传导,让他们又不能完全以村庄利益为唯一准则。为此,不得不在村庄权益、资本利益和上级任务之间寻求平衡,必要时要利用个人经济资源来化解村庄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弥合村民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歧,达成地方政府、下乡资本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均衡,进而使自己成为资本下乡实践中的黏合剂。即是说,村干部利用个人资源和治理技术对村庄和村民利益做了一定意义上的“补偿”,通过弥合村民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歧,完成了地方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政治任务,客观上也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当然,村干部得到的是政治资本、政治资源积累的“补偿”,使其治村实践同时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村民的认同。
从B村资本下乡这一微观案例可以看出,资本下乡的具体实践是在资本、地方政府与村干部的共同参与中发展和演进的,其中资本通过借助科层体制的压力逻辑实现了对村庄社会的嵌入,并对村干部产生了巨大的形塑作用,促使其功能角色产生分化。在下乡资本与村社共同体的对接和互动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行动策略与利益结构既相互博弈,又相互融合,促使资本在运作实践中不断吸纳正式权威,重组和再构基层社会治理形态,最终使村干部行为角色演变为“补偿型经纪”这一类型。这一类型并非村干部的理想角色定位,但其客观上有助于增强在压力型体制下村社组织实现因地制宜发展的自主性,调和村资利益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根除下乡资本“悬浮化”的痼疾,从而实现其由外生型向内生型资源的合理转变。
结合本个案的相关经验素材,补偿型经纪的形成一般需要三大基本要素:首先,压力型体制是建构补偿型经纪的外部因素,正是在这一体制下,相关的发展任务会自上而下并最终传导至基层社会,并且在当前村民自治程度仍稍显不足的背景下,村干部很难达致“保护型经纪”的基本要求。其次“自我实现型”[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在本个案中张某选择回乡担任村支书并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符合“自我实现”这一需求层级的基本特点。的村干部是形塑补偿型经纪的核心要素,即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仍主要以村社的公共利益为重并基于自身价值的自我实现。再次,拥有可观的经济资源是成为“补偿型经纪”的基础条件,正是由于具备这一显著优势才可以将此作为调和村资矛盾的后盾。因此,补偿型经纪承担着乡村治理中的“止压阀”“粘合剂”角色,尤其是在当前偏重于政治规训的治理生态下,这一角色通过一定的资源输入,可以有效化解资本下乡中的利益冲突,让资本下乡最终落地。
五、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要达成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农业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下乡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组织载体,更需要大量的人才流入乡村,引领乡村社会发展。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外出求学、务工以及定居,导致农村治理主体以及生产主体严重阙如,而这也成为制约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党中央强调,在坚持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下,要进一步拓宽村干部选任渠道,注重从致富能手、回乡知识青年、务工经商人员等人群中选拔村干部。因此如何扶持和引导更多的、拥有各种资源的“新乡贤”返乡并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这一重大战略中,需要在体制及机制上予以切实的保障、鼓励和规制,以实现人才对乡村社会的“回流”与“反哺”,并带动其他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进而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同时,随着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一些资本进入农村,如何规制这些资本及其代理人,让资本成为乡村发展的助推剂而非新的资源汲取者,尤其是规制那些拥有资本的村干部,使其合理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带动村庄发展,是富人治村实践中的现实要求。上述B村资本下乡实践中村干部角色的塑造与变化在一定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激励、引导、规制和监督的方向。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后扶贫时代项目制在基层的施用将更加倾向于普惠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要继续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家项目下乡的惠农强农初衷,按照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一肩挑”[注]中央文件再度明确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https://www.sohu.com/a/338125602_260616.的规定,不断消解村干部“代理人”“当家人”的角色冲突,乡村治理才能正本清源回归良善秩序,实现既稳定又富裕的乡村振兴愿景。
CompensationBroker:theRoleofVillageCadresintheStrategyofRuralRevital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B village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Wu Xiaoyan,Zhu Haoyang
(Party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Chengdu 610071,China)
Abstract:in the central top-level design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ual driv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farmers’ demand promotes the gradual infiltration of all kinds of capital resources into the field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village cadres who lead the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village cadres in rural construc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basically focused on the ideas of “dual role” and “brokerage mode”. However, in some villages where the rich govern villages, the exogenous village cadres in the pressure type system are not only in the dual role of “protective brokerage” and “profit-making brokerage”, that is, to maintain a certain role between the superior leaders and the villagers A balance of degrees. However, when the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cannot be considered, village cadres are more inclined to obey the interests of their superiors, so as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That is to say, village cadres who have changed to the role of “profit broker” based on their own economic resources, through certain capital input to the village collective, so a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mong local government, rural capital and village folk, thus “compensation type” The role type of the village cadres of “brokerage” can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compensation brokerage;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village cad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