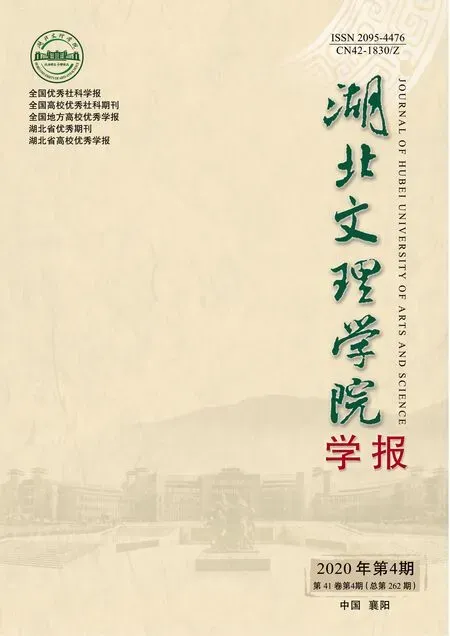Morpheme与语素、偏旁比较研究
张丁祺,朱 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Morpheme在英语中的定义是“Smallest unit of linguistic meaning or function”,即“最小的语义或功能单位”。Morpheme有两种类型,分别为“free morpheme”和“bound morpheme”。Free morpheme可以独立成词,或在组词过程中充当stem,例如:“open”“tour”。Bound morpheme则需附着在其他语言形式上才能成词,往往以affixe的形式出现,例如:“re-”“-ist”“-ed”“-s”等。
《马氏文通》仿照西方语言研究模式建立起汉语语法体系,奠定了汉语“词本位”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学界普遍认为汉语中与morpheme相对应的语言单位应当是“语素”。但经过具体分析,语素和morpheme之间虽有很多相似但仍存在诸多差异,而作为文字学研究领域下的“偏旁”虽与morpheme不属同一体系,却存在诸多对应,我们对此展开以下比较。
一
普遍观点认为,在汉语中与“morpheme”相对应的语言单位应当是语素。从词本位的宏观角度来说,两者确实都是组成词的基础单位。但在具体的语法和语用层面,笔者认为它们并不能完全对应。
从定义来看,语素的定义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morpheme的定义翻译过来是“最小的语义或功能单位”。这两个定义涉及语义、语音两个层面。
然而,morpheme定义中的“linguistic meanging”和语素定义中的“语义”完全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些bound morpheme:“ion-”表示动词的名词化,“re-”表示重复,“-ist”表示“……家”,“ex-”表示“前……”这些affixe所表示的“意义”不是一种准确的意义,它是一种意义的“趋向”,它具体表示什么意义取决于和什么stem进行组合,比如“review”表示“复习”,“pianist”表示“钢琴家”。所以说morpheme定义中的meanging所表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词本身的意思。汉语中语素的语义则是准确的、单一的,比如说“打”“玻璃”。因此,汉语语素的“语义”只能和free morpheme的“meanging”对应,而不能和bound morpheme的“meanging”对应。
在“语音”层面,也需要分类讨论。Bound morpheme不能单独发音,只有在附着成词后才具有整体语音,并且根据附着对象的不同,发音也可能不同。Free morpheme则有准确的语音,与语素一致。
除了语音、语义的层面,morpheme和语素在“判定”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在英语中,想要辨别出哪些是morpheme、有多少morpheme是很容易的,并且几乎不存在争论。但对于语素的判定并不是直接的,往往需要一个思维过程。在漫长的语言研究历程中,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诸多判断语素的方法,比如较为常见的“同形替代”法:如果一个语言结构AB可以用C替代A,也可以用D替代B,那么我们可以确定A、B的语法性质为词[1]。
语素的不确定性也是汉语词本位理论的困境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词类划分的问题,例如,该将副词归入实词还是虚词仍是语言学界至今争议颇大的问题;再者,复合构词法中的并列式、偏正式等几种类型的划分也可能重合,并且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而英语中,词类和句子很容易判断,比如其副词有明显的-ly作为词缀标志,句子有严谨的结构特征,因而划分显得轻而易举[2]。
姜望琪先生曾经从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一些中英语言概念的差别进行了阐释[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解释morpheme和语素的判定问题。Morpheme是抽象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有固定的数量和形式的限制。而语素和词句间存在“实现关系”[4],是被实际使用的,应当被看作“动态单位”。根据语用组合的不同,语素的数量和意义也不同。同理,sentence和句子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是中西语言学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二
偏旁,是指对合体字进行切分后得到的某个部分。以前称合体字的左方为“偏”,右方为“旁”;现在把合体字的组成部分统称为“偏旁”。偏旁分为“声旁”和“形旁”。形旁可以表示该字的大体意义,声旁则能体现出读音的相关性。
偏旁和morpheme的比较需要建立在合体字和兼有两种morpheme的英文单词的基础上。
形旁和morpheme的作用在一定层面上是相似的——它有固定数量,并且能表示该字的大体意义。例如:“金字旁”表示金属,可以衍生出“铜”“铁”“锅”等字;“木字旁”表示树木,可以衍生出“桂”“梅”“枫”等字……
不过,具体分析下来,形旁的表意和morpheme的表意也有细微差别。形旁表示的是事物的属性,比如金字旁、木字旁、提手旁、言字旁……在兼有两种morpheme的英文单词中,bound morpheme表示一种意义的趋向,比如“-ist”表示“……家”,“ex-”表示“前……”。Free morpheme则是传达单词的基本义,例如“tourist”中的“tour”,“friendship”中的“friend”。
形旁有没有语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形旁往往由独体字演化而来,比如“金”到“钅”,“水”到“氵”的变化。笔者认为,当汉字演变为形符,它就不再是原本的汉字了,只充当一个表意符号,它自身的语音也随之消失了。并且在绝大部分汉字中,形旁本体的发音与汉字发音都没有关联,也应证了形旁不具有表音特性。
声旁则是汉语中较为特殊的存在,它能起到表音的作用。声旁小部分是全表音,这意味着该字的整体读音和声旁完全一致,比如“芳”读“方”音;大部分是半表音——即声调不同或声母不同,比如“访”“放”之于“方”变了声调。和英语相比较,free morpheme有准确的语音,并且在组词过程中仍然发原音或存在细微变音。Bound morpheme没有独立发音,只有在附着成词后才具有整体语音,并且根据附着对象的不同,发音也可能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汉字中,有不到10%的汉字不属形声字范畴。汉字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古至今,汉字构型历经多次断裂式、跳跃式改变;现代简化汉字的过程中,也使用了大量改换偏旁、符号代替等方法,这不同程度地割裂了汉字的形义关系[5],造成某些字的偏旁表意作用弱化甚至丧失。比如:“养”是“養”的简化字,繁体形符为从“食”以示“供养”;“厦”,《说文新附考》:“廈,屋也。从广,夏声。”除此之外,汉字发音同样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声旁在现代表音并不准确,按声旁读音会读错,这也是应该注意的。同理,英语同样经历着复杂的演化过程,bound morpheme在某些单词中表意作用的模糊也是演化的结果,在此不多赘述。
将偏旁和morpheme进行比较还不得不涉及基本语言单位的争议。Morpheme是词本位领域的概念,而偏旁则是字本位领域的概念。这就决定了它们在语用功能方面的差异。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形旁、声旁赋予字语音或语义,bound morpheme则能改变单词的语音、语义及词性。比如,加上后缀“-ly”能使名词形容词化、副词化,加上“-ment”“-tion”则能使动词名词化。
不过,Word和字虽然不属于同一研究领域,但它们的构成有很大相似。Morpheme和偏旁作为基本单位,都是通过“复合”“派生”等方法构成Word和字的。这是两个语言系统的一个相似之处,也是偏旁和morpheme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
关于“语素和偏旁谁才是与morpheme相对应的语言单位”这一争论,根本分歧在于,汉语中语素和偏旁谁才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实际上汉语语素和偏旁皆具有音义特征,只是“音”“义”的层面不同——语素有准确发音和准确意义,而偏旁具备表音、表意的结构成分。对于“最小”的判断,也存在角度和立场的因素,即语素是语用层面上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偏旁可以称作结构层面上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不仅是汉语的语言学概念,英语的morpheme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类型的morpheme“音”“义”特征也不尽相同,需要分类讨论。
这些比较研究深刻地体现出了语言的民族性。不同民族的语言学概念之间存在诸多语法、语用、形式上的差异,同一语言概念也能从不同层面去理解。因此,所有语言研究都应当落到实处,在对比中研究,在运用中研究,明晰它的统一性与独立性。不管是建立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体系还是进行语言比较时,语言概念都不能生搬硬套,必须考虑到己方特点,提倡对比、借鉴的研究思路,才能走得长远。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