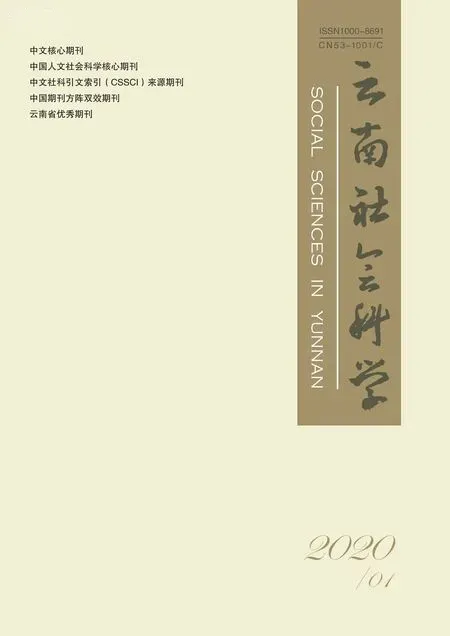遗产过程的两分路径:“成为遗产”和“成为遗产之后”
尹 凯
一、问题的提出:被表述的遗产
从最初的含义来看,遗产(heritage)指的是继承物和继承事实①根据《简编牛津英语词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词条来看,遗产指的是已经继承或可以继承;继承和世袭继承的事实;给予和接受的恰当所有物;继承的任何份额。。遗产研究中的遗产概念虽与之大相径庭,但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稳定属性和祖产的不可分割性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继承与延续,即假定物件、地方与实践的固有价值。这种“遗产自决”的理念并未将遗产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与主观情感有关的文化体系,颇有德国浪漫主义之风。
随后,以《威尼斯宪章》(1964)、《世界遗产公约》(1972)为代表的国际文件构成了遗产认知的权威与标准。这些国际文件和官方标准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将普世主义确立为全球伦理的基本法则。②UNESCO,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Pairs: UNESCO Publishing House, 1995, P﹒ 46﹒就遗产而言,普世主义价值体系制造了遗产的二元结构关系:地方的、直觉的、经验的、属于文化领域的遗产和认知的、理性的、全球的、属于文明领域的遗产。③Thomas Ericksen,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A Critical of the UNESCO Concept of Culture,” in Jane Cowen﹒ed﹒,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7;Robert Shepherd,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and the Chinese State: Whose Heritage and for Whom,” Heritage Management, Vol﹒2, issue﹒1(Spring 2009), PP﹒ 55-61﹒从“遗产自决”到“遗产名录”不仅意味着名相的变更,而且重置了遗产认知与阐释的背后逻辑,即千姿百态的遗产样态和不证自明的价值被等级结构与技术权威所裹挟。由此,一种基于西方进步观念和文明演进的遗产合法性建构起来,并成为有关遗产及其价值的保护、分类与认定的典范。随后的剧情围绕着遗产的二元结构关系铺陈开来。基于“文化”与“非西方”的遗产观念质疑基于“文明”和“西方”的遗产论调,并最终实现了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在国际层面上的平衡与并置。这场东西方的文化与政治博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加速有形文化遗产等诸多实践在无形文化领域的挪用,吞噬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促使无形文化遗产走向制度化道路和标准化程序,消解了原初的变革精神与活力。
如果采取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的遗产分类模式的话,上述两种遗产形态都属于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官方遗产。另外一类遗产是自下而上的非官方遗产,即在地方层面上,以人、物、空间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为根基形塑而成。①Rodney Harriso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8﹒之于前者,宋奕曾撰文系统爬梳过近四十年来“文化遗产话语”在国际层面上的历史轨迹,着眼于不同时期的国际文件,讨论特定语境下遗产的言说与实践体系。②宋奕:《“世界文化遗产”40年:由“物”到“人”再到“整合”的轨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10期;宋奕:《话语中的文化遗产:来自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8期。之于后者,强调边缘叙事、社区导向的遗产运动和社会博物馆学关注社区参与、文化赋权和政治民主等相关议题。③William Nitzky, Entanglements of “Living Heritage”: Ecomuseu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14, P﹒ 1﹒这两种书写模式对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进行分而论之的剖析与研究,呈现了自我修正与他者反叛的学术景观。
在“人人皆有个人遗产权利”的当代社会,遗产建构的社会参与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有关遗产研究的二元对立结构关系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在上述努力下,当代社会的物件、地方与实践获得遗产资格,并被遗产世界所接纳变得更加多样。为此,从微观层面分析遗产制造的过程变得尤为关键。本文以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e)入手,讨论某个物件、地方和实践是如何从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转变成为一种具有保护、研究与展示需求的遗产产品(Heritage Output)的。
二、从资源到遗产:遗产的过程路径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曾断言:“事实上,并不存在 所 谓 的 遗 产”(There is, really, no such thing as heritage)。④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1﹒史密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遗产的话,国际上的遗产组织究竟在做什么呢?在随后的段落中,史密斯自问自答,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遗产‘凝视’的主体并非是具有价值和意义体系的某种存在。遗产最终是一种文化实践,涉及到一系列价值和认知的建构与管理。”⑤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P﹒ 11﹒从遗产研究的脉络来看,史密斯挑战与解构的是以权威遗产话语为代表的遗产模式,即将遗产价值作为固定不变的本质主义。
从遗产的本质主义到遗产的建构学说仅仅是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开始,接下来是寻找一种理解遗产本质的新路径。在众多的替代性路径中,过程论的分析框架因其对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修正而被挪用到遗产研究领域。将“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过程”来理解的过程路径吸引了大批遗产研究学者的支持: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认为,遗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意义的沟通实践。⑥Bella Dicks, “Encoding and Decoding the People: Circuits of Communication at a Local Heritage Museum,”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5, no﹒1(March 2000), PP﹒ 61-78﹒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遗产定义为一个与人类行为和能动性有关的动词形式,并进一步指出遗产是一个与国家和其他文化或社会认同的权力合法化密切相关的过程。⑦David Harvey,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7, no﹒4(December 2001), P﹒ 327﹒史密斯认为,遗产是一个与记忆行为建立密切关系的文化过程,以此构建理解现在和参与现在的机会,因此,物件、地方与实践并非是遗产本身,而是促进遗产生成过程的文化工具。①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P﹒ 44﹒这些研究视角略有差异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遗产的过程路径的共同旨趣:一方面强调参与主体和行动者的角色与地位,关注其在遗产过程中的参与性与能动性;另一方面则将社会情境引入到遗产的文化维度,关注不同文化体系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商榷、互动与对话过程。
与上述有关过程路径的认识论共识不同,杰拉德·科赛(Gerard Corsane)从操作论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过程框架。在《遗产、博物馆与美术馆的相关议题》一文中,科赛绘制了从资源到遗产的意义生成过程。②Gerard Corsane, “Issues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Brief Introduction,”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5﹒在笔者看来,从资源到遗产的过程论述不仅在实践层面规范了遗产制造与管理的步骤,而且在理论层面构成遗产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底色。为此,笔者将在科赛建构的遗产运作的总体过程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讨论从文化资源到遗产产品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要谈及遗产的操作过程,遗产制造动机是率先考虑的要素,究竟是教育、学习,是经济、消费,亦或是赋权、民主呢?作为“回到过去”的表征③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遗产犹如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不得不让人们求助于遗产制造动机背后的主体及其历史语境。根据简·尼德文·皮特尔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对文化表征的认同主体的历史性梳理来看,21世纪的全球化思潮带来了认同主体的多元化,即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帝国和现代扩展到地方、区域、大陆、跨国与全球。④Jan Nerderveen Pieterse, “Multiculturalism and Museums: Discourses about Other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 PP﹒ 179-201﹒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历史维度的变迁不是更迭与替代的进化,而是一种在当代并存与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遗产制造动机也会因为诸多参与主体的互动、协商与对话而变得模糊,甚至会随着过程的进行而发生变动。无论如何,把握遗产制造的复杂动机及其主体是操作与理解遗产过程的首要环节。
随后,遗产过程进入到第二个环节,即物件、地方与实践等有形或无形文化资源的调查与记录阶段。就调查与记录的方法来说,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因其文化整体观、参与观察、深描等专业技能的训练而成为方法论层面上的不二选择。就调查与记录的对象来说,嵌入日常生活和传统叙事的文化资源不仅具有可挑选的代表性,而且紧密编织在当地的“意义之网”中。为此,形塑文化资源价值与意义的自然、社会、文化、政治情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调查的先决条件。在记录文化资源的一般或特殊信息时,自然生态、建筑环境、系列物件、档案材料、艺术形式、知识系统、信仰模式、口述传统、民歌、舞蹈、仪式、技艺、生活方式⑤Gerard Corsane, “Issues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Brief Introduction,”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 4﹒等内容都需要记录在案,这构成了后续深入研究和信息挑选的素材。
其实从上述有关文化资源的记录开始,遗产过程即已经进入物件、地方与实践等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范畴。这一环节主要由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组成:资源的具体研究和信息材料的过滤筛选。具体研究指的是聚焦于物件、地方与实践本身,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更加详实而具体的证据与价值,比如在博物馆运作中,解读藏品信息的研究功能就属于这一阶段。需要指出的是,物件、地方与实践等资源类型不同意味着不同研究学科和专家的介入:动植物标本需要自然史专家,出土材料需要考古学家,建筑形制需要古建专家,表演习俗需要民俗学家……任何物件、地方与实践等资源的背后信息是非常复杂的,包括起源、历史、功能、内容、形式、知识等。如果资源要成为遗产,并进入可展示与可参观的状态,那么就意味着与之相关的资源信息的过滤与筛选。
至此,开始了遗产生成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遗产的沟通与阐释环节。如果将物件、地方与实践作为具有社会生命的资源,那么成为可参观的遗产无疑意味着第二次生命的开始。在这一生命历程中,处于舞台中心的、被参观的遗产需要表述自己,并与观者建立沟通关系的策略。一般而言,推出遗产的机构和个人会为了达成沟通与阐释的效果,有意识地建构交流路径,包括陈列与展览、教育活动、活态阐释、导游参观、学术出版和信息服务等。①Gerard Corsane, “Issues in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Brief Introduction,”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 4﹒从操作层面来看,从资源到遗产的过程已经进入尾声,但是从认识层面来看,遗产的阐释和沟通尚未结束。根据传播学理论和建构主义学说,观者早已不再是信息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建构的能动参与者。②Rhiannon Mason, “Museums, Galleries and Heritage: Sites of Meaning-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221-237﹒为此,无论遗产沟通与阐释的内容具有地方特殊性,亦或具有文化普世性,观者个体或群体对遗产意义的解读也是理解遗产过程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嵌入日常生活中的资源经过动员与介入、调查与记录、研究与挑选、沟通与阐释等一系列过程的包装而成为一种可参观的遗产。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仅仅是一种基于诸多经验而归纳的理想类型。无论有关遗产制造之路的模式多么详尽,也无法穷尽围绕遗产所上演的复杂剧情。既然如此,这些思考是不是可以作为无用的知识而丢进垃圾桶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资源到遗产的过程路径不仅构成了实践遗产的参考方法,而且有助于评估、分析与理解遗产的本质。
“成为遗产”并不意味着操作层面上的完结,甚至在学术层面上,有关遗产本质的理解之战才刚刚打响。在下文中,笔者将着眼于从遗产过程中生成的关键议题,讨论遗产的本质及其争论。
三、从过程到议题:生成中的遗产思考
已有对遗产的研究具有一定内在的矛盾性:一来,遗产研究的开放性为诸多理论假说打开自由出入的大门;二来,遗产研究的内卷化基本上框定了学术思考的范式。换句话说,遗产研究并非自由之地,是有一定门槛的。只需稍微列举一下有关遗产议题的成熟思考,就可理解学者所面对的棘手局面。
之于遗产本质而言,格雷戈里·阿什沃思(Gregory Ashworth)、 约 翰· 坦 布 里 奇(John Tunbridge)的“遗产失调”(Heritage Dissonance)理论和迪克斯对遗产固有张力的洞悉奠定了遗产认知的基础。前者认为遗产的本质即是在意义与表征上呈现得不一致③John Tunbridge and Gregory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Chichester: Wiley, 1996﹒;后者则提出遗产内部以游客为导向的市场关系和呈现、歌颂真实文化之间的纠葛关系④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第124页。。之于遗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大卫·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历史试图呈现真实的过去,而遗产则坦率地捏造并且遗忘。⑤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1﹒李军以科学和信仰分别比附历史与遗产,并提出了遗产是一种政治分类的论断。⑥李军:《文化遗产与政治》,《美术馆》2009年第1期。之于遗产与记忆之间的关系,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直面残酷和耻辱的过去,从身份认同的分析视角出发,讨论黑色遗产的自我披露所带来的道德效果。⑦沙伦·麦克唐纳:《骚动不安的记忆——对棘手的公共遗迹的干预与争论》,陈春莉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2期;麦夏兰:《“棘手遗产”是否依旧“棘手”?——为何公开承认往日恶行不再颠覆集体身份认同》,申屠神悦译,《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之于遗产的功用而言,布莱恩·格雷厄姆(Brian Graham)等人提出了作为经济资源和作为社会政治资源的遗产之争,并试图从意识形态、阶级、性别和族群性等维度的分化与混杂对其进行诊断。⑧Brian Graham, Gregory Ashworth and John Tunbridge,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eritage,”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28-40﹒上述由遗产所衍生出来的关键议题已经逐渐被学界所接受,体现在对一些基于经验材料的个案分析中。当然还有其他尚未提及的遗产议题,由于版面所限,笔者暂不赘述。
虽然上述任何一个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但是笔者意不在此。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有关意义之网和阐释人类学①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的分析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具有启发作用。在格尔茨看来,文化阐释的关键在于从文化体系中找到一个“关键词”,之后则循着从“关键词”到“要素范畴”再到“文化体系”的分析路径展开,从而编织出所谓的意义之网。这与第二部分所述的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资源,从而经过一系列过程从而制造遗产的过程非常相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文化阐释或遗产过程路径的终点。格尔茨认为,接下来的步骤尤为关键,即让编织成的意义之网反向流动,进而去解释最早发现的“关键词”,从而达成一种完整的阐释循环。如果将此观点运用到遗产研究领域,那么,从资源到遗产仅仅是过程路径的半个循环,另外半个循环即是“成为遗产之后”的进程。如果在操作论和认识论层面上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将其联系在一起考虑,那么,一个理解遗产本质的完整的过程路径便可奏效。笔者就此展开讨论,主要聚焦于如下两个议题:一方面,“成为遗产”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成为遗产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近日,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华文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实践是“通过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还非遗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②陈华文:《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光明日报》2018年6月2日,第12版。。持此种乐观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其基本共识在于,从资源到遗产的过程是一个保护传统、传承文化、振兴乡村的有效举措。这种论断遮蔽了遗产面临的真正困境,还需要重新进行思考。
实际上,每一个从资源到遗产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物件、地方与实践在所有权、话语权、阐释权上的全面分离。如韦伯·恩多罗(Webber Ndoro)和基尔伯特·皮韦迪(Gilbert Pwiti)对南部非洲的物件、地方与实践是如何一步步完成遗产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③Webber Ndoro and Gilbert Pwiti, “Heritage Management in South Africa: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5, PP﹒ 154-168﹒,该过程也是地方社会被逐步剥夺与排斥的历史。其实,上述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即“成为遗产”意味着对物件、地方与实践等资源的捕获,同时发生的是对当地社会和群体的剥夺与排斥。学界所熟知的博物馆化即生成了物件、地方与实践的脱嵌:一方面从原初文化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价值的变迁。④尹凯:《物的诠释与沟通——当代博物馆藏品的学术思考》,见《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7页。虽然新博物馆学和遗产运动对此去情境化的困境有所反思,并试图以露天博物馆、遗产中心、主题公园、遗址公园等在地化的实践来修正博物馆化对当地社会的剥夺与排斥,然而收效甚微。只要一种资源被发现具有遗产价值的建构潜力,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当地人群的转移、搬迁,遗产规划对时间的冻结,物件、土地所有权的转让,遗产可参观性的制造,遗产名录的生成,去日常化的官方阐释等一系列过程。即便是被认定为世界遗产,这一遗产过程在实现与国际理念接轨的同时,也在地方层面实现脱轨。
如果说“成为遗产”意味着遗产与地方社会的分离,那么“成为遗产之后”的阶段则是地方社会能动策略得以彰显的过程,即以另一种姿态再次占有、整合遗产。 这时,地方社会能够动员政治议程、自我意识、生存策略作出应对,并以新的面貌重新影响当地社会。这一能动策略可能是随即出现的,也有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无须担心它在历史上的缺席。
20世纪70年代,有关随葬品、宗教圣物、仪式用具等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文物返还诉求,以及有关人体遗存的迁葬议题便是如此。诸多讨论试图从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夹缝中寻求出路,进而实现认同尊重和文化和解。⑤约翰·梅里曼编:《帝国主义、艺术与文物返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在此,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归还所生成的遗产过程议题,不能否认的是,当地社会对遗产的再次占有与遗产的重要性密切相关。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地社区因为先前被剥夺与排斥的事实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导致了与遗产相关的衍生现象的出现,即借遗产之名行土地、自决、认同、话语之实。当重新获得失去已久的遗产之后,当地社会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那就是如何重新整合与调适被打破的文化体系。这就涉及到遗产归还之后的地方社会何去何从的议题,有些地方群体就遗产归属展开争夺,有些群体则借遗产之名建构泛化的普遍认同,甚至导致了群体认同与群体关系的剧烈变动。①Jane Hubert and Cressida Fforde, “The Reburial Issu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Gerard Corsane﹒ed﹒,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16-132﹒“成为遗产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现象不仅体现了当地社会的能动策略,而且还涉及到了地方文化的重新整合。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地社会的能动策略一般应出现在“成为遗产”的过程中,与国际标准、专业知识共同协商、对话,共同制造遗产产品。然而,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制度化机构、科学知识体系、理性与实证精神、秩序化诉求等外部声音让当地社会处于沉默状态,由此而来的是自我表述和能动策略在破除认为“成为遗产之后”的重新崛起。当地社会经由遗产赋予的光环而“制造”文化、进而追求经济收益的行动随处可见,这不能被轻易认定为是遗产的经济功效,而应该放置在整个遗产过程路径中来予以理解。
四、余 论
从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Sites)到树木保护法规(Tree Preservation Order),从官方层面到个体层面,人类会发明不同的机制来保护那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物件、地方与实践。②Peter Davis, “Places, ‘Cultural Touchstones’ and the Ecomuseum,”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405﹒对于保护事实来看,基于宗教、性别、年龄、阶层的传统机制与基于文明的遗产机制在本质上是具有同等效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特殊重要性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情感、地方体验与地方精神,而后者的特殊重要性则是一种外在于当地社会的科学知识、文明理念和价值标准。这种固有的张力有可能导致如下情况的出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且被当地人认为是有价值的鲜活资源难以被遗产价值体系承认;一些在丧失地方特色,且被该地方的人认为早已经失去生命力的资源却获得遗产价值体系的青睐。不能否认的,特殊重要性的内外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即被认定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对地方社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资源。
遗产议题与生态博物馆学其实有很多的相似性。在生态博物馆学领域,加拿大博物馆学家皮埃尔·米兰达(Pierre Mayrand)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创意三角”(The Ecomuseum Creativity Triangle)。③Peter Davis, “Places, ‘Cultural Touchstones’ and the Ecomuseum,” in Gerard Corsane﹒ed﹒,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 410﹒在经由阐释提升某个地域的公共意识和知名度,随之建立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又会带来有关当地社会和专家学者的反馈,进而反馈给阐释,如此循环反复。这与“成为遗产”和“成为遗产之后”的两个过程路径如出一辙。
在遗产项目中,民族国家、身份政治、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等要素将介入其中。无论是遗产研究还是生态博物馆领域,在具体的项目与实践操作中,当地人在从资源到遗产的制造过程中似乎是沉默失声的。这种看法恐怕小看了当地人的能动策略和生存哲学。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破除认为“成为遗产”即意味着遗产过程的完结的想法。在笔者看来,遗产的过程路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成为遗产”的过程,二是“成为遗产之后”的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循环而完整的遗产过程路径。“成为遗产”意味着遗产与当地社会的脱嵌与分离:这种分离有时候体现为可见的资源迁徙与入藏,有时候体现为不可见的资源解读与阐释。此外,“成为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剥夺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景观:这种剥夺有时候以异地搬迁的形式出现,有时候则呈现为新的建筑形态对土地的占有。当某个物件、地方与实践被认定为遗产,并成为遗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当地声音的呐喊。这种凭借所有权、阐释权和文化权利等手段而合法化的地方话语往往要求对遗产的重新占有、整合和挪用。这种地方社会的生存智慧有多种意图:有时候要求物件的返还,有时候要求土地的权利,有时候要求经济的收益,有时候要求文化的自决。因此,在具体的能动策略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根据自身考量重塑某些物件、地方与实践的真实性,根据观者需求操弄文化的展示与表演,根据遗产的光晕垄断地方的生意与经营。在上一个过程中被剥夺与消费的当地社会,在这一个过程中却奇迹般地成为能动的生产者,它根据自身的诸多诉求而将遗产这个外来的异质元素重新整合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体系中,完成文化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