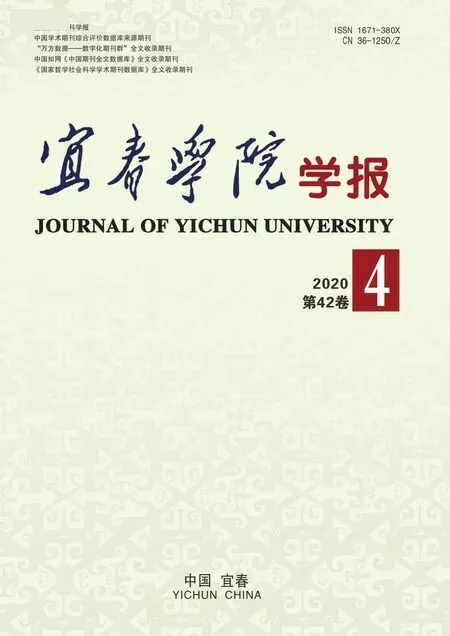惠能和道元禅学思想对比
米丽萍
(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佛教经朝鲜东渐日本。从唐朝开始,很多日本僧侣、学者来我国游学访问,日本曹洞宗祖师道元禅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入宋求法,归国之后,以永平寺为道场,弘扬和发展中国南禅宗。道元禅师在理解、接受中国禅宗思想的过程中,有着他独到的见解,《正法眼藏》就是记录道元独自禅学思想的宏篇巨著,也是研究曹洞宗日本化发展的重要蓝本。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对惠能、道元以及他们禅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中日两国有关惠能与道元禅学思想的对比研究则寥若晨星,说明对两位禅宗祖师禅学思想的对比研究亟待开始与深入。
细读《坛经》和《正法眼藏》,通过比较两经典中“即心是佛”“顿悟渐悟修行观”、“佛性论”“般若”等禅学思想,发现道元和惠能禅学思想有许多殊异之处。本文拟通过对比惠能和道元的禅法内涵,了解道元对惠能禅学思想的传承和变革创新。
一、六祖惠能的禅学思想
中国佛教自菩提达摩师资相承传至惠能,共有六代,惠能创立了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本土化。《坛经》由惠能弟子法海记录整理而成,记录了惠能的禅学思想及禅宗教义,是中国佛教史上唯一被称为“经”的著作。惠能禅学思想融合了大乘般若学和儒道等思想,开创了极具中国化特质的南宗禅。自中唐以来,凡是言及禅宗皆指曹溪[1]。中国佛教的心性论至禅宗而臻于完善[2],惠能“直指心源,见性成佛”的思想标志着禅宗心性论的成熟和完善[3]。《坛经》有云:“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引文明示了惠能禅学心性论之宗旨[4]。心性论是惠能禅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禅法实践的理论基础[4]。惠能以“见性成佛”作为南宗禅之宗旨,以“明心见性”“性净自悟”为南宗禅之枢机,提倡不立文字,弘扬“顿悟”,其禅法简易直接,禅风清新活泼[4]。
从菩提达摩到惠能的“纯禅时代”,禅学思想和禅法实践的内容、风格均已成熟,与印度佛教之禅相比,也有明显的发展和创新[4]。惠能禅注重于“明心见性”的禅悟,在禅修实践上,也一改自菩提达摩至五祖弘忍等禅宗祖师都践行的坐禅静修、观心静坐,转变为日常行住坐卧中的开悟见性[4]。“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坛经·决疑品》[5](P181),惠能禅不偏执于坐禅习定来禅修。惠能以见性、无念为宗旨,根据“明心见性,离相无念”的思想,强调“道由心悟”“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的修禅方式,对传统的禅定意义加以破斥,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形成了惠能南宗禅随缘自在、朴质无文、入世而超然的清新禅风[4]。
《坛经·定慧品》有云:“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5](P186)“无念、无相、无住”的“三无法门”是惠能禅法的核心,也是其禅法的认识论和实践方法[4]。“三无法门”的修持目的,在于彻底破除妄想、分别与执著,对于利根之人而言应该是最为契合的修行方法。惠能强调在世间的修持实践应融于日常生活,惠能认为持戒只在于自性的迷悟染净,善恶之分殊全凭一念心,主张禅宗破执和自然主义的修持态度。惠能禅不分阶级,不假文字,世人皆可参学。在禅修方法上简单易行,在家亦可修禅,为众生开辟了方便之门。
二、道元的禅学思想
六祖惠能创立了中国南宗禅以后,其弟子们开创了禅宗的“五宗七家”,虽然各流派都以“明心见性”相标榜,但却宗风不同,门庭各异,标志着惠能以后禅宗的发展和演变。五宗之一曹洞宗自唐代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创立以来,通过宋代宏智正觉阐扬“默照禅”而确立其禅风宗旨[6]。
道元是日本镰仓时代的禅师,1223年,24岁的道元随师明全入宋求法,访问阿育王山,径山等著名寺院,后师从曹洞宗第十三代法嗣天童山长翁如净禅师三年习“默照禅”,获如净印可。如净“只管打坐,身心脱落”的修禅证悟思想,直接为道元所秉承,成为道元禅修的核心内容和“修证一等”禅学理论的主要依据。1227年秋,道元回国后,先在京都南部的深草创建兴圣寺。1243年在越前(今福井县)复建大佛寺,后更名为永平寺(以佛教东传中国的永平年号命名),体现了道元尊崇中国佛教之意,也暗示了道元将中国曹洞宗,和中国的正统佛教真正传入日本的自信。道元以永平寺为主要道场,传禅说法,教化世人,著书立说。《正法眼藏》是道元众多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鸿篇巨著,论述了日本曹洞宗禅学思想的神髓,对一些重要的禅宗思想、禅修方法作了创造性的阐释,此书吸收了中国禅宗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使之日本化。
在禅学思想上,道元继承如净的“默照禅”并予以发展,强烈主张佛法的绝对性,主张唯有坐禅才是佛法正门[7]。道元有自己深邃的思想体系,《正法眼藏》中对佛性、般若、生死、实相、禅定等的阐释,尤为突出其思想的深度和原创性,佛性思想可谓贯穿道元禅学思想和宗教经验的最主要线索。
虽然道元极力强调自己的禅法是师承如净禅师的“默照禅”,谨奉如净禅师的“只管打坐,身心脱落”为修行法门;但是道元不喜禅宗之名称,排斥五家,自任自己为正传之佛法,不认可把禅置于诸教之外的教外别传的思想,对中国禅宗的五家进行了批判[8](P144)。道元称道:“佛祖单传,为师我释迦牟尼之正法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为无上菩提求道之辈,不可以佛祖单传直指无上正法而称禅宗者欤。”[9](P129)道元认为,“一叶五家”是作为偏离了“佛祖单传”的旁枝,应遭到谴责。道元在《正法眼藏》中就否定了五家宗名,禁止其门下自称洞山宗或曹洞宗[9](P386)。道元私淑六祖,在其《正法眼藏》中举唱六祖,竟达97处,常以曹溪高祖、大鉴高祖、曹溪古佛称呼六祖[8](P135),由此可见道元对惠能的尊崇和坚信自己所传为中国禅宗的正法。道元甚至对洞山良价的“正偏五位说”严加指摘,主张他自己的所传禅法是将曹溪惠能及其以后的禅法加以统一整合的产物。因此有学者对曹洞宗的传承世系重新做了界定:曹溪惠能…洞山良价→云居道膺→丹霞子淳→真歇清了→大休宗钰→足庵智鉴→长翁如净→永平道元[5]。此传承世系明晰地体现了道元对惠能禅法的一脉相承。
三、惠能和道元禅法思想的异同
对比《正法眼藏》和《坛经》发现,道元禅法和惠能禅法既有一脉相承之处,道元禅的日本本土化发展又衍生出自身的特色。因为道元在传承与弘扬中国南宗禅的时候,与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等相互碰撞、冲突、融合,最后演变为具有日本本土化特征的道元禅法。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比较惠能和道元的禅学思想异同。
(一)“即心即佛”思想对比
惠能的“即心即佛”说将一切万法和众生诸佛都归结于“自心”,强调只要本心契悟,即可见性成佛。在成佛的可能性上,惠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平等,亦即世人皆可成佛。惠能提倡的“即心即佛,见性成佛”之心性论,将染净诸法会归于心之体用,般若与自性体用一如,成为惠能顿悟禅法的理论基础[4]。慧能认为佛的原本含义是觉悟了真理的人,是证得了“真如本性”的自由解脱之人。人人皆具有先天原本的真如本性,慧能称其为“自性”。慧能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品》。)[5](P172)慧能认为能否圆证佛果之关键乃自心之迷悟,“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坛经·疑问品》)[5](P181)自心的觉悟就是自心般若之起用,在惠能禅学思想体系中,明心见性与开悟解脱具有相同的意义。众生只要在行住坐卧之中念念无执着,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心是佛。作为《坛经》核心思想的“即心是佛”,强调对自我内心的认知,以“心”为本原去实现成佛[4]。
《正法眼藏》(即心是仏)卷:谓即心是佛者,乃发心、修行、证菩提、涅槃之为诸佛也,未曾发心、修行、证菩提、涅槃者,不是即心是佛。设于一刹那中发心修证,亦是即心是佛。设于无量劫中发心修证,亦是即心是佛。
道元传承了惠能“识心见性、即心是佛”的思想,认为“发心、自心”是实现成佛的根本途径,也主张认识了“本心”“自见本性”才能证悟解脱。但是道元禅师并未如惠能禅师一般,单纯从“心”或“心性本净”的理念上去理解“即心是佛”。道元认为要“识心见性”,不重视身体上的坐禅修行,不可能真正地证悟成佛。道元继承了如净禅师所传“默照禅”的“只管打坐,身心脱落”的思想,将坐禅(修)与觉悟(证)视为一体,认为坐禅即是修行方法,又是觉悟的体现,即“修正一等”、“教修证一如”[10](P105)。它刷新了惠能的带有观念论倾向的“即心是佛”论,确立了唯有通过坐禅修行才能证悟成佛的道元自身的“即心是佛”论,是道元与惠能禅学思想的殊异之处。
(二)“顿悟修行观”与“渐悟修行观”对比
惠能提倡“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惠能认为从“迷”到“悟”只是一念之间,故曰:“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在生起般若观照这一刹那即悟入佛地,此乃“顿悟成佛”之义,是惠能禅法的骨纲,也是其宗门的旗帜[4]。此“悟”即人们当下之心“不思善、不思恶”时,一念之间本真之心的自然显露,此悟必为顿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应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品》)[5](P172)顿悟不假渐修,“悟说”是惠能禅法所特有的思想。惠能将“修”与“悟”紧密结合起来,融修于悟之中,即顿悟顿修,修悟不二,其本质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又一特点[4]。
惠能重新定义了“禅定”的含义,他根据无住无念即为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把禅融入了日常的行住坐卧中,对“禅定”的含义进行了创造性转换[11],认为“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外不乱即定。外禅内定,即为禅定。”[5](P191)惠能明确地提出了禅非坐卧,反对执着坐禅,证悟成佛的关键乃“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强调“道由心悟”,坐禅只是证悟的途径之一。
《正法眼藏·办道话》云:此单传正直之佛法,最上中之最上也。自参见知识始,勿须更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身心脱落。即使一时打坐,三业也标佛印。端坐三昧之时,遍法界皆是佛印,尽虚空皆为菩提。
如净禅师修正一如的法门为“只管打坐,身心脱落”。所谓“身心脱落”,就是摆脱肉体(身)和精神(心)的一切牵累和烦扰,如同肉体和精神皆脱落了一般,断绝感官、超越感觉和心识,达到“六处发现”的无所不通的境界,清净本心因而显现出来[10](P102)。道元继承如净衣钵,强调“只管打坐”为禅门正法,视之为禅宗真髓,认为只有秉持释迦摩尼自菩提树下坐禅成佛以来的正传佛法,才能真正领悟佛法真意,才能真正解脱成佛[6]。至于对坐禅所达到的悟境的理解,道元也得如净之精要,坐禅即行佛,坐禅即开悟。道元提倡“佛佛祖祖之坐禅”没有“邪见、著昧、骄慢”之病,是真正的“身心脱落”,有别于“凡夫外道之坐禅”。“凡夫外道之坐禅”无佛法之身心,虽身心劳苦,终无益也。[10](P104)
道元禅学法最主要的思想是“修证一等”或“教修证一如”,道元视坐禅(修)与觉悟(证)为一体,认为坐禅即是修行方法,又是觉悟的体现。惠能认为坐禅(修)只是达到觉悟成佛(证)的途径和方法之一,坐禅的重要性低于觉悟(证)本身。道元则主张“修证一等”“教修证一如”,抬高了坐禅的地位,认为只有通过心无旁骛的打坐,身心自然脱落,才能真正证悟。道元还强调,即使证悟了仍要继续坐禅修行,继续证佛而不休,永不懈怠[7]。在成佛的实践方法上,惠能主张顿悟,道元则主张渐悟,把本心和发愿融入到不断的坐禅中,始终坚持“只管打坐”的修证一等。道元对惠能“明心见佛”的思想一脉相承,而证佛的途径却大相径庭,具有渐修的色彩,这是道元与惠能禅风殊异之处。
(三)“佛性论”对比
惠能禅宗思想的核心和禅法实践的理论基础是佛性论与心性论,惠能佛性论的最显著特点是将“佛性”落实到具体的“人性”和“心性”上。惠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佛性亦无差别。“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这些都是《坛经》中惠能的佛性论主张,意为世人佛性本具,自身即佛,只要于一切法无所执着,即能证得佛身。惠能所言的佛性,正是世人当下现实的活泼泼的人心、人性。“自识本心,自见本性”,“除真除妄,即见佛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如惠能上述所言,他主张明心见佛,认为佛与众生的差别仅在于自心(自性)迷悟的不同,“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因而,人的心性迷悟成为成佛的关键,取决于人们的当下现实之心。
在认识佛性的道路上,惠能继承了佛性论的“本觉”思想,惠能不仅强调众生皆具佛性,也强调人人“自有本觉性”,但要通过修般若行来开发自身佛性。惠能认为,“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般若智慧是人心之本性,只要念念不愚,念念不住,此觉便可起用而生正真般若观照,一悟而至佛地[4]。此处的般若观照,是生起于本觉而远离分别的一种直觉认识[11](P35),故《坛经·般若品》有云:“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5](P171)
道元也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有佛性之有,当脱落”,传承了惠能的佛性论,但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差别。惠能的佛性论即心性论,强调“明心见性、道由心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道元的佛心论是“身心一如”,其在《正法眼藏·办道话卷》中曰:“须知佛法从本以来,谈身心一如,性相不二。”[12](P9)只有“身心一如,身心脱落”才能成佛。“皆一时身心明净,证大解脱地”“此坐禅人,便霍尔身心脱落,截断从来杂秽之知见思量,会证天真佛法。”[12](P3)从道元上述的证悟观可以看出,道元特别重视在达到证悟的禅修过程中“身”与“心”的同等作用,证悟成佛只有通过锲而不舍地“只管打坐”的禅修,才能达到“身心脱落”的证悟,这明显区别于惠能的“一悟即至佛地”,只要在心上用功,就可解脱成佛的佛性论思想。
(四)“般若”思想对比
般若即智慧,惠能特别强调般若之智,他认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是“迷”和“悟”的区别罢了,“一念愚则般若绝,一念智则般若生。”惠能在禅法上重视般若智慧的运用,“自性心地,以般若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惠能认为“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要做到无念,必须“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惠能强调以般若智慧关照,识心见性,才能进入般若三昧境界[13](P188)。内心常生智慧,恒自常照,不为任何外在境界所迷惑。惠能以非有非无、不执两边的般若正观来破除一切分别执著、转化一切烦恼[4]。在成就般若的方法上,惠能认为自性就是般若之性,般若之性存在于众生心中,不必外求,无上菩提要在明心见性中求得。
在《正法眼藏·办道话》中,道元宣称自己是佛法正传、正门,端坐参禅是正门、正道[14],“况人皆丰备般若正种,但以承当者稀、受用者寡尔。”[12](P15)道元虽然和惠能一样,强调世人皆具般若,但是由于承当或不承当在现实中会导致区别,因此承当者少而导致真正得法者少,缩小了具有般若正种者和能证悟得法者的范围。道元认为“无宿殖般若之正种,彼等不得为祖道之远孙”,那些没有宿殖般若正种,自称为祖师远孙的徒弟,不能传承正法,唯有宿殖般若正种者才能正传衣法。由于世人无法长出“般若正种”,不能得道,因此在成就般若的方法上,道元提出“以何而长般若正种,得得道之时哉?”之疑问。道元探讨了般若和坐禅的关系,他强调只有坐禅(正法)才能具有般若正种,才能证悟得道、传承正法,可开演般若[14]。他认为前生“宿殖”的般若正种则不知坐禅,而不知坐禅的僧侣都不是般若正种。
惠能认为人人皆具足般若性,明心见性即是般若三昧,并未强调坐禅与般若的关联性,坐禅与否与“具足般若性”亦无必然联系。但是在成就般若的方法上,道元观点十分鲜明,他主张只有坐禅悟道,才是般若正种,才能开演般若,这与惠能主张的“明心见性”成就般若的方法有着较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惠能和道元的禅学思想在“即心即佛、顿悟与渐悟修行观、佛性论、般若思想”等方面各有特色。惠能禅学理论和禅法实践的终极指向在于明心见性,获得绝对的自由和解脱。惠能强调“明心见性、道由心悟”的证悟成佛,比较注重对“心”的印可。道元则强调在证悟成佛的禅修过程中“身”与“心”的同等作用,只有通过“只管打坐”的禅修,才能达到“身心脱落”的证悟成佛;道元认为坐禅即是修行方法,又是觉悟的体现。惠能和道元禅学思想上的异同,既体现了道元对惠能禅学思想的传承,也体现了道元禅日本本土化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