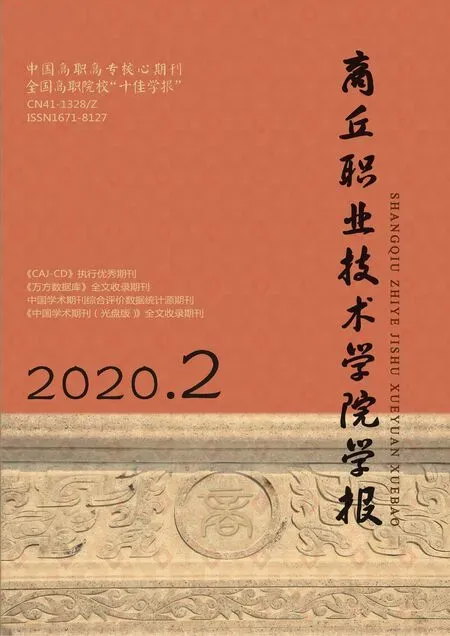被胁迫行为的刑法适用路径
蔡可睿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一、问题的引入
有学者在说明胁从犯时解释了“被胁迫”的含义,即“行为人受到暴力威胁或者精神威胁而被迫”[1]190。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除了胁从犯之外并没有在其他地方提到“被胁迫”的相关内容,导致大部分人认为《刑法》中的被胁迫行为仅仅存在于胁从犯之中。“被胁迫”几乎变成构成胁从犯的特定术语。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由于被胁迫参与犯罪,《刑法》通常认为该行为人构成胁从犯,而不能阻却犯罪的成立。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被胁迫行为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胁从犯之中。本文旨在明确被胁迫行为的内涵,厘清被胁迫行为与不可抗力、紧急避险和胁从犯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有关被胁迫行为的疑难问题。
二、《刑法》中的被胁迫行为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被迫行为是指行为人在自身或他人立时有生命危险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胁迫下,不得已而实施的某种行为”[2]。相似的观点认为,“被迫行为是指行为人受到他人以杀害或者重伤害相威胁,要求行为人去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为人按照胁迫者的要求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3]。
笔者认为,被胁迫行为的定义应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被胁迫行为也可称为被强制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本人或者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按照胁迫人的要求所实施的特定行为。例如,甲用刀威胁乙,要求乙将毒药投入丙的水杯中,否则就拿刀捅乙,乙在本人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按照甲的要求向丙的水杯里投入了毒药,乙的行为就构成了被胁迫行为。
由于《刑法》中的“被胁迫”一词仅仅被使用于胁从犯的规定之中,因此,刑法理论关于如何认识《刑法》规定中的被胁迫行为,存在两种思维路径:一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根据“被胁迫”一词找《刑法》中的相关规定,本质上是通过“被胁迫”一词在《刑法》中的定位来说明被胁迫行为的内涵。按照这种思维路径,由于我国仅在胁从犯的规定中才使用了“被胁迫”一词,因此,刑法理论界才会出现“被胁迫行为都构成胁从犯,不存在能够阻却犯罪的被胁迫行为”的观点。正如某位学者所言,“本来被胁迫行为的性质在我国刑法典中并没有特别地规定,但是,由于《刑法》第二十八条的出现,使被胁迫行为就具备了共同犯罪的特征。该条规定胁迫作为共犯的一种类型,这样就确立了它在犯罪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紧急避险的一般条件就不能被适用,这样,就出现了现实中对被胁迫行为定性的争议”[4]18。 二是根据被胁迫行为的实质内涵来寻找《刑法》中的相关规定,按照这种思维路径,可以得出胁从犯并不能涵盖被胁迫行为的所有类型的结论。当《刑法》规定中不存在与“被胁迫”这种概念称谓相同的词语时,我们就需要厘清被胁迫行为与《刑法》中关于“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等涉及被胁迫实质内涵的相关规定之间的关系。
笔者从第二种思维路径出发,认为被胁迫行为存在三种类型,包括行为人受到绝对强制无法做出选择(不可抗力)、行为人受到相对强制能够做出选择但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行为人的被胁迫行为成立犯罪(胁从犯)。笔者将在下文对三种类型展开论述。
三、《刑法》中的“不可抗力”
《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其中,不可抗力的来源包括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海啸;政府行为,例如政府颁发新的政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政府的征收征用行为;社会异常事件,例如罢工、社会骚乱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能抗拒的强制作用既包括自然力的强制作用,也包括非自然力的强制作用,即人的作用。不可抗力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行为人受到绝对强制时不成立犯罪的法律依据。在成立不可抗力的情形下,行为人由于受到绝对强制而不存在选择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刑法》第十六条规定了被胁迫行为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一直以来都是以第一种思维路径来考虑被胁迫行为,即使有学者从第二种思维路径出发去考虑问题,更多地也仅仅是将被胁迫行为与紧急避险、胁从犯联系起来,而没有从不可抗力的角度来思考被胁迫行为。实际上,应当看到不可抗力这种使行为人受到绝对强制而没有选择的情形也属于被胁迫行为。正如有的刑法学教科书在解释不可抗力时,认为“不可抗力的来源包括杀害威胁这种强制,并强调这种强制应足以使行为人完全丧失意志自由”[1]312。这意味着该观点认可《刑法》第十六条规定了行为人完全丧失意志自由的被胁迫行为,只是没有从概念的角度说明不可抗力事件和被胁迫行为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不包括精神的胁迫,在精神胁迫下而为的行为,如果不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仍然构成犯罪,有的情况下,可构成《刑法》第二十八条共同犯罪中的胁迫犯”[5]。
笔者认为,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同被胁迫行为之间的关系,应当从两个层面进行说明。
第一,不可抗力的来源是否包括杀害威胁或者精神威胁,即杀害威胁或者精神威胁是否会导致行为人完全丧失意志自由。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行为人受到的杀害威胁或者精神威胁能够使行为人完全丧失意志自由,那么不可抗力的来源就可以包括精神强制,而不是完全同精神强制不存在任何联系。例如,歹徒威胁甲杀了乙,如果甲不听从歹徒的指令,歹徒就会炸毁载满乘客的火车,所有乘客都会失去生命,在完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甲只好杀了乙。在这种情形下,甲受到绝对的精神强制,完全丧失了意志自由。因此,笔者认为,不可抗力的来源可以包括精神强制。
第二,若是承认不可抗力的来源包括精神强制,那么区分不可抗力和其他被胁迫行为(紧急避险、胁从犯)之间的关键就在于杀害威胁或精神威胁是否使行为人完全丧失自由意志。如果行为人在受到绝对精神强制的作用下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那么根据《刑法》中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可以认为行为人不成立犯罪;如果行为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自由意志,此时才进入下一阶段的判断,即分析行为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或者胁从犯。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涉及被胁迫行为的案件时,直接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紧急避险或者胁从犯的规定,就会在被胁迫行为的实质内涵理解上存在误区,进而低估了被胁迫行为内涵的丰富性。
综上,笔者从第二种思维路径出发,根据被胁迫行为的实质内涵探寻《刑法》中的相关规定认为,《刑法》第十六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描述了被胁迫行为的其中一种类型,即行为人受到绝对强制时的被胁迫行为。
四、《刑法》中的“紧急避险”
德国刑法对紧急避险作了区分规定,分为正当化的紧急避险和免责性的紧急避险,并且认为被胁迫行为能够适用于紧急避险的规定,其刑法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被胁迫行为应该属于正当化的紧急避险还是免责性的紧急避险。近年来,随着区分违法和有责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对我国刑法理论日渐深厚的影响,以及我国刑法学界对被胁迫行为的研究不断的深入,被胁迫行为的争议可谓直指紧急避险的规定是否包含了被胁迫行为以及被胁迫行为是否独立的阻却犯罪事由[6]。
笔者认为,要弄清紧急避险是否包含被胁迫行为,就要厘清紧急避险属于正当化事由还是免责性事由。只有在明确紧急避险的性质之后,才能确定紧急避险是否包含了被胁迫行为,以及如果被胁迫行为能够成立紧急避险,那么被胁迫行为是成立正当化的紧急避险还是免责性的紧急避险。
(一)紧急避险的性质
与德国现行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不同,我国刑法没有对紧急避险的类型做出明确的划分。因此,我国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于,紧急避险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是阻却违法还是阻却责任。刑法理论界对紧急避险的性质存在两种学说,即一元论紧急避险说和二元论紧急避险说。
1.一元论紧急避险说
一元论紧急避险说又分为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和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说。我国刑法学者田宏杰教授在讨论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时,主要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相关学说,在反思德日刑法理论并且立足于我国刑法学说中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否定区分紧急避险的性质,从正当化行为的角度统一把握紧急避险[7]325。也就是说,田宏杰教授赞成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在认定紧急避险能够阻却违法性时强调优越利益原则,此处的优越利益原则是指,以补充性和均衡性为条件的避险行为如果保护的利益价值高而损害的利益价值低,则不具有违法性。田宏杰教授认为,在避险行为所保护利益和损害利益价值相同的场合,由于法益均受法律保护,无优越利益存在,法秩序无法优先保护任一法益,故这种紧急避险行为不具有违法性[8]197。
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说更加关注在紧急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具有不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如果行为不具有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那么这种紧急避险行为就能够阻却责任。但是,赞成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的学者认为,《刑法》允许行为人为保护本人或者亲属之外的他人利益实施避险行为,该情形并不能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解释。这种观点对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说的反驳可谓一针见血。
2.二元论紧急避险说
在一元论紧急避险说之外,还存在二元论紧急避险说。二元论紧急避险说认为,应当区分紧急避险的性质,紧急避险既存在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还存在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现行的《德国刑法典》区分规定正当化的紧急避险和免责的紧急避险正是对这一学说的确认。
在二元论紧急避险说内部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学说将保护较高价值利益而牺牲较低价值利益的情形解释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将价值利益相同或者价值利益难以比较的情形解释为责任阻却事由。第二种学说除了将保护较高价值利益而牺牲较低价值利益的情形解释为违法阻却事由之外,还将保护利益与牺牲价值利益相同的情形也纳入违法阻却事由之中,当面对“生命与生命之间”“身体和身体之间”这种不能比较的情形时,统一归为责任阻却事由。第三种学说则认为,行为人为了保护某些法益而侵害无辜第三者的利益,原则上应当属于责任阻却事由。但是,如果该避险行为是为了保护价值利益显著较高的法益时,且可以受到“国民观念”的肯定,那么这种例外情况才可以被认为该避险行为能够阻却违法性。日本刑法学者川端博教授将第一种学说和第二种学说统称为“以阻却违法性为原则的二分说”,将第三种学说称为“以阻却罪责为原则的二分说[8]195-196。
笔者赞成以阻却违法性为原则的二元论紧急避险说,虽然《刑法》没有对紧急避险的性质做出明确的划分,但是,也没有将紧急避险的性质仅仅限定为正当化事由。《刑法》规定实施紧急避险的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不负刑事责任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即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可以认为,《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既包括阻却犯罪的紧急避险,也包括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正如某位学者所言,“目前学界多数学说则认为不受刑罚处罚的紧急避险可以区分为阻却违法与减免责任的紧急避难[9]。
(二)被胁迫行为成立正当化还是免责性的紧急避险
1.以一元论紧急避险说为视角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刑法》并没有在紧急避险的相关规定中使用“胁迫”“强制”等词语,导致刑法学界对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是否包括被胁迫行为产生了一定的争议。我国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学》一书中将被胁迫行为称为“受强制的紧急避险”[10]。在被胁迫行为是否属于紧急避险的问题上,田宏杰教授认为,应当首先确认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其次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和其他成立条件推导出被胁迫行为成立紧急避险的结论[7]296。笔者从第二种思维路径考虑,要判断被胁迫行为是不是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就要厘清被胁迫行为的正当化依据,只有联系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才能推导出紧急避险是否包含了被胁迫行为。
(1)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
按照一元论中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的观点,当行为人受到胁迫所保护的法益要大于行为人听从胁迫人的命令所侵害的法益时,由于行为人保护的法益要大于损害的法益,符合优越利益说主张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一种小利益的牺牲换取大利益的情形,因此被胁迫行为符合优越利益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被胁迫行为,如果在判断该行为的性质时,得出该被胁迫行为符合优越利益说的结论,那么可以认为该被胁迫行为成立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
此时被胁迫行为和紧急避险的关系是,两者都符合优越利益原则,同为违法阻却事由,被胁迫行为可以成立紧急避险。正如林山田教授所言:“被胁迫行为能否阻却违法性,只要考虑到行为人所受到的威胁程度,以及其在胁迫下所受到的威胁程度,即为足矣,无须区别被胁迫人面临的危险是自然灾害还是他人的违法胁迫行为,如果被胁迫人保全的利益和其所牺牲的利益符合利益衡量原则,那么被胁迫行为可以阻却违法性。”[11]林山田教授认为,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可以包括被胁迫行为,并将被胁迫行为称为“遭人强制的避难状态”。
我国刑法学者阮齐林教授赞同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包括被胁迫行为。他认为:“抢劫犯持枪劫持出租车司机,令司机将其送往某银行实施抢劫行为,按照普通人的公平感,追究该司机抢劫罪胁从犯罪责显属过分,若符合紧急情况下保全优势利益的要求,可以根据紧急避险排除其行为的犯罪性。”[12]
林山田教授和阮齐林教授都从优越利益原则出发,认为在符合优越利益原则的前提下,被胁迫行为与紧急避险形成了同为违法阻却事由的等同关系。
(2)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说
与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说不同,赞成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说者则认为,被胁迫行为是免责事由。在日本,大冢仁教授认为,被胁迫行为是不同于正当化紧急避险的阻却罪责事由[13],大谷实教授也认为,被胁迫行为是阻却罪责事由[14]。与此同时,日本刑法虽未对被胁迫行为作特别规定,但它也认为被胁迫行为是超法规的阻却罪责事由。这与认为紧急避险能够阻却责任的理由相同,即被胁迫行为能够阻却责任的依据是行为人缺乏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
由于实施被胁迫行为和紧急避险的行为人都缺乏期待可能性,因此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出发,被胁迫行为与紧急避险形成了同为责任阻却事由的等同关系。
2.以二元论紧急避险说为视角
二元论紧急避险说以紧急避险性质的区分为前提,如果支持二元论紧急避险说,那么无论被胁迫行为属于正当化事由还是免责事由,均能够与紧急避险形成等同关系,只是会产生被胁迫行为在何时等同于正当化的紧急避险,又在什么情况下等同于免责的紧急避险的问题。例如,在德国刑法学界,耶塞克教授、罗克辛教授、韦塞尔斯教授等学者将被胁迫行为视为免责的紧急避险,而施特拉腾韦特教授和库伦教授则认为,被胁迫行为既可能成立正当化的紧急避险,也可能成立免责的紧急避险[15]。我国有些刑法学者也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应当二元性地区分紧急避险和被胁迫行为的法律性质,从而使被胁迫行为能够成立正当化的紧急避险或者免责的紧急避险[16]。
笔者作为二元论紧急避险说的赞同者,也认为应当二元性地区分紧急避险和被胁迫行为的性质。紧急避险作为法定的阻却犯罪事由,不能被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紧急避险都能阻却违法性,当行为人保护的利益大于损害的利益时,可以阻却违法性,而当行为人保护的利益小于或等于所损害的利益,或者两种利益之间无法比较时,就需要将一部分类型的紧急避险从阻却违法性的体系中移入阻却责任的体系之中。
之所以赞同被胁迫行为可能成立正当化事由,也可能成立免责事由的二元论,是因为有些被胁迫行为发生的场合应当允许第三人对被胁迫人实施正当防卫,即此时被胁迫行为属于免责事由。举例而言,甲威胁乙去杀丙,否则自己就杀了乙,乙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转而去杀丙,此时丙就可以对乙实施正当防卫。在这种情形下,由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法益不能比较,该被胁迫行为属于责任阻却事由。但是,有些场合并没有第三人在场,例如胁迫人用刀指使被胁迫人帮助自己制造假币,这是一种被胁迫实施的帮助行为,由于这里不存在第三人,也就无法讨论第三人是否能实施正当防卫。有些场合即使有第三人在场,也不应当对被胁迫人实施正当防卫,而应当对胁迫人实施正当防卫,比如歹徒举枪胁迫飞行员将飞机开往其他地方降落,飞机上其他人的防卫对象应当是歹徒,而不是飞行员。在这种情形下,飞行员的被胁迫行为成立紧急避险,阻却了违法性,就不能以“应当允许第三人实施正当防卫”为理由将被胁迫行为视为免责事由。
正如前文所述,被胁迫行为的正当化依据和紧急避险的正当化依据相同,如果能够从正当化事由和免责事由两个角度区分理解紧急避险的性质,那么当被胁迫行为和紧急避险均为违法阻却事由或者均为责任阻却事由时,被胁迫行为和紧急避险之间又可以形成等同关系。
五、《刑法》中的“胁从犯”
《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可见,《刑法》在胁从犯的规定中使用了“被胁迫”一词,为减轻或者免除行为人的责任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被胁迫人成立胁从犯是以被胁迫行为成立故意犯罪为前提的,因此,胁从犯的规定并不意味着被胁迫行为一律成立犯罪。被胁迫行为与胁从犯之间的关系应当从以下两个层次的判断路径出发:第一,要判断被胁迫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只有被胁迫行为成立犯罪才有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而不是直接认为被胁迫行为成立胁从犯从而得出被胁迫行为不存在阻却犯罪的情形。因此,既然成立胁从犯的前提是被胁迫行为成立故意犯罪,那么就应当厘清符合犯罪阻却条件的被胁迫行为同胁从犯的关系。第二,当被胁迫行为构成故意犯罪时,胁从犯的规定就是关于被胁迫行为成立犯罪时如何量刑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被胁迫行为同胁从犯之间关系的争议较少,主要的争议在于,当被胁迫行为避险过当时,能否将被胁迫人按照胁从犯的规定处理[4]329。
由于成立胁从犯需要以被胁迫行为构成故意犯罪为前提,那么该问题的实质在于,判断被胁迫行为成立避险过当时应当属于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我国刑法理论在分析避险过当的罪过形式时,认为“避险过当不是独立的罪名,应当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及过当行为特征,按照刑法分则中的相应条款定罪处罚”。然而,关于行为人对避险过当的罪过形式为过失的情形,大部分观点仅根据特定罪名的性质区分了“不负刑事责任”和“过失犯罪”的认定方式[17]。
笔者认为,第一,在分析被胁迫行为属于紧急避险还是避险过当时,根据德国和日本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可以肯定避险行为已经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然后才从违法性阶层和罪责阶层两个层次来考虑避险行为是否能够阻却犯罪。如果避险行为超过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无法阻却犯罪从而成立避险过当时,在认定避险行为或者避险过当行为的罪名时,无论行为人对避险过当的结果持故意还是过失的心理,均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仅仅因为行为人对避险过当的结果持过失心理就将其行为认定为过失犯或者认为该行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当被胁迫行为成立避险过当时,该避险行为要么不能阻却违法性,要么不能阻却责任,但是,该行为仍然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因此,被胁迫行为成立避险过当时,胁迫人和被胁迫人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被胁迫人是可以成立胁从犯的。
第二,《刑法》对避险过当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胁从犯也规定了“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可见,《刑法》对避险过当和胁从犯都规定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两者的规定形成了竞合关系。因此,如果被胁迫行为由于避险过当成立胁从犯时,无论对该行为是适用避险过当的规定,还是胁从犯的规定,在量刑上不会存在矛盾和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被胁迫行为成立避险过当时可以将被胁迫人按照胁从犯的规定处理。
六、结语
如前文所述,判断被胁迫行为的性质时应当从第二种思维路径出发,根据被胁迫行为的实质内涵来探寻《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当行为人受到绝对强制且没有选择余地时,其实施的被胁迫行为符合《刑法》第十六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以二元论紧急避险说为前提,当行为人受到相对强制能够做出选择但是不负刑事责任时,无论该被胁迫行为是阻却违法性还是阻却责任,均能与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或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形成相应的等同关系;当被胁迫行为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被胁迫行为成立避险过当时,可以适用《刑法》第二十一条关于“胁从犯”的规定。因此,《刑法》中的被胁迫行为既包括阻却犯罪的被胁迫行为,也包括影响量刑的被胁迫行为两种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能将被胁迫行为仅仅局限于影响量刑的胁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