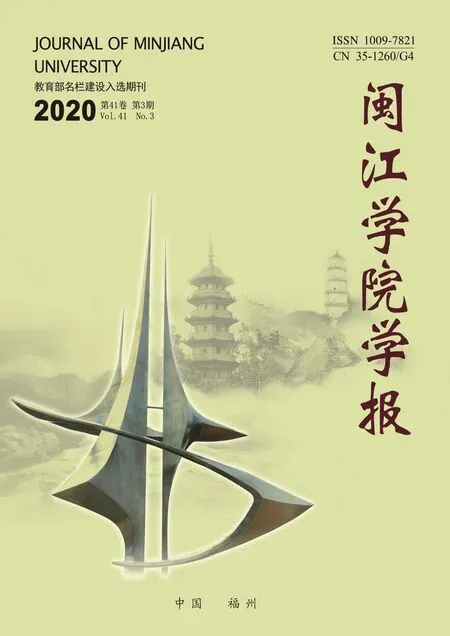道南学派发展视域下的杨时易学
肖满省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杨时,字中立,学者称龟山先生,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是道南学派的核心人物,对南宋及后世理学的影响很大。杨时著述丰富,南渡后又竭力与王安石新学斗争。他不仅在思想上对二程学说有所推进,在现实中也是二程之学扩大的关键人物。从地域上说,二程之学从中原传到南方;从政治空间上看,程学从伪学变为重新被朝廷重视的“正学”,这都是杨时的功劳。目前,学术界对杨时理学思想中的本体论、工夫论等问题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对其易学思想的研究也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1)据笔者所见,专题论文有:詹石窗、李育富的《杨时易学思想考论》( 《周易研究》2011 年第 1 期) ,王巧生的《杨时易论抉要》(《周易研究》2012年第6期),王巧生的《杨时解〈易〉的象数体例与特色》(《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谷继明的《杨时易学探义》(《中国文化研究》2018 年春之卷),以上论著对杨时的易学思想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着眼于“道南易学”的传承与发展,探讨杨时易学及其历史意义。
一、弘扬程子易学的重要举措:校正《伊川易传》
《伊川易传》是程颐唯一亲手写定的专门性著作,集中展现了程子的理学思想。该书成书于元符二年(1099)程颐编管涪州期间。至崇宁五年(1106),伊川致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1]345可知此书倾注了程颐一生的心血。正如尹焞所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1]345程颐对《易传》进行反复修改,直到临终前才将书稿交给门人张绎。不幸张绎不久后也就去世了,《伊川易传》未得到及时校正刊印,书稿后来才传到杨时手中。政和四年(1114)十一月,杨时在毗陵(今江苏无锡)校正《伊川易传》,并作《校正〈伊川易传〉后序》。杨时叙其始末说:
伊川先生著《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而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而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
先生道学足为世师,而于《易》尤尽心焉。其微辞妙旨,盖有书不能传者,恨得其书晚,不及亲受旨训。其谬误有疑而未达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辄加损也。 然学者读其书,得其意,忘言可也。[2]675-676
经杨时校订的《伊川易传》使程颐的易学思想得以较全面完整地留传下来。 《伊川易传》后世统称为《程氏易传》,省称为《程传》。《程氏易传》成书后即广受学者推崇,元代以后又与朱熹《周易本义》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因此,杨时校订《伊川易传》的重要意义,自是毋庸赘言的。
二、发挥程子治《易》方法:以心通《易》,以身行《易》
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因为学者秉性的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是不同的个体之间,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就易学发展的历史而言,汉末至唐前之治《易》者多重视训诂考据,致力于易学文本的解读和注疏,由此把握《周易》的思想内涵;宋代易学研究则“不追求《周易》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不停留在经文的表面字义上,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宋易中的各派,包括象数学派在内,都具有这一特征”[3]5。对义理的高度重视,是宋代易学的典型特征。
然而,语言文字毕竟是思想义理不可或缺的载体,不重视对语言文字的训诂,就难以把握其背后蕴含的思想义理。为此,程子提出了读书要“默识心通”的指导思想。《性理大全书》载程子答问曰:
问:何如学可谓之有得?
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为有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要诚意烛理上知,则颖悟自别;其次须以义理涵养而得之。凡志于求道者,可谓诚心矣。欲速助长而不中理,反不诚矣。[4]
程子指出,“闻之”“知之”都是“有得”,但是这样的“得”只是耳闻目见的得,是皮相之得,不是“真得”。真正的“有得”,应该要体道者“默识心通”,在“诚意烛理上知,则颖悟自别”。但是,“得道”之后,又“须以义理涵养”,却不可拔苗助长,否则就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不中理,反而不诚了。在治《易》方面也是如此,程颐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1]248在释《大壮》卦《彖传》时, 程颐又明确说:“正大之理,学者默识心通可也。”[1]870《周易》所蕴含的义理,也是要通过“默识心通”而获得。
基于“默识心通”以“求义理”“求道”的指导思想,程子因而告诫求学者,不能被外在的文字训诂所束缚。如程颐《二程全书·粹言一·论书》中说:“读《论语》而不知道,所谓‘虽多,奚为也’。于是有要约精至之言,能深穷之而有所见,则不难于观《五经》矣。”[1]1 209又说:“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信于辞,则或有害于义,曾不若无书之为愈也。”[1]1 204还说:“思索经义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见,资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误己,亦且误人也。”[1]1 186这都是说,读经书,贵在理解经义,即义理,特别是要有“自得”,不能停留在词句和文字上。他评论文章和训诂之学说:“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章,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是三者,则将安归?必趋于圣人之道矣。”[1]1 185《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又载程子之言曰:“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1]319求之于内即求之于身心之内,求之于外即求之于文字之表。“程颐的这些言论,代表宋学的基本倾向,同汉代经师和后来清代汉学家解经的学风是不同的。这种由经穷理或因经明义的学风,对宋易的形成影响很大。”[3]5
杨时继承程子的指导思想,也提出了“心通”的治《易》方法。他说:“《易》不比他经,须心通始得。……若非心通,纵说得分明彻了,不济事。”[2]380杨时明确地提出,《周易》一书不同于其他典籍,不能只在文字上用功,不能只是满足于文字训诂,而应该用心神去深入地领会,“心通”才能有得。杨时举易学发展的历史为其说法进行论证。他说:
自尧舜以前,载籍未具,世所有者,独伏牺所画八卦耳。当是之时,圣贤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系作之后,更秦汉以迄于今,其书至不可胜纪,人之所资以为学者,宜易于古,然其间千数百年,求一人如古之圣贤,卒不易得,何哉?岂道之所传,固不在于文字之多寡乎?夫尧、舜、禹、皋陶皆称“若稽古”,非无待于学也,其学果何以乎?由是观之,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其用心必有在矣。学者不可不察之也。[2]225
伏羲画八卦时,载籍未具,更谈不上有什么六经,世上所拥有的只有伏羲所画的八卦而已,但是那时的圣贤却很多。文王作辞、孔子作传之后,易学典籍日益丰富,至于今其书更是不可胜纪,但是,“其间千数百年,求一人如古之圣贤,卒不易得”,可见,“道之所传”,并不在于文字的多寡。当然,又正如《尚书》所说的“若稽古”,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文字又不是可以完全抛弃不顾的,那么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其用心必有在矣”。“圣贤之学用心之所在”,就是学者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要“心通”而“自得”。
至于“心通”的具体要领,杨时并未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但他曾介绍其读书、求道之心得说:
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 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象言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2]357
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 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自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谓口耳之学,非所望于吾友也。[2]720
可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是杨时读书、求道的重要心得。所谓“以身体之”者,近似于我们现在所常说的“身体力行”,“体”与“行”互训,即“体”之义为“行”。“以身体之”即是说以身行之,谓亲身践行书中所蕴含之义理与所求之至道。因此,杨时主张,圣贤之学, “要当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所谓“以心验之”,杨时有著名的未发之际体中、验中之论,他说“但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以心验之,时中之义自见”[2]535,又说“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2]565。这里,“以心体之”与“以心验之”的意义大体相同,都是“体悟”或“体知”之义[5]。因此,所谓“以心验之”,即是说以心去体悟书中的理义或所求之至道。
杨时除了继承程子主张以“心通”的方法治《易》外,还继承程子不要“求之于外”而要“求之于内”的治学主张,强调治《易》要“求之吾身”。他说:“大抵看《易》,须先识他根本,然后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见矣,岂应外求……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于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2]380
杨时所说的“求之吾身”,可以从他对《周易·系辞传》“乾坤其《易》之门邪”的解释中见其一斑。《龟山集·语录·南都所闻》记载:
问:《易》曰“乾坤其《易》之门耶?”所谓门,莫是学《易》自此入否?
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说,故有喻《易》为屋室,谓其入必有其门,则乾坤是也。为此言者,只为元不晓《易》。夫《易》与乾坤,岂有二物?……谓乾坤为《易》之门者,阴阳之气有动静屈伸尔,一动一静,或屈或伸,阖辟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所谓门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槖籥乎?”夫气之阖辟往来,岂有穷哉!有阖有辟,变由是生,其变无常,非《易》而何?……张横渠于《正蒙》中曾略说破云:“乾坤之阖辟出入,息之象也。”非见得彻,言不能及此。某旧曾作《明道哀词》云:“通阖辟于一息兮,尸者其谁?”盖言《易》之在我也。[2]379
《系辞传》载:“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周易正义》说:“《易》之变化,从乾坤而起,犹人之兴动,从门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门邪。”[2]418孔颖达认为,“乾坤其《易》之门耶”的说法,只是一种类比,正如人的出入必须经过门一样,《周易》的各种变化,都是从乾坤开始的。孔颖达的这种解释,通俗易懂,受到后人的广泛认可。但杨时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元不晓《易》”,是对《周易》的误读。在杨时看来,所谓“乾坤为《易》之门者,阴阳之气有动静屈伸尔。一动一静,或屈或伸,阖辟之象也”。也就是说,孔子是以门的开关“阖辟之象”来讲阴阳之气的动静、往来、屈伸。他进一步引张载的说法为其观点论证,张载在《正蒙·动物篇第五》中说:“动物本诸天,以呼吸为聚散之渐;植物本诸地,以阴阳升降为聚散之渐。……人之有息,盖刚柔相摩、乾坤阖辟之象也。”[6]也就是说,张载也认为,人类的一呼一吸,正与乾坤阖辟出入之象相似。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人类的一呼一吸,已蕴含了乾坤阖辟之象,反过来说,则是乾坤阖辟之象正在一呼一吸间,这正是杨时所说的“《易》之在我”。“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见矣。”正因为如此,杨时强调,读《周易》应求之于身心之内,而不能求之于文字之表。
杨时强调,治《易》首要的方法是“心通”“自得”。如果不能就自己的身心而求之,“未见《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说得深,即不是圣人作用处,若说得浅,常人之谈耳”[2]311。这都不能对《周易》做出正确的解读。但现实生活中,学者们对圣人经典的研究,却常常只是停留在经典文本的文字上,只注重文字训诂,被文字所束缚。这样的做法就受到杨时的批评,他说:“某常疑定夫学《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于《易》,只是理会文义,未必心通。……如龚深父说《易》,元无所见,可怜一生用功都无是处。”[2]380
在杨时看来,不仅他的同学游酢没有“心通”《周易》,就连龚原、王安石也都只是领会文义而无所得。不仅宋代的学者如此,前代的汉儒更是如此。他说:“汉之诸儒,若贾谊、相如、司马迁辈,用力亦勤矣。自书契以来,简册所存,下至阴阳星历、山经地志、虫鱼草木,殊名诡号,该洽无一或遗者,其文宏妙,殆非后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学渊源论笃者,终莫之与也。”[2]706在他看来,汉代诸儒虽涉猎甚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著书甚多,然而都未穷究道学,“区区汉儒不足学也”[2]707。汉儒这种心逐外物的做法,是不值得后人效法的。
杨时强调“心通”的治学方法,对后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朱子读书法中的“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就是对程子、杨时等人治学方法的提炼。有人问朱熹:“读《易》未能浃洽,何也?”朱熹回答:“此须是此心虚明宁静,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罗得许多义理。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7]2 227很明显,朱熹为学之方重点在内心之“虚明宁静”,也是求之于内而不是求之于外。
三、转程子易理为事理,补程氏易学以象数
目前所见杨时关于《周易》的论说,散见于《龟山集》和其他易学专著的载录。朱熹说,他所见到的《龟山易传》,“传出时已缺乾坤,只有草稿数段,不甚完备。《系辞》三四段,不绝笔,亦不成书”[8]。稍后于朱熹的黄震(1213—1281) 则曰:“《易》自《升》卦以后阙,余皆全书。”[9]481-482可见,其易学专著在宋代即已开始散佚。吕祖谦编纂的《周易系辞精义》曾称引杨时的解说。张栻《南轩易说》裒集程颐、张载、杨时《易》说而成,故部分杨时的《易》说收录于其中。与朱熹、吕祖谦约略同时的晋江人曾种,其所编纂的《大易粹言》也引用到较多的杨时《易说》。其他易学著作如《厚斋易学》《周易会通》《周易传义大全》《大易集义粹言》《周易折中》所引杨时关于《周易》的论说,基本上都出自前述这些资料。
通过阅读上述资料所载的杨时《易》说,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杨时易学最典型的特色就是继承程子以《易》阐发儒理。杨时对《周易》一书高度重视,曾说自己“有间即读《易》”[2]511,而且常常与游酢、陈莹中等学友讨论《易》学中的疑难问题,因此,于《易》多有自己的心得。正如南宋后期的黄震所说:“盖先生平生最用工于《易》,于程门理义之学多有发明。”[9]481-482朱熹也说:“用龟山《易》参看《易传》数段,见其大小得失。”[7]2 221杨时对“程门理义之学”的“发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列举一二。
(一)在义理阐述方面,比《程氏易传》更注重“切于民用”
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性人物,程子所论多涉及阴阳性命天理等内容。这一特色在《程氏易传》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要读懂侧重阐述《周易》义理的《程氏易传》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朱熹就多次说:
《易传》,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盖其所言义理极妙,初学者未曾使着,不识其味,都无启发。如《遗书》之类,人看着却有启发处。非是《易传》不好,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乃磨砻工夫。[7]2 216
《易传》难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无抑扬。若能看得有味,则其人亦大段知义理矣。盖《易》中说理,是豫先说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难。不若《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着便令人识蹊径。《诗》又能兴起人意思,皆易看。[7]2 216
正如朱熹所说的,《程氏易传》所言义理精妙,却不适合作为启蒙读物。尽管杨时在理学和易学上的主张与程颐基本一致,但在论述方式上仍有不同,其中既有对《程氏易传》的深化,更多的则是对《程氏易传》有关观点的具体化。可以说,《程氏易传》是较为纯粹抽象的哲学论说,而杨时的《易》说更多阐述的是贴近生活的人生处世哲理。兹举例说明。
1.如对《大畜》卦《象传》的解释,《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氏易传》说:
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也。[10]173
杨时《易》说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非徒资见闻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则所畜大矣。”[11]308其《孟子解》又曰: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世之学者,欲以雕绘组织为工,夸多斗靡以资见闻而已,故摭其华不茹其实,未尝畜德而反约也,彼亦乌用学为哉![11]308
程子教导人们,要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以畜成其德,由下学而上达,强调为学的积累功夫。杨时则着意强调,君子多识前言往行的目的是为了“畜德”,非徒资见闻而已,也就是要警醒世人,不能追求博而忘记了回归到约。应该说,杨时的警醒,还是有意义的。
2.如《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程氏易传》解释说:
九二居柔,宽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虽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静安恬之人处之,则能贞固而吉也。九二阳志上进,故有幽人之戒。
履道在于安静,其中恬正则所履安裕。中若躁动,岂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则能坚固而吉。盖其中心安静,不以利欲自乱也。[10]100
杨时《易》说解释道:
刚中而承柔,异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难也。居中处说而上无应,故曰幽人,颜渊在陋巷,不改其乐是也。非中不自乱,何以与此?苟有应乎上,则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圣人,虽在侧微,若将终身焉,中不自乱故也。若夫外骛而以纡朱怀金为乐,则利欲交战于胸中而能不自乱者,未之有也,其能贞吉,不亦远乎?[11]308
《程氏易传》指出,“幽人”是“幽静安恬之人”,强调其中心的恬正坚固,是从普遍的义理上阐发。杨时则从卦爻之象进行解说,认为幽人是“居中处说而上无应”之人。因为九二爻居于《履》卦()的下卦,即兑卦()之中,所以说是“居中处说”;九二爻对应九五爻,同为阳刚之爻,非阴阳正应,所以是“无应”。引申为人事,则为居于下位且朝堂上无荐举之人,但却能中心悦乐而不自乱。在此基础上,杨时引用“颜渊在陋巷,不改其乐”作为史证。因为,颜渊正是“居中处说而上无应”的典型人物。相对于《程氏易传》的大谈义理,杨时的解释无疑浅切明白多了。
(二)在取象方面,补《程氏易传》之所未备
众所周知,程子是义理易学的代表性人物,《程氏易传》主要侧重于对《周易》卦爻辞所蕴含的义理进行充分的发挥。正如程子在《易传序》中所宣称的:“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10]49也就是说,《周易》虽然具备“辞、变、象、占”这四种“圣人之道”,但“变、象、占”都寄寓于“辞”之中,易学研究者通过对“辞”的推究考察,就能知道“变、象、占”。由于“辞无所不备”,故程子说:“予所传者辞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程氏易传》对《周易》象数之学的阐发多有阙略。朱熹就针对程子这种重视义理而忽略象数的解《易》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
《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7]2 218
伊川只将一部《易》来作譬喻说了,恐圣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书。[7]2 218
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12]
虽然,杨时继承了程子以义理说《易》的传统,但与程子相比,杨时对《周易》的象数之学有较多的用心。如对《剥》卦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的解释,《程氏易传》说:
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将有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
阴道盛极之时,其乱可知,乱极则自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君子得舆也。《诗·匪风》《下泉》所以居变风之终也。理既如是,在卦亦众阴宗阳,为共载之象。小人剥庐,若小人则当剥之极,剥其庐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论爻之阴阳,但言小人处剥极,则及其庐矣。庐取在上之象。[10]161
《剥》卦上九爻《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程氏易传》解释说:
正道消剥既极,则人复思治,故阳刚君子为民所承载也。[10]162
杨时注《剥》卦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曰:
群阴剥阳,而一刚止乎上,硕果不食也。剥,《乾》五变也,故有硕果之象焉(自注:乾为木果) 。然君道也,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故阴虽上行,刚则不食,与《夬》之上六“不可长”异矣。夫坤顺而艮止,《剥》之成象也。硕果不食者,顺而有以止之故也。坤则顺而已矣。故“履霜坚冰至”,而卒有疑阳之战,顺而无以止之故也。故《坤》之《文言》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然剥终则复,乱极则思治。当是时,君子者,民所载也,故得舆。坤下承之,得舆之象也(自注: 坤为大舆) 。君子而得舆,道盛行也。小人无所庇其身,则剥庐矣。夫阴阳之往来屈伸,理之必至也。小人之为乱,至于剥庐而后已,盖亦不思而已矣。[11]280-281
对比杨时与程子的说法,可以看出,他们都用《剥》卦上九爻阐述“阴阳之往来屈伸”、社会政治之乱极必治,这一核心思想两者是一致的。但具体阐述过程中,则又有以下几点区别值得注意:
其一,程子说“硕果不食”,是“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 所谓“如……”,正是朱熹所说的“伊川只将一部《易》来作譬喻说了”[7]2 218。程子的说法承续王弼《易注》而来,王注说:“处卦之终,独全不落,故果至于硕而不见食也。”[13]212可见,程子与王弼一样,都是从义理上进行阐释。杨时则在此基础上,进而寻找其卦象上的依据。他指出,《剥》卦()是由《乾》卦()五变而来的,《说卦传》说“乾,为木果”,所以有“硕果”之象。此前,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侯果:“艮为果”之说,因为《说卦传》也说“艮,为果蓏”。杨时取象依据虽与前人不同,但其思路却是相通的。由此可见杨时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关注。杨时的这一说法,后来为胡炳文所吸收。
其二,程子说“君子得舆”, 是“乱极则自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君子得舆也。”[10]161所谓“众心愿载于君子”,依据古文常见之文法,此句子中的“于”为介词,表被动,其意译是百姓情愿受载于君子,即百姓愿意乘坐君子的车舆,也就是百姓心甘情愿追随君子。程子的这一解释,应该也是受了汉唐《易》说的影响。王弼注曰:“君子居之,则为民覆荫。”孔颖达疏曰:“君子得舆者,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荫于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之,则得车舆也。”又曰:“若君子居此位,养育其民,民所仰载也。”[13]212《周易集解》引侯果也说:“君子居此,万姓赖安,若得乘其车舆也。”[14]按照《周易正义》《周易集解》的说法,如果君子居《剥》卦之上位,则百姓得安全而有所庇护,百姓也因此得承载于君子的车舆。程子“众心愿载于君子”的说法,与此类似。然而,依照《周易正义》《周易集解》的说法,“君子得舆”的结果就会变成“君子得位”而百姓“得舆”。《周易正义》《周易集解》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该爻《象传》说“君子得舆,民所载也”,他们是将这两句话理解为顺承的关系,即“君子得舆,则民有所载”。这样的解释应该说是不太顺畅的。因此,程子在解释该爻《象传》“君子得舆,民所载也”时又说:“正道消剥既极,则人复思治,故阳刚君子为民所承载也。”[10]162这又是说万民愿意承载君子,那么,程子“众心愿载于君子”全句的真正内涵应该是说:社会乱极思治,百姓心甘情愿地承载君子,就像车载人、水载舟一样,因此有“君子得舆”之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程子《易传》一方面试图延续《周易正义》《周易集解》的说法,另一方面又做了调整和创新,着重阐述民众承载君子的意义,将“君子得舆”解读为“君子得民所承载”之象。与前文所述一样,也是从“譬喻”的角度解读“得舆”。杨时说:“君子者,民所载也,故得舆。”正是承程子“阳刚君子为民所承载”的说法而来。不仅如此,杨时还进一步从卦象上进行解说。“坤下承之,得舆之象也(自注: 坤为大舆)。”这就为“得舆”找到了“象”的依据,而不仅仅将“得舆”说成是一种“譬喻”了。此前,《周易集解》引虞翻、侯果亦以坤为车舆之象。由此可见杨时对汉代象数易学的继承。
其三,程子说,“上九一爻尚存”,是因为如果“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所以,圣人特意创设“硕果不食”的易象,“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10]161。这样说来,似乎上九的“硕果不食”,是圣人的“有意为之”。但杨时的解释与此不同,杨时是从《剥》卦()的卦象上进行解说上九爻的“硕果”之所以“不见食”的。杨时指出:“坤顺而艮止,《剥》之成象也。硕果不食者,顺而有以止之故也。”《剥》卦()由下坤卦()和上艮卦()组成,坤顺而艮止,顺而有以止之,因此,硕果得以“不食”。杨时还进一步引《坤》卦()来论证,《坤》卦()由上下两个坤卦()组成,只有顺而没有止,所以《坤》卦初爻“履霜坚冰至”,顺其势不断发展,到了上六爻,阳气完全被剥尽“而卒有疑阳之战”。与程子的说法相对比,杨时从卦象上解说无疑更切合《周易》的特质。
由此可见,虽然杨时接受了《程氏易传》的义理解释,但是他使用《说卦》的“乾为木果”“坤为大舆”之象来解释爻辞,却为《程氏易传》所无,王弼、胡瑗也未及此。可见,杨时对汉代象数易学的态度与其他义理派的易家有一定的区别。
四、杨时易学的历史定位
王夫之曾指出:“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15]王夫之指出,周敦颐的学说因得到二程的表彰而广为世人所认可,程子则因其学说的声名远播而天下之英才皆聚集于其门下。由此可以看出,在学术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师生双方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情况,在程子与其门生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全祖望说:“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16]除此之外,另有荦荦大者如:洛学之入蜀也以谯定,其入闽也,则有杨时、游酢。其中,由杨时、游酢传入闽地的道南一系对朱熹闽学的产生与发展至为重要。黄百家说:
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观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17]944
僻处海峤的闽人杨时、游酢,不远千里慕名从学于二程,以“程门立雪”精铭刻苦之精神,奋发向上,深受器重,且都跻身程门四大弟子之列。其中,杨时尤得大程子明道称许:“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其归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17]944杨时、游酢二人亦不负程子之厚望,南归后大力弘扬二程学说,并最终形成了宋元以来影响学界极为深远的“道南学派”。
而“道南学派”似亦不能仅局限于福建地域之内。全祖望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17]944龟山因天假其年,在赵氏南渡之后,硕果仅存,成为南宋初期传播学术的核心人物,对“东南三贤”学说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为南宋学术的传承与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