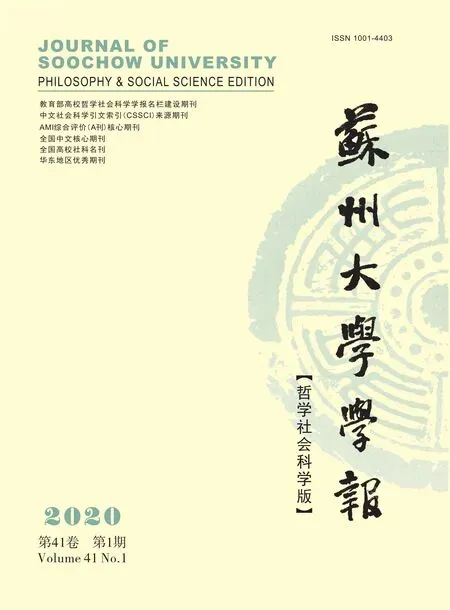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交叉研究的双向进路
代海强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引言
从古至今,意识研究是一个重要难题,科学和哲学都尝试对其进行解答。当下,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出现在神经科学领域。它在近几十年得到了迅猛发展,一方面,要归功于实验技术的不断改善,尤其是功能核磁共振(fMRI)和脑电图(EEG)等非损伤探测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在行为主义在心理现象研究的式微,导致对内在心理神经结构探索的复苏。这样的背景之下,神经科学对大脑意识的研究日臻成熟。与此相应,心灵哲学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也臻于完善,哲学家对意识给出的种种解释几乎穷尽了所有可能性。虽然这两个领域都处理意识问题,但是长久以来二者缺乏合作对话。直到20世纪90年代,哲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问题才逐渐出现在学者视野。不过,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并不在意心灵哲学家的问题,大多数心灵哲学家也不重视神经科学家的发现。因而,彼此之间还处在比较疏远的状态。这种局面导致两种主要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哲学优先论,以查尔莫斯(D.Chalmers)为代表,认为科学问题无法解决哲学问题,哲学因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先性;另一种是以取消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优先论,以丘奇兰德(P.Churchland)为主要倡导者,主张用科学的经验知识取代哲学的抽象思辨,哲学语言应当让位于科学语言。随着争论不断升级,人们开始反思这两种观点,更多人将目光转向开放的立场:尝试建立神经科学与哲学的交叉研究,由此出现了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之间的交叉领域。但是,这个领域的具体性质和处理问题的范围,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立足于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背景,反思二者的关系。概括而言,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为何要交叉?二者应当如何交叉?交叉的范围和限度在哪里?
一、意识难题的两种解决路径
前面提到,针对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关系,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主张神经科学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意识的核心问题;另一种主张用神经科学的研究取代心灵哲学研究。这两种观点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下思考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关系,带有鲜明的倾向,因而值得考察。
伴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意识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有关意识问题的追问却基本上没有脱离以下几个框架:意识是什么,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意识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意识的神经基础是什么。按照查尔莫斯的分类,这里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意识的难问题和意识的易问题。意识的易问题解释意识的现象,对意识的产生机制、功能特性、神经机制进行研究。相比较而言,关于意识本质的说明属于意识的难问题。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的划分彰显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这两门领域的差异。按照查尔莫斯的观点,无论神经科学对意识的发生机制做出怎样的研究和说明,都无法触及意识的难问题。
查尔莫斯的观点有着很强的传统哲学渊源,很多哲学家对经验科学的解释路径持怀疑态度,认为哲学和科学本身属于不同的领域,二者存在学科间的巨大差异。比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经验事实与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分野,前者无法渗透到后者的领域之中。这一精神在哈克那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哲学关注的始终是概念问题,而科学关注的是经验问题,二者的混淆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他说道:“哲学方法因此被理解为完全是先验的,它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或解决办法都被先验的论证证实或反驳,正如数学问题所面对的情况那样。”[1]462-463哈克同维特根斯坦一样,将哲学问题限定在运用语法分析进行概念澄清的框架之内。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并不寻求解释与概念相关的经验事实,而是通过描述语言使用澄清概念的意义。在这种策略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诉诸经验事实解决相关哲学问题都是无望的。(1)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其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态度实际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请比较《哲学研究》第109节:“说我们的考察完全与自然科学无关,这是对的。下面这种感受‘与我们的预想观念相反,可能这样想或者那样想’——无论它指的是什么意思——都不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逻辑哲学论》第4.111码段:“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哲学’一词所指的东西,应该在自然科学之上或者之下,而不是与之平行。)”查尔莫斯在哲学与科学相区分的问题上,与维特根斯坦和哈克处在相似立场。不过,对他而言,这里的区分不是概念和事实之间,而是不同性质的实体(属性)之间。他指出,用大脑神经过程的事实解释意识会产生解释鸿沟,这种鸿沟无法用神经科学内部的理论加以弥补。这就从根本上否决了用神经科学解决意识难题的可能性。
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是丘奇兰德提倡的取消主义。他认为:“我们对心理现象的常识概念构成了一个根本错误的理论,这个理论的错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的原则和本体论最终不是会被顺利地简化,而是会被复杂的神经科学所取代。民间心理学所使用的心理语言概念都不准确甚至错误,它们应该被神经科学的语言概念取代。”[2]67丘奇兰德的思想受到另一种哲学流派的影响,这以奎因和萨拉斯为代表,认为哲学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批判了经验命题与先验命题的区分,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从而为哲学问题的自然科学化路径提供了理由和保证。坚持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寻找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合作的基础。
丘奇兰德的取消主义借用了两组科学概念取代日常概念的经典例子。燃素和热流是比较民间的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氧化作用和粒子动能概念逐渐取代了它们。在丘奇兰德看来,这种取代的现象也适用于民间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关系,心理学中的概念也应该被未来神经科学发展出的概念取消。丘奇兰德用神经科学中的发现构建了一套理论来支撑自己的取消主义。概括来说,他认为矢量运动是大脑表征的核心种类,矢量—矢量的传送转换是大脑计算的核心模型。按照这种理论,意识活动能在这一框架中获得最终解释,而民间心理学中的欲望、信念、高兴等概念都应该相应地被取消,因为后者主要是依赖于命题表征和逻辑语义计算模型的设定。如果取消主义策略成功,那么心灵的彻底自然化就能实现。
应当说,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丘奇兰德的自然化解决路径引发了深远影响。但是,丘奇兰德的取消主义是一种极端版本的意识自然化路径。通过认真反思取消主义,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其理论内部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
二、取消主义的困境
取消主义作为一种极端自然化路径,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困境:理论重构的方法谬误,体现为错误类比的应用;理论构建的结果谬误,体现为意义的丧失。这两者都显示出取消主义本身的困难,因而将其作为解决意识问题的方案值得怀疑。
第一,错误的类比。前面谈到,取消主义依赖于科学史上成功取消的案例。但是将这种类比全盘放在“意识-神经”关系上却值得怀疑。一方面,燃素与氧化作用之间不存在本体论的差别,也就是说,燃素与氧化作用都处在物理层面,用后者代替前者并不需要本体论的解释保证。但是对于“意识-神经”关系来说,它们二者是否属于同一本体领域恰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取消主义不能以神经等同于并可取消意识概念的假设作为出发点,这一假设反而需要另外的本体论解释。从这一角度来说,取消主义在做类比的时候,需要进一步论证“意识-神经”的关系能够合法的类比于“燃素-氧化”的关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了进一步说明这里的错误类比,我们需要仔细审查下取消的内涵。一般来说,我们会面对两种类型的取消:
(a)系统内的取消:当且仅当在同一个系统内存在能被替代的理论时,取消才能发生。
(b)系统间的取消:当且仅当在不同系统之间存在能被替代的理论时,取消才能发生。
丘奇兰德主张的取消论实际上是系统间的取消,是意识现象和神经事件之间的取代关系;但是他的类比所依赖的原型却是系统内的取消,是相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物理事件之间的替代关系。这里存在着跨系统的鸿沟,需要更多的辩护说明。
另一方面,取消主义所遵从的类比模式不能套用在“意识-神经”关系之上。以燃素说和氧化作用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所做类比的实质。燃素说是三百年前化学家用来解释火燃烧这一现象的学说,认为火是由细小而活跃的微粒组成的,能够和其他元素结合,也能够自己单独游离存在。大量游离的燃素微粒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火焰。而近代化学家发现,所谓的燃素说根本不能成立,实际上火是由氧化作用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取消的案例之中,实际上有三个要素:燃素、氧化作用、火。这里被取消的是燃素,而不是火。现在我们依然使用火这个词语,并且用氧化作用来理解它,尽管不再使用燃素这个概念。但是在“意识-神经”关系中,有一点被取消主义忽略:这里并没有出现三个概念,而是只有两个概念。如图所示:

以信念为例,我们发现,实际上按照“燃素-氧化”模式所需要取消的X并没有真正出现。日常心理学所用的信念概念本身不是为了解释某个心理事件,而是对心理事件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经语言的被替代物不是信念这个概念,“意识-神经”关系中的取消模型打错了靶子。
第二,意义的丢失。心理概念的使用,是主体为了传达自己的内心生活,除了表达主体的内心感受外,还具有和听者交流的作用。当一个人说“我很疼”是为了报告自己当下的状态,或者寻求别人的帮助,或者为了获取别人的同情。听者要么会想办法安慰这个人,要么寻求医学手段为其治疗从而减轻痛苦。因而,每个心理概念的使用,几乎都承载特殊的意义。但是,当把心理概念替换成神经语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将“我很疼”换成“我的神经细胞中的X被激活”,后面这句话要表达什么?并且,听众在听到后面这个报道时会有什么反应?在这里,我们发现,心理概念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一个心理事实,还在于表达其他内容,比如寻求帮助、需求治疗,等等。而神经语言更多是在描述一个事件发生时的神经事实。这两种语言本身属于不同的概念系统,在进行替换时,会导致前者意义的缺失或者扭曲。取消主义或许会反驳:当我说“我的神经细胞中的X被激活”时,我就是表达与“我很疼”相同的意义。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不借助心理语言,神经语言能够全部保持本该被心理语言乘载的意义吗?答案是不能。并且,既然不能,那么就需要借助心理语言进行解释,但是,如果神经语言的意义依赖于心理语言对其进行解释,那么对心理语言的取消就变得没有道理。
通过以上考察,本文认为,取消主义企图用神经科学的发现完全取代日常心理概念,从而也连带取消心灵哲学研究的方式,不具有决定性证据,充其量提供了一个未来研究方向的可能性。就目前情况而言,它的前景并不乐观。与此相对,查尔莫斯在二元论背景下强调意识的难问题似乎将神经科学发展限制在一定界限之内。但是,考虑到后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成果,我们认为查尔莫斯的观点也存在实践的缺口,很多最新的研究都尝试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突破意识的难问题(下面将会具体讨论)。实际上,除了上述两种典型观点以外,目前更多的观点处在这二者区间之内,它们显示了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交叉的领域和范围。在讨论二者的进路和关系的问题时,存在两个进路:一是心灵哲学向神经科学的进路,这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灵哲学对神经科学的反思,另一个是心灵哲学对神经科学的影响;二是神经科学向心灵哲学的进路,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神经科学对传统心灵哲学问题的解决,另一个是神经科学对心灵哲学中的概念的修订和补充。下面我们分别对它们展开讨论。
三、心灵哲学对神经科学的反思:方法论的沉思
神经科学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领域之内不断完善发展。但是,对其成果进行反思却是心灵哲学需要做的工作。神经科学的发现证明了什么?其发现成果的本质是什么?其研究方法的局限在哪里?这都需要心灵哲学介入思考,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被称为关于神经科学的心灵哲学。神经科学对大脑意识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对从低级感觉到高级理性推理的大脑功能的解释,直接落脚于大脑神经元活动的区域定位。这种策略的兴起有赖于单细胞电位记录的应用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的崛起,它能够为大脑功能作用提供基于神经元活动的解释。哈德卡斯尔(V.Hardcastle)对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进行了反思,指出在神经科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和局限。这些反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经科学的过去和未来。
哈德卡斯尔考察了神经科学在发育神经生物学(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效,承认这为细胞、分子水平上的认知结构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但是,她指出,这些研究成果的未来走向并不乐观。对神经元中单细胞电位记录而言,它假设所处理的对象是一个离散神经系统。依靠电位记录方法,至少可以确认脑皮层中的不同加工区域,比如,对视觉系统来说,已经在脑皮层中确认了36种不同的视觉加工区域。这些研究成果不断累加,使得脑功能图谱更加丰富多样。不过,哈德卡斯尔指出单细胞记录面临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难题。
在宏观层面,单细胞记录与认知活动的解释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裂缝。目前科学最多能够同时记录150个神经元,而大脑中实际存在的神经元有数十万之多,这些神经元在类型、应答特性、与其他细胞的关联性方面具有巨大差异,这无疑为揭露整个大脑意识活动的真实状态设置了巨大障碍。正如哈德卡斯尔所说:“他们关于所有被记录细胞行为的结论都将局限于非常基本的刺激-反应研究,以及有关神经元亚型的关联分析。因此,他们基于这些相对数量有限的实验而总结出的功能远远无法真实反应细胞的真实作用。”[3]365
微观层面,单细胞动作电位记录面临技术操作和方法论上的困难。科学家使用单细胞附近的电极进行记录,这会得出细胞的动作电位。但是,除了这些动作电位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电位被记录下来,这包括轴突束产生的电位差或是来自平行的一系列树突的场电位。除此之外,当微电极的阻抗相对较低时,细胞外电极会在相同时间内获得来自多个神经元的信号,它们是对象细胞附近区域所有的细胞记录。而科学家面临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困难,即如何从这些复杂电位数据中分离出他们想要的信号,并且从电极输出的记录中得到真实、可信、有效的数据。一种可行的路径是采取合适的方法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解释。认知科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即理论渗透对于观察数据的影响无法避免。在神经科学领域,观察数据的理论渗透性更为明显,比如“通过使用公认的方法论技巧对原始数据进行操纵,可以轻松改变观察的基本属性。恰当的数据修饰与数据捏造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3]369在具体实验面前,对于数据的判断既会涉及明确的计算或者推导形式,也会涉及个人的判断和技能。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是相同的实验数据,也存在被不同解读的可能。不同的分类选择方法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数据,而这里并不存在哪个算法或者方法更好的问题。
此外,哈德卡斯尔对广泛使用的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了反思。这种非侵入式记录装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单细胞记录的不足,能够观察整个大脑认知活动在某一时刻的神经活动。但是关于成像技术,还存在很多困难:第一,神经活动与大脑活动的断裂问题。核磁共振的空间分辨率有0.1毫米,每个扫描样本大概只能涉及半秒钟的活动,这种不精确性离完整解释大脑整体活动还存在很大距离。第二,减数法(subtraction method)的局限性。所谓减数法,是建立在实验条件的对比之上。功能成像的研究会假设两个实验条件,然后认为这两个实验条件会伴随着所研究的认知或知觉过程而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两个实验条件的大脑活动记录加以对比,寻找两个活动之间的区域差异。这种获得的区域差异被认为包含了所研究对象的神经基质。这里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这种减数法不能确认所发现的差异的确与认知过程有关,而不是与其他同时碰巧发生的过程有关。二是减数法作用的效果依赖于测量设备的灵敏性,其结果是,仪器越差,这种方法对于定位来说就越有效。但是,随着技术的改进,低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s)也会增加,那么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神经位点会在实验中表现出差异。这种效应会不断扩大,直至位点多到像是整个大脑都参与了每一个认知过程。这种效应导致的结果是:将这种效应贯彻到底,科学家可能最终找到一种统一的、简练的方法描述大脑的活动区域。任何寻找特定区域功能的方式都是错误的。
哈德卡斯尔对神经科学做的反思,显示了认知科学哲学面临的诸多难题,这为我们提供几点重要启示。首先,神经科学的测量手段决定并限定了其实验报告的信息维度。对测量手段而言:一方面,受到先前手段所支撑的理论框架的影响,其结果是在这些框架的范围内的补充和增益,这就导致实验的信息输出被局限在了特定的范式之内;另一方面,随着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测量手段也在不断改变,其结果是工具一直更新换代,最优工具几乎永远不能实现。比如,神经科学神经元层面的“刺激—反应—观察—记录”的模式并非是唯一的解释认知心理活动的方法。除了向下的神经元、分子等微观层次的技术外,我们或许还需要细胞组织、神经簇等中等层次的观察技术,甚至是大脑区域组织、跨区域组织等高级层次的观察手段。除此之外,亚神经元等更微观层面的生物活动也应当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这却显示出神经科学的发现总是在纠错路径上前行,很难说某一时期掌握的信息就是现实的终极解释。神经科学并没有为事实解释提供终极答案,只是提供了特定工具测量条件下的某种解释维度,神经科学的各种发现很难穷尽所有认知心理活动。
其次,在神经元信息和日常心理学事件之间存在着领域鸿沟。无论是神经元电位记录还是功能磁共振成像,它们所提供的都是大脑神经的部分活动信息,这些信息与日常心理学的认知现象之间的关系只能采取两种措施予以连接,一种是彻底的心理-物理还原策略,另一种是建立桥接原则。对于前者而言,还原的纲领并没有在科学家之内达成普遍一致,并且,日常心理学广泛存在的事实,也为这种还原路径设置了很大障碍。对于后者而言,桥接原则无法回避第三者无穷倒退的难题,在神经事件A和认知心理事件B之间的任何中间环节X,都需要补充X与A和B之间的关系要素X1,X2…,这就使得桥接策略面临操作上的难题。
以上反思在方法论上指出了神经科学发现的实质和方法论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它揭示了神经科学理论自身的适用范围。将这一反思运用到心灵哲学问题上会发现,神经科学要想完全取代心灵哲学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如果说神经科学是关于大脑功能意识的解释进路,那么可以说,它并不是唯一的进路,在其理论所不适用、观察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则是心灵哲学发挥作用的领地。
四、心灵哲学对神经科学的启示
心灵哲学对神经科学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局部和全局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在具体的心灵现象上,心灵哲学能够提供概念的分析和抽象的思辨,从概念和思辨角度提供对心理现象的考察。后者是指,心灵哲学能够在基本问题层面,反思心理现象问题的本质,促进神经科学定位研究问题。这两个层面对认知科学都具有重要影响,也是促进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交叉、共同解决意识问题的重要途径。
在局部层面,心灵哲学家在具体心灵现象问题上能够提出新的概念,为神经科学提供新的概念图景。以信念为例,哲学家钱德勒(T. Gendler)提出了alief(准信念)和belief(信念)的区别,他指出alief是一种心灵状态,具有联合表征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内容,能够被主体内在或者外在环境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激活。这种状态“比信念或者想象更为原初,并且能够直接影响行为”。[4]634-663塔马尔认为,alief概念能够解释很多传统信念论很难处理的不同寻常现象,例如玻璃栈道上的恐慌者案例。这个概念的提出为神经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可能的解释路径。例如,在这个概念的假设下(2)这个概念只能算是一个假设,既未在经验上得到确证,也未在哲学上获得一致认可。曼德尔鲍姆(E.Mandelbaum)就对alief这一概念提出了反驳,他认为alief可能有两种版本:(1)强健的准信念(a robust notion of alief),这种信念具有命题内容;(2)紧缩的准信念(a deflated notion of alief) ,这种信念没有命题内容只有关联内容(associative content)。但是,这两个信念都不具有理论上的可靠性。他据此认为:“没有理由发明一种新的强健的准信念概念。”[5]197本文不打算介入这场争论之中,只是想表明,新概念的提出需要更可靠的支持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可以根据alief和belief两个概念的差别设计实验,从而为解决某些现象的难题提供依据。而且,这一概念的提出如果成功的话,神经科学的研究将会因为新概念的出现而影响之前的理论框架和系统。
从全局层面来说,心灵哲学会对意识现象的本质进行界定和澄清,这将有助于神经科学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神经科学主要研究大脑意识和认知,这方面的内容在哲学中也有相应的心灵哲学进行研究。心灵哲学在处理意识问题时,对意识核心问题的定位对神经科学有启发作用。在神经科学发展内部,广泛存在着默认的观点,即神经科学是关于大脑意识本质的研究,它能揭示大脑的结构、功能、意识内容等。因此,很多人认为神经科学处理的问题包含了意识最核心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观点遭到了很多心灵哲学家的反思批判。查尔莫斯指出,意识的易问题并没有触及意识的核心领域,“对它们作出解释的问题是难题(puzzle)而不是谜题(mystery)。这种观念,即一个物理系统可能在这些意义上是‘有意识的’,原则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问题,最终用神经生物学或者计算的术语来解释这些现象也没有明显的障碍”[6]119。真正困扰哲学家的谜题是意识的难问题,或者说关于意识经验本身的主观性问题:人们有成为他们自己的某种感觉,当具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可以说他/她有意识。意识的易问题之所以容易,是因为它只需要解释某些行为或认知的功能,也就是说解释在因果作用机制下意识的功能如何发挥作用。而意识的难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不要求解释这些功能,而是要解释:“为什么这些功能的执行会伴随着经验?”[6]120显然,难问题与易问题不属于相同的问题,因此需要不同的回答。
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否认上述区别。丘奇兰德认为,查尔莫斯对意识的难问题的论述依赖于概念论证,即在概念上论述存在难问题的可能性。查尔莫斯提供的一种论证策略是“解释鸿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具有相同神经结构的生物具有不同的意识体验,也就是说,神经结构功能的解释无法回答意识的产生问题。但是,在丘奇兰德看来,这种“可想象性”其实是一种谬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想法,是因为人们对神经科学的具体机制还不了解,一旦对这里的复杂机制能够充分说明,那种“可想象性”就并不存在。
除了针对意识的难问题的直接否定外,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对意识的难问题发起挑战。普林斯(J. Prinz)认为,由于意识的难问题对人们的长期影响,使得人们认为对意识的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无关紧要。他指出,这种看法不足取,除了意识的难问题之外,很多问题都和意识的本质问题相关,包括意识是什么,意识的内容是什么,意识在大脑什么位置发生,意识在什么条件下产生,意识如何从物理状态中产生,等等。其中,他认为最后一个问题类似于意识的难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除了查尔莫斯提出的形式以外,还能以另外的形式被提出:“将有意识的状态和无意识的状态区别开的心理或者神经机制和过程究竟是什么?”[7]381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的难问题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它完全可以在神经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被解决。并且,从普林斯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将意识问题看作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系统问题,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伴随另外问题的解决,不同问题之间能够相互推进。他指出:“机制和过程的问题能够通过探索另一个问题而获得解决:在什么条件下潜在的意识状态能够变为意识状态?一旦我们知道了意识的内容是什么和意识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我们就能着手处理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具有意识状态?并且最后这里有一个谁的问题:是谁具有意识?除了人以外的动物有吗?婴儿有吗?机器有吗?”[7]382对于普林斯来说,意识的自然化研究比起意识的难问题而言,一点也不缺少重要性,而且,在这一探究之中,意识的难问题也有望解决。
其实,丘奇兰德和普林斯都尝试以神经科学进路解决意识的难问题,但是这种路径本身只是建立在对未来科学的想象上的,这种可想象性与查尔莫斯提出的可想象性都没有决定性依据。不过,丘奇兰德与普林斯二者的进路也有差异,各自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丘奇兰德认为神经科学能够完全解释意识经验,这具有经验可能性。对普林斯来说,他没有给出如何解决查尔莫斯的意识的难问题的门路,只是尝试为意识的难问题进行重构。但是,这种诉诸神经机制和过程的重构缺乏说服力,其做法更像是回避问题,因为对查尔莫斯来说,意识的机制和过程研究根本无法触及意识的难问题本身。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发现心灵哲学对意识本质问题的概念澄清能够帮助神经科学对其所声称的意识本质研究进行反思。心灵哲学能够帮助神经科学区分出原因解释和理由解释:原因的解释——找出因果机制和功能解释;理由解释——在描述中,为心灵现象给出更多说明。在这些问题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意识本质是什么,当我们从第一人称视角思考的时候,我们如何将其与第三人称(科学的观察)进行区分?在心灵哲学家看来,这些问题恐怕还不能通过神经科学的原因解释得到完满回答。如果神经科学希望在意识本质问题上走得更远,那么就需要来自心灵哲学的思考和建议,并且正视心灵哲学家提出的挑战和难题。
五、神经科学对心灵哲学的推动
神经科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成果能在自身领域之外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归功于它对一些现象背后机制的发现和解释。这些机制帮助心灵哲学更好地理解意识活动的因果关系、功能机制、神经生物基础和内在过程等内容。心灵哲学在思考相关意识现象和解决意识问题时,很难再忽略神经科学的这些发现,这对心灵哲学更好的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我们看到,在具体细节方面,神经科学也为心灵哲学提供了修正和补充。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很多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能够提供给心灵哲学,帮助后者完善哲学思辨。我们知道,哲学研究起于思辨、落脚于常识,而终于思辨。很多哲学思辨的基础是一些基本的常识或者直觉。但是,当哲学家诉诸常识或者直觉的时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这些常识具有稳固的结构而不被轻易推翻,那么风险就不会太大;反之,如果这些常识或者直觉自身具有严重不稳定性,那么依赖于它们的思辨的风险就会增加。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发现在介入常识或直觉的过程中,能够改变常识或直觉变更的周期,或者打破原有的常识或直觉的坚实基础。
在神经科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可以随处找到比较典型的案例。例如,神经科学对感觉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领域的发展表明某些传统的观点是错的。在常识中,人们倾向于认为感觉是直接表征外部实在,感觉系统被认为是“诚实的”(veridical)。这种传统观点具有三个特点:(1)要素对应性:感觉系统中的信号对应于外部对象的性质;(2)结构对应性:感觉系统中的状态结构对应于被其反映的外部对象的构成性质之间的结构;(3)系统安全性:感觉系统的加工过程不会歪曲外部事件。但是,阿金斯(K.Akins)通过对皮肤上的热感接收系统的研究表明,感觉系统是“孤芳自赏的”(narcissistic)[8]345,而不是“诚实的”,并且表明上述三个特点都是错误的。再比如,传统观点认为疼痛是一个典型的感觉案例,因而投入大量的研究想要通过揭示疼痛的奥秘从而解决其他感觉问题。但是,哈德卡斯尔通过研究发现,在疼痛和其他感觉之间并不存在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共同点,因此“不能将疼痛经验作为意识的直观且无问题的案例”[9]384。尽管对于疼痛的解释出现了很多,比如取消主义、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等,但是这里缺乏一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理论家在基本事实面前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对基本的神经科学知识背景知之甚少。另外,即使对于愿意取用神经科学知识的哲学家来说,他们对神经科学的细节普遍无视。当真正进入关于疼痛的精细机制研究,会发现更多的内容和细节。哈德卡斯尔指出,疼痛的神经机制其实可分离的双重系统:一个是和其他感觉相似的系统;另一个是疼痛经验独特的抑制系统。这表明疼痛是非典型的感觉系统。类似的发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意向性上面也同样具有这种颠覆性的表现。正如比克尔(J.Bickle)等人所说:“自然科学在细节上的有用发现不断显示出一些传统方案的天真幼稚。”[10]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神经科学的进步对于处在传统哲学论证底部的一些常识或者直觉来说具有决定性的矫正作用,它对一些基本内容的修正,将为以基本知识为出发点的哲学思辨提供更为稳固的平台;反之,如果哲学思辨建立在一些错误的直觉之上,将会导致哲学领域争论不休的局面。因此,从这方面来看,神经科学的持续发展,对哲学思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修正作用以外,神经科学的发现也会扩充经验概念,神经科学的发现理应积极运用到心灵哲学的思考之中,为心灵哲学的研究提供最新的信息和素材。比如著名的盲视现象,它是指“缺乏意识承认情况下的视觉能力”[11]x。对于盲视者来说,他的视皮层的初级区域受到损伤,他会声称自己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在随后的询问中,他对视觉对象的位置或者运动所作的判断远远大于随机猜测。这种现象打破了意识和视觉经验的必然连接关系,显示出存在无意识状态的视觉经验。而这种意识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为相关的哲学思辨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在盲视案例出现以后,心灵哲学家很难无视无意识视觉经验的存在,从而需要重新考虑视觉经验的意识问题。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神经科学和心灵哲学的交叉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关系之中,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是,正是因为前途未卜,才为二者的交叉前景增添了无穷魅力。本文提出的双向进路既是对以往研究状况的概括反思,也是对未来可能发展的预期。面对意识问题,神经科学需要心灵哲学的培育,心灵哲学也需要神经科学的滋养。与此同时,真正跨学科的合作更需要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对神经科学中各个细节工作的把握将有助于哲学家重新反思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问题;从哲学视角出发去从事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能促进后者扩大自身研究范围,拓展新的研究视野。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势必在未来更加繁荣昌盛,为人类意识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