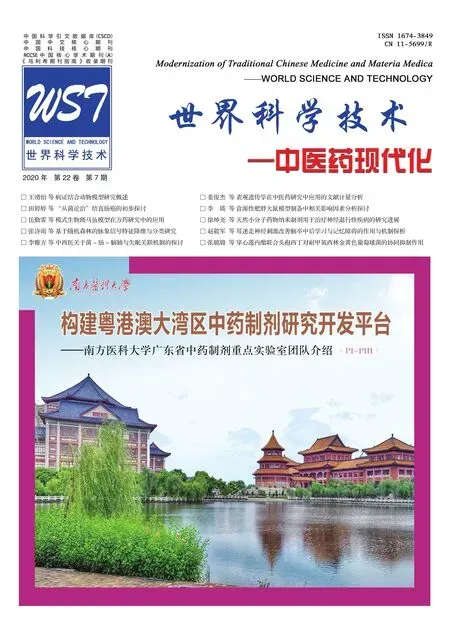基于数据挖掘对溃疡性结肠炎中医用药规律的分析*
彭卓嵛,陶丽芬,蓝斯莹,蔡林坤,李桂贤**
(1.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宁 530023;2. 广西中医药大学 南宁 530001)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病因未明的慢性肠道炎性疾病,目前西药常规治疗UC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未取得让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在临床缓解维持和内镜缓解方面的证据质量相对不足[1]。中医药在治疗UC 上显示出其标本兼治、副作用小、可长期用药、远期疗效可观等特有优势,但各医家观念不一、治疗方法繁杂,用药差异性大且缺乏大样本的临床研究[2-3]。本研究通过搜集近十年来中医药治疗UC 的文献并提取相关信息,对该病的证型分布及用药规律进行数据挖掘、分析,以期探索该病药物配伍规律,从而指导临床制定合理有效的方药。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检索数据库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Pubmed,时间限定在 2009 年 1 月至 2019 年5 月,采用数据库高级检索,检索词包括:溃疡性结肠炎、中医、中药、中医药,以中国知网展示检索式为例,知网:SU=溃疡性结肠炎and(SU=中医or SU=中药or SU=中医药)。
1.2 纳入标准
本研究的纳入标准:①纳入的研究对象经诊断标准确诊为UC;②涉及处方用药的与中医药治疗UC 相关的各种临床研究文献;③观察组样本量≥30例;④处方需包含证型(或据症状、治则可判定证型)、药物组成、剂量,且只计主方用药,兼证及伴随症状的加减用药忽略不计;⑤纳入的方药经研究证明临床疗效确切,总有效率≥80%;⑥纳入处方均为煎煮汤剂。
1.3 排除标准
本研究的排除标准:①不符合所列的纳入标准;②动物实验研究、单纯理论性研究及综述性研究;③个案、验案;④观察组采用联合灌肠、针灸、贴敷等方法难以排除影响者;⑤观察组中西医联合治疗,不能排除其影响者;⑥一稿多投或同一药方发表的多篇文章,只取其中1篇,余不计。
1.4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中医证候规范参照《中医诊断学》[4]及《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5],如湿热证、湿热蕴结证均归为大肠湿热证,脾虚湿蕴证、脾虚湿盛证归为脾虚湿困证,脾胃气虚证、脾胃虚弱证均以脾气虚证计,一方治疗多证者经规范证型后保留其所有证型,两书中未见有相对应证型者保留其原有证型。中药名及性味、归经、归类的规范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6]及《中药学》[7]进行标准化处理,中药名如湘曲、建曲→神曲,天丁→皂角刺,红藤→大血藤。统计性味、归经时以每一性味、经别出现1 次为1 个统计单位,凡一药归数性味、数经别者分别统计之。
1.5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首先,应用Excel 表格依据方名、证型、药名、功效、性味、归经建立数据库,采用双人复核输入法录入;其次,运用SPSS 22.0 软件进行频数统计及聚类分析;最后,运用Modeler 15.0 软件将188 味药物通过Apriori 算法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挖掘处方中的药物关系关联的强弱。
2 结果
2.1 证型频数分布描述
本次研究初检出752篇文献,据纳排标准纳入184篇,经规范后共得到49 个证型,频次最高的六个证型分布为大肠湿热证63 个(25.93%)、脾肾阳虚证36 个(14.81%)、肝郁脾虚证20 个(8.23%)、脾虚湿困证18个(7.41%)、脾气虚证17 个(7.00%)、寒热错杂证14 个(5.76%),该六证占总证型频次的69.14%。
2.2 药物频数分布描述
本研究纳入方剂243 首,药物188 味,运用SPSS 22.0 软件对药物进行频次统计,共用药频次2773 次,对用药频次大于29 次以上的列入表1,其中用药频次最高为甘草169 次,最低为秦皮、地榆均29 次。

表1 用药频数分布表
2.3 药物关联规则分析
运用Modeler 15.0 软件,选用Apriori 算法对188味中药进行关联规则挖掘,其中设定最低条件支持度(S)为14%,最小规则置信度(C)为90%,最大前项数 为 4,且 提 升 度(L)≥1.0,得 出 关 联 规 则 结 果见表2。
2.4 聚类结果分析
在频数统计结果基础上,本研究采用SPSS 22.0软件对前28 味高频药物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可得到冰柱图(见图1)和树状图(见图2),由图可见6 个聚类结果,分别是:补骨脂-五味子-吴茱萸-肉豆蔻-肉桂(脾肾阳虚证)、柴胡-防风-干姜-附子-乌梅(寒热错杂证兼肝郁证)、黄柏-秦皮-白头翁-地榆-赤芍-黄芩(大肠湿热证)、薏苡仁-山药-陈皮(脾虚湿困证)、白术-党参-茯苓(脾气虚证)、黄连-木香-白芍-当归-甘草(大肠湿热证)。
2.5 功效、性味、归经
2.5.1 药物功效分类统计
由表3 可见,药物使用总频次为2773 次,功效分类涉及18类,前六类分布为:补虚药(32.53%)、清热药(16.80%)、理气药(8.44%)、收涩药(6.56%)、利水渗湿药(6.24%)、温里药(6.20%),其中尤以补虚药及清热药为主,二者占药物类别总频次的49.33%。
2.5.2 药物四气统计
药物四气总频次为2756 次,由表4 可知,临床大多数药物偏温(38.03%)、寒(28.41%)、平(23.73%)三性,占四气总频次的90.17%。

表2 药物关联规则表(S≥14%,C≥90%,L≥1.0)

图1 高频药物聚类冰柱图

表3 药物功效频次分布

表4 药物的四气频次分布
2.5.3 药物五味统计
用药五味总频次为4475 次,以苦(30.50%)、甘味(29.56%)为最,其次为辛(23.31%)、酸(7.96%)、涩(4.60%)、淡(3.64%)、咸味(0.42%)。具体见表5。
2.5.4 药物归经统计
所用药物归经总频次为8496 次,其中以脾胃经(38.58%)为最,其次为肝、肺、心、肾、大肠、胆、膀胱、小肠、三焦、心包经。见表6。

表5 药物五味频次分布

图2 高频药物聚类树状图
3 讨论
3.1 中医辨证分型特点
本次研究发现,频次最高的六个证型分布为大肠湿热证(25.93%)、脾肾阳虚证(14.81%)、肝郁脾虚证(8.23%)、脾虚湿困证(7.41%)、脾气虚证(7.00%)、寒热错杂证(5.76%)。其中又以大肠湿热证为首,表明湿热为UC 最主要的病理因素,这与该病脾虚的基本病机是密切相关的。中医学认为,UC 的发生多由于感受外邪、饮食所伤、情志不畅、劳倦过度等使脾气受损,脾虚湿滞,久则湿从热化,湿热壅滞,气血互搏,损伤肠络,导致血败肉腐,内溃成疡。且湿热日久易伤及脏腑阴阳气血,出现脾肾俱阳虚,后期形成寒热、虚实错杂之证。由此可见,脾虚为其本虚,气滞、湿热、瘀毒为其病理产物,尤其湿热乃为UC 的一大病机及核心病理产物,其可加速该病病程进展[8],湿热不祛,脾虚难复是本病复发难愈的根源所在,并且迁延不愈易导致患者肝郁气滞,情志失调为诱因又为影响因素,故临床上肝郁脾虚证亦常有之。综上可知,本研究结果中临床常见辨证分型分布情况与UC 慢性病证演变过程是基本相吻合的。

表6 药物归经频次分布
3.2 用药规律分析
3.2.1 基本病机及治则
从本研究的关联规则结果来看,在S≥14%,C≥90%,L≥1.0 条件下,挖掘出的 28 个关联规则中,以白术出现20 次最高,其次是甘草、党参、白芍、茯苓、陈皮、木香、当归、黄连、山药、黄芪、吴茱萸、黄芩、防风,可知在临床常用的关联性较强的药物多为补气健脾药、清热燥湿药、温里药和理气药。且以上主要的二阶、三阶、四阶关联规则中配伍规律多为补气健脾药+理气药、补气健脾药+清热燥湿药、补气健脾药+温里药、补气健脾药+理血药、补气健脾药+解表药、补气健脾药+利水渗湿药、补气健脾药+理气药+利水渗湿药、补气健脾药+理气药+清热燥湿药,从中不难发现补气健脾药在UC 治疗中的主导作用,从中可窥探脾虚湿滞为UC 发病基本病机和关键作用因素,引伸出该病从脾论治的基本治疗大法。并且在置信度为100%时挖掘出的陈皮and 党参→白术及陈皮and 党参and 甘草→白术关联规则中均用到健脾燥湿要药之白术,均配伍甘、平补益之党参和芳香理气之陈皮,这两药物组合规律也充分体现UC 治疗中从脾论治为其关键所在。除补气健脾药以外,清热燥湿药、理气药、理血药、温里药、利水渗湿药、解表药等多种功效药物都涉及该病的治疗,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分别契合病机各个侧面以达到治疗或者辅助治疗的目的,符合了UC 多病因综合作用、多病理因素堆积的病机特点,临床上当在明辨病因病机基础上,以补气、健脾、清热、理气、活血等多法联用方能取得满意疗效。
结合药物功效、性味、归经等统计结果分析,使用频率最高的依次为补虚药、清热药、理气药,用药以温、寒、平三性为主,药物偏苦、甘、辛、酸,归经多为脾胃经、肝经、肺经、心经、肾经、大肠经。可见UC发病主脏在脾(胃),还与肝、肺、心、肾、大肠密切相关,与UC 发病初期以脾病为先,久病及肝、肺、心、大肠,后期致脾肾俱虚的疾病发展特点相一致。用药功效多为补虚、清热、理气类,体现了该病临床治疗从脾论治为主,清热除湿、调气理血并重,后期注重补火助阳的治疗思想。在四气、五味方面,二者均可反映中药作用的共性和基本特点,结合药物功效分析,甘可补可缓以补益脾气,苦燥湿以健脾除湿,辛发散以行气活血、调和气机,酸收涩以涩肠止泻,温性可温肾助阳,寒性可发挥协苦味而清热燥湿,平性药作用和缓而顾护脾肾之本虚,诸药性味合参、多法协用以达标本兼治的目的。不难发现,以上UC 用药特征、治则与明代李中梓提出的著名治泄九法中的“清凉、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六法相一致。与关联规则结果相对照,两相印证了该病脾虚湿滞的基本病机,符合久病及肾,湿热、气滞、血瘀诸邪夹杂的病理特点。故临床用药施治多以补气健脾、温肾暖脾、清热燥湿、疏肝理脾、活血化瘀立法,多法联用以标本兼治,往往能奏显疗效。
此外,从单味药统计频次上看,使用频次大于150次的药物为甘草(169次)和白术(152次),其次是黄连(118 次)、党参(118 次)、白芍(118 次)、木香(105 次)、茯苓(100次),与关联规则中强关联药物使用频次前8味相同,从中亦可发现,甘草和白术用药频次要远高于其它药物。从功效上分析,两者均为补气药,甘草性甘平能补脾而益气,白术功善益气补脾而燥湿,为健脾要药,可见益气健脾为治疗UC 的关键治则,反映了脾虚湿滞为其基本病机并贯穿于整个病程始终,临床治疗当顾护脾气,标本兼治。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证实,甘草和白术均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癌、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作用[9-10],为胃肠道疾病常用药。关于其具体机制,国内外实验表明甘草可通过抑制NF-κB 调节的促炎信号通路有效治疗UC[11-12]。白术提取物可通过调节激酶抑制炎症介质而改善结肠炎症[13],或通过促进多胺介导的上皮细胞迁移、增加TGF-β1及EGFR的基因的表达、调控钙离子以促细胞迁移及E-钙黏蛋白表达等不同机制促进肠粘膜损伤的修复[14-16]。
3.2.2 辨证处方规律
本次研究通过前28 味高频药物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提取出6 个聚类结果,分别是:①补骨脂-五味子-吴茱萸-肉豆蔻-肉桂,为四神丸加肉桂而成,该方的运用体现了脾肾阳虚致泻的证机,正如《医方集解》所言:“久泻皆由肾命火衰,不能专责脾胃”,肾阳虚衰,火不暖土,脾失健运,肠失固涩而成泄泻,故采用具有温肾健脾、涩肠止泻之功的四神丸原方配伍补火助阳要药之肉桂治疗。②柴胡-防风-干姜-附子-乌梅,为乌梅汤加减而成,该方的运用从侧面反映了该病日久致气滞、寒热、虚实夹杂的复杂病情变化特点。UC 的发生常与感受风邪、情志不畅相关,是以《素问》曰:“以春伤于风……乃为洞泄”,《景岳全书》曰:“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此肝脾二脏之病也”。故该方切合此病因在乌梅汤基础上配伍了两味风药,一取柴胡疏肝理气之力,二取防风轻扬升散且具燥湿之性,可助脾升清并助肝气升发,配伍精妙得当,适用于寒热错杂证兼肝郁者。③黄连-木香-白芍-当归-甘草,为芍药汤的主要组成方药。UC 发病以脾虚为基本病机,日久湿从热化,湿热壅肠,气血搏结伤络,血败肉腐成疡。芍药汤是针对大肠湿热证证机而拟定的要方,具有清热燥湿、调和气血之功,方中黄连苦寒入大肠经,功善清热燥湿解毒,白芍、当归、甘草和营理血、缓急止痛,木香调气则后重自除,组方体现了“行血则便脓自愈”之义。④黄柏-秦皮-白头翁-地榆-赤芍-黄芩,为白头翁汤加减而成。重度UC 病理特征表现以热毒为主,热毒深陷血分,燔灼肠胃气血而见下痢脓血。该方药物组合侧重于切合热毒血痢的证机特点,白头翁苦寒入血分可清热解毒、凉血止痢,黄柏、秦皮、黄芩清热燥湿止痢,赤芍清热凉血解毒,地榆凉血止血,全方共奏清热解毒、凉血止痢之功。⑤薏苡仁-山药-陈皮,为参苓白术散部分组成方药,脾虚失运是UC 的基本病机,乃脾虚湿蕴,饮食不化而为泻。方中运用淡渗甘补之薏苡仁,既利水渗湿又健脾止泻,且利水不伤正,补脾不滋腻。山药具有“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之效,配伍陈皮既能理气又可燥湿,三药合用可使脾健湿除,泄泻可止。⑥白术-党参-茯苓,为四君子汤主要方药。脾气虚弱既是UC的发病基础[17],又始终贯穿于整个病程中。党参甘平以益气补脾,配伍白术以补气健脾除湿,佐以补利兼优之茯苓,可助白术健运脾气,且使参、术补而不滞,并以其淡渗之性渗利湿浊。三药相合补气健脾之效强,用于UC 脾气虚证证方相宜,疗效可彰。
3.3 小结
UC 基于其难治愈、易复发的疾病特点,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现代难治病之一,中医药在治疗UC 上显示出其标本兼治、副作用小、可长期用药、远期疗效可观等特有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UC 发病率呈明显升高趋势,关于该病的中医临床研究逐年增多,但各医家治疗方法繁杂,用药差异性大。目前,国内对本病的辨证治疗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了中医药疗效评价机制的形成和有效方剂的推广使用。本次研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中的频数统计、聚类分析、关联规则等方法,较全面的对近十年中医治疗UC的用药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通过此次数据挖掘发现,UC 发病以脾虚为本,湿热壅滞为核心病理因素,与肝、肾、肺密切相关,证型分布以大肠湿热证、脾肾阳虚证、肝郁脾虚证、脾虚湿困证、脾气虚证、寒热错杂证为主。核心用药多味苦、甘,入脾胃经,功效上以补虚、清热、理气、收涩、渗湿、温里药为主。聚类出的核心药物组合多由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四神丸、乌梅丸、芍药汤、白头翁汤等经典方剂化裁而来,挖掘出的大部分强关联药对及潜在方剂组合均体现了从脾论治的用药思路,且清热除湿、调气理血并重,后期注重补火助阳,扶正祛邪并用,临床上常多药相合,多法并用以达标本兼治目的。
本次研究在宏观层次上分析了中医药治疗UC 的配伍特点,对完善该病的中医辨证论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挖掘出的部分强关联药对及潜在方剂组合可为临床中医药治疗该病提供一些借鉴和新的思路,也能更好的指导临床进行合理有效的处方用药。但鉴于本次数据挖掘整体上纳入文献的标本量较小,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研究,纳入文献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且此次挖掘出的潜在方剂组合还需临床实践进一步验证,故临床医者选方遣药仍当明辨病机,随症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