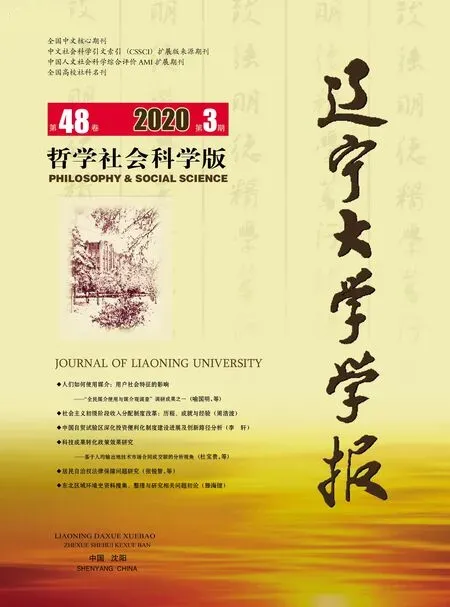谱了曲子的诗:《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群众歌曲的文学分析
罗 曼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人民日报》(1949-1966)副刊是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广涉艺术的全部门类,其中的音乐主要是以群众歌曲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群众歌曲属于大众文艺的组成部分,易为群众喜爱,易于广泛传播。根据不完全检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登载的群众歌曲近300首,这同那个时期全国创作的群众歌曲达数万首的总量相比,还是个很小的数字。如“根据中国音乐家协会一九五三年不完全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年中,各地产生了一万首群众歌曲”〔1〕;1961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曾有“三万件作品应征”〔2〕。同其相比,《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登载的不足百分之一。不过,《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终究是一个“高品位”平台,它登载的作品通常是优中选优,择优刊用,所以其典型性、代表性还是很强的。
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细化,对歌词的重视与研究日渐增多,一些歌词选集和研究专著,如晨枫的《中国当代歌词史》(漓江出版社,2002)、刘楚材的《中国歌词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曾宪瑞的《中国当代歌词精选》(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等,也相继面世。被誉为“歌词泰斗”的乔羽曾说过,“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一直沿着两种轨道在发展。一种是与音乐相结合的,这便是歌词。一种是所谓自由体的诗,它不受音乐的制约……许多年来,歌词一直支持了新诗,使新诗不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我阅读范围所及,文学史家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写中国新诗史吧,我相信田汉、塞克、光未然、贺敬之等人的歌词作品,会在这部诗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3〕乔羽之后,崔健的摇滚乐《一无所有》被选入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七卷八十年代的诗类作品,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专辟一节讨论,盛赞其“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绝佳境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登载的群众歌曲,作一个有益的历史回顾和文学分析。
一、“唱报纸上的歌”:《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群众歌曲概述
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曾由无数人民英雄为之牺牲奋斗的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一个“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4〕的时代,用胡风的抒情话语说,这是“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宇宙都在向你祝贺”〔5〕,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满怀幸福、自豪、乐观、向上的情感走向新生活的时代。唱歌抒情成了那个时代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唱报纸上的歌”成了那个时代最美的文化时尚。“不论形势变化多么快,报纸会给我们一些适当的歌唱材料。由此,群众对报纸上的歌曲,有了深刻的信仰,唱的是一天比一天多,有些人更以先会唱报纸上的歌曲为光荣”,“工厂里,学校里,部队中,电台上,以及有关部门的行政领导干部,每当选择新歌的时候,都是先找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又成了新歌曲的传播者。”〔6〕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正是构建“唱报纸上的歌”这一社会文化时尚,并使之延续至60年代的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报媒传播者。
“唱报纸上的歌”,首先是报纸上有歌。歌有多少,是怎样的状态等,需要的是数据描述分析,亦可名之为概述。
根据不完全检索,《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登载的歌词有近300首,登载的类型多为首次发表的新歌,如《歌唱祖国》①凡行文中提及的出自《人民日报》的歌曲作品,因数量太大,均不予加注。《打败美帝野心狼》等,也有一些是转载社会传唱的“热歌”,如《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在登载的这些歌词中,大部分是词谱完整的歌曲,也有一部分没有谱曲的纯歌词。这里将它们分为谱曲的歌词与没有谱曲的歌词,也是数据描述分析的第一个内容。
一是谱了曲的歌词,如王莘的《歌唱祖国》;安波和木青的《哈瓦那的孩子》;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张士燮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周振佳的《学大寨赶大寨》;闫肃的《学习那英雄的解放军》;郭沫若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李准的《奔向农业前线》《一条大道在眼前》;光未然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有200余首。
二是没有谱曲的歌词,但在原载中已明确标注为“歌词”,如郭沫若的《新华颂(歌词)》;放平的《春光好(歌词)》《祖国颂(歌词)》《葵林曲(歌词)》《湖南屈原农场》《我有一颗跃进心(歌词)》《山外青山楼外楼(歌词)》;管桦的《植树歌(歌词)》;洪源的《哥哥复员我当兵(歌词)》;文莽彦的《对歌赞公社(歌词)》;刘岚山的《新丝绸之路歌(歌词)》;章明的《钢八连赞(歌词)》;“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工农兵业余演出队的《达斡尔人民最听毛主席的话(歌词)》;张永枚的《春天(歌词二首)》《胜利的旗帜(歌词二首)》《前进!革命接班人!(歌词)》《扛枪干革命(歌词)》;党永庵的《我们这一代(歌词)》《贫农下中农之歌(歌词)》;田间的《为歌唱列宁诞辰纪念作——歌词二首》;司马宇文的《草原上来了筑路工人(歌词)》;《古巴民兵歌词集锦》;司马文森的《衷心赞美——献给英雄的阿尔及利亚(歌词)》;昆明部队某部业余演出队创作的《咱连有个神枪手(表演唱歌词)》;(苗族)石太瑞的《快把姑娘接进庄(表演唱歌词)》等,30余首。
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引发我们对歌词与曲谱或音乐的关系,特别是歌词与诗的关系的思考。
数据描述分析的第二个内容,是歌词作者群。歌词作者群是歌词作为生产的第一环节,其大小、水平直接关系到歌词的优劣。依据检索,这里把歌词作者分为三类。
一是音乐界的作曲家或词作家。作曲家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曲者、著名作曲家瞿希贤,创作的歌词有《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斗!》《苏联人民干得好》等多首;《白毛女》的曲作者、著名音乐家马可,创作的歌词有《歌唱毛主席(歌曲)》;《在村外小河旁》《老房东查铺》的作曲者、国宝级的作曲家唐诃,创作的歌词有《红旗插上济州岛(歌词)》;当代蒙古族戏剧音乐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著名作曲家美丽其格,创作的歌词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词)》;《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作者、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劫夫,创作的歌词有《我们走在大路上(歌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等儿童歌曲的作曲者、被人们誉为当代“儿歌大王”的作曲家潘振声,创作的歌词有《过春节》;《兄妹开荒》编剧之一的作曲家安波,创作的歌词有《哈瓦那的孩子(歌曲)》《啊,睦南关!啊,红河!(歌曲)》《睡过一夜到早晨(献给亚、非、拉丁美洲被压迫的弟兄)(歌曲)》等。
词作家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刘三姐》的词作者乔羽,创作的歌词有《拳头对准美国佬!(歌词)》;《卖报歌》《渔光曲》的词作者、田汉夫人安娥,创作的歌词有《中苏友好歌(歌词)》;《社会主义好》《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词作者希扬,创作的歌词有《胜利进行曲(歌曲)》《干革命,干到底(歌词)》;《敢问路在何方》的词作者闫肃,创作的歌词有《学习那英雄的解放军(歌词)》;《在村外小河旁》的词作者、音乐期刊编辑周振佳,创作的歌词有《学大寨赶大寨》,以及招司创作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词)》,党永庵创作的《贫农下中农之歌(歌词)》,林非相创作的《向毛主席敬礼(歌词)》,韩乐群创作的《开门红(歌词)》等。
二是音乐界外的作家、诗人等。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的作家、诗人和知识分子,对歌词的写作是极为看重的,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歌词的写作经历,如瞿秋白、郭沫若、沈心工、李叔同、刘大白、陶行知、刘半农、闻一多、周若无、徐志摩、黎锦辉、田汉、安娥、老舍、光未然、公木、端木蕻良、蔡楚生、贺敬之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登载了大批的由作家诗人写作的歌词。具体有郭沫若的《新华颂》《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歌词)》《铁路运输歌(歌词)》《六一国际儿童节歌(歌词)》《人民的领袖万万岁(歌词)》等;马凡陀(袁水拍)的《送军粮(歌词)》《“六一”国际儿童歌(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歌词)》《金日成将军之歌(歌曲)》等;管桦的《我们签名拥护世界和平(歌词)》《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歌曲)》《植树歌(歌词)》《祖国(独唱歌曲)》《走进英雄的行列》《庄严的声明,愤怒的吼声(曲谱)》;田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王亚平的《朝鲜人民胜利歌(歌词)》;刘白羽的《歌唱白云山(歌词)》;邹荻帆的《中缅两国是胞波(歌曲)》《欢唱天安门(歌曲)》;李准的《一条大道在眼前(歌曲)》《奔向农业前线(歌曲)》;田间的《歌唱党(歌曲)》《大跃进颂》《为歌唱列宁诞辰纪念作——歌词二首》《列宁颂(歌曲)》《民兵战歌(歌曲)》;欧阳山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歌(歌词)》,司马文森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歌曲)》《衷心赞美——献给英雄的阿尔及利亚(歌词)》;丁毅的《我爱我的祖国(歌词)》;萧三《北京——哈瓦那之歌(歌曲)》《毛主席来到天安门(歌曲)》;艾青的《中苏人民并肩前进(歌曲)》;魏传统的《中朝人民好比亲兄弟(歌曲)》;李季的《石油小唱(歌曲)》;高占祥的《我们是有志气的青年(歌曲)》;徐迟的《峨眉山歌(歌曲)》;郭小川的《中苏友谊颂(歌曲)》;张志民的《反对头号大坏蛋(歌曲)》;张永枚的《前进!革命接班人!(歌词)》《扛枪干革命(歌词)》《春天(歌词二首)》《胜利的旗帜(歌词二首)》;刘岚山的《新丝绸之路歌(歌词)》;贺敬之的《南泥湾(歌曲)》;金波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曲)》等。
三是业余的词作者。群众歌曲原本就是一种民间创作,工农兵参与歌词写作是一种天然的力量资源。文艺副刊同样有一批这样的写作者,时任北京《人民日报》副刊主编的王亚平曾讲到,“在来稿中,每天收到的十分之六七都是快板、诗、歌曲。写稿的多半是工人、学生、农村知识分子,和城市的文艺工作者。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大家面对着光明、胜利、新鲜的事物,不由得触动感情,发为歌唱。”〔7〕如《捍卫人民的祖国》的词作者是解放军“一一九师王德英”;《打败美国野心狼》的词作者是“平生只写过一首歌词”,时任志愿军炮兵连指导员的“麻扶摇”;《东方红(歌曲)》的词作者是农民歌手李有源;《我是一个兵》的词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某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后并入中南军区艺术剧院虽事专职写作,但更是“激情满怀的解放军战士”〔8〕的“陆原”;《乘胜前进》的词作者是北京第一机械厂工人温承训;《毛主席著作如宝灯》的词作者是农民诗人王老九;《赠缅甸友人》的词作者是陈毅元帅;《越南小英雄》的词作者是北京市黄化门小学的白雪燕;《永远在我身边(歌曲)》的词作者是时任青海日报社编辑朱丁;《支持越南,声讨美帝》的词作者是空军某部战士演出队王秀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词作者是伊犁军分区的宣传干事李之金;《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蕉萍(原名姚筱舟,笔名取自“焦坪煤矿”);《人民公社就是好》的词作者是淄博七中老师李步霖;《向北京致敬(歌曲)》的词作者是新疆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塔依浦江;《歌唱毛主席(歌曲)》的词作者是山海关红瓦店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于爱体等。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力量齐整的歌词作者群,它是新中国十几年广大群众喜欢“唱报纸上的歌”的资源保证。《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以其平台优势集合了这样一个歌词作者群,对推进群众歌曲创作和传唱的意义是长期的、持久的。
二、群众歌曲的歌词形式与内容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群众歌曲包含着一些有意味的启示,并体现于歌词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
就歌词的形式而言,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文艺副刊发表了一批没有谱曲的歌词。这些歌词既是作为“诗”来发表的“歌词”,又是没有谱曲,甚至也可说是不需谱曲的“诗”。这使人不免联想到五四以来新诗创作中曾有过的现象,“有些诗人并非有意去写歌词,但他的诗被谱了曲,人们争唱,如徐志摩的《海韵》等。有些人的诗被谱了曲,但大家并不唱它,而只当诗来读,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9〕歌词与诗本为同宗,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有的,比如最简单的事实是,歌词是唱的,要求“合乐”,诗是读的,不受乐的限制,但也要讲究韵律。五四新文学中的新诗创作曾一度散文化到连韵律也不讲究,所以鲁迅曾说过“诗歌虽有眼看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住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1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新诗创作,或在会议上,或约诗人如臧克家和袁水拍等,反复谈到新诗问题,谈论的观点和鲁迅大体是一致的。处在同一节点的群众歌曲的歌词写作同样也有一个探索的需要,而核心就是歌词的“合乐”,满足唱的需要。下面是几首曾被广泛传唱的“热歌”歌词,以其为例,试做分析: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麻扶摇《打败美国野心狼》,《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0日第3版)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嘿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他不留情。(陆原、岳寄《我是一个兵》,《人民日报》1952年8月15日第3版)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她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 坚决学习,大寨人/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呀嘛另安排/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周振佳《学大寨赶大寨》,《人民日报》1964年3月10日第6版)
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心欢/北京城里的毛主席啊/我虽然没有见过您/您给我的幸福却永远在我身边。(红旗歌谣《永远在我身边(歌曲)》,《人民日报》1961年6月30日第8版)
这几首歌词并非出自名作家、名诗人之笔,但曾脍炙人口,谱曲后广为传播。其共同特征:
一是短小精练,“一听就懂”。歌曲是音乐艺术中规模最小、篇幅最短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群众歌曲,一般在3分钟左右,歌词要受其时长制约,短小是必须的。张永枚说“歌曲是时间的艺术,听众一不注意,就滑过去再不回来了”〔11〕。所以听歌不比读诗,读诗可以玩味,听歌听的是即时感受,“一听就懂”才谈得上感受,因此要求语言“口语化”,张永枚称之为语言的“易解性”。上述几首歌词都具备这样的特点,称得上好歌词。即便像《永远在我身边(歌曲)》有诗的优美与含蓄,也是“一听就懂”。与之相反的例子也有,如《葵林曲》,登载时明确标识为“歌词”,其第二首是:
一叠葵叶怀中抱/姑娘生来最勤劳/左手编出团圞月/右手编出金银绦/团圞月,金银绦,亚赛织女把花挑/人重风流物重用/换得幸福价更高。(放平作词,《人民日报》1962年3月10日第6版)
在诗的结尾处有两注:“*圞〔luán〕”“*绦〔tāo〕”。这两注只解决了读音,而听歌者还要加上释义,如“圞”即圆的意思,“绦”多作衣物边沿的装饰品,此外,“亚赛”“释义为类似,好似”,也需要解释。短短几句歌词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谱曲是不会有人去做的。歌词拒绝“晦涩”。
二是语言凝聚,犹似水气凝聚而为露珠。水气是要表现的内容,露珠是由内容凝聚而成的情感。歌词是“发乎情”的创作,要的就是这个情感。上述四首诗,题材内容分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新中国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农业建设中大寨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应该说题材都很大,但歌词中全然没有对题材内容的宏大叙述,也没有繁文缛节的修饰,而是分别凝聚为“雄赳赳气昂昂”的乐观与自信、“嘿嘿嘿枪杆握得紧”的坚定不移、“干起来,干起来”的大寨精神、在“没有”背后是“永远在我身边”的幸福感。如果说诗有“诗眼”,文有“文眼”,那么这就像是歌词的“词眼”。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的赵元任曾说过,“读诗有读诗的味儿,唱歌有唱歌的味儿,而且不是能够同时并赏的,诗唱成歌就得牺牲掉它的一部分的本味,这是不得不承认的。”〔12〕这里说的是欣赏,创作也是这样,歌词写作不得不牺牲掉诗歌写作可能要表现的内容。周巍峙曾讲到一个“词句空洞”的例子,说《歌唱毛主席》(大民、朱孟词,耿介、怡明曲)这首歌“从中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像太阳,毛主席像爹娘写起,接着就写毛主席如何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组织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粉碎五次围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北上抗日,建立陕甘宁边区,深入敌后,打得鬼子投了降,后来又进行解放战争,农民们实行土改闹生产,翻身做主人,一直唱到‘军民团结消灭贼老蒋,全中国解放,幸福永无疆’”〔13〕。这首歌词,什么都不舍,散而不聚,没有情感的“露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空洞”。
三是歌词的语言内孕着音乐的节奏感。歌词“合乐”也有着很复杂的内容,择其简单的,如语言节奏感与音乐节拍的协调试作说明。上述几首歌词,除了“押大致相近的韵”外,就是有着极强的节奏感,即便不是唱,而是读,它也会强制你读出节奏来。以《我是一个兵》为例,词作者创作历经了“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的《枪杆诗》的启示,到联想“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抗日歌曲中的歌词,再到写出“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七字句的歌词,最后锤炼成以五字句为主的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14〕这个过程是语言的锤炼,减少了可有可无的语言交代,强化语言节奏感,为配曲带来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这些就是优秀的群众歌曲可以使我们悟到的一些启示。
从内容上看,新的群众歌曲歌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红色内涵”。
群众歌曲可以说古已有之,但按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音乐家吕骥的看法:“新的群众歌曲”产生于1930年代,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为标志,以“作为群众革命斗争的武器”为基本特征〔15〕。《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秉承这一传统和精神,其登载和发表的群众歌曲体现了这一特征,即在题材和主题上体现为进步性、革命性的特征,这里把它概括为“红色内涵”。
“红色歌曲”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是1952年8月19日登载的一篇歌颂红军的民间故事,其中写道:
从这时起,人们唱起了红色的歌曲:山高遮不住太阳/黑夜过去天要亮/洪水滚滚掀波浪/潘家河来了共产党……(《“红军老祖”的故事》,《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3版)
按照这个故事,红色歌曲出现于1930年代,与吕骥所说的群众歌曲产生的时间是一致的。
在新中国十几年的时间里,二者是融合为一的,而且逐渐强化。这种强化是通过《人民日报》的两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体现出来的:一是1958年1月7日发表的《肃清黄色歌曲》,一是1958年1月30日发表的《掀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歌咏运动》。在后一篇文章中,针对群众歌咏活动,回顾了抗战时期,“反动的黄色歌曲异常猖獗”,具体指《何日君再来》《处处吻》《卖相思》等,“但革命的红色歌曲却像狂风暴雨,成为时代的主流”。这里说的“红色歌曲”,是指聂耳、冼星海当时创作的群众歌曲,如《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救国军歌)、《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保卫卢沟桥)及《胜利的开始》《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这样,“红色歌曲”就成了一个与“黄色歌曲”相对立的概念。之后,又有署名文章推广红色歌曲〔16〕。1960年代初,在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中,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推荐八首革命歌曲为标志,有了“群众革命歌曲”的提法,“大家来唱革命歌曲”成为了社会文化时尚的一种新形态。再之后,开始有《红色歌曲》(江西省音乐工作者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革命歌曲大家唱》(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音乐出版社,1964)《革命歌曲大家唱(第二集)》(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音乐出版社,1965)先后出版。这些,大体包含了作为大众文艺的群众歌曲在那一时期的演进脉络。知道了这一脉络,就可以理解这一时期群众歌曲的题材与主题,最终都集中于“歌颂”。
一是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祖国。如《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在我身边》等。
二是歌颂英雄、歌颂模范、歌颂子弟兵、歌颂人民的精神风貌。如《学习那英雄的解放军》《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娘子军连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听话要听党的话》《我们走在大路上》《人人歌唱好八连》《焦裕禄是俺们的知心人》《歌唱二郎山》《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王杰的枪我们扛》等。
三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人民公社就是好》《学大寨赶大寨》《社员都是向阳花》《一条大道在眼前》《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等。
四是歌颂和平与国际友谊。那个时代我国结交了不少亚非拉朋友,这方面的歌曲也比较多,如《赠缅甸友人》《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哈瓦那的孩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紧》《莫斯科——北京(歌曲)》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的歌曲总要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有人将新中国十几年的历程分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六十年代前半期。按照这种说法,群众歌曲表现的主题精神也是有变化的。如新中国初期,歌颂新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平与国际友谊的歌曲就多些,其中还包括译介的苏联、朝鲜等的歌曲;社会主义建设和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题材的歌曲多些;六十年代前半期,歌颂英雄、模范、子弟兵和人民精神风貌的歌曲多些。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歌颂性创作带来的口号式写作倾向。这个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存在,如王亚平曾说到许多歌词“只能做一些空洞的叫喊与政治口号的呕(应为讴——笔者注)歌”,“和快板犯着同样的毛病,只从题目上来看,尽是‘打到江南去’‘百万大军下江南’‘打到南京去’‘我们要和平’等等。歌词的内容也不外‘南京解放了!南京解放了!’‘活捉李宗仁,捉住坏老蒋’,‘要和平,要和平,争取自由平等!’‘刀光闪闪,号声嘹亮,百万大军过长江’。”〔17〕新中国建立后,这种写作倾向并没有完全解决。
三、歌词作为“好诗”的生成形态
歌词是为“唱”而写作的诗,因此歌词写作比诗人写诗多了一层“合作”的心理意识,词作者写词必须想着“合乐”,想着曲作者。
1957年,管桦在故乡有感而发,为孩子们写了一首歌词,回京后请瞿希贤谱曲。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诗。后经反复研读,渐为所感,创作了那首为人们深情传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个故事,说出了50年代就有的一个简单道理:“被谱了曲的诗(歌词),不一定是好诗;好诗却应该是可以谱曲的”,“诗人和作曲家的合作,应该表现在歌词同曲谱的‘天衣无缝’上。”〔18〕深究细查,发现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登载或发表的优秀歌曲背后,都有一些词曲合成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歌词作为“好诗”的生成形态。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
一是与好曲同步完成的“好诗”。
典型的例子是王莘创作的被誉为“第二国歌”的《歌唱祖国》。他在晚年曾说,“我一生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
王莘在延安时,曾师从冼星海、吕骥等学习音乐,还参加过《黄河大合唱》的排练、演出,曾担任过《河边对口曲》中王老七的领唱,是一个作词、作曲、表演都经历过的艺术家。他带领着群众剧社,还有一架在张家口缴获的钢琴,转战南北,天津解放后,定居天津。
1950年9月,王莘去北京购买乐器路过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蔚蓝的天空”等场景,令他心潮澎湃,兴奋极了,酝酿已久的歌唱祖国的创作欲望,瞬间“找到了形象生动的切入点”。在返程的车上,那铿锵有力、富于节奏的歌词随口吟唱而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回到天津后,他激动得彻夜难眠……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推敲和修改,终于完成了初稿,三段歌词和副歌的和声也配好了。”〔20〕
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首歌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王莘作《歌唱祖国》,《人民日报》1951年9月15日第3版)
不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主席得知王莘就是《歌唱祖国》作者时说:“这首歌好”,还特地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送给王莘,并为他亲笔签名。2019年6月,《歌唱祖国》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与曲谱同步完成的“好诗”,再一典型例子是《我是一个兵》。词作者陆原酷爱写作,尤其喜欢音乐,抗战胜利后认识了曲作者岳仑。两个人都是兵,又是“唐山老乡”,又在一起搞文艺工作,一个任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一个任音乐分队长,志趣相同,经“商量,决心要写一首‘兵之歌’”。经长期酝酿,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敲定歌词后,“岳仑吸取民歌乐曲和鼓点节奏,一鼓作气谱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曲调,谱曲几乎冲口而出。不到1个小时,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激情满怀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21〕它不仅传播到了赴朝参战部队,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而且在国内军民同唱,家喻户晓。最令人激动的是,1959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由230名将军们组成的“将军业余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轰动全场,轰动全国,轰动世界。
二是因诗好而被谱曲的“好诗”。
这类好诗,其创作初衷大多并不是为谱曲而作,但因诗好而为作曲家相中,其间包含感动,于是为之谱曲。这类被谱曲的好诗比较多。典型的如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是一首至今还有人误认为是雷锋写过的诗,其实不然。这首诗最初发表于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后陆续收入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中。雷锋很可能读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新民歌三百首》,并在日记中做了摘抄。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登载了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本报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雷锋日记摘抄》和《雷锋的生活片断(图片)》。在《雷锋日记摘抄》中“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写的是: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音乐家朱践耳说:“《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是我在阅读《人民日报》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朱践耳读完这首小诗”,“受到了感染”,很快为之谱了曲,并将之发表在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上,署名为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歌名为《雷锋的歌》。1963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推荐八首革命歌曲”,其一便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但词作者署名不再是雷锋,而是“蕉萍”。这中间,有一个朱践耳苦心查找原作者的过程。“蕉萍”原来是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采矿技术员姚筱舟的笔名。姚筱舟回忆说,“当初我写诗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歌词”〔22〕。但就像“书有自己的命运”(马克思语),“好诗”也会不胫而走,音乐人总是热衷于为之谱曲。
与之相似的例子很多,如曾唱出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乐观与自信的《打败美国野心狼》,后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其歌词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526团某连政治指导员麻扶摇于1950年10月所作的出征誓词。因为它是一首“好诗”,先由连队中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谱曲在连队传唱;继而在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的《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中引为开头语;最后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作曲家周巍峙看到该战地通讯电讯稿,深为感动,不到半小时就为出征誓词谱了曲,并于1950年11月30日首刊于《人民日报》。由于周巍峙当时不知词作者是谁,发表时只有曲作者。直到该歌曲获1954年文化部一等奖才找到词作者麻扶摇。再如《永远在我身边》,首发时词作者署名为“红旗歌谣词”。《红旗歌谣》为郭沫若、周扬所编,瞿希贤从中筛选了这首“好诗”而为之谱曲。另据,郭沫若也视之为“好诗”,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后由中央乐团配器演唱,这也就是后来社会广泛传唱的《金瓶似的小山》。一首好诗,两度被名家谱曲,这在音乐史上也是常见的事。后查知词作者为青海日报社朱丁。还有陈毅的诗《赠缅甸友人》:“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刘兆江为之谱曲为同名歌曲,也属于这种情况。
三是借用名曲为之配词的“好诗”。
这种情况最早出现于新文化运动初。乔羽曾回忆道:“时代变化了,人们要唱新的歌,限于历史条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新的作曲家。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想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而且时间持续甚久”,“等到赵元任出现的时候,中国便有了自己的掌握现代音乐技巧的作曲家,从而结束了按旧有曲调填词的时代。”〔23〕
这里说的“结束”,应该是指按“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填写新词,不是指按乐配词。按乐配词在中国素有传统,新中国歌曲创作由于历史的某些特殊性,有时还会根据需要被用来为现实服务。最典型的是洛水(祝一明)创作的《歌唱二郎山》: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那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那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誓把公路修到那西藏。(洛水词《歌唱二郎山》,《人民日报》1952年8月18日第3版)
1950年,毛泽东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进军西藏的伟大号令,并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修建川藏公路是新中国开国后的一项重大工程,历时四年,数千军民英勇捐躯。二郎山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其工程环境险恶,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为它献出生命。1951年夏天,时任副政委的剧作家魏风,率领文工团到二郎山慰问筑路部队,大家都为筑路指战员的豪情壮志和英雄事迹所感动,男高音歌唱演员孙蘸白因感而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时乐濛作曲的大合唱《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建议把这首曲子填上修筑川藏公路的内容。魏风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把填词的任务交给了洛水。洛水也在感动之中,欣然接受任务,投入创作。就这样,一首利用时乐濛《千里跃进大别山》,具体应为其中的《盼望红军快回来》的原曲,由洛水配词,饱含着热情与激情,颂扬筑路英雄的歌曲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诞生了。歌曲第一次演出就获得了筑路官兵的欢迎,三次“返场”。很快,它就成了在祖国建设的各处工地传唱的热歌〔24〕。
新的群众歌曲的创新性和生命力不是借西方曲调配词,也不是沿用古曲填词,而是从民歌中吸收营养,或借助民歌曲调,或借鉴民歌风韵,创造新歌。这在新中国群众歌曲创作中成功的经验还是不少的。洛水的《歌唱二郎山》所借用的曲调《盼望红军快回来》就是吸收民间曲调而来。更为典型的是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东方红》的曲调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在《人民日报》既可以看到《骑白马》曲调的《东方红》(陕北民歌1952年11月2日第3版),还可以看到在这之前另一首《骑白马》曲调的《带着群众干》(1949年2月2日第4版),如下图:
或许歌词《带着群众干》是歌词《东方红》的前身,最终《东方红》借民歌曲调而成为经典,可视为借用名曲为之配词的“好诗”。美丽其格在1951年国庆前夕闭门拉奏着音域宽厚的马头琴,写下了那首总会唤起人们美好回忆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也可列为此类。
古人说,“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管子·戒》第二十六)与这话匹配的莫过于歌词。歌词藉谱曲可“无翼而飞”,歌词“发乎情”能“无根而固”。《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群众歌曲中的歌词,特别是其中那些优秀的歌词,借助歌唱,或走进千家万户,或唱遍大江南北;因“发乎情”,或给前行者以激励,或为民族自强而助力,成为那个时代的“热歌”,甚而传之久远,成为经典,成为人们回望历史的情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