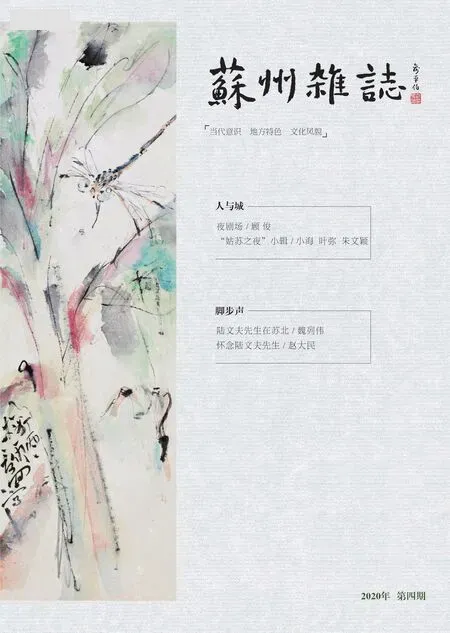『姑苏之夜』小辑

☉ 摄影:孙建
浮生六记 小 海
我不知道苏式生活如何定义,但我晓得和生活于斯土斯邦的人密切相关,哪怕是虚拟人物。比如沈三白,比如芸娘。人们还喜欢从熟悉的吴地代表作家陆文夫、范小青、苏童等人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我想,苏式生活的当代况味,倒也可以从已故老友陶文瑜的《探梅》一诗中,略窥其风雅之一斑。像是当代沈三白写给他的芸娘的。原诗如下:
缥缈山下看梅花,又看旧人又看花,
花是萍水相逢人,人是一生一世花。
什么样的生活堪称苏式夜生活?你问一百个苏州人,恐怕会有一百零一种回答。在这些答案中,总会有人想起并提及沈三白和芸娘的故事。闺房食粥、夜读《西厢》、七夕夜拜、中秋夜游、易装同行等等。这是二百年前,文人虚拟的一种苏式夜生活。
记得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写过一篇谈古城保护的文章。大意是,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古城古镇古村落的价值反而会愈发凸显,因为越古典的越先锋,越传统的越时尚,越陈旧的越青春,越破落的越现代,越缓慢的越自我,越沉静的越自在。
《浮生六记》园林版、剧场版、厅堂版的三个戏剧版本,在当下越来越受欢迎,也许可以为上述这番话作个小小注脚。抬头看到我的书架上,有两位文友去年出版的《浮生六记》“译本”。一本是李晖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本是周公度从古文翻译过来的。虽然还没弄明白,为什么要将英文和那么近的古文翻成今文。哦,明摆着是市场有需求。
总有怀抱梦想的人,想把过往的苏式生活复刻到现实中来。将纸上的苏式生活搬来当下的现场。想打造一个现代版的《浮生六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苏州人太熟悉沈三白和芸娘的事儿了。甚至,许多男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芸娘”。林语堂不是早就信誓旦旦地说了,“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浮生六记》的出品人是萧雁导演。她选择了将苏州文化的几个代表性符号昆曲、古典园林与经典作品《浮生六记》相结合。于是,昆曲《浮生六记》园林版,首次以浸入式的方式,在故事的发生地沧浪亭上演了。
熟悉萧雁,源于她制作并出品了诗人韩东的一部舞台剧《妖言惑众》。去年5月,我们还一起受邀在苏州为韩东作品分享活动做嘉宾。
从2017年底开始,萧雁就在为古城核心区量身打造“戏剧+”演出项目——沉浸式昆曲《浮生六记》作准备了。我从新闻中得知,自2018年七夕节首演以来,在不到一年(2018年8月至11月,2019年4月至11月)里演出120场。据说是创下了国内新编戏曲演出的纪录。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沦陷时期,被誉为“诗人导演”,执导过《小城之春》的苏州籍导演费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由银幕转向舞台,曾排演过话剧《浮生六记》,前后上演6次,计342场,可谓盛极一时,在商演和话剧史上留下了骄人口碑。
显然,萧雁志不在小。不同于费穆版的话剧,她的《浮生六记》,通过两年的探索与打磨,在“夜游经济”“文旅融合”“非遗创新”三个方面,成了全国的样本,还被文旅部外联局委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主推的“聚焦中国”选中,与孟京辉《茶馆》等其他4部中国戏剧一起,亮相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在巴黎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 摄影:孙建
我不知道萧雁的《浮生六记》是否达到了预期,但我知道她的付出。比如,有朋友从外地过来,我们约她餐叙。晚上可是演出的黄金时段,她只能在餐后茶点时才得以脱身匆匆一晤;为了保留昆曲精髓,《浮生六记》的舞台版她请来昆曲界名家名师汪世瑜、白爱莲、孙建安等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导演、作曲;为了营造跨越时空的对话张力,她请来曹禺戏剧奖得主、编剧周眠加盟了团队;为了贴切原著,贴切苏州,贴近生活,她的团队与知名文化学者、民俗专家们反复推敲,以求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增加苏式生活气息和文化含量。
《浮生六记》已在苏州夜生活中“火”了好一阵子了。疫情防控平稳后的“五一”复工首演前,她在微信上征询我意见,想请诗人韩东、画家毛焰等一起来苏州看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她对这部戏的信心。这次《苏州杂志》策划了一个“苏州夜经济”专题,我想到萧雁,问她:“《浮生六记》是夜经济的内容吗?”她立马就回复我了:“哈哈,是的,我们是头部内容。”
《浮生六记》已经有了园林版、剧场版,今年为进一步配合打造苏州夜经济,又推出了厅堂版、游船版。萧雁的《浮生六记》沉浸式品牌,除了为传统经典的当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外,运营方还推出了另一个品牌——结合古风市集、线下店和电商小程序的“浮生集”。毫无疑问,这个戏剧项目现在不止是在不同的场景演出,还营造出了沉浸式的消费场景。
风传花信,雨濯春尘。良辰美景,不轻放过。“姑苏八点半”,苏州夜经济,将后疫情时期的苏州之夜点燃了。注入了苏州核心文化元素的夜经济,会唤醒或重塑古城的苏式夜生活模式吗?我们有理由期待。正是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一批文旅精品的推出,让夜经济里的市井烟火气中,飘逸出了文化韵味、文艺气息,将姑苏之夜装扮得愈发迷人。
苏州之夜 叶 弥
我记忆里的苏州之夜有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断。我三四岁的时候,妈妈在小学校里当代课老师。夜里七八点钟,她抱着我弟弟,我拖着她的后衣襟,三个人朝家里走。从南门路小学开始,目的地是叶家弄。我们会尽量走大路。那个时候,即使是大路,傍晚时分就杳无人迹了。我最害怕的是路上的梧桐树,一盏盏小小的路灯隔得很远,昏黄的路灯光打着近处的梧桐叶,投射到脚底下,仿佛隐藏着某种鬼怪。我觉得我妈妈心里也是害怕的,抱着我弟弟一股劲地赶路,三个人在路上从不说话。那种情景是诡异的。周围充满冷清、孤独、惧怕。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
我三年级那年,从苏北乡下回到苏州,准备过完暑假在苏州读书。我家全家下放到盐城阜宁县,独把我的户口留在了苏州,说是女孩子出路少,以后可以回苏州嫁人。我住在建设弄外公外婆家里。建设弄在人民路上,邮电大楼边上,斜对面就是第一百货商店。建设弄的弄堂口,是十一路汽车的始发地和终点站。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大宅院,里面住着六七户人家。其中有一家的女主人爱好看书。有一次,我在她家见到了一册《海岛女民兵》,就向她借来看。那时候书很少,所以我白天看了,晚上还到人民路的路灯下继续看。那时候,人民路不再那么凄清了,夜里也有人走来走去。路灯还是隔得那么远,比60年代明亮了一些。但是路灯上密密麻麻地舞动着一层趋光飞虫,飞虫的品种真不少。我在路灯下看书的姿态引来了几个夜里闲逛的少年,他们围到我身边,把我推推搡搡,并且讥嘲。我的二舅舅正好也在路边玩,冲过来,一把揪住领头少女的头发,赶走了他们。这是1973年。

☉ 夜读苏州(苏州市全民阅读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提供)
上世纪80年代初,外公他们搬到了观前街的牛角浜。在玄妙观三清殿后面。我三年级那年,并没有在苏州的小学读成书,重新回到阜宁乡下读到初二,又回到苏州读初三,跟着外公他们住在牛角浜。观前街上的灯,间隔不那么远了。入夜,街上每一寸地都看得清清楚楚。虽然还不能形容为“灯火通明”,但也是有点大城市的味道了。观前街边上的小弄堂里还是很幽暗的,有一些角落里散发着尿味。那时的新华书店里,书渐渐地多起来了,但关门很早。有一阵子,观前街允许摆夜摊,那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几乎什么都有,也有旧书摊。摆摊的人大都缺少经验,也缺乏素养,三天两头有吵架打架的。
上世纪90年代,苏州大街上的灯才到了“灯火通明”的地步,通明而亮如白昼。任何地方都被灯光覆盖,凄清、孤独、惧怕不再是夜的特性。苏州在改革开放中,历经苏南模式和经济上的转型升级,由一个小城市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如今随着夜经济的蓬勃发展,苏州的夜读生活越来越有起色。今年4月底,苏州开展了“夜读苏州”活动,有“书影纪”“双塔书市”“共夜读”“结书缘”等一系列活动。苏州自古富庶,读书人多。读书人多了,书店也多。明代藏书家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有记录:姑苏书肆,比于京师。当年我国四大书业中心分别是:北京、苏州、金陵、杭州。
世上每一座繁华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越繁华,越书香。
君到姑苏月下见 朱文颖
一
在苏州,很多与文化有关的故事与细节都发生在暮色之中。
“夜半钟声到客船”——写下《枫桥夜泊》的这一年,在唐都长安的大明宫中,张继高中进士。本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本该在朝堂之中施展抱负,将二十载寒窗岁月化为报国热忱。谁知世事无常,安史之乱爆发。张继流落到江南,在姑苏夜半浸满江水的冷月当中,迎接他的,是一座寺院——以及遥遥传来的钟声。
只有在静谧的深夜,那钟声、枫叶、渔火才能彰显出人世的无常、生命之幽微以及永恒。而最终使得这首诗、这座寺院成为人人皆知、却又各自寄托不同生命感悟的寓言。
夜色中,除了生命的质感,还有红尘的欢欣。腊月之后观前街的灯市,“夜走三桥避百病”,石湖串月,夏夜乘风凉,走月亮……唐宋以来,作为江南之中心的苏州,夜生活向来非常丰富。而其间最热闹的两个阶段,一是明清时期的阊门,还有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观前老街了。
二
前些天吧,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几句话:
一下雪,苏州就成了姑苏城
苏州下雪了
其他地方都只是将就
我觉得这里雪的概念可以有所扩展。比如说,一下雨,又比如说,一入夜。作为中国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苏州的雪、烟雨以及夜色,都有着魔术般的效能。它们让一切变慢。变得更加优美而轻盈。
入夜的观前街一向就是市民生活的圣地。在老一辈苏州人的脑海里,观前街的石板路上,来来往往、走来走去的行人大都穿着长袍马褂,走路时速度很慢,笃悠悠的,如果遇到熟人,就远远地停下来打个招呼,鞠个躬,作个揖。如果走在观前街上突然下起雨来,则完全可以站在两边街旁的店檐下躲雨……所以以前的苏州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苏城街,雨后看绣鞋”。就是说即便你穿着一双绣花鞋,在下着濛濛细雨的观前街上行走,绣花鞋是不会弄湿的。
而苏州的美食,最精彩的部分也在入夜以后徐徐展开。著名作家陆文夫在《美食家》里记朱自冶在自家花园里宴客,他是这样来描绘女主人公孔碧霞摆出来的一个圆桌筵席的:“洁白的抽纱布台布上,放着一整套玲珑瓷的餐具,蓝边淡青中暗藏着半透明的花纹,放射着晶莹的光辉。桌子上没有花,十二只冷盆就是十二朵鲜花。”
“丰盛的酒席不作兴一开始便扫冷盆,冷盆是小吃,是在两道菜的间隔中随意吃点,免得停筷停杯。”于是接着就上热炒,第一道是番茄塞虾仁,然后“各种热炒纷纷摆上台面,我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只知道三只炒菜之后必有一道甜食”。十道菜后,“下半场的大幕拉开,热菜、大菜、点心滚滚而来:松鼠桂鱼、蜜汁火腿、翡翠包子、水晶烧卖……一只‘三套鸭’把剧情推到了顶点。”
这或许也是苏州人夜生活的某种写照:热闹里可见韵律;物质中可见精神;俗中有雅,处处蕴藏着艺术的匠心。
三
提起苏州,就不能不提昆曲和评弹。但是,如果没有天上那一轮皎皎明月,我想,昆曲和评弹的魅力也一定会大减了吧。
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中,记载着明代群众性拍曲子盛事“虎丘曲会”的情况:“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剑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毯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山。”从列举的参加者可以看出,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到了场,那热烈的场景,张岱形容为“动天翻地,雷轰鼎沸,呼叫不闻”,可见当时昆曲的群众基础是何等的深厚。
而在苏州评弹博物馆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青铜雕像。它为我们展现了旧时评弹演员赶赴书场的景象,有端坐在黄包车上的评弹演员,也有拱手相迎的书场老板……这一幕场景仿佛将我们瞬间拉入了那个评弹最辉煌的年代。那时苏州茶楼书场的门前都挂着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糊了一张红纸,或者直接书写“特请某某先生弹唱、或开讲某书,某日某时开书,风雨无阻”。书场内贴着墙搭设一只高两尺、约有六七平方米的书台。书台正中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条幅,上面写着“恕不迎送”四个大字。左右一副对联,上联是“把往事今朝重提起”,下联是“破功夫明日早些来”。
月上柳梢头……而书场内,听书、会谈、喝茶、嗑瓜子、逗乐子、啼笑因缘、浮想联翩。生活的细节就是消费与商业的程式,它们如同水滴一般自然流淌,因此才得以细水长流、生根开花。
四
文化苏州的骨子里是慢的。
如果走完同里三桥,临着江南的微风细雨站在桥上眺望。这里炊烟起来了。那里一只鱼鹰歪在船头打瞌睡。雾气一会儿起来一会儿下去。一个骑车人慢悠悠地像从浓雾深处滑行而来……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
“环护城河”水上观光也一直在推广以及完善,然而,无论是站在山塘河边、上塘河沿,或者吴江运河古纤道旁去看那条著名的大运河,最触动我情感、最让我感受真切的部分,却永远是这样一幅场景:
远远的一艘夜航船开过来,船的速度很慢,就像一个懒人在大运河当中散步。天上有弯月,甚至满月,在这么慢的船上,自然是想赏月的,但那是一个雾夜,周围都是烟水的气息,月亮是一点也看不见。虽然看不见月亮未免遗憾,但在烟水的气息中缓慢地航行,也是不错的。不知什么时候,雾忽然散开了,在雾的空缺处,静静地悬着一轮圆月……
或许,快和慢其实并不矛盾。或许,一场特殊时期用来加速经济的文化品牌活动,慢恰恰是它难能可贵的本色与优长。为一个暂时停摆的世界加速——用“慢”作为它的品质,让“快”成为它的翅膀——
夜已至。我们、你们、他们……推门而出。
而苏州城中早已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