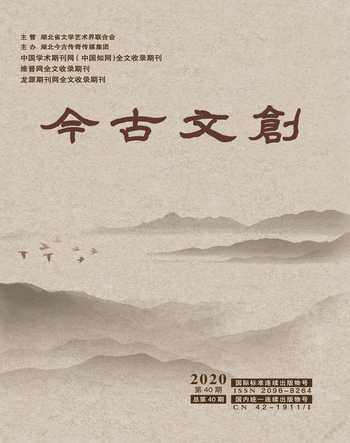《婚约天使》中女巫形象的重构
【摘要】 “巫师即女性”的观念和对女巫形象的丑恶化建构有着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的原因,与二元对立模式下对身体和女性的贬抑有关。拜厄特在《婚约天使》中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灵媒这一群体,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建构的女性“家庭天使”形象和传统的女巫形象进行了双重解构,重新建构了一种彰显自身主体性的灵媒形象和独特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同时还对身心二元论进行了颠覆,破除了二元对立模式。
【关键词】 女性灵媒;《婚约天使》;拜厄特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0-0008-02
A.S.拜厄特在《婚约天使》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盛行一时的通灵思潮进行了展现,在作品中塑造了与刻板印象不同的一群女性灵媒,《婚约天使》中的通灵者身上展现的气质神秘并不指向邪恶。作家书写她们的人生际遇,表现了她们对于精神与物质领域种种问题的思考和选择,颠覆了童话故事里狰狞、恶毒、妖魔化的女巫形象。
一、女巫形象刻板化溯源
巫术与性别的粘连由来已久。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对巫术有着崇拜和寄托情感的需求,巫师自然地位神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生产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女性巫师更是受到尊崇。如王贵元在《女巫与巫术》中提出“女巫本身即是神”[1]这一时期作为人神沟通媒介的女巫的地位与后来大有不同,关于女巫的刻板印象是被社会文化建构而成的,而非本质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受哲学和宗教以及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巫术的社会影响力发生变化,女巫形象也随之被丑恶化,成为邪恶的符号。巫术在基督教宣扬的善恶二元论中作为恶的一面存在。《圣经》的很多章节中都提到了上帝对巫术的厌恶,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圣经·利未记》)再加上巫术与魔鬼学说融合,巫术便被当作人类与魔鬼定约获得的作恶工具。因此,在欧洲近代早期以来很长的一段的历史中,巫师,尤其是女巫都是作为邪恶形象而存在的。
据统计,“以15-18世纪初的猎巫运动为例,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猎巫运动中,约有10万到20万巫师受到审判,有5到10万被处死”[2],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巫术的恐慌与排斥。欧洲中世纪的猎巫运动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受迫害的大多为女性。男权社会认为女性代表肉欲,赋予女性“非理性”“强烈的性欲”“易受引诱”“肉身化”等标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巫师是女性”的刻板印象。另外,女巫形象的丑恶化建构,还与社会对身体的排斥贬低紧密相关,而女性天然被划归到物质或身体的阵营。
从古希腊到19世纪,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二元对立模式里,身体都是遭到贬抑的。因此,拜厄特的重构最终要涉及精神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和二元对立模式下身体的遮蔽与解蔽。
二、女性灵媒的重构
拜厄特在《婚约天使》中刻画的帕帕盖太太、索菲等女性灵媒形象,一方面是聚焦“灵媒”,消解了丑恶化、妖魔化、欲望化等关于女巫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是聚焦“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建构中,温顺优雅的“家庭天使”是女性的完美典范。同时,文学作品与权力共谋,对女性的描写也常常是围绕婚姻、爱情等话题,形成对女性全面的空间限制,因此,拜厄特对女性灵媒的书写和重构同时也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建构的女性“家庭天使”气质的消解。
拜厄特塑造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灵媒形象中,年老的并不丑恶,她们不行恶术,反而怀有深沉情感;年轻女巫也不是沉溺于欲望的妖艳形象,而是如索菲般纯粹专注于超自然力量和精神世界。并且,她们颠覆了刻板印象中对于女性灵媒被动性的强调,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主动探求人生答案。拜厄特对女性灵媒的塑造不仅停留在女性灵媒对自身主体性的弃绝阶段,而是更进一步将其以立体的姿态呈现出来,她们只在降神会这一特定场所中,才展现出作为灵媒的特别之处,而那也并非是歇斯底里的疯魔状态,而是凭借超强直觉能力对表象世界的超越。这样一来就消解了传统社会与宗教共谋之下建构的丑恶的女巫形象,重构了一种积极主动追寻人生真谛和现世生活美好的女性灵媒形象。
另一方面,从性别——空间角度来看,女性灵媒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所规定的女性空间的突围。“空间能够生产主体,能够有目标地生产一种新的主体类型。人在特定的空间中被锻造。”[3]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空间分布模式是:男性活动在公共政治领域,女性活动在私人的家庭领域。然而在家庭领域内的劳动,是不被承认为“工作”的,遑论报酬。而“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始终与她们的经济依赖性紧密相关。”[4]这样,權力就经由空间分布,操控经济分配,以达到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话语控制。女性在历史中是失声的“不在场”,是被“凝视”的一方,比如拜厄特通过艾米莉的回忆,呈现出哈勒姆更多的是将艾米莉当作是一种审美客体,在艾米莉的回忆中,“亚瑟待她就像集女神、居家天使、小孩与可爱宠物羊等形象于一身。”[5]而女性灵媒以通灵术为媒介进入社会规定的男性空间,就消解了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女性气质,拥有了自己的声音,打破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被遮蔽状态。
维多利亚时期,通灵术和招魂术的盛行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一批女性得以走出家庭领域,以充当灵媒的方式突破社会规定的性别空间,获得工作和经济来源。女性灵媒“身份赋予女性特定范围内的一种话语权,她们作为降神会等仪式的执行者,具有一定的权威。”[6]因此,一方面,女性灵媒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家庭天使”所规定的女性温驯气质的解构。另一方面,女性灵媒群体也打破了既定的性别空间结构,在降神会上,充当灵媒的女性角色具有了话语权,处于中间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对两性关系进行了暂时的颠覆。
三、二元对立模式的破除
拜厄特对女性灵媒的解构与重新建构是为了发掘不在场的声音和被遮蔽的历史,继而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二元对立模式,破除男—女、身—心的对立关系,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霸权压制。在文本中,这个过程是通过灵肉关系的探讨进行的,拜厄特首先重新定义了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身心和谐观”,从而也就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下与精神相连的男性和与身体相关的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西方文学传统中灵与肉的冲突、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是长久存在的母题。在父权统治下的性别政治里,社会自然认为男性拥有理性,属于精神领域,女性代表肉欲,属于物质领域。对理性的推崇与对直觉、幻想等非理性因素的压制是一体的,20世纪之前西方的灵肉冲突中,总是推崇精神,贬斥肉欲。在身心二元对立,且身体处于被贬抑地位的身心观基础上,两性关系中被规定为身体与物质领域的女性,自然就处于“低劣”的一方。因此,在建立女性与巫师之间的联系时,女性具有强烈的性欲的刻板印象建构和对物质/身体的贬低是同时进行的。
《婚约天使》中的灵肉冲突集中表现在霍克先生与帕帕盖太太的观点中。霍克先生援引《圣经》中的话表达他对物质的贬斥,但是同时,霍克先生又完全在肉欲的驱动下向帕帕盖太太求爱。而帕帕盖太太对阿图罗的爱既有灵魂的,也有身体的,她无法使对阿图罗的思念战胜对物质关怀的渴求,但与霍克先生灵魂共鸣上的缺失也使她拒绝了对方的求爱。她所渴望的是肉体与灵魂两个层面上契合的婚姻。因此,拜厄特所表现的不再是二元对立结构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而是身心两方面的和谐状态。她对于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和精神高于身体的驳斥,也是对传统巫术理论建构中将女巫与性欲相粘连的反叛,性欲所指向的身体和物质性既然不是低劣的,那么以强烈性欲作为对女巫的指控也就失去了立腳点。
无论是两性之间的性别对立关系还是身心二元论,其背后的主导逻辑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导下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中必有一方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一方对边缘化的一方进行压制,如西方哲学史上长久的一段时期中理性对非理性的抑制,声音对文字的排斥,在场对不在场的压制,以及上述的灵魂对身体的贬抑,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此,拜厄特对女巫形象和女性“家庭气质”的重构,实际上也是对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破除,是对霸权话语的消解。
四、结语
拜厄特对女巫形象的重构,颠覆了西方文学传统中妖魔化的女巫形象,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她在对传统女巫形象的颠覆中,揭露了披着理性外衣的新的霸权话语,让被历史所遮蔽另一个性别重现。父权制社会以来,女性长久处于失语状态。拜厄特以女性视角进行叙事,对性别政治中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压制进行反抗,将维多利亚时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从被否定状态中解放出来,建构女性自身的主体性,使她们拥有话语权。然而拜厄特绝不止步于此,她要重现的并不是一个性别群体的话语,而是所有历史中的“失语者”。拜厄特在对传统秩序进行反叛的过程中,打破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建构了一种多元化的包容空间。
参考文献:
[1]王贵元.女巫与巫术[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1.
[2]徐善伟.15至18世纪初欧洲女性被迫害的现实及其理论根源[J].世界历史,2007,(04).
[3]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5.
[4]米利特.性政治[M].宋伟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8.
[5]A.S.拜厄特.天使与昆虫[M].杨向荣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2:238.
[6]金冰.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3.
作者简介:
崔舒敏,女,汉族,河南人,兰州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