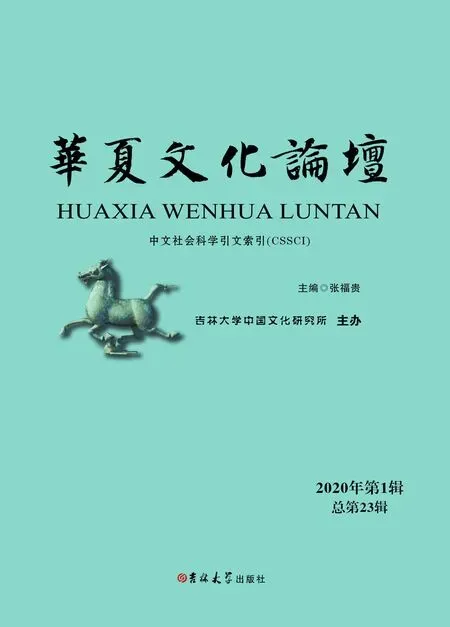碎片化:温庭筠词的特殊文本空间结构及其艺术功效
宋学达
【内容提要】“碎片化”是温庭筠构建文本空间的主要方式,也是其词作文本空间最突出的特征。“碎片化”文本空间有两种互为表里的存在状态:散落的自然状态与读者意识介入后的拼合状态,后者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有较强的依赖性。“碎片化”文本空间对温词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负面的限制作用,使其空间感狭小促碎,同时又赋予了温词极大的阐释张力,使其较小的文本空间可以负载较多的内涵,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作家将其感知到的现实空间压缩为文字,便形成了存在于作品内部的文本空间。在作家艺术思维的作用下,文本空间相对于作家原本感知到的现实空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乃至多种时空维度上的拆分重组。文本空间所表现出的有别于现实空间的特征,往往体现着作品独特的艺术质素,以及作家独运的艺术匠心。
温庭筠在词作中构建的文本空间结构,以“碎片化”为最突出特征。所谓“碎片化”,即作品的文本空间由不同部分的碎片排列拼合而成。这种空间结构,迥异于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空间,是温词中最常见、特征最显著的文本空间存在形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本空间的构建方式,对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赋予了温词极富弹性的阐释张力。
一、“碎片”拼合的空间结构
正常状态下,人类在自然界所感知到的空间是完整、延续的,而温庭筠在其词作中构建的“碎片化”文本空间,则与我们所感知的自然空间不同,它可以被划分为不同单元,而每个单元即是构成作品整体文本空间的一个碎片。因此,“碎片化”文本空间有时呈现为不连续的跳跃状态,甚至彼此割裂,如下面这首《菩萨蛮》①本文引用温词文本,皆依据赵崇祚、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为方便论述,我们直接划分其空间单元:


“杏花含露”与“绿杨陌上”表明第一单元的空间为室外,而第二单元则转至从“灯在月胧明”到“觉来”的室内。从室外到室内,中间没有承接过渡,而是直接跳跃。第三单元写“翠幕”中的女子,这一女子可以理解为第二单元中“觉来”之人,因此二、三单元尚可衔接。然而这种理解之下,第四单元却出现了断裂,女子在第二单元已“觉来”,如何又回到“春梦”之中?如果正在“春梦”的是第三单元之女子,那么其与第二单元之衔接便不成立。第二、四单元之间的断裂,导致中间的第三单元或与第二单元衔接,或与第四单元衔接,不可兼得。而第五单元与第四单元之间又出现了跳跃,虽然二者皆为室内,但“镜中蝉鬓轻”描写的是女子梳妆的情境,从睡梦状态到梳妆,中间的过程被省略了,因此两个碎片之间亦难做到比较紧密地衔接。再来看一首在时间上跳跃的《荷叶杯》:

第一单元写“秋月”“如雪”,空间被定为在夜间,而第二单元却跳跃至白天,写“采莲”的“小娘”,第三单元抒情,可以视为情感空间。虽然第三单元与第二单元的空间在性质有差异,但衔接相对紧密,但第一、二两个单元之间,无疑是断裂的。
空间单元之间的衔接不紧密,在某些词作中也体现为空间感分布极不均匀,如《菩萨蛮》:

第一单元聚焦于女子妆饰,空间感极狭小,而第二单元却马上转到开阔的“吴山”①有注家将“吴山”释为屏风上的画作,正是为了调和这种跨度过大的跳跃,而出现这种略显生硬的解释,恰恰证明两句之间难以顺承衔接,存在断裂的间隙。,跳跃跨度极大。第三单元转入送别场景,空间从“吴山”缩小至“驿桥”。词的上片中,三个缺乏有效衔接的空间碎片依次展现了极小、极大、较小三种空间感,导致空间感在词中分布极不均匀,转换亦不平滑。而下片中的三个碎片,彼此之间又是断裂的,第四单元的“画楼音信断”似乎可以与第六单元中表现女子孤寂心境的情感空间产生联系,却被第五单元不知具体所指的室外空间描写所间隔。类似这种原本存在的逻辑联系被隔断的例子,还可举出《思帝乡》:

这首词文本空间的第五单元“惟有阮郎春尽,不归家”与第二单元“罗袖画帘肠断”本来存在因果逻辑,但二者之间插入的“卓香车”与“回面共人闲语,战篦金凤斜”两个单元却大大冲淡了这种逻辑联系的紧密性,使得词作的整个文本空间依然呈现为排列松散的空间碎片。
“碎片化”文本空间呈现为空间碎片的排列,其间有时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造成作品出现断裂感,这表明构成“碎片化”文本空间的碎片之间,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温庭筠通过“碎片化”方式去构建文本空间,不会产生圆融完整的作品,如《河传》:

第二单元的景致,被收纳于第一单元的“闲望”二字中,进而与“湖上”的场景得到有效的衔接,而第三单元的“谢娘”正好可以被理解为第一单元的“闲望”之人。“闲望”之“闲”又能与“谢娘”之“愁不消”相衔接,组成“闲愁”意蕴,与第五单元的“荡子天涯”产生因果逻辑。处于第三、五单元之间的第四单元,亦非阻隔二者的碎片,因第三单元中的“终朝”二字正好与“晚潮”对应。第六单元的“肠断”继续承接第五单元的“荡子天涯”,又进一步将第八单元“不闻郎马嘶”与之相勾连,而“郎马嘶”的地点在“柳堤”,正是第七单元“溪水西”所指示的方位。由此可见,虽然这首词的文本空间可被划分的单元多达八个,但其彼此间皆存在必要的逻辑联系,因此并不显得松散,是一幅比较完整的拼图,恰如《古今词统》载徐士俊评语:“笔致宽舒,语气联属,斯为妙手。”①[明]卓人月:《古今词统》//《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0页。
杨景龙指出:“温词有时仿佛印象派绘画,只涂抹色彩,而不用线条连贯勾勒;又如影视的蒙太奇镜头,只并置画面,而不作任何解释说明。局部清晰,整体朦胧,词句之间往往出现不可解处,甚至整篇无解。”②[后蜀]赵崇祚、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02-103页。可谓直接道出了温词“碎片化”空间拼合的基本特征。总的来说,温庭筠构建“碎片化”文本空间的手法,即是将相对独立的空间碎片排列成词。如果碎片之间存在必要的逻辑衔接,则可成为相对圆融完整的作品,但大多数情况下,温庭筠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而“碎片化”文本空间的作品,大多呈松散乃至断裂的状态,从而使读者对词意感到费解,但反过来也促成了对温词的多元解读。
二、读者意志与“碎片”的连缀
温词“碎片化”文本空间中的碎片,大多数不存在直接而明显的逻辑联系,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认定它们不存在被连缀的可能?甚至,是否可以认为这大多数具备“碎片化”文本空间的作品是温庭筠创作的败笔?结论似乎并不能武断。且看下面这首《蕃女怨》:

词中,第一单元的“双燕”与第三单元的“画梁相见”应当是联属的,但被第二单元的聚焦描写所隔断,第三单元刚刚写到“画梁相见”,第四单元却直接大跨度跳跃到“飞回”。空间碎片之间的逻辑关系或难成立,或被隔断,或跳跃性太强,其存在状态是零散的。但如果我们抛弃这种一字一句的顺向分析,整体去体会这首词作,则俨然可以看到一个故事:独守闺中的思妇在花开的初春看到细雨中的双燕,想到了戍边的征夫,但直到燕子飞回也没有等到良人归来的消息。
逐句分析与整体理解出现分歧,是因为我们在整体解读时,调换了空间碎片的排列顺序,使被隔断的逻辑联系得到拼合,同时可以压缩碎片之间的跳跃性。这表明,“碎片化”文本空间可以在读者意志的作用下得到重组连缀。因此,就算是彼此相对独立甚至存在断裂的文本空间碎片,依然存在被整体解读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性依赖读者意志而存在,如果读者愿意并且能够连缀这些碎片,碎片才可以被连缀、拼合,如果读者不愿意这么想,则碎片依然是碎片。
文本空间碎片被拼合的可能性对于读者意志的依赖,在有争议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李冰若评此词“翠钗”两句称:“以一句或二句描写一简单之妆饰,而其下突接别意,使词意不贯,浪费丽字,转成赘疣,为温词之通病。”①李冰若:《栩庄漫记》//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34页。而张以仁则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所谓‘心事’者,实即卿卿我我双宿双飞之意愿也。际此佳辰今夕,月白风清,睹春花之盛放,末二句岂但言‘别意’?实更涵触景伤怀惜流光而怨幽独之不尽感伤,正与此双股双蝶之意紧扣密接,乃栩庄讥其‘词意不贯’,何也?”②张以仁:《温飞卿词旧说商榷》,《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1年第1辑,第145页。两位词学前辈对这首词的不同理解与评价,正是顺向的逐句分析与整体解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导致的。
我们从文本空间角度来看这首词,情侣在第一单元“相见”,第二单元“别离”,第三单元聚焦女子妆饰,第四单元则又是对“别离”情境的描写。关于此词“词意不贯”的争论,集中在第三、四单元的过渡上。单看词之下片,从对女子妆饰的聚焦到“别离”情境,中间确实缺乏衔接;再结合上片看,第二、四单元皆为“别离”,中间的第三单元亦有强行插入的突兀感。因此,李冰若“词意不贯”的批评,是对词作的顺向解读的结果;而张以仁的观点亦非全无道理,他的解读是将四个空间单元混成一体,尤其将第二、四单元直接拼合,淡化了空间感极弱的第三单元。由于第二、四单元在空间内涵上具有一致性,而插入其中的第三单元空间感又极弱,所以将整首词置于“暂来”到“别离”的时间线性中整体解读,也是合理的。
再看一首争议更大的《酒泉子》:

陆侃如、冯沅君认为这首词“前后舛错”:“此词的背景,若就‘千里云影薄’‘日映纱窗’诸句看,显然是白昼;但就‘背兰釭’句论,又似乎是夜间。……这些隐晦艰涩、前后舛错的作品,便是温词失败的处所。”①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1页。詹安泰不认同“前后舛错”:“前阕写日色穿窗,到默对炉香,背着灯光,由外写到内;后阕写倚阁怅望,看看远景,看看近景,紧接上节自内向外,后由远到近,由模糊到明晰,而以景结情终,含有余不尽之味。通篇思路流贯,层次分明……写的不是一天的情事,而是两天的情事(也可以说是日复一日的情事),过阕已用‘宿妆’两字交代清楚。”②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3-364页。
对于这首词是否“前后舛错”的争论,同样是顺向解读与混成解读两种不同方法造成的。词中五个空间单元,第一、三单元为室内,第二单元怀想故乡,是一种想象空间,第四、五单元转移至室外。这五个空间单元,如果我们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去看,先是在第一、三单元的室内空间中完成了一个晨昏的时间流动,而换头转入室外空间,既可顺向解读为没有直接联系的空间跳跃,也可以将文本空间浑融一体,理解为另一次昏晨的时间流动。
同时,在第一、三单元之间,夹杂着一个想象空间单元。从室内空间到想象空间,再回到室内空间,没有任何过渡,这种强行插入式的突转亦可视为犯李冰若所谓“通病”之处,只是前两句所写不是“妆饰”而已。
前辈评家关于上述两首词作“词意不贯”或“前后舛错”的争论,皆源于“碎片化”文本空间建构方式。两首词的文本空间,都可分列为联系并不太紧密的几个碎片,存在或多或少的突兀感,需要读者运用主观意志的解读去抚平、润色。正如俞平伯评《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
飞卿之词,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眼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问其脉络神理如何如何,而脉络神理按之则俨然自在。③俞平伯:《读词偶得》//《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04页。
所谓“杂置一处”的“诸印象”,即为文本空间碎片,其间要产生“脉络神理”般的有机结合,有赖于读者自行通过见仁见智的慧眼去拼合,否则词作仅仅是碎片的堆砌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温庭筠“碎片化”文本空间两个层面的存在状态:其一,散落、堆砌、断裂的自然状态;其二,依赖读者阅读与阐释能力的拼合状态。自然状态,即文本尚未被读者意识尝试拼合的自在排列状态,这种情况下的碎片只是碎片,就算是脉络神理俨然自在的优秀作品,也只是具备被统合的潜在可能性。拼合状态,则是读者意识介入后的文本空间状态,从逻辑上讲,这种状态下的每首“碎片化”的词作都介于难以拼合与完美拼合之间,但无论是何种程度的拼合状态,都需要读者的阐释与解读去维持,失去了读者的主观意志,拼合状态的文本空间只能重新散落为自然状态。
三、“碎片化”空间与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文本空间是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范畴,其本身的广狭直接体现为艺术审美中空间感的大小与深浅。读者从温词“碎片化”文本空间中读到的空间感,总体来说是狭小的,如《菩萨蛮》:
翠翘金缕双鸂鶒,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
上片可统一于一个整体的园池空间内,但并不广阔;下片四句每一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碎片,前三句都是对女子身处空间的描绘,最后一句突然拉到遥远的“玉关”,但由于这只是拼图中的一块碎片,因此并没能在整体上扩大空间感,整首词上给人的空间感依然是以一位闺中女子为核心的方寸之境。文本空间的“碎片化”存在形态,使得具有较广阔空间感的句子难以完全发挥其空间拉伸作用,淹没于大量空间狭小的碎片中。
或曰,温词空间感的狭小是题材限制所致。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温词乃至整个《花间集》内描写相思女子的作品,确实总体上都是处于狭小的闺阁空间中,然而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如《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
同样书写一位望归的寂寞女子,但“望江楼”“千帆”等字句却开拓出一片辽远的空间。女子相思题材确实可能会对作品的空间感起到限制作用,但例外的存在,也说明这种限制并不是必然的。
“碎片化”作为一种文本空间的艺术表现形态,限制了温词在艺术审美中空间感的广度,而其作为一种文本空间的构建方法,也对温词空间感的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借用王世贞评价《花间集》的“促碎”二字加以总结。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花间犹伤促碎”①[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87页。。文本空间的“碎片化”对温词艺术特质的负面影响,即表现在这种“促碎”之“伤”。
如前文所论,温庭筠将诸多文本空间碎片“杂置一处”,如果要产生脉络神理俨然自在的效果,有赖于读者意志的发挥。但是,以“碎片化”结构文本空间的温词中,也存在一部分碎片过于繁琐或“调和”过于牵强的作品。如《诉衷情》,便是空间过于碎片化的失败案例: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皇帷。柳弱蝶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
从“莺语,花舞,春昼午”的晴朗明丽到“雨霏微”的料峭微冷,没有任何过渡,其后罗列的“金带枕,宫锦,凤皇帷”更无衔接,之后的“柳弱蝶交飞。依依”似乎又回到了开篇的明丽之境,最后突转到思妇心绪,似乎是有意将前面的种种碎片提炼一处,然而整首词所罗列的物象及其背后的空间过于琐碎,使得提炼并不成功,整首词给人的直观感觉只是彼此分立的诸多碎片而已。正如胡国瑞所言:“开始平列四种景物,接着又平列三种饰物,彼此间没有承接的关系,又没有情感的融注,令人只觉是丽辞的堆积。”①胡国瑞:《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2页。同样失败的例子还可举出一首《更漏子》,词云: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如果说“柳丝”“春雨”与“塞雁”“城乌”尚可勉强统一于一种描写室外景物的文本空间,突转室内的“画屏金鹧鸪”则实在难以与前文找到任何逻辑联结点。李冰若云:“‘画屏金鹧鸪’一句强植其间,文理均因而扞格矣”②李冰若:《栩庄漫记》//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35-2236页。,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文本空间的断裂,面对“画屏金鹧鸪”这一强行植入的碎片,读者不仅难以“见仁见智”地将其拼合到词作的整体空间中,更难解其意,难以达到脉络神理俨然自在的境界。
在以“碎片化”方式建构文本空间的温词中,由于有这样一部分并不完美的作品存在,导致读者产生断裂、堆砌等负面审美印象,进而被王世贞总结为“促碎”。“促碎”的文本空间,自然无法给读者以辽远、广阔的空间感。因此,“碎片化”作为一种空间构建方式,同样限制了温词在空间感方面的开拓,形成一种负面的艺术价值。
最后,关于本文对“碎片化”文本空间导致“促碎”的负面评价,还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有两位词论家并不认为“促碎”是一种艺术的“伤”,其一沈增植,他针对王世贞的观点辩称:
卮言谓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余本色,所谓词之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词促数,北宋盛时啴缓,皆缘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想其缠拍。③[清]沈增植:《菌阁琐谈》//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606页。
一方面将“促碎”认同为“非诗之所能至”的“词之境界”,另一方面则认为“促碎”是五代时期词体倚声的必然要求。其二蔡嵩云,针对《河传》立论曰:
河传调,创自飞卿。其后变体甚繁,花间集所载数家,圆转宛折,均逊温体。此调句法长短参差相间,温体配合最为适宜。……又温体韵密多短句,填时须一韵一境,一句一境。换叶必须换意,转一韵,即增一境。①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915-4916页。
所谓“一韵一境,一句一境”“必须换意”,即是要求“意”多、“境”多,也就是“促碎”。而将“促碎”的“温体”视为填作此调的最适宜之“体”,也就是承认了“促碎”在艺术上的合理性。
沈、蔡二家赋予“促碎”正面的艺术价值,是基于其各自对唐五代词的审美认知与偏好。而本文视“促碎”为负面,则是站在温词空间感的艺术表现力这一层面进行论述。故对于沈、蔡之观点,本文无意反驳,因为艺术评价从根本上讲都是开放式的,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绝非你死我活,更何况本文与沈、蔡观点的对立乃基于不同层面的论述。而关于“促碎”的形成源于词之音乐性的观点,一方面我们如今已无法真正在实证层面完全辨明词体所倚之声的性质;另一方面,即便可以确证音乐对温词“促碎”特质的孕成作用,也不排斥文本空间的“碎片化”具有同一方向的作用力。
总之,通过考察“碎片化”文本空间之于温词的艺术功用,我们发现无论“碎片化”是作为一种文本空间的存在状态,还是一种构建方式,它对于温词空间感的艺术表现力皆起到负面的限制作用。因此,在“碎片化”文本空间之下,虽然也可以产生脉络神理俨然自在的优秀作品,但也存在根本上的艺术局限。
四、“碎片化”空间与作品的阐释张力
通过上文的论述,得出了“碎片化”文本空间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对温词作产生了负面价值的结论,那么是否可以认定“碎片化”文本空间是一种于文学艺术有害的因素?对于这一疑问,同样不能武断地肯定。虽然“碎片化”文本空间对温词空间感的艺术表现主要起到了限制作用,但在文本的阐释空间方面,却赋予了温词极大的张力。
文本空间以构成作品的文字为载体,因此,文本空间的广狭与作品字数的多寡亦有直接关系。温词皆为短章,其文本空间的体量具有相当低的上限。而文本空间的体量又对作品的内涵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进一步推论,温词可供阐释的内涵也是不多的。
第一步的推论,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论述可基本落实。而第二步推论,却似乎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一首短小的《南歌子》进行说明:

这首词书写了怎样的内涵?杨景龙竟然疏解出三个答案:“一谓从男子角度,写对女子的追慕之情,前二句形容女子的美丽,后三句交代这是在黄昏的大街上,男子从香车卷起的帘子内一瞥所见,于是,男子上演了一幕张泌《浣溪沙》里也写过的‘晚逐香车’闹剧。一谓从女子角度,写美丽的女子黄昏盼归,她卷帘凭眺,看到九衢暮色中车马驰逐的热闹,愈发衬出她内心的孤寂。一谓词写闹市红尘中的香车女子,或是游春晚归,或是赶赴约会,推敲不定。”①[后蜀]赵崇祚、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63-164页。如果上述第二种推论正确,那么这首可疏解出三种内涵的《南歌子》一定具备很大的文本空间,可事实并非如此。该作的文本空间之第一单元聚焦于人物,是狭窄的;第二单元只写了卷帘,同样狭窄;第三单元描绘的“九衢”空间略大,然而焦点却在“香车”,空间也没有扩大太多。这首词的文本空间并不大,合乎第一种推论,而这首23字的小词又为何可以被阐释出如此多的内涵?似乎答案只能在文本空间的“碎片化”上。
词作三个单元的文本空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第一单元中的人物,可以是第二单元卷帘动作的发出者,也可以不是。第二单元中被卷的帘,可以是挂在第三单元的车窗上,也可以不是。因此,读者通过各自见仁见智的解读,可以任意赋予三个单元合理的逻辑关系,也就可以形成多种阐释结果。由此可见,赋予这首《南歌子》极大阐释空间的,不是文本空间本身,而是其“碎片化”的构建方式。正如杨景龙在“三解”后说道:“小词简略的句子,句与句之间连接关系的省却,都加大了解读的弹性和难度。”②[后蜀]赵崇祚、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64页。
由于温词文本空间的诸多“碎片”之间往往缺乏必要逻辑联系,因而赋予了读者极大的联想空间,有时甚至会以“增字解经”的方式来阐释词作,如前文提到的俞平伯用以说明“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③俞平伯:《读词偶得》//《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4页。的《菩萨蛮》词,詹安泰对该词的解读便有“增字解经”之嫌。词曰: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④[后蜀]赵崇祚、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7页。
詹安泰承认:“篇中只罗列了各种各样的现象,人物活动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因此阐释这首词需要去“猜”,但不认为词中所罗列的物象是“杂置一处”,而是“一幅完整而又鲜明的异常动人的画面”⑤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3页。。詹安泰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对这首词的疏解:
这首词只是作者一桩风流事迹的追述,是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的。第一、二句是说,他曾经歇宿过那个地方的设备非常精美,有水晶帘,有玻璃枕,还有又暖又香能惹好梦的鸳鸯被。第三、四句是说,在一个足以引动离愁的风景凄清的早上,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第五、六句是说,那女子打扮得很漂亮,穿上淡黄色的衣服,簪上玉钗,还戴上“花胜”来送他。第七、八句是说,那女子划着小艇,穿过花港,摇摇荡荡地送他到岸上。⑥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页。
这一疏解十分流畅,然而若仔细对应词作文本,就会发现詹安泰自出机杼地添加了三个要素:第一,“风流事迹”中的“他”;第二,女子“划着小艇”;第三,女子“穿过花港”。
要素一是词作可以被故事化为“风流事迹”的关键所在,因为在词作文本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女子,若没有其情人的存在,便无所谓“事迹”。这一要素被添加的依据是词中的“柳如烟”一语,柳在古典文学中常作为送别的意象,如果将“柳如烟”理解为送别之意,那么词中暗含女子的情人便是合理的。然而,这一男子的存在是依赖于对“柳如烟”的理解,如果我们不作送别解,则这一男子就失去了在文本中存在的根基。使得词作可以被解释为“风流事迹”的男子,虽然在文本中有一丝薄弱的存在依据,但也是根据读者的理解额外添加的要素。要素二和要素三的添加是为了解释“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二句,对此,詹安泰解释云:
“双鬓隔香红”,是那女子的双鬓隔开了又香又红的东西,那只有在花丛中穿过,才有这种现象,好像后来严仁《鹧鸪天》的“紫骝嚼勒金衔响,冲破飞花一道红”一样,只是骑马和划艇有所不同罢了。为什么知道那女子是划着小艇呢?“玉钗头上风”已写得很清楚。玉钗簪在头上,本身是不会生风的,风也吹不动它,只有当着头上不断摇摆的时候,玉钗才会在头上颤动得煞像给风吹着一样。头为什么会不断摇摆?那不是划着小艇用力穿过花港是什么?①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363页。
虽然这一解释很精彩,但在词作文本中,既没有对应“小艇”的文字,也没有对应“花港”的文字。这两种要素,都是詹安泰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自行添入的。
可见,詹安泰对这首《菩萨蛮》的流畅疏解,是通过添加三种要素完成的,而之所以能够添加要素使“碎片化”文本空间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正是由于空间碎片之间留有足够的缝隙,使读者的想象力可以填充其中,从而得到“一幅完整而又鲜明的异常动人的画面”。然而,这种通过“增字解经”得到的完整的画面是溢出文本的,它属于阐释空间而非文本空间。这首词作的文本空间,依然是“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的碎片化状态。
通过对《南歌子》与《菩萨蛮》两首词及其内涵的分析,可以发现“碎片化”的文本空间并不等同于阐释空间。虽然阐释空间基于文本空间,却具有可扩展的张力。同时,阐释空间张力的大小,又与文本空间的完整程度成反比,如果文本空间备足无余,则不会为读者的想象力留下太多余地。温词的“碎片化”文本空间,为读者的想象力提供了最大的驰骋空间,从而也就赋予了阐释空间极大的张力,使词作可以借由较小的文本空间承载较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