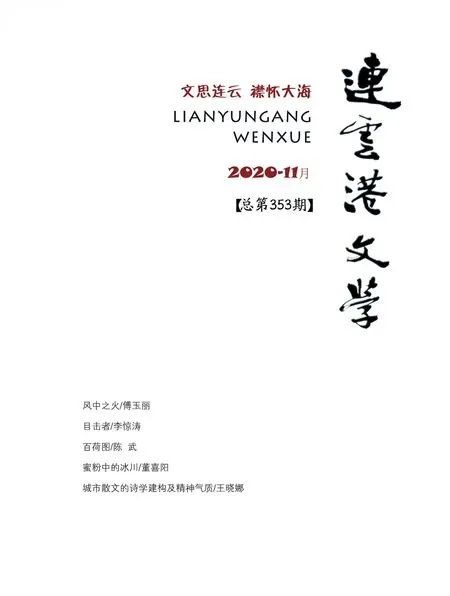风中之火
傅玉丽
人年纪大了,就会怀旧,母亲就是这样。没事总说从前老家的人和事儿,还会说到老屋。我听得太多了,最后就跟没听到似的。直到那年春天的一个电话打来。
“谁呀?……唔……好啊好啊。”母亲颇为激动,“你们好吗?”电话是一连来了几天,母亲甚是欢喜,后来就叫我,“小力,小力,来——”让我分享似的,她把电话给我。
我一接才知道,是母亲多年未联系的乡下亲戚的后代,两人说起从前的事儿好来劲儿。说了几日,这亲戚就开始跟她说卖老屋给他的事儿。我不知道乡下的房子能不能卖,因为我很早就离开乡下,没在乡下待过。我问母亲:“妈,是什么房子?”
“就是从前我们家的,你姥爷姥姥原来住的。我小时候在里面长大的。那灶最好了,上面蒸饭,蒸得直冒气儿,下面可以捂鸡蛋烤土豆,后面还有鸡窝……”
见我没反应,母亲提醒道:“你小时候可是没少划那门呢。”这一唠叨,我似乎想起来了,隐约有那么一座小小的老旧之屋,可其他不记得了,只对老屋的门还有点印象。
那门对我来说,就是好玩。年月久了,色泽比较暗淡,像个老妇人的脸,黑黑粗糙不已。门上面每年都会换上不同的画,开始是画着两个凶巴巴的人,我问过母亲,说是门神,帮我们守门的。后来门神不见了,换上穿着军大衣的解放军战士,戴着棉帽,手里握着把枪,浓浓的眉毛,眼睛很有神,很威武。再后来,是胖娃娃坐在一条大鱼上……
反正那厚厚的门就像块画板,画着不同的画。2 岁离开,仅有的几次回去,这可是我在城里难得见到的。村里其他地方总是喜欢刷着标语,真不好看。我隐约记得那村边有条河流,被四周绿色的田野包裹着似的,河面波光粼粼。那扇门很厚,那木纹也像一张画,上面布满了流动的线条。里面用力会感觉还松软,我会用指甲使劲儿去掐,较劲儿似的,会掐出一个个小半月形来。
从母亲一辈开始,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城里。现在她年纪大了,几乎不出门。我脱口而出,“卖了算了,留着反正也没用。”
“你就少这个钱?再说了,乡下房子什么卖不卖的,不像城里。”母亲听了一脸的不高兴,“那可是祖上留下的,以后我还要回去住的。”我才知道,乡下是村民间自己交易,不同于城里的商品房买卖。但村民互相交易也能赚点钱就是了。“你退休也能回去住。”
虽然母亲说得离谱,可也不能不说是个好点子。虽然我对那里人生地不熟,却突然间感觉自己成了地主似的,好像乡下的青山绿水已拥入怀中。现在不是讲究到自然中去吗?讲究回归吗?城里有房不算什么,乡下有就不同了。再说,母亲是把那祖屋当根、当念想呢,能留着也好啊。我便回复亲戚说,祖屋不卖。
不料,那叫阿财的亲戚着急起来,“卖不卖没关系,现在乡下不一样了,还有好多人到这里打工,需要租房的。你不能不管,得修一下呀。”
“……”我还未反应过来。阿财又叹息道:“不能忘本啊,你有空来看看吧。”
“你清明就去。”母亲听了催促说,“阿财是为我们好。”
“几十年没回去了,我谁也不认识,怎么弄呀?”母亲平时说话经常一行白鹭上青天似的,可这次不同,语气果断,“阿财是你爸爸表兄的儿子,我看着他长大的,他会帮你的。”
母亲说的阿财站在了我面前,高个儿,圆头圆脑,眼睛也圆,腰也圆,穿着很时尚的T恤,脸色白净,真不像个乡下人。他向我递来一根烟,“哎呀,几十年了,该来看看了。”得知我来,阿财特意在村口等我。
还未进村庄,远远就看见一片楼房,比从前扩大了几倍。走进村庄,才发现每家楼房一般三层高,还有许多网吧、小超市什么的。
“那老屋,你家的,现在可是落伍了……”阿财笑容满面,线条很硬朗,他边带我往老屋走去边说。我都记不得在哪个位置了。走到进村的路边第三家,他指给我看。
一栋不高的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透着岁月的痕迹,不过还算结实,只是小而高的窗子糊的是塑料,塑料纸在飘动。我移目大门,一副对联余了几条淡红色的细条,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板子裂口发黑,屋里面也是灰尘遍布。“我一直帮你们照看着的。”阿财说:“我现在早建了新房。”他指着不远处说:“那是我的房子。”我没听他后来说什么,盯着木门细看,摸了一下粗糙的门面,突然就像什么东西打了一下似的,一阵麻木,继而一阵酸胀,心中升腾起一丝火苗,似乎一下明白母亲所忠告的不能卖的原因。我感谢阿财提醒,这与其他房屋比像叫花子的老屋,该修修。
原来村里那条闪亮宽阔的河流,远看成了一条细线。“现在乡下不比从前了。我们这里想不到会来这么多人。”阿财声音颇为得意。我到的时候是上午,可并没有看到什么人,跟其他乡下一样,只有些孩子和老人的身影,许多房子安安静静的。
恍惚中,我一时如入旧境。
一转向边上的小巷,“得得得……”传来了清晰的马蹄声。一个人驾着马车迎面而来,驾车人与父亲打了个招呼,马车从身边开过,“哼——”马突然还打了个响鼻,把我吓得跳了起来。“远着呢,别怕。”父亲还拍了拍我。在老屋,我似乎在梦游。
“小红啊。”阿财声音响起,口气亲昵而果断,打断了我。却见一个女人从巷口深处伸出脖子,望着我们。
叫小红的人走出来,我发现她脖子真长,脑袋扭来扭去的,像脖子痒似的。
“这老屋的人回来看看。他在城里工作的。”
“唔。”小红收回狐疑的眼神,马上迎上来说:“好好,要看看,你家这屋子都是我们帮看着呢。邻居,多来往。从前我妈妈常常说到你妈妈的。”
听了她的话,尽管我搞不清这些关系,可刚才还陌生的村子,忽然觉得亲切起来。这亲切坚定了我修屋的决心。回来把乡下的情况跟母亲说了。母亲听着听着,眼里潮润起来,“我做梦都会梦到那里,要修一下。”
过了两个月,我就着手开始修老屋了。
“这是谁啊?”
“听说好像是阿彩婆家的小子。”……
离开几十年,以为没什么人来。不料修房子时,总有人来观望。他们会问站在一边监督修房子的阿财,阿财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还有的人会问起我父亲、母亲的情况。然后说自己是谁谁谁,这一说可都是父亲、母亲的亲戚。我顿时有一股暖流涌上。
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工程一开工,麻烦就来了。我真的体会到了装修房子就像上贼船的感觉。我住城里,又要上班不可能天天到现场,阿财很热情,主动帮我当监工,还招募了装修队伍。“村里搞房子搞得多了,我自己也搞过,比较熟悉。你放心好了。”我感觉不能不依靠他。
只是,不时会有想不到的事儿发生。比如“有人偷水泥”。刚买了水泥,一转身,五袋水泥就不见了。我不知到哪儿去找,便跟阿财说。阿财脸上严肃起来“还有这事?我去帮你找找。”他不知从哪儿转了一圈回来,扛回来一袋水泥。“累死我了,在村里找了,都没有,结果大老远跑到河边找到的。还好没被水打湿。我估计是有人想偷到河那边。”
而找回被偷的水泥不久,施工的冲击钻又不见了。
“哎呀,你家的东西又给人偷了,是冲击电钻。”阿财打电话告诉我时,我正在办公室。
“啊,那怎么办?”
“还怎么办?我也不可能一家家去找。施工要紧。再买一台吧。”
“好,你先帮我买着。”我去不了,就吩咐阿财帮我买。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虽然我有点生疑,却也无法分辨事情的真相。阿财就有这种不容置疑的架势,在他面前我莫名地听话。我只能把钱打给他。我负责大件的物资购置,一些小事,就由他处理。他总说村里现在外来人多了,有点乱,防不胜防。
我感觉不太舒服,正想着如何让阿财听我的。可开始挖桩的那天发生的事,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我亲临现场,正在开工,突然冲出个人,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房子要倒了——”声音嘶哑,喊得惊人。
我惊得一身冷汗。老屋后侧有家低矮的房子,很破旧,年久失修,已有裂缝。可显然不是我施工造成的。“都是你搞坏的,把我房子的房基震松了,你赔。”拉我的老太太声音凄厉,左眼下有块大黑痣。
看着是个老人,我打算顺便叫人帮她修补一下。“老人家,别急,我正好装修。等我修好了,哪天我叫他们也帮你把那些缝补上……”
“王阿婆,这是阿彩婆的儿子,你应该认识的。放手!”阿财赶紧过来,一手往另一只手上拉着衣袖,拉完了,肚子一挺对老太太严肃地说。
“哎呀,我们这里讲风水的,他在这里动土,惊了土地神了。”老太太放了手,却叫了一声。
“不要乱说,村里不是修了这么多房子?动了什么神了。”阿财圆眼睛一鼓,轻轻喝道,“你这不是迷信吗!”他有种不怒而威的气息。
“神,你看不见。我看得见呢……”老太太继续说。阿财一挥手,不客气地打断了她。“说房子呢,你怎么回事,听见没有?”声音更含威严。“嗯——”老太太像拍了一掌,声音像转了个弯儿,“房子?对,我的房子怎么动了,不能再打了啊。”
“老人家,这跟我打桩没什么关系。”我辩解说。目测了一下距离,她的房子隔了一米多宽的巷子,怎么可能影响到?
“啊,你不能不管啊。”老太太抬头向我,一屁股坐下去,马上拉扯住我裤角。
这时周围晃动着几个村民的身影。我听见他们低声议论起来,“怎么跟老人计较!”“这种人啊,城里好好的,又不回来,修来做什么?”……我正想发作,突然看见了那个长脖子小红。这家伙远远地看过我修屋,脖子像条蛇似的,扭过来扭过去。她早不来,晚不来,现在来干什么?
为这次装修,我准备了两个月,可等我回来装修了,想把我的车停在祖屋旁的一条小道上,车头却进不去。我纳闷,这小道是从外面的大路拐进来的,就我们两家人比较多出入,比较宽敞的,停一台车没问题,怎么突然间停不了?我只好把车停在远处。下车后,我到小道里看了看,小路依旧,但小道旁多了一堵新砌的砖墙,墙上却写着一组数字“4 月3 日,10 点”,崭新的、歪歪扭扭,不是粉笔写的,是油漆刷上的,很有力,像要刻进墙里似的。
围上来的村民,有的抽着烟,有的背着手。却见小红赶过来拿着皮尺在我老屋地基与她新盖的房子间,丈量来丈量去,我猛地明白过来,“4 月3 日”,不就是我上次回来的时间?那堵新砌的墙上的字是她写的。她本来就住在小道对面的那户人家,她是在警告我不许过界。可前段时间还那么宽的小道,一夜间被她家偷偷占了一半,这也太明显了。
“说房子,就说房子。”阿财低声吼道。
老太太立马又开始发作:“你这是欺负我啊,在城里那么好,跑到这里干什么呢,我真是命苦啊。”
我张口结舌,感觉脸上烧了起来,阿财这时敛住笑容,靠近我低声说:“她是你太爷爷弟弟的小儿媳,一个人,哎——给点钱算了。”
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还未开口,或许是猜到了阿财跟我说什么,老太太干脆躺倒在地上。她一句话好像就划分了一条深深的界线,是我这城里人,专门回来欺负她。我难道吃多了没事干!眼前晃动着小红扭动长脖子的身影,她写的那行字,跳字幕一样闪现,我脑袋嗡嗡地响起来。
“塞点钱,就算了。”阿财仍在急切地压低声音道。我一时心里堵得很,非常难为情,恼怒地摸出三百块钱,扭脸递给阿财。阿财转手交给老太太,她接了钱,马上起来走开了。
“这个……唔,这个……”阿财好像在找字眼,“我家修房子她也来过,我也给了她钱的。她可不好惹。”缓了缓又说,“大钱都花了,这小钱就算了。一个村的,大气点,装修为要。”
见没戏看,村民都散了去。我却气得没地方发泄,就把小红墙上写字、丈量尺寸的事告诉了阿财。“这是个刺头。你别理她,有什么事找我。现在你也拿不出证据,没办法。”
“你们不要过界,不要搞得人家走不了路。”我还没回过神来,却听见那小红呵斥我的施工队的人。
“哎呀,乡里乡亲的,你爷爷和他爸爸还是老朋友呢,互相让一下让一下——”
阿财马上笑着,大声接着小红的话叫道。说完还转向我,似乎在期待什么。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可不能发作。与她计较,实在不值,想到今后这里会拓宽成能通车的马路,就叫工人停工,将地基线往里移动50 厘米,重新让小道能容得下一辆车通过。我没跟母亲说这些。母亲见我真的去修复老屋了,那段日子她那高兴劲,使我报喜不报忧。
后来阿财打电话给我:“我跟小红再沟通过了,不许她再移过来。否则以后过不了车。”阿财又说:“他家儿子也打算买车的。我说万一你家以后要买车怎么办?她答应了。”还说墙上的数字,被批荡上去的水泥覆盖住了。
慢慢我知道了,有好多老板在村里搞服装加工,需要大量的工人。一些外来工就在这里住下。来的一般是一家人,上午睡觉,下午开始工作,直至深夜,甚至凌晨。我想,村里变得复杂了。老屋两层,我就想越简单越好,不想变动太大。可阿财却替我紧张,一拍我的肩,“你来,你来。”他把我拉到外面,指了一下周围,“这里可不是贫困村,要当贫困村还当不了。你得按照村里的规矩维修房子。”
“什么规矩?”
“搞两层,或加一层,每层改成有间隔的单间,带卫生间、厨房的。”
“我没那么多人住。”
“你怎么知道?听我的没错。”
照他说法,要想以后把房子租出去,就得根据租客情况建。来这里打工的都是一家人,需要这样的结构。我尽管想反对,可他已动作了,我说过我不可能天天去,加上连续发生的几件事,让我更不想去。所以除了没有再加层,都依他的意见将原来的房间布局改了。
那段时间,回到办公室我心情才好些。同事知道我去乡村装修房子都羡慕地说:“啊,你有乡村别墅,真好啊。现在城市空气不好,吵得厉害,老了还是要到安静的地方。”
我听了心里莫名地受用。他们去乡下只能开车跑来跑去到农家乐吃个饭摘点果子,过上一朝半晚,而我乡下有座房子。我感觉在办公室很有面子,跟上了时代。不过小小的虚荣心,还没到村子那条河前,就销声匿迹了。我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奔走,心里安慰自己,自己不回来,总要为老人做点什么吧。可我真不知道,母亲何时会回去。到了后面,我心里也越来越烦,感觉不是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就盼着早点完工。
幸亏我家老屋装修动作不大,否则这一天天的太难挨了。房子装修好了,我也不想再在村里待了。我对阿财说:“我不回来住的。”阿财好像知道我心思,笑着说:“那由你由你。先租出去吧。”
“我不想租出去。”我又说。
其实不是我不想出租,而是装修完那天,我在村里转了下,不见有张贴招租的信息。“这里不贴招租广告的?”我问阿财。
“广告?我们这里人嘴巴就是广告。”我没听他的,就自己写了个,张贴在村子中心的墙上。可是半天过去了,没一个人看,也没一个问的。
“房子要有人气的。不然就坏了。”见我想早点回城,阿财乐呵呵地说。
“你不能这样等。我在这儿呢。”阿财微笑了一下,关切地说。“我们是亲戚,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吧。”听见他的话,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总不能不回城里。
母亲也怪,没维修房子,她老向我唠叨,现在房子修好了,还在我耳边磨叽。说我还是能干的,帮家里做了件大事。我真的感觉不是我在装修,是阿财在装修,自己只是听他吩咐罢了。就像被他推着走。我不想多说什么,心里不想理阿财。可回城不久,阿财来了电话:“终于租出去了,费老劲儿了,三百一个月。村里招租这事儿,你一个城里人哪会这个,还是要靠我。”他电话里口气很大,带点自夸。听他说话,村里招租,不似城里,是靠关系,一个介绍一个,没人去看广告。
想到他知道这个还让我去贴,去招,我就奇怪,他这是什么意思。敢情阿财就是想让我知道,乡村有乡村的法子,不能依我所想行事。我想到自己这次回村修房子,几乎是包给阿财做了,他开多少就多少,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也没法子。现在回到家,我有种逃开了的莫名轻松之感。我于是随便说了句:“什么租金不租金的,算了。”心里真是算了的感觉,不想再跟他联系了。
“哎,我阿财讲究亲兄弟明算账的。你就安心工作吧,我会每月把租金打给你。”意外的是,阿财倒认真地说,“你看看,装修了下,你再来村里多有面子。”我心想,装的又不是我希望的样子,想起来就不舒服。何况谁认识我呀,什么面子不面子。还没想完,就听阿财道:“村里那些人一般只短租,又换来换去,流动性大。保证不了收足十二个月的,你就按十个月算。这情况你要知道,那也是不错了。我在村里可得天天帮你盯着。”一番话,倒搞得我没话说了。
看到打来的钱,母亲感激地对我说:“还是阿财有办法,真得谢谢人家啊。等你退休了我们可以回去住了。”我“好好”地答应着,却不敢据实相告。
我终究还是带母亲回去了一次。母亲“啊啊”地面对着老屋,连说“不认得了,不认得了。”阿财接话:“时代不一样了,该变变了。你看,这多新啊。”
母亲僵硬地摸着大门,连说:“好好。”一圈下来,这成了她说得最多的话。其他时候都是听阿财说。还是后来,母亲到阿财家跟他说起从前的事儿,才缓过点劲儿。我和母亲回来之后,她没再说什么。只是会叨叨过去屋子里有什么有什么。“你还记得?”我问。
“那不是还在那里嘛?那土灶我最喜欢,下面老捂鸡蛋烤土豆呢,后边就是鸡窝……”母亲的话让我不敢再问了。难道母亲……我担心起来。
“那门……”母亲似在沉思。我一惊,我想保留做扇新木门,最后还是改成了同村里村民一样的金属大门,当我抚摸之时,只觉一冷冰冷、坚硬,没有了从前的自然与亲切。
“哎,漂亮得很。”没料到母亲又转了回来,叹息了一声,我吓得不敢吭声,只能随声答应着
我一点也没有心思回乡下去,母亲也没说这事儿。不过,看到阿财有钱打过来,还是显得高兴,每次都会说:“有房子真好。”“是啊是啊。”我附和着,“我最喜欢那灶头了,土灶……”每回母亲总是陷入过去,似乎又在祖屋里游历了一回,每每此时,我心里说不出的味道。
开始陆陆续续地有些小钱打过来,由母亲收着,后来也没有了。我也不想问。倒是母亲什么也没说。不是有时同事开我玩笑,说我是地主,我都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乡下别墅”。我能说什么呢,母亲都没有回去住,我以后就会?时间一年年过去,我感觉到母亲的老去。每次跟母亲说话,母亲都会说到从前,说到老屋还有里面的人。好像还生活在里面。“那土灶我最喜欢,下面老捂鸡蛋烤土豆呢,后边就是鸡窝……”“老屋真好。”我总这样接着她的话。事后又难过一阵子。或者就是这个原因,有一天,我莫名地想到乡下转转。其实那天天气阴沉,像要下雨,不宜出行,我还是出发了。
我还没走到老屋,远远看到老屋里一个中年妇女套着睡衣走出来,她一身的灰尘与疲惫,脸上呆滞,头上飘着似有若无的细线与布丝,无神地看了我一眼。“租房的?”她问道,不待我回答,又道:“我们刚租下,你到别处去看下。”我想什么眼神呀,是不是晚上一直盯着缝纫机,眼花了。老屋高大锃亮的铁门上重新贴上了门神,只是门神没有了小时候那种威势,不再吓人。
那女人似乎也没有与我交谈的兴致,就趿拉着拖鞋,嘚嘚地进了边上的巷子,一会儿不见了。我转身走向车,想把车拐向这小道里,但我的车又一次开不进去,小道像橡皮筋又变窄了。没办法,我又得把车停到老屋前。下车向小道走去。边走边看,却发现,原来长脖子小红家还有另一个门,在小道尽头拐向外面大路的地方,她们完全可以不走这条路,就能开车进门。
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个呢?阿财没说,她也没说。我还想着让路,不是白让了。我是哑巴吃了黄连似的,嘴巴里涌上一波酸苦之水。村子很静,空气似乎也凝滞不动,一条大黄狗低头匆匆而过,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听见自己的喘息声,一扭头,我返身走出让我感觉到窒息的小道,我也不知往哪儿走,信步往前。还未到中心,便见好些牌子立于路旁边。有宣传牌,也有广告牌。
就在一块上面,七歪八拐地贴满了招租的信息“一房一厅,租金一千”、“大房一千,套间租金一千三……美观大方”。
时代变了,我感叹道。我拿出烟,点燃,猛吸了一口。这时却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呀,你……不是?”一个老太太声音。
有个老人弯着腰走到我面前。左眼上有个痣!这不是那个耍赖躺地上要钱的老太太吗?几年不见,她变老了,腰弯了。
“我现在也有新房子了。”她这次没乱叫,而是自豪地指着老屋方向的后面,那里露出一座新盖起的楼房一角。“政府帮盖的,不像你们要花钱。”说得脸上的痣似乎都在抖,看来她的日子现在好了,向我宣传呢。
“那好呀,祝福你。”我想她不需要讹钱生活了,真诚地说。
“你家的房子是不是卖给阿财了?”老太太疑惑地问。
“卖了?我没卖呀,只是让他帮我租出去。”我吃惊地说。
“还不如卖了。都在打麻将呢。”老太太鼻子哼了下,嘴巴朝向阿财家楼顶一呶。她着急地压低声音说道:“我可没神经呀,不要听村里人乱说。那年我清楚看见他叫小红把水泥扛回家,他也扛过。现在他家,不,你家房子,”老太太撇撇嘴,“又成了他家生蛋的鸡,生金蛋呢。”
“你说什么?”
“小红家肯定没少给他钱,要不然她家院子怎么那么宽了?”老太太得意地摇着头,我惊讶不已。“可是个会赚的人呀,整天不干活,收租金就行了。他赚了租金不说,还故意让租客再转租,然后再向那些人收转租费……”老太太还在絮叨。可能见我神情有变,老太太可怜地扫了我一眼,改口了,可说出的话差点让我跳起来。“我老了,可我知道呀,我可没怎么你。那个,还是阿财叫我去找你要钱的。他后来从我这儿,还拿走了200 块……”
真是个神经病!我听到心里咚咚响起来。
我的脚自己倒退几步,带着我转身向老屋方向快步走去。
我边走边拿出手机,想打阿财电话,可拨了三个数字,却停住了。我一口把烟吐出,开动了车子。
一路上,绿色的田野迎面而来,我望向那条小河,虽然舒缓地流动着,却如一条爬动的蛇似的。它怎么干枯了?为啥不闪亮呀。我胡思乱想着,老屋木门厚实、沧桑、贴满各种图画的画面也闪现出来。难道我错怪了那些来打工的?装修老屋时的情景也涌了上来……
“我做梦都梦到那里。”突然耳边回响起母亲的声音。我使劲踩下油门,速度提到180 迈,像逃离什么似的飞跑起来。
一路之上,绿色的田野纷纷倒退,天上的白云也跟着急退,阳光躲进云层,白云变成了灰色,然后迅速变成黑色,如沉沉的乌鸦拥在天际。突然之间,它们纷纷扇动翅膀,集体翻飞起来。
不一会儿,眼前就层层水气笼罩,耳旁电闪雷鸣。似在问我,如果不来这儿,是不是没这些事?如果不修老屋,是不是不会这样?好几年了,我想不清这个问题,也不愿意想这个问题。可是不想不想,还是会想;会想会想,还不能跟人讲。尤其是母亲,我不能跟她讲,不能跟她提。这一想,我突然发现,这几年,母亲也没跟我提那老屋重修之事,难道她也是和我一样……
雨水持续抽打着车子,乌鸦飞散开去,我心中曾经升腾起来的那丝细细火苗,已在风雨中飘摇,随着它们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