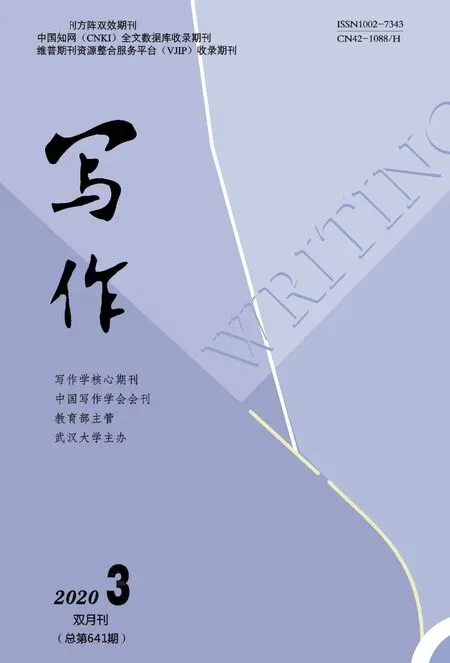笔记体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文学创意
——《俗世奇人全本》文本细读之二
刘海涛
冯骥才在2018年以笔记体微型小说《俗世奇人》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后,接着又续写了18篇新作。202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俗世奇人》“之一”(1995)、“之二”(2017)和“之三”(2019)荟萃为《俗世奇人全本》出版。这部历时30年创作时间的“俗世奇人系列”,传承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神韵精髓,融进现代意识,兼收欧风西雨,创造性地将微型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思想性、艺术性融为一体,展现了笔记体小说新的文体形态。这54个各自独立的篇章,生动描写了清末民初底层能人的生存状态和个性特征,概括着天津本土众多奇士能人的集体人格,也为小说研究者总结人物塑造和立意创建的写作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活的研究文例。
一、独特写人细节与突变故事情节
54个“活着”的市井奇人,如“苏七块”“刷子李”等,个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言行个性和行业绝技;像“蓝眼”“旗杆儿”等,个个都有让人唏嘘的人生命运和传奇故事①《苏七块》《刷子李》《蓝眼》《旗杆儿》,见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这些奇特的个性和传奇的命运,几十年来一直在冯骥才的脑中盘旋活跃,这些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又让人惊奇的绝技和言行的奇人奇事是他创作题材的敏感区。在《俗世奇人全本》的创作过程中,冯骥才有两个特别的笔记体微型小说的写人方法:一是用“独特的写人细节”勾画奇人们的反常言行,二是用特有的“转折性突变情节”来描述奇人的传奇命运。
冯骥才是这样采用“动作性+传奇性”写人细节来刻画这54个奇人的独特言行:
《张大力》是“胳膊笔直、笑容满面,好像举着一大把花似的大石锁”的画面;《钓鸡》里的“活时迁”,那“蹲在墙角,抽着旱烟,将黄豆、线绳、铜笔帽几下就把鸡拉到眼前”的特景;《泥人张》里的张明山,“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旧端杯饮酒,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要灵巧”的动作……均生动传神地将奇人的独特形象描现纸上。①《张大力》《钓鸡》《泥人张》,见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用精心提炼的“动作性细节”传神表达人物的独特言行是冯骥才写活奇人的第一绝招。
冯骥才的第二个写人的绝招是让一组“动作性细节”结构成“变化型情节”。他把一个“核心写人细节”与若干个“卫星发展细节”组成了“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这些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完整的微型小说故事形态,常常有个或反转、或曲转、或骤升的变化过程,而且又是在精炼的文学篇幅里快速完成“艺术突变”,加深读者对奇人的奇言奇行的深刻印象,引导读者富有情趣地深入探究奇人的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
《刷子李》写到了一个专干粉刷行的奇人,他立下一个规矩:刷浆时穿一身黑,若身上沾到白浆点,“白刷不要钱”。他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时,冯骥才放笔用“场面描写”描绘了刷子李的特异的动作与形象。如果把这个动作性的场面描写设定为“A”的话,那么故事的发展情节就突变为“-A”了:徒弟曹小三突然发现师傅裤子上出现了白点,这下子刷子李要“倒面”了(“白刷不要钱”)。但最后的“高潮细节”:那个黄豆大小的白点,原来是刷子李抽烟时不小心烧的一个小洞,里面的白衬裤透出了白点。这样的“变化型情节”,可用A→-A→A的回到原点式的“反转”情节来归纳。
《酒婆》《蓝眼》《蔡二少爷》②《酒婆》《蓝眼》《蔡二少爷》,见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作品的“原点式反转”突变型情节更是精致丰满,已经出现A→-A→A→-A的“多重反转”模型;除此,这本《俗世奇人全本》还有:以《苏七块》《刷子李》《死鸟》等作品为代表的A→A’→A”“重复斜升式”的突变情节(A’代表斜升式突变);还有以《张大力》《青云楼主》《泥人张》《绝盗》为代表的A→B式的“曲转突变式情节”。冯骥才的“变化型情节”之所以具备阅读情趣和艺术冲击力,最主要是他的“反转、曲转、斜升”等各种“翻三翻、升三级”的情节技法娴熟、恰当地使用。
冯骥才用“动作性细节”和“突变型情节”写活奇人还不是他最终的艺术目的。冯骥才在奇人的个性和命运上,寄寓了他比一般作家更深刻的人格认知和人性理解。附着在奇人身上的深邃的“文学创意”是这一本《俗世奇人全本》最有艺术价值的地方。冯骥才是这样构思与表达的思路:
先用“动作性细节”突出地勾勒奇人的奇特言行。因为有奇人的奇特言行,所以我们读到作品文本到了2/5的“发展细节”的部位时,常常被奇人的奇特言行引发惊奇和震撼;冯骥才接着使用或“反转”、或“曲转”、或“斜升”等3个左右的“发展细节”,把奇人的“奇特”做“翻三翻”(反转与曲转)或“升三级”(斜升)的渲染、铺垫,奇人的奇特言行被夸张表现到了极致;当读者最充分地感受到“奇特、怪异”之后,冯骥才才在“高潮细节”和“结局细节”里,通过“全点破、半点破、全留白”等艺术方式,创建寄寓奇人独特言行之上的从奇到不奇、从反常到正常的“因果性文学立意”,从而让读者理解、认同奇特言行背后的“历史的逻辑性”和“人性的合理性”,让读者领悟、思索在奇人奇事的合理性之中寄寓着的作家独特的人性思考和审美褒贬。至此,作家在奇人奇事的“独特性叙事”与“合理性解读”中创建了智慧的“文学立意”。
二、奇人奇事的因果与哲理
《苏七块》为《俗世奇人全本》的开篇之作,20世纪90年代首发《收获》,现收入教育部五年级语文统编教材。《苏七块》精妙的文学叙述方法和描写技巧,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微型小说人物典型;挖掘了这个典型人物里的文化立意和人性内涵。
《苏七块》的故事流程是“概括叙述与具体叙述”有机完美的结合。故事叙述人在“背景细节”里用个性化的语言简叙苏大夫的骨科医术的名气(第1段);接着描述苏七块带特征的外貌和动作性很强的治骨病的过程(第2段);再用夹叙夹议的语言介绍苏大夫“苏七块”外号的由来(第3段)。三个自然段的快节奏讲述把苏大夫的奇人奇事,有声有色、由远至近地做了叙述。
从第4段至第9段,就是《苏七块》的具体叙述了。它具体地描写了“一个场面里的一件奇事”:苏大夫在家里和华大夫等人打牌,三轮车夫张四摔坏了胳膊来求医,因为没有码上7块银元,苏大夫就是不理不睬;华大夫看不下去,悄悄给了张四7块银元,而当张四码上了7块银元后,苏大夫即刻接诊并免费赠送活血止痛药;牌局散后,苏大夫退还华大夫的7块银元,并说:“您别以为我这个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个规矩不能改。”
这个场面的单一事件从故事情节的转折性和意外结局看,它急转了两个弯——苏大夫看到张四的7块银元后,从不理不睬转为闪电般接诊;牌局散后,苏大夫却把收到的7块银元还回华大夫,这第二个弯转得有些出人意料了。故事情节的转折性和意外结局在这个具体描述的“一个场面的单一事件”里得到了最符合微型小说文体特征的“文学叙事”。
从人物单一性格元素描写的“二重组合”来看,它对苏大夫坚持“要7个银元才看病”的表面的独特言行与“不要7块银元”(还回华大夫)的人物行为动机,做了对比性的客观叙述。这个叙述把苏大夫“要7个银元”的“怪”和“还7个银元”的“善”,这两个矛盾着的人物言行艺术地组合在一起,实现了真实立体地写活一个微型小说人物典型的艺术目的。
综合“单一场面单一事件”的“转折性”和“人物单一性格元素”描写的“二重性”来看作品的创意,作家在写足了事件的奇、人物的怪后,通过苏大夫一句“金句式语言”点破了他的奇和怪背后的因果——原来是他“立的这规矩不能改!”这一点破,把苏大夫的奇人奇事背后的行为动机的“合理”瞬间给揭示了。苏大夫的这个“不能改规矩”的理由,包含着相当深刻、相当有概括性的“文化内涵”。苏大夫行医是有自己的规矩的,他始终不改的“规矩”是他行医做人的根本;客观地说,他在那个时代的天津卫能创建如此的医术品牌,也是和这个“规矩”分不开的;而再延伸扩大说来,不光是苏大夫,就是整个医学界,乃至是人类所有的谋生行业,都有一个立规矩而不能随意改的“处事原则”。这就是人类所有行业的处事原则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奇人+奇事+正理”的微型小说人物典型的塑造方法。
这个“奇人+奇事+正理”的人物描写有一个很出彩的地方——苏大夫这个奇人做出了如此的奇事确实有不近人情的地方,尽管苏大夫最后是用了自己的“金句式”的语言点破了奇人奇事背后的普遍哲理,让奇人奇事体现了中国传统民间医术行业里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而在具体的人物塑造过程中,作家是客观真实而水到渠成般地写到了苏大夫奇人奇事背后的一个核心动作——他早就知道张四这7个银元是华大夫给的;在有意避开了所有人以后他才还回了华大夫的7个银元。这是一个典型的人物表象与人物内心的矛盾组合。表面上看苏大夫的“不改规矩”不讨人喜欢;而他内心深处里还是有一颗救人济世之心和并不贪财的善人之举,苏大夫实际上是用了一个不利于自己的名声,树立一个“贪财”的形象来坚守着行业规矩。表面的丑与内心的善的“二重组合描写”,才是写真、写活一个奇人形象的艺术基点。微型小说在“一个故事场面”里,创造一个“二重组合式”的奇人,这个经验和方法值得总结。
作家在“奇人奇事”背后的正常哲理和文化内涵的表达,更有着微型小说创建立意的艺术规律。请留心作品的最后一段(第10段):“华大夫把这个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华大夫想不清楚,就是说,苏大夫对张四的做法,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或者是又对又错呢?作家在这里精彩地使用了“半破立意”的方法,为读者展开艺术想象而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
如果说《苏七块》使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全点破”了苏大夫奇特言行的正常因果的话,那么《齐老太太》则是通过故事叙述人的夹叙夹议的语言“半点破”了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
《齐老太太》有五个情节。第一个情节单元讲述的是正常形态的材料——齐老太太过着有滋有味的大院生活,唯一念想就是自家这个两儿一女的家庭别散了。第二个情节单元就快速进入了故事的反常——一家人像往常那样打牌时,老二媳妇的结婚陪嫁的戒指突然不见了,反复寻找没有结果。第三情节单元的反常立刻升级了——齐老太太头一遭发火,要全家人都搜身,结果搜遍了全家人仍然无果。第四个情节单元就出现了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常——齐老太太突然承认,戒指是自己因有急用拿走了,这令全家人非常疑惑;从此全家人虽不再嘀咕此事,但大家和和睦睦快乐打牌的日子就再也没有重现。第五情节单元是故事高潮——一年多后齐老太太过世,老三在堂屋软榻的地缝里找到了那只丢失的金戒指。老三流泪说:“你干嘛躲在这儿了,你要了我娘的命啊!”最后一段是第三人称叙事者的议论,直接点破了产生三次离奇、反常情节的因果,把故事主人公的反常的言行动机和人物的善良、故事的底蕴给直接揭示了:“这家人想到这位大仁大义的老太太,为了全家人的和和气气,抱团不散,有难独当,忍辱负重,郁闷至死,不知不觉全都淌下泪来。”
这篇作品的情节轨迹和创意方法可用“斜升曲转+全点破”来概括。从正常形态的故事材料开始讲述,然后连续用3个有力度的反常的情节材料来一步步地斜升渲染故事的怪异奇特,最后的曲转结局揭示了反常的真实原因:既不是家里的人偷走的,也不是齐老太太拿走的,而是掉在地砖的缝隙里了。
曲转的结局解开了三次离奇反常事件的正常原因。值得赞赏的是:这样一个普通天津居民从平常到反常的传奇故事,通过第三人称故事讲述人的“议论式描写”,全点破了人物的善良动机和故事的底蕴,使得前面对齐老太太所有的动作性和个性化兼备的形象描写,瞬间点亮她的深层的人性内涵,齐老太太宁愿自己委屈受冤,也想维护一个中国式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这个人性中的亮点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理想人格,在这里得到了合情合理的文学描写。类似《苏七块》《齐老太太》这样通过在情节高潮部位,用人物的独特言行或叙述人的议论对奇人奇事的历史因果、人性因果做“全点破”后,迅速形成作品的意外结局,推进读者对附着其上的生活底蕴和审美评价做深入探究的创作方法,在《俗世奇人全本》的54篇作品中还有《大回》《绝盗》《黑头》等13篇作品,约占全书的24%。
三、文学创意的点破与留白
《蓝眼》是附着在“变化型情节”里把“因果创意”给“半点破”了。蓝眼是天津古玩行中最能识破假画的高手;有一次一个书生打扮的人来到铺子里,欲出售石涛的“大涤子湖天春色图”,蓝眼判断是真品,以不高也不低的18两金买下了;不久津门古玩街传开了:蓝眼买的东西是西头黄三爷的赝品,真品在针市街一个崔姓人家手里。蓝眼在佟老板的授意下,去崔家查看,蓝眼这才认定崔家的是真画(情节至此是“一正一反”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蓝眼和佟老板为保全面子,用了比先前多花近三倍的钱买下崔家的真品,但买回后两副画挂在一起对比,才发现先前买的是真画,而这次买崔家的才是假画(变化型的情节又是“一反一正”来了个180度大反转,这是典型的“多重反转”情节模型);蓝眼大病一场后卷起包袱离开了裕成公。在“高潮细节”,冯骥才通过叙述蓝眼的内心反思,明白了那个黄三爷不是冲着钱来的,而是冲着他和他的名声来的:黄三爷给他设了一个圈套,让他手里攒着真画再去用天价买他造的假画。
注意,这个一正一反的“多重反转”传奇故事的因果关系,是典型的“半点破”——故事叙述人没有让黄三爷出场,黄三爷为什么要陷害他?黄三爷究竟是如何设计圈套、一步步地部署、实现这个阴毒的策划的?作品一个字也没有写,全留给读者去自由想象了;而仅仅是通过蓝眼的内心的反思,确认自己一世英名被毁全是黄三爷的陷害,可以说这就是“半点破”的因果情节和故事底蕴。这既创造了一个暗写的黄三爷的狡诈、阴毒的形象,又留下了天津民国时代古玩界的种种传奇和包含在传奇中“职业和人品的深刻底蕴”。这样的“半点破”,拓展了读者阅读的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审美信息供读者展开艺术的想象。类似《蓝眼》这样的“半点破”创意方法在《俗世奇人》中还有《刷子李》《酒婆》《冯五爷》《好嘴扬巴》等28篇作品,占全书的52%。
如果说《苏七块》《齐老太太》的创意形成是“全点破”、《蓝眼》是“半点破”的话,那么,《鼓一张》则可以说是“全留白”了。
天津卫的杨柳青镇做年画的白小宝,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一张毁了版的老年画《莲年有余》在那一年卖疯了,他赚了一笔大钱(他们的行话就叫“鼓一张”);他盼着这张年画来年继续“鼓着”,但转年风水变了,鼓的不再是《莲年有余》,而是6个女人在打太平鼓的《太平世家》。从情节变化的模型来说,这是曲转,但曲转变化的原因,冯骥才一个字都不写,这个“曲转因果”全靠读者的想象了。是否时代变了,人心变了,时尚也跟着变呢?还是社会心理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跟着发生变化了?这一切全由着大家的自由想象。正是这样的自由想象,才为这篇作品的文学创意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审美再创造的空间。
如果说《鼓一张》是“情节曲转”后留下空白供读者想象,那么则可以说《冷脸》是通过“斜升式反转”的变化情节来给读者暗示作品创意。《冷脸》里铁匠的奇特在于他从来不笑,脸总是阴着,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冷脸”。“冷脸”被几个天津小子按在地上胳肢,他“上边流泪下边尿尿,大喊求饶,”可就是不笑。第二个“发展细节”,这个从不会笑的人却喜欢听相声,但相声场里大家都笑了,冷脸仍然不笑。这个“发展细节(2)”是将“冷脸”的奇特做了“斜升式重复”。在“发展细节(3)”里,北京两个相声高手使出了全套本事也仍然逗不笑“冷脸”,直到北京的相声高手说:“这位爷,你要是再不笑,我俩可真要脱裤子了。”全场大笑了,冷脸仍不笑;“高潮细节”却是个“反转式重复”,北京的相声高手走后,没人再往南门外说相声了,“冷脸”从此不再喜听相声而远走高飞了。从爱听相声到不再听相声,这个“反转”后的情节内容是“冷脸”的“仍不笑”,所以说这个高潮细节是“反转式重复”。“冷脸”的奇特通过这“斜升式重复”和“反转式重复”的渲染、夸张,已经“奇”到了顶点。现在探究因果:“冷脸”为什么永远不笑?故事的讲述人连甩三问:那天他要是真夸毛猴的相声棒,为什么不笑?他要是真的不会笑,干嘛非要来听相声?他要真的爱听相声,干嘛从那天起与相声一刀两断?冯骥才把因果“全留白”了,读者完全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寻找“冷脸”不笑的生理和心理的原因,正是这样的“创意因果全留白”,才制造了这篇作品的阅读情趣。类似《冷脸》的写法,还有《死鸟》《青云楼主》《刘道元活出殡》等13篇,占了《俗世奇人全本》的24%。因此,“全点破、半点破、全留白”作品的文学创意,是冯骥才“写人与创意”的三大绝招。
根据上述作品分析和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俗世奇人全本》的故事情节和意外结局,冯骥才用的较多的方法是:抓住奇人的某一个性格元素,用斜升式情节来做“升三级”、或用“反转或曲转”式情节来做“翻三翻”的铺垫、渲染乃至是夸张,达到把奇人的奇特性格元素和行为方式写出特征、写出极致的艺术目标,以此形成对读者的阅读吸引力。
《俗世奇人全本》在奇人身上创建立意的方法多数为“半点破”和“全留白”(两项相加有41篇,占全部作品的76%),这与微型小说的创作规律与文体特点较为吻合。微型小说文体就是需要这样,通过真正智慧的艺术构思和正面的、侧面的以及含蓄的细节描述,在短小的篇幅里制造更多的审美信息,激活读者的阅读想象力。
即使是采用“全点破”的立意方法,冯骥才也有着自己独到的“冯氏全点破立意方法”——不使用精炼的理性语言、或像报告文学的政论性抒情语言那样直接明示、告白,而常常是通过故事主人公的言行描写和心理描写,点破奇人奇事的因果关系,创造一个完整的从反常到正常的“因果艺术体”,把故事主人公的“点破性”的独特言行当作故事进程和故事叙述的“有机情节”,即当作不脱离奇人故事的一部分,让奇人奇事的因果逻辑在读者的阅读中,形成顿悟点和震撼力。“奇”而不再“奇”,“奇”蕴涵着带有普遍性的人格的合理性与人生的逻辑性。
四、“故事叙述人”的个性特征与塑造方法
用“系列微型小说”来申报鲁迅文学奖已成为“标配”。微型小说创作要成“系列化”,除了题材选择、人物描写、情节提炼、故事叙述、立意创建等各个创作环节要形成基本的、统一的艺术风格外,还有一个目前并没有被太多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论及的地方——这就是整个“系列微型小说”在讲述故事时,“叙述人形象”必须确立、成活并形成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在研读《俗世奇人全本》时,可以发现这个“冯氏故事叙述人”的独特形象。我们通过细读《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来研究《俗世奇人全本》的微型小说叙事方法,特别是研究“冯氏故事叙述人”的形象机制和塑造方法。
先看作品的故事梗概:北京艺人小杨月楼在天津演出,遇到洪水,当完了自己的十几个戏箱也未能返回京城;找天津卫的“混混头儿”李金鏊帮忙,但小杨月楼与李金鏊初次相见时,破屋和穷像让小杨月楼根本不相信这个又穷又横的李金鏊能帮自己;但李金鏊来到“万城当铺”交涉,十几个戏箱立马还回;接着天津卫的“锅伙们”都来替李金鏊交赎金,小杨月楼寄回赎当钱时,李金鏊又将钱还给代他付钱的兄弟们;到了高潮情节,李金鏊和上千个码头脚夫在上海遇到冰灾无法返回,小杨月楼组织了上海的名角义演3天,所有的戏票钱全交李金鏊及上千个码头脚夫处理。整个多重反转的故事,将李金鏊外表粗俗而内心重义及与小杨月楼那种超越金钱关系的兄弟情谊写得十分感人。
“冯氏故事叙述人”与作家冯骥才既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艺术与生活极分明的区别。“他”是这样开讲这个“粗人与艺人”的兄弟传奇的:
民国28年,龙王爷闯进天津卫,大小楼房全赛站在水里。三层楼房水过腿,两层楼房水齐腰,小平房便都落得“没顶之灾”了。街上行船,窗户当门,买卖停业,车辆不通,小杨月楼和他的一班人马被困在南市的庆云戏院。那个时候人都泡在水里,哪有心思看戏?这班子二十来号人便睡在戏台上。①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60页。
这一段非常能代表“冯氏故事叙述人”启动细节的叙述方式。第一,叙述语言的内容有特定时代的文化元素。龙王爷“闯进天津卫”,“全赛站在水里”,“困在南市的庆云戏院”,类似的体现地域文化元素的叙述内容,在54个故事中比比皆是。第二,叙述语言的形式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学与说书形式中的“四字句型”和“七字排比”。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说书艺术的语言形式在《俗世奇人全本》中均被活用了。第三,叙述语言在推进过程中形成了“概括叙述+具体叙述”的叙事技巧。小杨月楼的戏班子被水困到什么程度呢?“二十来号人便睡在戏台上”——“睡在戏台”这就是细节,这一句足以概括戏班子的所遇困难。因此,“冯氏故事讲述人”常用“地方文化元素+传统说书句型+特别文学细节”来组成“启动细节”的叙述。这样一开始就能先声夺人,显示冯氏故事的惊奇魅力。
现在看作品如何展开故事主人公的外貌描写和性格刻画:“李金鏊是天津卫出名的一位大锅伙,混混头儿。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绝不含糊,死千一个。”看李金鏊说话时的语言神态:“没想到这人说话嘴上赛扣个罐子,瓮声瓮气问道:找我干嘛?口气挺硬,眼神极横,错不了,李金鏊!”除了继续有“地域文化内容+说书语言形式”外,这里一方面是注意到人物外表的概括叙述,更重要的是,“冯氏故事叙述人”纵横开合,极为巧妙地将故事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叙述改变成为故事叙述人的叙述语言——“口气挺硬,眼神极横,错不了,李金鏊!”头两句是“4字说书语”的对人物外貌的“特征化概述”,后两句实际上是从小杨月楼的角度展开的内心活动。冯骥才在此巧妙地将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描绘,化为了“故事叙述人”的叙述。本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方法,尽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讲”的叙述优势,但它的短板却是:故事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你怎么知道、怎么叙述呢?冯骥才贯穿于全书的叙述方式有个特点,他常常能全方位调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入笔记体小说的人物内心,将故事主人公的内心语言,自然地转变为叙述人的叙述语言,这就是说叙述人的语言与故事主人公的内心语言全融为一体了,这就是一种叙述语态丰富、故事信息量巨大、叙述节奏快捷的“冯式故事叙述人”语言,这种“故事叙述全程+故事人物内心”的转换和铸炼,在《俗世奇人全本》中经常出现,形成“冯氏故事叙述人”的叙述语言特色。
现在再看“冯氏故事叙述人”怎样叙述高潮细节。一个粗人李金鏊与一个艺人小杨月楼的互相救助、肝胆相照的情义传奇是作品的故事内核,而故事内核中带着物品细节和人物个性的高潮细节则是故事内核中的核心细节。作品的高潮部分是小杨月楼召集上海的名角义演3天,让李金鏊和上千个码头脚夫拿着戏票去卖,这就是作品的核心细节了,冯骥才的“故事叙述人”这样开始高潮部分的叙述:
赶到大舞台时,小杨月楼正是闭幕卸妆的时候,听说天津的李金鏊在大门外等候,脸上带着油彩就跑出来。只见台阶下大雪里站着一条高高的汉子。他口呼:“二哥!”三步并两步跑下台阶。脚底板冰雪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下,仰脸对李金鏊还满是欢笑。
一个粗人与艺人的相见场面被“冯氏故事叙述人”描述得相当动人而且精彩。冯骥才在这里一是抓住人物的动作特征;二是准确地使用动词;三是加快相见场面的叙述节奏。这3条形成为“冯氏故事叙述人”的“白描式叙述”的方法技巧。这个“白描式叙述”展开的元素是“语言+动作+神态”的快节奏叙述,这样的“白描式叙述”与“比喻式叙述”刚好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冯骥才处理高潮部分的场面描写的基本方法。
最后看“冯氏故事叙述人”如何叙述结局细节:
小杨月楼叫李金鏊这一席话说得又热又辣,五体流畅,第二天唱《花木兰》,分外的精气神足,嗓门冒光,整场都是满堂彩。
这是“留白式侧叙”。表面上是用两个“4字句”来说小杨月楼第二天的戏发挥得好,实际上是讲两个人超越了金钱关系的情义所带来的传奇故事。虽然不用点破故事的底蕴与创意,但侧面叙述的事件与信息已在读者的阅读领会方面充分地展开了。
因此,冯骥才打造“冯式故事叙述人”形象的常用策略是:
用“文化元素+说书句型+文学细节”来启动故事的背景叙事。
用“全知叙述+人物内心”来打造故事叙述人特定的叙述语态。
用“语言+动作+神态”组成“白描式叙述”渲染故事的高潮细节。
用“留白+侧叙”制造结局细节的多层信息,调动读者参与故事创作的兴趣与积极性。
这就是《俗世奇人全本》的艺术构思和叙述风格的基本特征,也是冯骥才用自己的佳作昭示着微型小说文体在创造人物、构思情节、创建立意上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峰,更是冯骥才用自己的经典为微型小说文体的“创作原理和方法”的总结所做出的、其他人无可替代的艺术贡献。
五、故事叙述人的全知视角与创意方式
《大关丁》是“俗世奇人”之三的开头篇,代表着冯骥才“俗世奇人之三”的写法变化与艺术特征。首先,在篇幅上,《大关丁》比“俗世奇人之一”的篇首《苏七块》长了一倍以上。篇幅虽然长了,但《大关丁》的故事内核是微型小说型的,它的叙事方法则是短篇小说式的了。先看它的6个情节:
A、北大关丁家的大少爷丁伯钰生长在富裕的望族家庭(背景细节);
B、会玩会吃的丁家少爷是天津卫第一个玩自行车的人(启动细节);
C、丁家少爷喜欢吃糖堆,专门请京城御膳房的王老五来做(发展细节一);
D、八国联军血洗天津老城后,丁家被烧毁,大关丁陷入贫困(发展细节二);
E、大关丁偶然通过做糖堆卖,让自己和全家度过了绝境(发展细节三);
F、大关丁用王老五做糖堆的绝技,做成了糖堆品牌,让自已和全家重新站了起来(高潮细节)。
从这6个情节单元可见,故事主人公在吃、做糖堆这一个核心细节上经历了从爱玩爱吃到抄家毁家再到创业救家的大起大落,这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带转折性的微型小说故事内核。冯骥才展开讲述这个故事内核时,下列的笔记体微型小说的叙事技法值得总结:
第一,在启动细节里,是讲会吃会玩的丁家少爷耷拉着一根辫子,骑着洋人的自行车在天津城飞驰。这个具体的动作性细节与全篇故事内核展开时的主干情节(吃、做糖堆)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它对形象细致地描述大关丁的性格,是个生动丰满的艺术铺垫。
第二,在发展细节(一)里忽然离开对大关丁的直接讲述,而“花开两枝”似地写起王老五做糖堆的场面来。这一个情节单元表面上看也离开了正写大关丁的故事,属于短篇小说的“闲笔铺叙”,但是它从容地、有情趣地描叙京津城里的民俗风情;而这个“折叠”进来的王老五的绝技将是后面故事高潮大关丁东山再起时的“故事因果”。这个发展细节(一)与启动细节,虽然可算作“短篇小说的闲笔插入”,但冯骥才这一笔属于微型小说“例外”的情节描述,却对这篇微型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铺叙,有着直接的艺术关联。这是对微型小说叙事方法的一种有效的创新性改造,丰富和发展了微型小说特有的叙事艺术。
第三,在作品的高潮细节,作家生动形象地写出大关丁成功地做、卖糖堆的吆喝场面后,故事叙述人这样结束作品:“他身上总还有点当年大关丁的派头。天津人再没人贬他,反而佩服他。人要阔得起,也得穷得起。阔不糟钱,穷就挣钱。能阔也能穷,世间自称雄。”①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5页。这是故事叙述人点破人物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传奇命运的底蕴的一段“议论”。这个点破,概括了附着在大时代里类似大关丁这样的命运大起大落、性格二重组合的传奇人物所体现的审美意义,这样的“阔得起也穷得起”的个性和品德,正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集体意识。这种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结尾中常见的“全点破议论”,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睿智深刻的体现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思维方式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者”形象,精炼地点破故事人物身上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创造性地在笔记体微型小说的创作中,机智地运用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点题技巧,用“议论式金句”升华作品人物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总之,《大关丁》创造性地活用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点题方法来叙述一个微型小说型的故事内核,克服微型小说叙事艺术的某些短板,丰富发展了当代笔记体微型小说的叙事艺术。
《白四爷说小说》活灵活现地塑造一个能同时在四五家报馆开武侠小说专栏的作家白云飞的艺术形象。白四爷的个性奇在哪?奇在他开设武侠小说专栏时,自己不动笔,全靠在澡堂泡完澡后,轮流对着在一旁等稿的报馆编辑说一段武侠小说。冯骥才写活这样的一个奇特作家奇特的创作情形,同样用上了饱满的并带上短篇小说叙事情调和艺术氛围的叙事方法。先赏读作品的传奇情节:
A、天津人爱看武侠小说,而写武侠的三位高手中就有一个白四爷(背景细节)。
B、概述白四爷是在澡堂泡好澡后才开始他独特的“口述创作”(启动细节)。
C、具体叙述给《庸报》记者说《武当争雄记》中明天要发排的500字稿(发展细节一)。
D、具体描写白四爷对《369画报》秦编辑口述正在连载的《发面侠》,同时概述白四爷“声情并茂、出口成章地说武侠小说”的场景(发展细节二)。
E、使用“概括叙述+具体叙述”的方式,再次描述白四爷“泡澡、搓背、喝茶、嗑着瓜子,指天画地一通乱侃”就把“活”干了的情景;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几个脚趾头设置为《天成镖局》中尤家的几个女人的有趣情景(发展细节三)。
F、使用故事叙述人的口吻概述白四爷把日常生活化为武侠小说材料的独特本事,他曾把自己梳头发的梳子写成是《鹰潭三杰》的利刃(发展细节四)。
G、简洁概述白四爷红了30年,被澡堂掉下的一块屋顶砸坏了颈椎后,退出了武侠小说界(高潮结局细节)。
上述7个情节写出白四爷的奇特才华和创作武侠小说的新奇情形,用到的情节链比一般的写“单一场面的单一事件”的微型小说情节链要丰满。具体描写两个报馆编辑等稿、录稿的过程,相当生动有情趣,既写了他们趣味盎然的对话,也具体展示了白四爷口述武侠小说的文本内容,除了有两个递进式串联的具体场面描写,作家又进一步增加了两个夹进了细节的概括叙述。于是“两个具体叙述、两个概括叙述”的材料一组合,就把白四爷用口说的、编辑用笔录的方式来创作武侠小说的新奇方式,饱满地、饶有情趣地雕塑成型了。“两个概括叙述+两个具体叙述”构成的斜升式情节的主干,是短篇小说常用的叙事方法。微型小说叙事的“单一场面的单一事件”,常常会像《苏七块》那样,在一个精短的篇幅里快速完成故事的突变。这确实是微型小说的叙事特长,也正因为这是微型小说的叙事特长,也蕴涵着天然的艺术短板:因阅读时间的限制,微型小说的审美信息还是不如短篇小说故事那样从容、细致和精美化,作家这种为微型小说故事核心情节增加叙事空间而带来的好的叙事效果,是将笔记体微型小说的叙事方法做了有益的创新发展。
这篇作品的故事叙述人对白四爷的奇特的创作能力和后来的命运的评价属于全点破,但这篇作品全点破的方法和《大关丁》不同。《大关丁》是一个思想睿智的全知全能的讲述人全点破人物个性和底蕴的“概括性哲理”(人要阔得起,也得穷得起),而《白四爷说小说》则像一个历经沧桑的智者从全知全能的角度,补叙了传奇人物和故事的“完整性情节”。请看结尾的高潮部分:
行内的事行内明白。不过,作家圈里的谁也不肯认头这是白四爷天生的本事,只骂他“述而不作”,自己不会写,借人家的笔杆子弄钱出名。说这个话的人还是位名家。于是有人为他愤愤不平骂那个名家,你躺在澡堂子里说几段看看。人家白四爷不单脑袋瓜阔,还出口成章,记下来就是文章,不用编辑改一个字。你拿嘴说的话到了纸上,还不乱了套?……于是,原先有一种说法重新冒了出来,他一离开澡堂子小说就没有,白四爷的小说全是光屁股说出来的。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只要打开他的小说一看,还得服人家。①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
这位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故事叙述人通过补叙的方式,简要交代有人嫉妒、不服白四爷的“说小说”的本事,这是用其他人的负面评价来侧写、反衬白四爷“澡堂说小说”的奇特本事。特别注意:故事叙述在侧写反衬白四爷时,将反驳负面意见的人的语言与故事叙述语言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既补充故事材料,使这个传奇故事有了一个完整形态,又将故事叙述人的叙述语言与故事中的人物语言紧密融合,创造了一种叙述明快,信息完整,并使故事叙述人的个性与情感褒贬得以彰显。这就形成了故事叙述人从“法官代言人”的角度,补充进具体的故事材料,使一个传奇故事有一个完整形态供读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这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者”的一种“全点破”的方式。这与《大关丁》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者从“睿智思想家”的角度,用极简洁的“故事金句式”的议论语言,直接点破、揭示独特个性人物和传奇人物命运的底蕴,以此形成能升华的生活哲理、人性内涵,正是两种区别鲜明的故事立意的“全点破”方式。
冯骥才的故事叙述人像《白四爷说小说》这样的从“法官代理人”的角度,通过补充传奇人物故事或因果或相关的材料形成的“全点破立意”,在《俗世奇人全本》的13篇“全点破立意”的作品中,还有《大回》《黑头》《神医王十二》《钓鸡》等 4篇;像《大关丁》这样的从“睿智思想者”的角度、通过用故事叙述人“议论式金句”语言直接点破传奇人物命运的故事底蕴的“全点破立意”,在《俗世奇人全本》13篇“全点破立意”的作品中,还有《绝盗》《洋相》《崔家炮》《十三不靠》《毛贾二人》等7篇。无论哪一种全点破方式,冯骥才都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事功能和优势,并创造性地吸收时代生活和现代艺术的创新元素,塑造了一个有生命力和高度审美价值的“冯氏故事叙述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