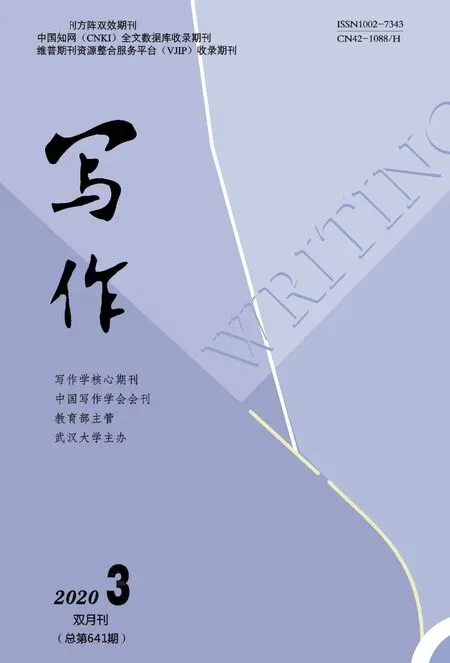中国城市文学书写新变
——以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为例
向 迅
中国的城市文学,追溯起来有着较为悠久的书写历史,像唐传奇、宋代话本小说、明清小说,诸多文本都是以市民阶层为书写对象,将之归为城市文学,大体没有问题。如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世情小说”的代表作《金瓶梅》,“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①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插图本),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页。,相当于一幅描写晚明市井生活和世俗人情的“清明上河图”。民国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城市生活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和体会,加之他们大都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且多有留洋背景,确立了现代人的身份和意识,因此书写城市文学的作家不在少数,茅盾、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苏青等,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那一时期的城市生活、社会状况和社会氛围有过十分贴切的书写。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真正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如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据许子东回忆,20世纪90年代,百名评论家曾投票评选“你心目中最重要的十个作家十部作品”。在最终评选出的10部堪称中国当代经典的作品中,只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和贾平凹的《废都》属于城市文学②徐瑞哲:《中国当代文学“农村包围城市”?许子东孙甘露毕飞宇等作家学者说,城市文学还是非主流》,上观网,网址:https://web.shobserver.com/news/detail? id=69625,发表日期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而城市文学处于支流地位,或者说从属地位。这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生活背景和成长背景密不可分。现在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尤其是50后、60后作家,多半是在成年以后才进入城市生活,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即便他们把写作背景转移到城市,转型书写城市生活,但遗留在他们骨子里的非现代性的、非都市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仍在起支配作用。正如《三城记》中的张薇袆说:“当代作家最擅长的就是乡土题材,最好的作家都在写乡村。他们一写自己身处其中的城市就捉襟见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童话’作家,或者‘故事大王’,没有现实感。当代城市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真的是太缺乏。”①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而且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举世瞩目,城镇化人口大幅度增加,但遗憾的是,中国作家并没有创作出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文学。这是中国文学滞后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表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著名批评家张柠推出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三城记》。
一、《三城记》:中国城市文学的最新样本
简单一点说,张柠的《三城记》写的是80后顾明笛以及一群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三座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的工作、生活、恋爱与蜕变的经历。很显然,顾明笛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加之他出生于中国大陆最现代最开放的城市上海,他身上具有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时代新人”气息,其价值观、恋爱观、生活观与工作观都与传统观念迥然有别。
正是因为这样的选题角度,让我在阅读这部长篇小说时,不免有些担心。只不过我的担心与王春林的有所不同,他担心的是批评家理念先行的问题②王春林:《从一己经验到外部世界——读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及其他》,《文艺报》2018年11月21日第3版。,而我担心的是,作为一位50后作家,张柠在成年以前,有过较长时间的乡村生活经历,这种乡村生活经验会不会成为他书写城市的障碍;由于年龄差距,他能不能准确把握80后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令人惊异的是,张柠在这部作品中,不仅特别精准地呈现了上海、北京、广州这三座城市不同的时空感、文化形态、城市性格与人际关系,而且也写出了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的一代人的迷惘与成长。这与他离开乡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有关。
从某种意义而言,顾明笛的人生轨迹与张柠的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重叠之处。甚至,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度将顾明笛想象成张柠。张柠先后在上海、广州学习和工作,然后北上北京,而且他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工作,深谙现代主义精神。他自身在“北上广”这三座城市的经历与长期坚持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使得他解决了个体精神非现代化、非都市化的问题。
作为一位“新锐”小说家,相较于池莉的《烦恼人生》、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等城市文学,张柠的《三城记》很显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池莉的《烦恼人生》主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贾平凹的《废都》主要表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灵与肉的冲突,王安忆的《长恨歌》主要写的是中国女性在大时代变迁之下的命运沉浮,金宇澄的《繁花》与《烦恼人生》有相似之处,但他写的是带有一点乡土味儿的上海,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上海。
换言之,池莉、贾平凹、王安忆、金宇澄笔下的城市文学呈现的是过去时态的城市,而张柠笔下呈现的是当下时态的城市。他不仅从宏观和微观双角度对“三城”所代表的典型环境进行了勾勒与描绘,让不同城市的文化差异跃然纸上,而且还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典型人物形象:顾明笛。80后这一代人自此作为典型的文学形象登上文学舞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21世纪中国城市文学书写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在张柠的笔下,上海、北京、广州“三城”被描写得活色生香,大到城市景观、街道样貌、建筑格局、历史形态、人际关系,小到菜肴菜式乃至气息气味,都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张柠写上海,“上海文化表面上看很洋气、很国际,像外国文化似的,其实它骨子里浸润着江南的灵秀之气,它的根基是吴越文化。它将现代世界的理性和实用,与江南文化的审美和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世界文化精神。”①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72、73、363-364、363、9页。他写北京,“北京的主要特点就是大,能够容得下更多的东西”②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72、73、363-364、363、9页。。“空间太大,就容易杂乱而显得粗糙。这种粗糙影响到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形态。……粗暴且奢侈的帝王文化,悲壮凛然的古燕赵文化,是北京精神的底子。……在北京那种过于严肃又有点粗糙的外表下,总是涌动着一种年轻的气息……”③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72、73、363-364、363、9页。
张柠借施越北之口写广州:“广州这座两千多岁的老城,却羞涩得像个新人,低调不声张,任人评说。它是一座真正的平民城市,雅的俗的,穷的富的,忙的闲的,咸的淡的,都无所谓。高头坐大马,马死落地行。……高头大马可以坐,步履蹒跚也能行。”④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72、73、363-364、363、9页。他甚至还借施越北之口对深圳性格进行了总结式分析:“深圳这座城市,外表在模仿香港,骨子里却在模仿北京,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座有精神分裂症候的城市。”⑤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72、73、363-364、363、9页。如此精准到位的分析,确实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我们甚至可以根据“顾明笛”的活动轨迹,绘制出一张张局部的立体的具有方向感的城市地图,比如2005年10月的一个周日,顾明笛前往张薇袆家中的路线;他到《时报》面试后,游历北京的路线;2011年2月8日,他和裴志武到广州投奔施越北,施越北载着他们奔向目的地的路线,都可以绘制出地图。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张柠是一个方向感十分强的作家。而我认为这是写好城市题材小说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本领。如果一个人没有方向感,那么他在城市的迷宫中一定会迷路,他对城市的认识一定是不完整的,是混沌的。
但也不是没有疑惑。刚开始阅读的时候,觉得张柠或借助顾明笛的思考或借他人之口对城市进行大段大段地介绍,有贩卖知识之嫌,可当我读完整本书合上书页时,我才意识到张柠的用心。一般而言,在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作为地理和物质层面的城市,都只是烘托主人公的背景,是为主人公服务的,不宜大肆动用笔墨,否则有喧宾夺主之嫌。但在《三城记》中,张柠对城市景观的描绘,对城市性格的分析,对城市文化的认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正是张柠对“北上广”“三城”文化的呈现与比较,丰富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内涵。“三城”文化与顾明笛在三座城市的生活、工作与恋爱的故事主线,共同构成了一部驳杂而又多姿多色的“三城记”。我认为这是《三城记》作为中国新城市文学一个最新样本的题中之义。
张柠要呈现的文学意义上的“三城记”,与现实中作为标志意义的“北上广”一样,同样是一个开阔的、多元的、丰富的,具有生长性和无限可能的空间。
二、塑造具有“多余人”特征的时代新人
作为一部描写80后精神成长史的长篇小说,我更关心张柠到底塑造了怎样一位主人公。
出生于上海的顾明笛,衣食无忧,大学毕业后很顺利地到了东山公园管理处工作,与父亲顾秋池在同一单位上班。不同的是,父亲的工作是种树浇花,他是坐办公室。父亲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但顾明笛认为每天的生活毫无意义,完全是浪费生命。他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够摆脱那些熟悉而无聊的面孔、表情和语言”⑥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72、73、363-364、363、9页。。最终他在乌先生“行动哲学”的鼓舞下,辞职离开上海,北上北京,入职《时报》专刊部。见习期结束后,顺利转入深度报道部。因为与裴志武调查“沙漠污染”事件被打而一举成名,同时也受到了报社的处分;紧接着又因准备调查东部某大型水果种植基地的污染情况而被调到文化新闻部。他在新部门干得风生水起,却也麻烦不断,最终因一起灾难性事件而辞职。在程毓苏副教授的建议下,经过备考,考上了B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攻读中国现代思想史,却又因为论文开题报告和感情问题而导致情绪激动被学校送进“安定医院”,导师要求将其开除,最后在母亲的争取下休学一年。休学期间,他和裴志武南下广州,投奔在此创业的施越北,遇到日后将再一次让他面临重大人生抉择的劳雨燕。
可以说,在《三城记》中,张柠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时代新人形象。顾明笛之所以离开舒适的工作岗位,北上北京,南下广州,是因为他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富有正义感,心高气傲,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敏感而且真诚”,“是我们时代的稀罕物”。同时,他的身上患有典型的都市病和现代病。正如《时报》专刊部柳童对他的评价:“尽管你看上去很有个性,但你身上同样有这个时代青年的通病,就是‘小资情调’。这种小资情调是都市精神症候的典型表现形式。对于古典时代而言,它或许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它的局限性则暴露无遗。比如自我意识太强,过于自恋甚至自私,太在乎自我实现和自我形象,因而没有合作精神和牺牲精神。”①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正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他的“不谙世事、认死理儿”,所以在《时报》工作时不按行业潜规则出牌,收了红包却不发稿,被举报,落了个留报察看的处分;攻读博士期间,因观点与导师相左,论文开题报告迟迟不能拿出;到广州后,急于想与施越北谈论调整网站思路的事情而适得其反。
从这个意义而言,顾明笛的所作所为无疑具有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典型特征。他在攻读博士期间也一再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多余人,走到哪里都多余”②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我最近有点迷失了似的……到处都令人失望,自己也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但又如他自己分析的那样,“19世纪的俄国文学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型的人,可人家那是自以为多余的悲观论者,我这里是别人把我当多余的人,谁都可以对我视而不见,忽略我。”③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顾明笛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比“多余人”要丰富得多。他在写给张薇袆的邮件里坦言,“我提前一个月来到这个世界,从小体弱多病,长大后有嗜睡的毛病。特别讨厌的是,我坐着就打瞌睡,躺下就醒了,失眠也是常事,后来我就习惯睡在睡袋里面,会感觉踏实一些”④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他的生活离不开睡袋,而且养成了一个古怪的习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钻进睡袋睡觉,或者有跟人拥抱的隐秘冲动。在他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时,他的母亲竺秀敏为他准备的行李箱,除了“吃的、穿的、用的”,“还有两个睡袋,厚的和薄的各一个,北极熊牌,温标、材质、体感都是一流的”⑤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正是因为这样古怪的生活习惯,以至于他打量这个世界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睡袋。如他到《时报》报到后,坐在小方格里的桌子前,对那个大约两平方米的半封闭空间产生了好感,他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竖起腰杆能够看到其他人,往下弯腰便消失了,谁也看不见你,就像钻进了睡袋一样。”⑥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而且这种习惯影响到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恋爱。他恋爱,可能就是为了寻找一件睡袋的替代品。譬如他在何鸢的宿舍与其“云行雨施”之后的那几天里,“他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前些日子积下来的那些大烦恼和小烦恼,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都暂时丢在了脑后。他连睡袋也不要了,晚上往床上一挺,直接就面带微笑进入了梦乡。”⑦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按照精神分析学观点,他的这些表现属于不折不扣的“俄狄浦斯情结”。
张柠在“卷四”中对顾明笛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恋母情结”有所分析:“按照心理分析学的观点,睡袋应该是母体的替代品。它是一个由物质制造的精神假象,导致依赖者的精神变态。最明显的症候,就是有‘恋母情结’,其实就是返回母体和子宫的冲动。要摆脱睡袋依赖,就需要另一个‘母体’,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回忆之中的。在顾明笛接触的女性中,最有可能替代的,就是何鸢,但阴差阳错没有成功。最近,他的心理又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对劳雨燕的依赖已经萌芽,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感正在破土而出。”⑧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310、314、36、81、96、309、422页。
具有“恋母情结”的人,肯定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张薇袆发现顾明笛的标准坐姿,就是蜷缩在沙发里。再小的沙发他都能蜷进去,然后抱紧自己的双肩。事实上,他的这个坐姿,也正是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标准姿势。对此,张柠有一个神来之笔。在一次沙龙结束之后,由于时间太晚,张薇袆到顾明笛处留宿。第二天清晨,张薇袆惊讶地发现不算宽敞的床上,竟然还摆着一个睡袋。顾明笛醒了。张柠借助张薇袆的观察如此描写顾明笛接下来的行为:“他像小孩子一样钻出来。”①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4、161页。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忍俊不禁。
作为一个在精神上没有长大的孩子而言,顾明笛的恋爱史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我本来挺看好他与张薇袆的恋情,可哪里想到,就在张薇袆像个幸福的家庭主妇那样,为他精心烹饪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他却逃跑了。原因很简单,“面对张薇袆烹制的一桌美味,顾明笛却看到了日常生活对自己的吞噬,看到在庸常中沉沦的自己的身影,看到衰老、终结和无意义,并由此而焦虑不安”。“他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过那种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小日子。他还怀抱着憧憬和希望,想要过一种目的不明的、随性的、混乱的、充满了冒险精神的生活。”②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4、161页。那么,他在此之前,为什么要邀请张薇袆到他家里留宿呢?
到北京后,与彭姝朦胧的情感,因为一次有关爱情的讨论而产生罅隙。就在彭姝与程烟分手后,顾明笛又不知所以地将彭姝教训了一番,终致隔阂难消。与何鸢激情相遇后,他一周不曾露面,被何鸢“判死刑”,而他居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不仅如此,他还将原因推到何鸢身上。
如此糟糕的情感经历,加上论文开题报告的影响,让他一边经受失眠症的煎熬,一边考虑着严肃的重大事情:我能做什么?我爱什么人?事实上,他的这些表现,正是张薇袆对他做出的宣判:爱无能。他的大学同学万嫣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她说顾明笛“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有很强的自卑情结。你总是觉得所有的女人都瞧不起你,因此你想在女人身上得到‘顾明笛很棒’的结论。一旦得到确认,你就觉得索然无味,然后不顾一切撤离。”③张柠:《三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4、161页。他抱紧双肩蜷缩进沙发的姿势,正是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现。
这一切的问题,直到他在广州遇到劳雨燕之后,才得到了改善。而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历许多事情,相对以前要成熟稳重不少,对恋人也产生了责任感。完成了一次内在的蜕变与成长。
另外,张柠在《三城记》中写到了众多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像竺秀敏、顾秋池、张薇袆、汤明、乌先生、施越北、裴志武、彭姝、柳童、徐苏力、唐婉约、程烟、刘炜阳、杨菲、何鸢、夏慕春、童诗珺、程毓苏、卫德翔、谭东亮、朱志皓、劳雨燕等等,都各具鲜明性格,而且面目清晰,就连“惯例酒吧”文化沙龙成员和郝家堡工友夜校的成员,都各有性格与出处。可见张柠确实是下过一番苦功,做足了案头功夫,也得以窥见他的写作野心。
身处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如何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面孔,每一个人的出处,正是文学要做的事情。张柠以他对文学的理解和尊重,做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而言,他是一位身怀普世价值的作家,《三城记》也因此而超越了单一作为城市文学或是成长文学文本存在的价值。
归根结底,《三城记》是一本描绘世情与书写人性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