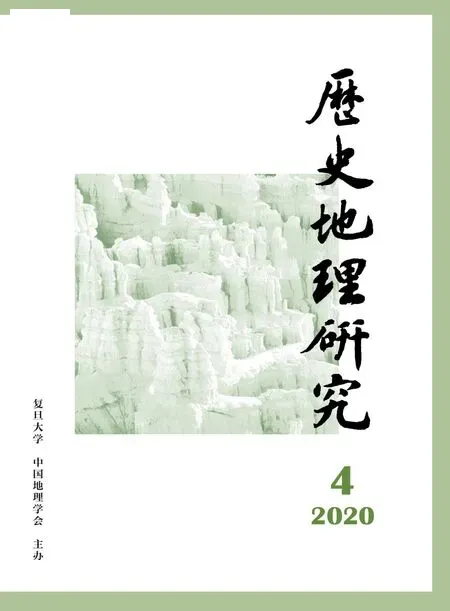《椿庐史地论稿续编》选读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2005年,邹逸麟先生论文集《椿庐史地论稿》出版,奉王振忠教授邀约,我写了一篇读后感,较为系统地汇报了研读先生论著的感受、心得以及从先生论著所受到的启发和学习到的方法。先生辞世时,疫情尚未结束,不能前往沪上和先生告别,连追思会都无法参加。人生无常,本是世间常法,先生走得体面尊严,哀痛之辞,不必多言。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或者正是研读先生的论著,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沿着先生指示的方向,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下去。所以,我把手边所有的先生的著作集中起来,摆在书桌上,一本本地摩挲翻阅,回忆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那些文章再读过,重温当年曾体会到的先生的教诲。
读《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的时候,我还在师从李涵先生读辽金史。1987年秋天,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考察团,到赤峰等地去考察,跑了宁城、翁牛特、林西、巴林左右旗等地方,看了辽中京、上京、祖州等遗址,对西拉木伦河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李涵老师当时正在研究辽金时代的奚族,奚族的农业生产正是她所关注的一个方面。邹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在《辽金史论集》第二辑里,我记得大约是在1988年夏天(或者更晚)才读到的。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中使用《辽史·地理志》的记载,讨论上京、中京道各府州县汉、渤海人的分布。先生说上京、中京道三十余万汉和渤海的人口大多集中在灌溉和土壤条件比较好的河流中上游地区,我就想起在宁城辽中京城故址看到的大片玉米田,以及贾敬颜先生站在西拉木伦河桥头上指点山川的情景。当时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读《辽史》之《地理志》《兵卫志》《营卫志》的札记,是从陈述先生《契丹政治史略论稿》中关于汉人移民垦殖草原的路子出发的,模仿的是贾敬颜先生五代宋人使北行记疏证(当时是单行的油印本)里的方法,也参考了邹先生区域开发的分析方法。那是婴儿学步级别的作业,早就没有价值了。但我也一直没有舍得丢弃,后来以它为源头,写成了《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乡里制度及其演变》一文,直到2019年才发表出来。拙文中关于临潢府所属各县汉、渤海户口来源、居地与管理的分析,最初即来自邹先生这篇文章的启发。
读《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时,我正在汉水中上游考察。先是沿着汉水两岸,后来溯着丹水、堵水、金钱河(甲水)等支流,走向郧西、淅川、竹山、竹溪、柞水,进到山里。我想去看那里的山、水、人家,去看祖祖辈辈在那种艰苦环境下生存的人。那段时间读的基本史料是严如熤的《三省边防备览》;主要论著是赖家度先生的《明代郧阳农民起义》、傅衣凌先生关于闽浙赣山地经济开发的研究,以及萧正洪先生关于清代陕南种植业分布与演变的研究。邹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复旦学报》上,我是在无意中读到的,对其中的第二节《流民的生计》与第三节《环境破坏》印象深刻。将移民进入、经济开发与环境变化(特别是恶化)三者联系起来的思想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方法,但论者一般使用“经济开发”或“地区(山区)开发”,很少使用“生计”这个概念。邹先生这样提出问题:“连续数百年,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进入鄂、豫、陕三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究竟何以为生呢?”这个问题伴随了我很多年,可以说,在2000年前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在有关汉水流域的研究中,我使用“生计方式”的概念探讨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生计方式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生计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不同影响,虽然思想方法上的来源是多元的,但邹先生的文章确实是较早的源头之一。
《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一文,最初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一整版,我是在武大历史系资料室的《光明日报》上读到的。那年长江流域大水,我们在武汉更有切身的体会。邹先生说:“这场洪水无疑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它表明改善我国生存环境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是当时政府、社会与学术界的共识。在这篇文章里,邹先生简要地回顾了我国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分析了洪涝灾害越来越频繁、严重的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面对洪灾,当时舆论以及学术界主流的声音都是指责长江中上游地区过度垦殖、开发造成了植被破坏加重了水土流失,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某种“科学的自然中心论”倾向。我对这种倾向并不认同,可也不知道怎样对待。在文章中,邹先生写道:“如果没有黄河流域的普遍开发,何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汉唐文明?没有宋代以来长江流域围湖造田,何来近千年来高度发展的长江文明?因此我们回顾环境变迁的历史并非为了责备古人,而是想从古人行为的轨迹中寻找对今人有用的经验教训。”我相信这才是学者应持的态度。邹先生又说:“建国以来的前30年,我国人口数倍增长,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新辟耕地,10多亿的人口如何养活?……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我国要保持人口—生存—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平衡,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有时甚至陷于两难的境地。例如,最近我国政府下令禁止砍伐原始森林,强调退田还湖,这都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为当地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这种政策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呢?”20多年后重读这些话,邹先生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的情怀,仍灼然可见;而2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政策及其实践,也仍然在邹先生所说的两难境地里摸索前行。这篇文章很短,当时一口气读完,觉得先生的情怀、才识与智慧尽萃于其中,非常感佩。也因为这个源头,我着意梳理有关人地关系的理论,并努力做些思考,而在思考的过程中,则更着意人类生存的艰难与生计方式的意义。
有一段时间,我侧重于做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江汉平原湖泊演变的研究。关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我主要从谭先生、邹先生等关于黄河中下游河道的研究以及张修桂、周凤琴等先生关于荆江河床演化的研究中学习方法;关于湖泊变迁的研究,则较多地受蔡述明、金伯欣等先生江汉湖群研究的影响。邹先生的《广德湖考》是一篇较小的考证文章,其所考证的广德湖是明州鄞县境内一个不太大的湖泊,而且后来消失了。这篇文章在我摸索江汉湖泊研究的路径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江汉平原上的很多湖泊规模都不大,与广德湖相似,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不多。邹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根据一些零星的资料,将广德湖的具体位置和范围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考察其水利功能,进而分析围绕围湖、复湖的争论与纠纷。这种研究路径给我很大启发,我在考察汈汊湖、沉湖、白露湖等江汉平原较小湖泊时,也基本遵循这样的研究路线。
《〈宋史·河渠志〉浙江海塘西湖篇笺释》和《两宋时代的钱塘江》两篇文章,我读得比较晚。2013年以后,我着手做滨海地域的研究。2017年秋季学期,我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每天从求是校区经过杨公堤到之江校区。黄昏时分散步,就到了钱塘江边,看大江辽阔,潮汐来往,不免生出些感慨,给自己找了个题目: 历代海潮论疏证。因为在杭州,就从燕肃的《海潮论》着手,自然而然地就读到《宋史·河渠志》的相关记载。我这才知道邹先生给《河渠志》的浙江海塘部分做过详细的笺释,早已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想起家里有这一辑,却没有注意过,真是不应当。于是我对照着几种《临安志》以及地图,认真地读了。邹先生的注释非常精审,论断确然可信,揭开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给我指示了方向。如邹先生说,钱镠筑海塘时所立的三个刻有水则的铁幢,一在今候潮门东南旧便门街东南小巷,一在旧荐桥门(今城关巷北口)外,一在利津桥(今南星桥东)北。邹先生说:“据铁幢的方位,吴越时海塘位置大致可知。”我根据邹先生的指示,去看了上述三个点,遥想昔年钱塘海塘的位置与图景,虽然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仍然可以捕捉到某些历史的信息,觉得非常高兴。记得那天下午,从南星桥沿着中河,一直走到了钱塘江边,穿过老钱塘铁路桥,回到之江校区,心中除了沧海桑田的感慨,也充满着对邹先生的感佩。
我没能有机会做邹先生的学生。20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历史系,特别是古代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1996年后改称“历史地理研究所”)遴选博士生导师、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好几次都是请邹先生给予帮助。那时我给石泉先生和各位师兄做后勤服务工作,所以一般是我负责接送,其实有不少机会接触先生。只是年轻无知,又自惭形秽,并不敢和先生多说话。一直到2009年秋,复旦史地所给我两个月的驻访学习机会,我住的离邹先生家很近,经常在路上、食堂和史地所资料室遇见先生,更承先生赏过两次饭,才有机会较多地聆听先生的教诲,领略先生的言谈风采。
我自己的研究题目都比较小,和先生曾参与、领导的大型研究项目隔得比较远,所以研读先生的论著多是与自己研究相关的单篇论文,对先生的学术体系并没有系统地学习,更谈不上全面理解与认识。我所读先生的一些论著,在先生的学术体系中也可能并不是重要的部分。回想起来,自己学习、研究的每一步,又都从先生那里汲取过营养,得到过启发。我想,先生虽然不在了,但先生的学问在;先生的学问在,先生就永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