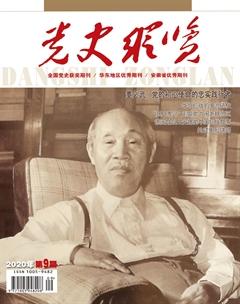“兵工泰斗”刘鼎助力闽浙赣苏区
陈家鹦


1931年,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等国统区的斗争形势迅速恶化。193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大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刘鼎,这位后来被誉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的中央特科得力干部也奉命赴中央苏区。1933年春,当他化名为“戴良”,途经安徽秘密进入闽浙赣苏区后,却被求贤若渴的苏区主要领导人方志敏留了下来,为他的传奇人生又增添一段佳话。
“我们闽浙赣很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啊!”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0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他自幼机灵好动,爱舞弄锯子、刨子、凿子等工具。一只破闹钟,他都反复拆装,乐此不疲。小学时,他对于图画、手工、算术、理化常识就很爱好;在江安的省立第三中学和叙府(今宜宾)联合中学读书时,他对数理化兴趣更浓,尤其喜爱实验。高中末期,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其间,他深受同乡、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孙炳文的影响,进而积极宣传劳工神圣和新文化运动,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3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刘鼎在孙炳文的指引和帮助下,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为追求真理而赴欧留学的朱德。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刘鼎在德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团的书记。1925年,刘鼎转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并兼做翻译,还担任过东方大学中共总支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支部的支部书记。从1926年到1928年,他擔任过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报电话等军事课程的翻译。为了做好翻译工作,也为了切实掌握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刘鼎又涉猎军事技术课程,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打下了基础。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途中被阻于苏联远东伯力几个月。其间,他参加了刘伯承领导的远东工人游击队,担任第一中队指导员兼全游击队的武器教员,向战士们讲解枪炮弹药知识。回国后,于1930年在上海中央特科任二科(情报科)副科长。
刘鼎到达闽浙赣苏区时,正逢中央苏区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原闽浙赣苏区红十军被调往中央苏区作战。红军主力离开后,闽浙赣苏区干部奇缺,文武兼备的优秀人才更是无处寻觅。作为苏区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对此十分犯愁。因此,当他得知从上海经皖南转道的刘鼎已在葛源住下,滞留数日后即将赴中央苏区的消息后,便欣喜地前去拜访,希望刘鼎可以留下。方志敏向刘鼎详细介绍了赣东北根据地发展至闽浙赣苏区的艰难历史,并苦苦相劝:“哪里都是干革命,就请留下吧!我们闽浙赣很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啊!”
刘鼎认真听了方志敏的一番介绍,被这位视革命根据地事业为生命的革命家的激情所感染。他联想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与年长自己3岁的方志敏何其相似。他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于是便接受了方志敏的邀请。在征得中央同意后,刘鼎被委以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的重任。
在红大五分校,刘鼎教授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等课程。他旁征博引,将那些枯燥的理论讲述得生动有趣,使这些山沟里的军校学员很快学会了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分析事物,解决问题。他的课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开眼界。日子不长,刘鼎就在学员中获得很高的赞誉。
两件“分外事”,更令闽浙赣苏区军民刮目相看
这年夏季,刘鼎做了两件“分外事”,更令闽浙赣苏区军民刮目相看。
一天,刘鼎从学校讲完课回军区机关,见军区仓库大门敞开,管理员正在整理库存物资。刘鼎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电话机、电线、瓷瓶等器材,杂七杂八新旧都有,便好奇地上前搭话。管理员说:“这都是缴获来的战利品。堆了好几年,方主席不准丢弃,说日后或许有大用处。”刘鼎明白了,赶紧去找方志敏:“方主席,仓库里那一堆电话器材,可以利用起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电话网。”
方志敏早就谋划着建立苏区内部的电话线路,红军每次攻城略地时,他都叮嘱部队,注意搜集电讯器材。几年积累下来,电线、电话机等器材堆满了军区仓库。但因为没人懂行,技术力量跟不上,方志敏也只好望洋兴叹。今天见刘鼎提出这个建议,正中下怀:“戴良同志,这件事我想了很久,苦于没人会搞,你既然有这个想法,肯定懂行吧?”
刘鼎谦虚地答道:“我试试看吧!”
于是,刘鼎从五分校选调了一批学员组成电话队,自己编写教材,对学员进行短期培训,教授他们安装电话、架设线路的技术。随后,他又带着他们施工架线,自己更是带头操作、指导。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率先给葛源的党政军机关及各经济、文化、金融等单位安装了电话,继而扩延到周边50多公里的范围,建成了闽浙赣苏区的第一个电话通信系统。
在讲课之余,刘鼎经常带学员下部队实习。在实践观察中,他发现闽浙赣苏区多丘陵山地,沟河纵横,通信极不方便。有时候,虽然只是一水之隔、两山之间,可传送个信息要绕很多路,走半天。打起仗来,红军指挥员一般靠司号员吹号发令,或者叫通信员跑步送信,但这两种办法在实战中都出现过弊端。另外,军号的音调简单,作战单靠军号发令的话,较复杂的命令就会受到限制,无法传达清楚。此外,吹军号也不利于保密。
1931年5月,红十军从闽北凯旋经敌防区,派出一个排占领山顶制高点,掩护大部队行动。全军渡过河后,军部派了个通信员去通知山顶上的那个排撤下来。可是,这个通信员没有上到山顶,只在山腰吼了几声,没听到人回答,见大队已经走远,就连忙跑了回来,结果造成这个排一半战士壮烈牺牲。无独有偶,1932年8月,出击外线作战的赤色警卫师回师赣东北后,奉命与红十军联合发起贵溪夜战。但原定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营联系不上,司号员吹号也调不来。战后,在一个很远的山沟里才找到这个营。营长说,人生地不熟,迷了路,他也在找大部队,根本没听见集结号响。营长说的也许是事实,但军法无情,结果按战场违令处理。战场通信不畅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这几个事例令刘鼎痛心疾首,他急红军将士之所急,很快为部队设计了一套旗语通信的方法。基本动作是:举起一面旗,表示一点,举起两面旗,表示一横,一点一横可以分别表示两个信号。点和横还可以搭配组合,表示若干信号和军事用语。只要在可视范围内,就可以用旗语发布命令,甚至可以像发电报一样传达复杂内容,不必靠通信员跑路和吹号了。
刘鼎的建议立即得到红军将领的赞同,省委同意实施,方志敏更是全力支持。刘鼎随即在五分校内办了一个旗语培训班,讲授旗语发令和通信方法,培训司号员和参谋人员,使旗语发令在部队中得到普及,应用于战场指挥。同时军号也不废除,需要时以壮气势。这一套办法,很快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
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改变作战计划,组编北路军,以金溪、黎川两县为界,将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划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以陈诚为总指挥,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东区以赵观涛为总指挥,重点“清剿”闽浙赣苏区。赵观涛率6个师、2个旅,将闽浙赣苏区分为4个区,分区堵截,妄图切断我苏区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
一日,敌五十三师来势汹汹,进犯乐平县界首村一带。闽浙赣省新组建的红十军,在乐平红军独立营的配合下,沉着应战、声东击西、灵活机动,运用旗语调动部队,游刃自如,包抄围歼敌1个团,缴获机枪7挺,步枪千余支。其中,八十一团与八十二团配合默契,打得英勇顽强,歼敌缴获最多,被誉为“战斗模范团”。指战员们兴奋地说:“旗语指挥,灵光得很。”
“只有你看见过炮,请你想想办法”
方志敏知道刘鼎在留苏期间学习过军工知识,特意安排他去参观设在德兴县山区的闽浙赣省兵工厂,顺便指导工作。该厂坐落在一个叫洋源的山村,苏区军民习惯地称它为洋源兵工厂。刘鼎在厂长黄令正的带领下,认真查看了兵工厂的生产情况。参观结束后,他赞不绝口,还兴致勃勃地提了几个建议:装填地雷、炸弹的黑火药配方可以改进,提高爆炸力;地雷的形状,可以改成冬瓜型,提高杀伤力;手榴弹的直径适当减小,外壳铸成网状,增加爆破碎片。黄令正一听:这位首长是个内行啊!他连忙按刘鼎说的进行试验,地雷、手榴弹的威力果然比过去大多了!黄令正向方志敏汇报,说戴部长不是一般的懂,而是行家,并补充一句:“我们厂找不出戴部长这样的高手。”方志敏听了,心中暗喜,决定将心中早有的一个打算向刘鼎挑明。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汲取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在苏区周围筑起几万个碉堡,企图一步步压缩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闽浙赣苏区周围也被五六千个碉堡包围。红军作战时,每次遇到敌人的碉堡工事,便无计可施。如苦打硬攻,往往牺牲惨重,令人痛心。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方志敏感到压力很大,他决定调刘鼎到洋源兵工厂任政委,请他组织设计、制造能摧毁敌人碉堡的小钢炮。50多年后的1985年夏天,刘鼎在回忆“洋源兵工厂”情况时说:方志敏同志要我到工厂制造小钢炮,攻打敌人的碉堡。我不是炮兵出身,只是在苏联见过炮,没有造炮的知识和技能。可方志敏却对我说:“我考虑很久,找不着别人,只有你看见过炮,请你想想办法。”
背负着方志敏深切的期望,刘鼎毅然接受了造炮的任务。洋源兵工厂原有技术力量薄弱,主要依靠手工作业生产地雷、手榴弹及修理枪械,厂里连个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而制造小钢炮所需的技术要求很高,即便刘鼎既当政委又当技术员也忙不过来。于是,他从五分校中挑选了几个文化知识较高的学员,搭配几名经验丰富的老技工,组成一支队伍专门研制小钢炮。
按照正常的技术要求,炮管要使用德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可在被四面封锁的苏区,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这些材料!刘鼎绞尽脑汁,以生铁为原料,通过熔铁炉将生铁化为铁水,浇铸成型,等三四天铸件冷却后将心轴取出,再仔细打磨,使管内外光滑。他夜以继日地绘图、制模、翻砂、组装……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带领一班人造出了3门35毫米的平射炮,同时生产出与之配套的铸铁炮弹。
造炮难,靠简陋的设备制造炮弹更难更危险。一次,刘鼎正带人拆除哑弹上的雷管,突然“轰”的一声,他身后钳工台上虎钳夹着的一枚哑弹爆炸了!刘鼎急忙转过身子询问情况,查看受伤的同志伤在哪儿。这时,有人发现刘鼎的裤子上全是血,“戴政委,你那里怎么了?”
刘鼎低头一看,只见鲜血顺着自己的大腿根涌流出来,地面上已积了一大摊血,他这才发现自己也负伤了。这时,他感到头晕目眩,昏了过去。
大家赶忙将刘鼎抬到卫生所去。经检查,发现有一块炮弹碎片嵌进他的大腿肉里,需要手术取出。可是,当时战事紧张,伤员多,军区卫生部有限的麻药已经用完了。结果,刘鼎硬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手术,在大腿上动刀动剪,从肉里挖出了炮弹碎片。
洋源兵工厂研制出的步兵炮,是人民兵工史上最早的一批火炮。在炮弹试射成功后,刘鼎将这些造炮的学员编成一个班,带着参加实战。他回忆说:“第一次我带着他们配合红军攻打敌人的碉堡,打了几发,敌人见红军有炮就跑了。还有一次是炮兵班自告奋勇,在夜间抵近敌人的碉堡试射,打了3发,敌人有死伤。据老乡反映,第二天敌人下山找棺材……”
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一文里这样称赞道:“这里,我要说到我们兵工厂的工友了!他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是令人敬佩!在五次战役中,他们加紧工作,子弹比较以前多造出百分之三百,榴弹多造出百分之五百,迫击炮弹改良了,而且多造出百分之四百。他们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只有一架车床),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又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
后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方志敏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闽浙赣苏区。随着苏区的失陷,洋源兵工厂奉命埋藏全厂的机器设备,遣散工人,于1934年底结束了它的使命。劉鼎等人则转入游击战争,并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刘鼎终于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他奉命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其出色的工作,获得了毛泽东的夸赞:“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刘鼎都担任我军军工部门的负责人,为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鼎曾出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二机部副部长等职,1986年7月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