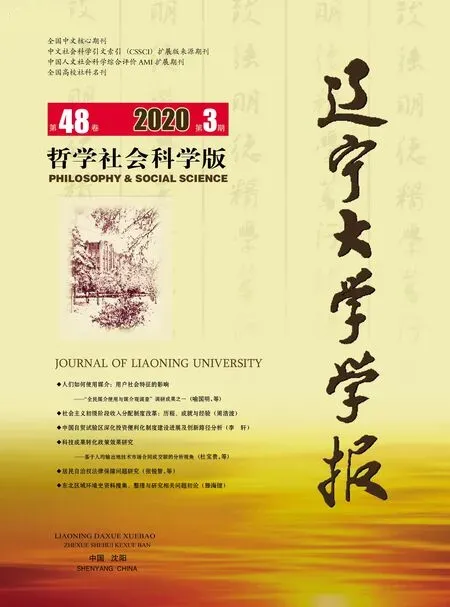论杨绛的作家批评
刘 巍 王亭绣月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作家批评古已有之,近年来却颇有蔚然成风之势,越来越多的作家涉猎批评,其中自有作家本人写作之余的意犹未尽,次有编辑出版的推广之意,亦有为读者阅读阐释的文史资料留存之旨。通常来看,作家批评常给人先入为主的印象——感性成分多、主观体验多、文字优美流畅、风格自然亲切,文采斐然,可读性强。当然也有论者持不同意见,指出作家批评的史料真实性、论说权威性等有待商榷之处。例如文学批评中的作家创作谈,研究者认为作者本人的“回忆”在“证词”和“标准”两个层面上都不具备合法性。只有打破“自传契约”,克服创作谈崇拜情结,才能最大限度地唤回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和创造本质〔1〕。文学批评中“证人的回忆”“自传契约”的误导使批评家难以抵达文学真实、主体真实和社会真实。可见,由于批评主体的人生经历、阅读资源、文学理念的不同,作家批评也有诸多层级和差异,不能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对其探究不失为极富张力的研究命题。
文学批评内涵的普泛导致了它外延的模糊与虚化,因无明确概念界定,似乎除作品之外的关于文学的论述皆可纳入其中。批评无非是这样几层关系: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为何评,评为何?这几层关系的内部及相互之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融入了新的质素。作家批评的身份规定与主体资格本无需强调,作家既是写作主体也是批评主体。依照阿尔贝·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将他所处时代的文学批评大致分类:即时的批评(报刊文学作者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学教授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作家的批评)〔2〕,包括杨绛在内的诸多作家批评都是三者合一的,批评者既是作家,又在大学或科研院所教书,批评文章发在媒体上,所以主体的界限边界日益模糊。从批评对象上看,探讨作家批评不应仅局限于作家所写的学术文章,还应纳入作家的自序、为他人作序、翻译作品的序言、散文等作品中所表达的文学观,只言片语而微言大义;从批评格式上看,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章法整饬的纯学术类文章,也有较为随性的随感体、通信体等;从批评风格上看,有些文章是刻意为之的,有些文章则是自然倾泻的。有的批评较为客观,有的较为情绪化,有的幽默,有的讽刺,不一而足。
作家批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经验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合一,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的合一(作家批评的批评对象包括他自己),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合一,将艺术活动的前端与末端融合在一起。作家批评大致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识评价型的,较为感性的评价类似于在学校教书,作家(老师)以自己的阅读体验告诉读者(学生),某部作品的情节、人物、对话是怎么样被创作出来的,好处是什么,哪些经验可以汲取等等。批评者也是讲故事的人,比如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本来也是她的课堂讲义),几乎就是用她自己的方式把经典讲出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较为深层的评价则有文学史的高度,从社会历史批评的层面给作家作品定位,比如茅盾所撰写的《冰心论》《庐隐论》,胡风的《林语堂论》,是后世编写文学史所尊崇的经典。第二类是生产型或能动型的批评,是接受美学中所谓“理想的读者”所发表的观点,他们不仅具备阅读理解的知识结构,更具备超越普通读者审美常规的期待视野。作家对某部作品的阅读及批评过程中所展现的技巧辨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意义判断能力使作家批评与理论批评有不同特质。特别是,作家们能够凭借话语能力、逻辑能力、形式能力和结构能力寻找到并且填补上原作叙事的空白,成为有创造的批评。毕飞宇《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正传〉》,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等都属于这类批评,取一点可能性或确定性的因由而点染。第三类是形而上意义型的批评,就作家批评而言,这是有难度和高度的批评,关涉文学理论的性质、功能、价值。比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等关于文章价值、作家才性一致的论断;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斯达尔夫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所提出的“自然环境决定论”和“民族精神”学说等,这样的作家批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当然,作家批评的历史源远流长,以上列出的不过是大致的分类,这三类作家批评也是有交叉的,有些作家批评既是知识型的也是理论型的,比如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有些作家批评既是旁征博引,也是情感生发,比如李健吾的《咀华集》,并不是意在评价作品优劣,而是着眼于自身对艺术和人生的个性评价。如他所说,“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3〕
杨绛的文学批评既属于作家批评的范畴,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批评,因她学养深厚、涉猎广博,所以她的文学批评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现有的研究多是关注杨绛的批评本身,她的文学修养、遣词造句等具体问题,这也是现有多数作家批评所呈现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所做的也是“细读”的工作,视野未免局促、琐碎,有创见的观点不多,总归是谈到作家批评时力图寻找出作家的人生理念、研究方法、话语表达等区分度较高的特征,研究价值很有限。
不论从历时的标准还是共时的角度评定,杨绛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不是该领域的翘楚,她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评专家,她实践的是“隐身的串门”。本文以杨绛为例谈作家批评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批评的长度。杨绛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成为研究员,文学研究时长60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背景、话语和标准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与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文学史编撰相比,批评则是轻骑兵和晴雨表,所受影响及其对时代的反作用也最甚,杨绛反而在风潮中保留了批评相对的纯粹。当代文学批评被赋予历史使命,同政治、阶级密切结合,功利性远超于文学性。而杨绛在这时代的变革中似乎是个异数,她的批评文章鲜有政治敏感度。《杨绛文集》共收录20篇批评文章,18篇针对外国文学批评,另两篇为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杨绛极少在公开场合发表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钱钟书除外),她对时代主潮的疏离反而保持了批评的延续性。其二,批评的跨度。这跨度既是文学内部各文体之间的,也是文学形式各语言之间的。杨绛所涉文体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因为有英、法、西班牙等语言功底,她的翻译作品能够在多种语言中入乎内、出乎外。与杨绛略早或同时代或较晚的作家,比如苏雪林、冰心、林徽因、张洁、王安忆、残雪、徐坤等相比,杨绛有着语言融创的优势。其三,批评的融合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各自的特质,作家批评要证明他的知识结构能胜任这份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杨绛年谱来看,她的创作、译作、批评文章形成了循环互证的样态,批评的标准、立场在创作的实践中获得彰显,又反作用于创作。以杨绛为对象考察现当代作家批评的整体风貌、样态乃至范式,既可对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支脉加以梳理,又可以由杨绛文学批评文章中的诸多问题勾连出作家批评之特色及功能指向。
一、作家批评之批评观念的自洽
批评实践受控于批评观念,探讨一个人的文学批评文章,一定要先弄清他的文学批评观念,比如批评家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等特征的看法。没有形成观念的批评只能是单一的、零散的,此文章与彼文章的某些观点甚至彼此冲突,难以自洽也就难以以理服人。自洽批评观念的优点是一以贯之,自我一致、自圆其说,是自我设计的话语系统;其局限是自我超越的难度较大。作家批评通常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过程进行,自我证实观点的正确性,却并非意指他者观点的非正确。作家批评往往首先是作家在认知层面上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和鉴赏,然后经由作家主观情感的移情、浸润,再以文字的形式将其表达,这批评与思想性、理论性的文章相比个性化、创造性较强。杨绛文学批评的“自洽”表现为她的研究对象是可感知的作品、她的评价标准是可理解的理论。
作家批评与学院批评最显著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对文学的敏感与热爱,作家进行的是面对文学作品、面对读者的发言与对话,作家批评是“有感而孕”的批评——是“在作者的头脑中形成一个胎儿,一旦长成,就不得不诞生”〔4〕。作家对作品的感知和对理论的理解既是实践也是理念,是基于审美的共振,而非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辩证。批评多是因事而发,寻找文学依据,而非理论依据;批评性少、描述性多,却也是作家文学观的具体体现。“关于小说,有许多深微的问题值得探索……可是我苦于对超越具体作品的理论了解不深,兴趣不浓……”〔5〕“我暂且撇开理论——理论只在下文所谈的经验里逐渐体现。”〔6〕当然,这并非意味作家批评忽视理论,作家批评有它的自我调适功能,有它的变化生成性。作家批评的理论积淀是前理解,是内驱力,他们同样在文章中探讨“真实”“典型”与“叙述的可靠性”问题,只不过,批评家首先代表个人,读者在批评中看到的不是“巨型读者”,不是经世致用,而是批评家审美个体的差异性感动。这才是所谓“好的批评”,“永远不能是别人的经验和理论的重复,永远是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批评对象实际的交往与搏斗。只有在这样实际的交往和搏斗中才会有我们所说的‘批评的发现’。”〔7〕
文学批评主要以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象思辨的、形象的、情感的特质决定了批评的特质,批评者的审美立场、价值认同与批评对象常常是相契合的,因此研究对象的取舍可见研究者的审美气质。就如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理论、原理和标准是不能在真空中得到的:历史上每个批评家都是通过接触(正如弗莱本人一样)具体艺术作品来发展他的理论的。这些作品是他得去选择、解释、分析并且还要进行评价的。”〔8〕杨绛文论所涉及的对象不论是《红楼梦》还是《堂吉诃德》《傲慢与偏见》,都是经过淘洗的经典之作,而不是某一时期的时尚或流行。“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9〕可见,杨绛的阅读不是顺势而为,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别人读什么自己也去读什么,而是在对文学的历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才选择那些更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来阅读的,并且阅读的时候不是仅仅看重其表面的兴趣,而是更加重视体味其内在的意味。这同时也像擦亮了隔在我们和作品之间的那层布满烟雾的玻璃一样,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批评和写作面对的都是生存与存在、手段与目的,批评家的批评标准常常也是他对自己写作高度的厘定,关乎文学的尊严。比如文学与生活的拟合度或黏合度;比如伦理的困惑,欲望的期许与欲望达成之间的冲突等。因作家自身关于世界、人性和文学的领悟力不同,作家批评有的拒绝判断、有的过度判断、有的偏颇判断。现代以降,文学批评宗派林立: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学批评,引入西学、融通中学,宣告现代批评时代的来临;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以“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为批评之宗;以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化精神批评,“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10〕。中国文学批评的正面传承给一代代学者指明了方向,但它的负面影响便成为蒂博代所谓的不光彩的“作坊批评”,时而是“礼尚往来式”的溢美,时而是“箭林石雨般”的攻讦〔11〕。朱光潜提出关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那么杨绛批评标准是文学审美的,可归纳为这样几个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本体论的批评是理论形而上层面——什么是文学或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或什么是难?关于对话,关于喜剧,关于小说或戏剧的结构布局,比如《事实——故事——真实》等;认识论层面的关涉阅读与欣赏某一作家作品,《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介绍〈小癞子〉》等;实践论的批评,也是批评之批评,《李渔论戏剧结构》《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等,不一一赘述。而那些她不赞成的批评模式,则难以进入“自洽”的领域。“五点文”是杨绛归纳出的1950年代论文的模式,讽刺意味十足,“一九五六年我为《吉尔·布拉斯》译本作序,学写了一篇‘八股文’,我称为‘五点文’……接着摆了五点:时代和社会背景,思想性,艺术性,局限性和影响。”〔12〕实际上,这样的模式在今天的硕士博士论文中依然盛行。
二、作家批评之批评实践的构入性
作家批评的一大特征是,就大多数作家批评而言,作家要先成为作品的一部分,然后才能进行评价。如果将批评的方式简单分为代入式的和构入式的,杨绛的文评显然是后者,她进行的不是一般的置身其外的对象性研究,而是参与其中、构入其中的具有自身主体身份的研究,她与所阐述对象发生的是实证和情感并重的化学反应。杨绛的构入是沈从文所建造的优美、健康、不悖人性的希腊小庙,是李长之的“感情的型”之情愫,而非丁玲般的以文学为武器,要给这社会一个分析,亦非弗吉尼亚·伍尔夫式的理念批评——伍尔夫的批评文章直接演绎她的“主义”。作家批评在构入中将自己与批评对象融为一体,与其一起生成为同一作品。就如日内瓦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布莱所说的“当代批评的特征”:“阅读行为(这是一切真正的批评思维的归宿)意味着两个意识的结合,即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的结合。”〔13〕
作为沟通两种文化及语言的桥梁,翻译者虽有“一仆二主”之难,却也是话语权力的执掌者和文学接受的把关人,就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及经典阐释时说:“这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14〕如果这“中间人”在译介的过程中遮蔽了某些意义,那他就是不称职的。翻译者的批评文章应是参与性的建构态,批评更应该注重的是这一过程的敞开及交融的多向度。我们常说中西合璧,但这是怎样的“合”?是中国的瓶子装盛了西洋的酒?还是像鸡尾酒那样有着比例与配方的多元融合?是否应为多方支流从不同方向涌到一起的泉水,交汇、碰撞然后成为合流。《吉尔·布拉斯》《小癞子》《堂吉诃德》等都是杨绛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她掌握着第一手资料。“批评家是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来阐发作品的异质之处,从而生产出作品在其身又不止于其身的内涵。”〔15〕杨绛在《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一文中详细谈到了“选字”“造句”“成章”等“翻译度”的问题,论述极为细致。对译者而言,批评是翻译的延续,杨绛的批评实践主要表现在为作品作“序”、对版本的考据、对小说流派的命名几方面。
关于序言。翻译者的《序》给我们提供的是间性沟通,《序》常常是读者了解作品的敲门砖,介绍作家作品、介绍写作背景与该书特色等。翻译者在补充、修正、阐释作品的同时也会以他的思维模式确立一种人生观与文学观,可见译者的话语权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解构学家斯皮瓦克论及序言时称:“序言,大胆地通过另外的方式重复和重构作品,展示的仅仅是这样一种已经存在的情形:对作品的重复总是异于作品本身。”〔16〕杨绛在《介绍〈小癞子〉》中说,这部书已经出了五六版了,读者常有这样的看法:“《小癞子》,我读过,顶好玩儿的。”即便是原著作者也说,“就算他(读者)不求甚解,也可以消闲解闷”,但这样的阅读会低估作品的价值。杨绛认为这本书不是消遣的,而是需要深入求解的。她在文章中悉数道来自己的遗憾:“作为译者,始终没把这本体积不大的经典郑重向读者介绍,显然是没有尽责。”〔17〕及下,杨绛如数家珍般介绍了“流浪汉”小说的源流、文学史价值、《小癞子》的艺术魅力等,以印证该书的地位。杨绛在这里进行的是超越了原作品与原作者的工作,“一部小说如有价值,自会有读者欣赏,不依靠评论家的考语。可是我们如果不细细品尝原作,只抓住一个故事,照着框框来评断……那么一手‘拿来’一手又扔了。”〔18〕
关于版本。中国文学批评历来有着“实证”的传承,早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就曾提出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这样一种带有“实证”色彩的批评方式与理念对后代的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的文学批评与诗学批评也采用了具有“实证”特点的“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即便到了近现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以史解诗”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科学精神。杨绛的版本研究可见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实证”之功底。在《〈堂吉诃德〉校订本译者前言》中,杨绛将自己的旧译与原著校勘,分别列举了阿巴叶-阿塞的编著版本、穆里留编著的版本及马林的编注本,并客观地将自己的不当之处加以修改,可见杨绛的考据功底。当代文学批评因为作家作品的切近存在,本不注重这类“知识考古”研究,杨绛这样做就是为了“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不想当“不相识、不相知的人”,更不当“胡说乱道之辈”〔19〕。中国文学界较为典型的版本研究要数《红楼梦》,围绕程甲本、程乙本、甲戌本等版本的研究有大量的相关文章,一度将红学研究推上高潮。西方学者也十分重视版本研究,关于莎士比亚的戏剧的对开本与四开本的探讨就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章。而在电子数字发达的当下,好多作品存在“速朽”的风险,“证史”会使文学批评真正坐实,为文学作品提供完备、公正、客观的备份。
关于命名。能够给某一流派、某一写法、某一体式命名是需要信心和底气的,需要文学理论的积淀、阅读经验的积累和锐利敏感的眼光。杨绛对于某一流派的命名,比如流浪汉小说、意识流手法(详见《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流浪汉小说”的界定,杨绛的观点是,主角必须是流浪汉,故事必须是流浪汉的自述。杨绛从该流派小说的源头推至1499年出版的《薛蕾丝蒂娜》,其对后世的影响延伸至多部作品,但不同国家的流浪汉小说衍生出不同的风格,也就偏离了该命名最初的定义,这也印证了“文体愈推广,愈繁衍,就离原始命名的意义愈泛愈远了”〔20〕。首先从“流浪汉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的角度来说,文学中的流浪汉逐渐发展成无赖、小偷、暴徒等人物群像的集合体,流浪汉的身份与形象已经溢出了原本对流浪汉的角色定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喜爱吹牛的福斯塔夫,这一形象不是严格意义的流浪汉,但是在西方文学史上却被视为流浪汉的杰出代表。其次叙述视角在不同国家的流浪汉小说中也有变化。法国作家萨勒日的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中第三卷第十二章写到了主人公与曾经的恋人萝合相遇,之后的一章专门以萝合的视角叙述萝合自己的故事,这样一来同样也偏离了杨绛对流浪汉小说的定义。在杨绛文学批评较为集中的《春泥集》《关于小说》总计12篇文论中,关于“散文体的滑稽史诗”就占了一半,可见她对于“流浪汉”探讨的持续性。这种“渊源批评”和“演进批评”的研究隶属于创作学或文本发生学的范畴,让我们能够爬梳出作家及流派的写作轨迹。
不论是作序、版本考据还是流派命名,杨绛的批评文章中都有“我”的在场,以“我”的经验积累与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批评像可留存的文献,这无疑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做的历史呈现。“批评就某种程度来说乃是一种总结……它是针对既成事实和历史的……它产生于一种保存、整理、清点和复制某些文献的努力。”〔21〕批评不寻求结论的达成,每个人都有对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看法,批评的价值就是要确保这一看法以及善用它。故而杨绛会在文章中说,“这篇文章总结我翻译的经验。翻译欠妥的例句,都是我自己的。”〔22〕
三、作家批评之取譬连类的批评方法
杨绛的理论资源受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浸染甚深,她的理论储备得益于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及批评主张,她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情感模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深受多重文化影响,这影响以非自觉方式、在更为潜在的层面上传承下来,成为她文学批评的艺术根据,取譬连类是杨绛进行作家批评的重要方法。
取譬连类出自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孔颖达用取譬连类对“兴”作了具有独到性的解读。他认为取譬连类的关键在于“起发己心”,途径在于通过横向或者纵向的联想,旁征博引其他例证进而达到对相关对象的说明。取譬连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常用的说理方式,比如《文心雕龙》中写“赋”,《诗品》中评价潘岳等,都是在诸多作品的比较中凸显研究对象的特质的。“取譬连类”是援引相似的例证说明问题,可达深入浅出,在具体的认识中提炼理论,而不是略过特异性去寻求普遍性。每个作家的批评文章都有独到之处,杨绛的博学修为是别人无法复制的底蕴,她的取譬连类行文流畅、信手拈来、复沓回环,却也有着朴素的质感。取譬连类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接近取譬、对比连类、互文以证。这些在杨绛的作家批评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接近取譬,是指两个或多个文学例证在审美经验、审美思维及审美表达上相接近,由一个文本事实的阅读会引起对另一个文本事实的联想,从而产生相应的审美接受。杨绛在考据元稹《梦井》一诗时,联想到元稹另外一首《江陵三梦》——“古原三丈穴,深埋一枝琼”,并找到了诗人在“梦井”中将落在井里的吊桶,当作埋在深矿下的亡妻化身之悲痛缘由。杨绛从诗人自身体验出发,将深井与深矿、吊桶与亡妻进行类比,勾连了二者的隐秘关联,将诗人的心像感物流转。在《论萨克雷的〈名利场〉》中,杨绛随作者一起浸入那个“唯势是趋、唯利是图”的世界,并由此联想起《镜花缘》中无啓国的故事,指出两本小说皆指向“败坏的人类品性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基于萨克雷对细节的驾轻就熟,杨绛评价他为与巴尔扎克有着相同笔法的“草创者”,真实地展现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段。
对比连类,是指对于性质或特点相反的事物的比较。多种事物在范畴、特征、表达等方面存在相反的特点,人们在认知到一种事物时会从反面想到另一种事物。杨绛在评价柯灵散文的“情”“景”交融时指出:“作者并不像杜少陵那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或陆放翁那样‘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露出诗人自我欣赏的姿态”〔23〕,而是关注“夜航讴歌的舟子”“饥寒温饱的打渔人”“傍岸的采菱妇女”或“沉默的摆渡老人和来往渡客”,将柯灵和古代诗人的抒情内涵形成对比,生动地抒发了作者全身心地比肩于苍茫众生,与他们冷暖与共的真挚情感。杨绛对《红楼梦》的批评另辟蹊径,从《西厢记》《墙头马上》《牡丹亭》男女主人公的一见倾心而提炼出“恋爱速成”的模式,又横向比照到古希腊小说《埃修匹加》《琉席贝与克利多峰》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同样的情节,最终得出“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24〕这一结论。杨绛认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恋爱模式不同于“恋爱速成”的模式,他俩是一见倾心也是日久生情,是“好事多磨”,这无疑给小说作者设置了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25〕,这独特的风格便是因“艺术就是克服困难”而成。由此可见,对比连类在杨绛的文学批评中也有着自觉的应用。
互文以证,是指多文本互以为文,“‘互文性’的基本含义是文本指涉文本,或文本引述前文本。互文性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影响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26〕就是说,互文的发生至少在两个文本之间,单一文本在此种关联中是不存在的,A只有在和B产生间性关联时才有意义。杨绛的互文有显性与隐性之别,显性表现在她对批评对象一以贯之的自觉关注,比如“堂吉诃德”的重读、琐缀、修订,《红楼梦》的偶记与漫谈,对“五点文”的砍余及补充等;隐性互文较为典型的是杨绛关于真实与虚构的论述,发表在《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的《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与《记钱钟书与〈围城〉》先后脱稿,用“事实——故事——真实”小说创作原则以回应当时非常普遍的将方鸿渐等同于钱钟书的看法。“小说里的人物不是现成的真人,而是创造,或者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捏造’,把不同来源的成分‘捏’成一团”〔27〕。故而,这两篇文章与更早些发表的《事实——故事——真实》可视为隐性的互文。
“‘互文性’这一术语作为一种阅读方法,把所有的文本结合在一起,意在找出其中的相似点或不同之处,同时‘互文性’又确信所有的文本和观念都是历史、社会、意识形态和文本诸联系的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8〕既是作家,批评方法的实践自会灌注于创作之中,就如杨绛在《艺术与克服困难》中指出的,“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逼使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使合乎他自建的形式。”〔29〕在论述“事实——故事——真实”三者的关系时,杨绛以史实为依据,引用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中所述:“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30〕,意指虚构的人物也能抵达普遍的真实,也就是莎士比亚所谓的“最真的诗是最假的话”〔31〕,“虚构的事可以依据事实,而表达真实”〔32〕。这种真实——虚构观自是影响了她的创作,在谈到《洗澡》时,她说,“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33〕。杨绛的文学批评不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而是通融练达、温婉平和,是那种能“把书卷气的文雅、精致和口语化的随和、自然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因素相当理想地交融于一体”〔34〕的文字。这“雅”已变成了杨绛不必刻意求之的内在气质。在《洗澡》这部小说中,“雅”成了杨绛那种“聪明”的一种延伸或者说一种实现。“雅”在中国是一种源自上古的文学传统,与那种直面淋漓的“风”传统相反,它代表着一种对本色生活的过滤和修饰,代表着一种不无做作的人工化和规范化〔35〕。可见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的“互文”功力。
批评方法是批评观念的具体运用,是以何种方式实现批评目的的路径。杨绛的取譬连类、互文以证,一方面具体体现了作家批评在经验层面的实践功能,一方面生动再现了写作与批评的同质化过程。文学事实与史实的罗列大大增强了作家批评介入文学理论的具体操练能力,是批评的敏锐性向理论的深刻性迈进之旅。
四、自我平衡的“残瓣”
随着时间的推演,对杨绛的研究难免有些情绪性、趣味性甚至消费性的成分,有些记载过于美化,有些评价又过于失实,这两极都背离批评的初衷。作为批评之批评,本文亦应客观地指出杨绛文学批评亦有缺憾,以使研究跳出研究对象的体系而观之。
杨绛对自己文章入集的删改显出她守正之不足力。中国文人历来有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自我平衡心态,这心态使杨绛难以将个性保留至极致,而使其像李健吾式批评般“灵魂在杰作间相遇”,或像残雪般将文学批评视为沟通自己和经典作家的“灵魂通道”〔36〕。1957年,杨绛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本有上、中、下三部分,写斐尔丁的小说理论、小说实践。杨绛的评说运用了体验批评、比较批评和实证批评等方法,是她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代表作。然而,1958年,文章被扣上“人性论”“资产阶级写真实论”的帽子被批判,说她“歪曲贬低了斐尔丁作品的意义”“介绍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37〕。杨绛对此并无太多辩解,只在《将饮茶》中戏谑地描述她瞥见自己的“头衔”——“资本主义学者”的心态。在1979年出版的《春泥集》和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中,这篇文章都只保留了“上”,被称为将“一朵完整的花摧折成‘残瓣’”。这固然是她对那段岁月的讳言,是她将一切了然的心态,却也是她批评生涯的遗珠之憾。
杨绛的批评中,感知和理解甚或掩盖了价值判断,难免限制了研究者的格局。就如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小引》中所揭示的杨绛在叙事上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小”:“‘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38〕“小”实则并不妨碍“好”,刘熙载就在《艺概》中说过“虽小却好”的话,但如果只注重小处,而无法将“点”置放到更广博的网块之中,也就显出“自洽”的闭锁。巴赞在《作者论》中指出,“作者论”是“选择个人化的元素作为相关的尺度,然后将其持续永恒地贯彻到一个又一个的作品中”〔39〕。杨绛生前将她的作品有目的地择录,《杨绛全集》并不“全”,而是她对自己的一份文学总结。一如钱钟书1990年前后在给江苏一位出版社编辑的信中所说:“……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40〕这倒也无妨,评说身后事。实际上,关于作家批评的研究,重要的并非各自的个性,而在于他们的共性,即作为一类批评,他们正视写作的难度,他们所能企及的高度,以及他们为文学批评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