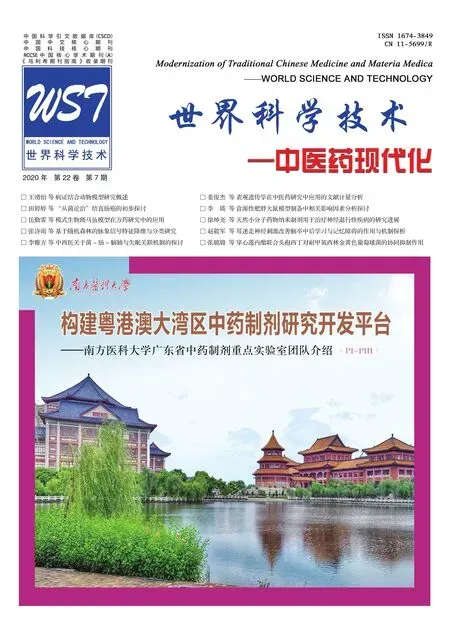耳迷走神经刺激改善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作用与机制探析*
赵敬军,王正辉,周立群,张金铃,荣培晶**
(1.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2.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 453100;3. 北京中医药大学武当医学研究院 北京 100029;4.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学习与记忆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状,可持续多年,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卒中后1个月认知障碍的发生率为28%,3 个月可达35%~55%。许多脑卒中患者在恢复后期存在明显的认知功能障碍,尤其是学习记忆障碍。这些认知障碍对患者的功能独立性有负面影响,而且会阻碍患者如运动等其他方面的康复进程[1],脑卒中的损害不仅仅表现运动障碍,还包括注意力、执行能力、学习记忆、思维、语言等认知障碍[2]。而其中学习与记忆障碍是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一组核心症状,是导致脑卒中持久后遗症的首要因素[3]。
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有关学习与记忆障碍,归属于“痴呆”“健忘”“呆病”“遗忘”等范畴。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脑为髓之海”,该病应“从脑论治”。现代医家认为,本病为中风后气机逆乱,气血、阴阳不向续接,痰癖内生损及人体阴阳、气血,致使“脑神失养”“神失所藏”而发为本病。
耳迷走神经刺激(Transcutaneous Auricular VNS,ta-VNS),是中医耳针现代化表现形式的一种,是针灸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耳穴定位是根据1958年法国医学博士P·Nogier 的耳穴图演变而来,这也成为现代较早具有代表性的系统耳穴图谱。其实,耳穴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内经”时代已经形成,《灵枢·口问》记载:“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耳与经络的关系在《黄帝内经》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而后世医家也多有应用与发挥,《丹溪心法》记载:“盖十二经络,上络于耳”“耳为诸宗脉客所附”等。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有记载“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脑”,耳与大脑的联系不仅是古代杰出医学家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认知,而且已经被现代的神经解剖证实,两耳与脑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听力上的,还有更加丰富的神经联系,特别是耳甲部的迷走神经,和大脑的诸多核团与皮层具有丰富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4],且有研究表明,ta-VNS对缺血性卒中后的学习与记忆障碍具有显著改善效应[5]。
1 耳迷走神经刺激改善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效应
耳迷走神经为迷走神经的唯一浅表分支,密集分布于耳甲区,国际标准耳穴图谱耳穴中的心,脑等位置代表区即这一区域。该神经发自上神经节后分布于耳郭后面及外耳道的皮肤。因此,基于经络耳部循行与联系、迷走神经刺激及解剖学而发展起来的ta-VNS,具有和VNS 相近的效果。有研究发现,ta-VNS在癫痫和抑郁的缓解上,机制与传统的迷走神经刺激相似,疗效也接近[6-8]。动物实验证实,0.5 mA/20 HZ的ta-VNS 能有效抑制缺血性脑卒中后再灌注损伤[9],且经皮迷走神经刺激可以明显抑制炎症反应并改善认知[10]。
临床试验表明,康复过程中的迷走神经刺激促进了脑卒中患者的学习与记忆功能恢复[11]。迷走神经刺激直接和间接地通过慢性间歇性重复电刺激迷走神经调节皮质下和皮质的脑功能,目前,迷走神经刺激已经被美国FDA 批准用于难治性癫痫与抑郁症,迷走神经刺激正被研究用于脑卒中、心血管系统疾病、偏头痛、儿童自闭症等[12-13]。耳穴与迷走神经的特异性联系被从形态学和功能学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证实[14-16],形态学表明,迷走神经耳支不仅投射到躯体感觉中枢-三叉神经脊束核,而且还有纤维投射到内脏感觉中枢-孤束核。电生理学方法,研究了耳迷走神经刺激和躯体穴位对孤束核和迷走神经背核放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ta-VNS 能更好地激活孤束核和迷走神经背核神经元放电,因此,研究认为耳甲区神经调控效应与迷走神经活动密切相关,这为研究ta-VNS 改善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建立了神经科学基础。
2 耳迷走神经刺激改善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机制
2.1 耳迷走神经刺激促进突触可塑性
突触可塑性是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突触传递效率增强或减弱的现象,突触可塑性对神经系统疾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可塑性,神经系统形成精密的环路结构。突触可塑性为很多学习,记忆和发育模型提供了神经环路基础,也为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和可能,突触前、突触后机制均可以影响突触可塑性。突触可塑性主要有:短时程突触可塑性和长时程突触可塑性。大多数形式的短时程突触可塑性,是由短暂的活动爆发引起的,这些活动导致钙离子在突触前神经末梢中短暂聚集。突触前钙离子的这种增加反过来通过直接改变构成突触小泡胞吐作用的生化过程而导致神经递质释放[17],短时程增强(LTP)和长时程抑制(LTD)是突触的学习记忆活动在细胞水平的生物学基础[18]。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Neurotrophin-3(NT-3)等都被证实与脑卒中后突触的可塑性有关[19]。而迷走神经调控可以有效改变突触可塑性,研究表明,迷走神经刺激可通过减轻脑线粒体功能障碍,改善脑胰岛素敏感性,减少细胞凋亡和增加树突棘密度来减轻肥胖胰岛素抵抗大鼠的认知能力下降[20]。
有研究显示,在脑卒中早期即开展相应的康复训练或治疗,患者脑功能重组的水平较没有开展康复的患者相比有明显的提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21],这提示脑的可塑性在脑卒中后早期即出现[22],在细胞水平上,记忆形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调节神经元之间兴奋性突触的突触强度[23]。因此ta-VNS 参与脑卒中后的早期干预可能对卒中后认知功能恢复更有意义。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恢复依赖大脑皮层,尤其是海马的功能重组,而皮层及海马的功能重组则与突触可塑性紧密相关,因此,如何促进脑卒中后大脑皮质及海马突触的可塑性是实现和加速学习记忆功能恢复的关键环节,这也是ta-VNS应用于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研究的意义所在。
2.2 迷走神经刺激调节脑功能网络状态
中枢神经系统是迷走神经刺激效应的主要调控部位,随着脑科学的发展,近年来ta-VNS在治疗癫痫、抑郁症、偏头痛、儿童自闭症、心血管保护等,以及对神经免疫网络调节、默认脑网络和消化系统功能调节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表明,经皮耳甲迷走神经刺激可以经由孤束核将神经冲动投射到大脑皮层,调节紊乱的脑连接和脑功能状态,改善脑功能网络连接,还通过孤束核等中枢核团介导感觉传导、将神经信号投射到边缘系统以调动脑机制来促进情感、学习和记忆障碍的恢复;迷走神经刺激还通过胆碱能抗炎系统,抑制脑损伤后炎症反应,对脑血管及心血管起到抗炎和保护效应,维持脑功能网络稳态。
迷走神经刺激在缺血性脑卒中,主要通过减弱兴奋性毒性和抑制急性期炎症和调节恢复期的神经可塑性发挥作用。在脑缺血的发病机制中,谷氨酸兴奋性毒性发生在急性期,在脑卒中发生后谷氨酸的过量突触释放可引起谷氨酸兴奋毒性[24]。迷走神经刺激可以减轻大脑皮层微梗塞,并且这种神经保护作用与抑制血脑屏障通透性,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有关[25]。有研究证实:一方面,迷走神经刺激与海马中的谷氨酸释放和神经保护相关[26];另一方面,迷走神经刺激还能调节NO、Ach,NE 和BDNF 的释放,且能使海马的长时程增强[27]。然而,迷走神经刺激依赖性神经可塑性背后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仍不清楚。
3 Eph-MAPK/ERK信号通路在突触可塑性中的作用
红细胞生成素生成的肝细胞(Eph)受体[28]及其细胞表面配体ephrin 统称为Eph 家族蛋白。近年来,Ephs 和ephrins 被发现可能在记忆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人类的长期和短期记忆是通过改变突触神经传递形成的。研究发现,Ephs和ephrins都存在于脑部参与记忆形成的区域,如海马和皮层[29]。Eph 受体和肝配蛋白可以通过调节树突棘形态发生,突触前递质释放,突触后谷氨酸受体运输和谷氨酸再摄取在突触可塑性过程中发挥作用。中枢系统损伤发生后,复杂的病理过程涉及多个细胞成分,目前研究显示先前的各种方法并不能使死亡的神经元及其功能得到恢复。因此,Eph/ephrin 在中枢神经可塑性中的作用,使其成为在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进行干预研究的切入点,Eph/ephrin 双向信号传导在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的大多数区域和细胞类型中表达,发挥不同的作用。Eph/ephrin 复合物介导神经再发生和血管生成,促进神经胶质瘢痕形成,调节内分泌水平,抑制髓鞘形成并加重由损伤引起的炎症和神经疼痛,促进神经修复[31]。成熟的神经元中,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s)的激活是由兴奋性谷氨酸信号刺激的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级联,因此,可能在突触可塑性中发挥作用[32]。
研究表明,Eph/ephrin 在成年脑和脊髓中仍然发挥生理效应,在神经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33],Eph/ephrin 信号通路也是一条可由针刺干预调节的重要信号通路[34]。Eph/ephrin主要在突触部位分布,在大脑皮质、海马、边缘系统神经元的突触部位中普遍存在,Eph/Ephrin 信号通路作用于表达Ephrin 细胞的双向信号通道,其中反向信号传导(reverse signaling)通过Ephrin 激活表达Ephrin 的细胞中的分子信号通路[35]。因此Eph-MAPK/ERK 信号通路可能是ta-VNS 干预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重要作用途径。
4 总结与展望
目前,耳迷走神经刺激用于脑卒中后康复的相关工作处于始发阶段,在传统的经典耳穴领域,耳针是使用磁珠、王不留行籽等采用贴压的方法刺激一定的耳穴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耳穴贴存在认穴不准、使用繁琐、容易导致皮肤过敏等一系列问题,虽然传统耳针的应用范围很广泛,但是相对集中于疼痛控制、失眠改善、情绪管控、以及与消化、心血管相关的内科疾病。使用现代耳迷走神经刺激辅助治疗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临床研究开展的相对较少,不系统,也不够深入。
耳迷走神经刺激用于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康复,还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①现在还缺乏高质量临床研究文献支持,耳迷走神经刺激对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康复到底有什么样的效应,然而目前某些相关研究还只是配合其他康复方法做的临床初步观察,无法观察到其独立的真实效应;②关于耳迷走神经刺激位置问题,经典耳穴刺激心、脑等相关代表区域,目前临床所用一般是基于耳甲区的迷走神经刺激,两者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因此对经典传统耳穴与耳甲迷走神经刺激刺激的关系要搞清楚,且迷走神经刺激与耳迷走神经刺激效应的差异性也要做进一步研究确定。
既往的研究证实,耳迷走神经刺激可以有效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相关症状、改善抑郁症和失眠,对癫痫、自闭症也有较好的治疗效应[36-38]。耳迷走神经刺激能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有效抑制损伤组织的炎症性反应[39],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且迷走神经刺激能有效减低脑缺血模型大鼠的脑梗死面积,改善模式动物的神经功能[40],相关的研究已经有丰富的基础研究数据作为支撑,作为耳迷走神经刺激干预脑卒中后学习与记忆障碍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工作也必将丰富中医耳针的研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