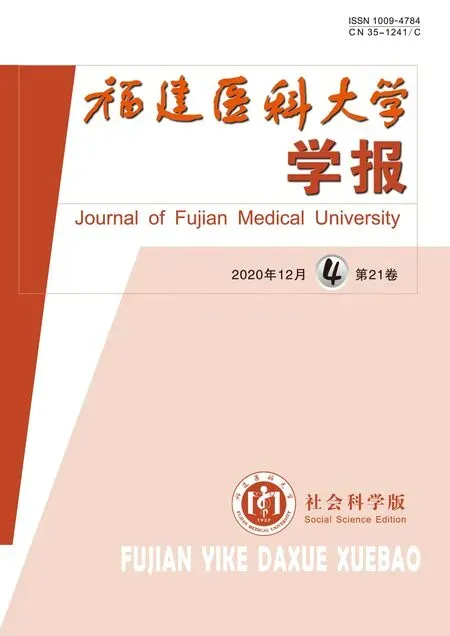大学英语词汇学习中的词性效应:中国EFL环境视角
黄洪志
(福建医科大学 文理艺术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22)
词性及其句法功能不仅是词汇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影响词汇学习效果。学者们认为不同词性对词汇学习的影响不一样,实词与大多数词汇学习问题密切相关,而虚词与这些问题关系不大[1]。目前,词性因素影响词汇学习效果的研究多在国外二语环境下开展;在汉语环境下,鲜有文献实证研究词性因素对外语词汇学习的影响。词性因素在我国外语学习者词汇学习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有必要通过实证方式研究词性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潜在影响。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是否存在词性效应,具体的词性效应是什么;(2)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间词汇学习的词性效应是否相同。
一、词性因素影响词汇学习效果的研究背景
(一)词性因素与词汇语义网络类型建构紧密相关
早期词汇语义研究认为语言的词汇集合具有系统性,集合内各词项间的语义关系与其词性紧密联系,且不同词性的单词组成词汇网络的方式有差异[2]。在后续的词汇语义网络建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在词汇语义网络中名词主要以上下义关系组成树状等级结构,形容词以反义关系组成“哑铃“状的集合和类似名词的等级结构[3-4],而动词的语义组织结构最为复杂,其集合包含以语义增添、融合为主的方式关系形成的语义网络和以词义蕴涵、因果关系、反义关系组成的语义网络[4]。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动词形成的语义结构与形容词和名词的组织结构迥异,结构松散、语义特征复杂,关联不强[5-6]。可见,不同词性的词汇形成语义网络的条理性和有序性迥异。这种差异可能影响相关词汇的学习效率,有序的语义网络便于新学词汇与所在网络建立联系,而结构松散、关系复杂的语义网络则需要学习者付出更多努力来习得词汇。
(二)词性因素与词汇学习负荷大小相关
英语词汇习得研究者认为,词性不同的单词所产生的学习负荷有差异,单词学习负荷与各词性的词形变化和句法功能复杂程度有关,词形变化和句法功能越复杂,学习负荷越大[7-8]。与名词或动词比,形容词的词形变化和句法功能相对简单[9];有些学者认为形容词主要句法作用在于区别名词特征和属性,容易引起学习者注意,有利于习得[10-11];而与名词比,动词用丰富词形变化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以及复杂的句法关系,学习难度大,不利于习得[12-13]。另外,在二语习得中,语际的词类差异越大,词汇学习负荷也越重,越不利于习得[6]。因此,词类的学习负荷不同也预示着词性对词汇学习效果有潜在影响。
(三)词性因素实证研究的发现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词汇直接学习或附带性学习考察词性因素的影响,证实了词汇学习中存在词性效应,但是对具体的词性效应却得出与上述理论预测不一致甚至相悖的结论。有些研究通过词汇直接学习来考察词性因素的影响,认为名词具有习得优势,各词性单词的习得容易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14-21];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动词最易学习,各词性单词的习得容易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22-27]。还有一些研究通过阅读任务考察词性因素对词汇附带性习得的影响,但结论也莫衷一是[28-29]:前者认为名词学习效果比动词或形容词好,副词最差;后者发现在即时测试中形容词学习效果好于名词或动词,但在延时测试中名词学习效果却好于形容词或动词。现有实证研究虽然对词汇学习中存在词性效应达成共识,但是对具体的词性效应仍存分歧。因此,词性效应有待进一步探讨。
(四)词性因素实证研究的不足
虽然词汇的语义网络类型建构和二语词汇学习负荷的研究均提示形容词比动词或名词具有习得优势,但现有的词性因素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却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来揭示词性因素对词汇学习的具体影响,词性效应结论不一致是否与各研究的实验条件控制差异有关:(1)实验条件不匹配。无论是直接或附带性的词汇学习,许多研究存在实验材料的匹配条件不对等,在单词频次、词长、测试词数量以及是否为单一词性等方面匹配程度差异较大[16,21,25,28-29];有的研究被试或测试词数量偏少[18,21,23,25]。(2)实验材料呈现方式不同,有的呈现方式的科学性存疑。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的实验材料以词对翻译学习的方式呈现,一些学者通过分析语料错误来考察词性对词汇学习效果的影响[22],也有一些学者采用选词填空来考察词性对词汇学习的影响[26-27]。这一方式是否能够反映被试实际的词汇学习过程有待考证。(3)语际同源的干扰。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在拼音语言的环境下开展,测试词选择无法排除一语/母语与二语间存在的音形相似、语义同源以及词类词形变化复杂程度差异等因素对测试结果的潜在干扰。另外,这些实验设计差异和语际因素可能共同干扰词性因素对词汇学习的作用,以致无法对研究结论进行横向比较,并对词性因素在词汇学习中的作用给出明确结论。
有鉴于此,有必要改进上述研究设计中的不足,同时避开母语与二语的语际同源干扰。本研究选择中国EFL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充分利用汉语与英语的文字形态差异,从而避开母语与二语的语言类型相似所产生的相关潜在干扰,选择相对匹配的英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类词汇,考察词性因素是否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学习。
二、研究设计及过程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单词词性(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为自变量,词汇学习效果为因变量。影响词性效应的潜在干扰因素控制如下:一方面,选择匹配条件相当的测试词,包括词长、词频、单一词性和测试词数量。由于单词音节长度不等,本研究把测试词的音节长度分为双音节和多音节(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两个水平加以控制。在此条件下,分别选择相等数量、词性单一的单词作为备选测试词;检查测试词的词频匹配,确保词频匹配无差异。另一方面,选择基本同质的被试,包括类似的学习英语经历和大学英语教学环境等。为了进一步排除被试外语水平对词性效应的潜在影响,按被试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择最高分35人为高水平组,最低分35人为低水平组,考察这2组不同外语水平的被试在学习匹配相同的词汇时可能出现的词性效应。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2组被试语言水平差距有统计学意义(t=-19.068,P<0.001)。
(二)被试
本研究被试为某医科大学三年级临床专业(本硕连读)的109位学生(男女比例为57∶52,平均年龄为20周岁),这一阶段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使用已经趋于稳定[30]。被试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由中国英语教师授课,无出国学习或短期逗留经历,参加测试时英语学习时间至少为11年;大学英语学习在相同的母语和外语学习环境下进行,由同一位教师使用相同教材和相同的课堂教学方法授课。被试中有103人通过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学习动机强烈,了解英语对自身专业学习和从业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学习环境基本同质和学习策略使用稳定的条件下,同一被试学习匹配相当的测试词的学习效果差异可能由所选的自变量造成。
(三)实验材料
根据研究设计和参加测试学生的情况,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附录词汇表里选词,将该表中标记为1~4级领会式词汇列为备选测试单词。先按照表中标注的单词词性分别建立名词、动词、形容词3个备选词库,剔除有多个词性的单词;在3个备选词库中,分别建立双音节和多音节两个分备选词库;按照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的词频标记对入库备选测试单词进行词频标记,从双音节词库和多音节词库中尽量选择词频相当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各40个,形成用于正式测试的240个测试词。经Kruskal-Wallis检验,各类测试词的词频无统计学意义(双音节水平χ2=3.667,P=0.160;多音节水平χ2=4.663,P=0.097)。240个测试词随机排序在1份测试卷上。测试词分3次(每次80个测试词)对学生进行测试,被试按要求把测试词翻译成汉语对应词。
(四)测试过程及评分
测试卷注明每个测试词词性,以提示被试该测试词词类,要求被试不得借助词典等工具,把测试词翻译成词性匹配的汉语对应词。测试在课堂教学时间内进行,被试有足够时间完成测试项目。测试在2周内完成。为避免被试刻意准备测试,事先并未通知被试有关测试事宜。
试卷按以下标准进行评分:如果被试给出的答案意思正确且词性相符,得1分;如果被试答案出现汉语意思不够准确但词性相符,或汉语意思正确但词性不符,表明被试对所学单词部分习得,如“rigid adj.”翻译为“严厉的” (意思不够准确) 或“prejudice n.”翻译成“有偏见”(词性不符),得0.5分;若被试没有给出答案,该题得0分。
三、结 果
(一)词性效应的总体统计结果描述
在统计分析之前,被试的词汇测试结果经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双音节和多音节水平的各类测试词学习成绩均满足正态性(P=0.200);经过方差齐性检验,不同词长和不同词性单词的成绩具有方差齐性(分别为P=0.652,P=0.380),说明测试结果有效。SPSS 24.0统计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方差分析显示,词性因素与词长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F(2,648)=2.541,P>0.05;在音节水平上,多音节词汇的学习效果比双音节词汇好,多音节的3个词性水平的均值分别比双音节的3个词性水平的均值高;在词性水平上,形容词学习效果最好,名词次之,动词最差 (表1)。

表1 各类测试词学习效果基本情况表
(二)词性效应比较
词性水平经方差检验、两两比较的结果表明,不同词性之间的学习效果差异不同,其中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形容词与名词或动词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形容词学习效果比动词或名词好 (表2)。
同一音节水平的词性两两比较表明,不同词性之间的学习效果差异不同,其中双音节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音节名词与动词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形容词与名词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音节,P<0.001;多音节,P<0.05);形容词与动词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个音节水平均为P<0.001) (表3)。
(三)不同语言水平被试的词性效应
在分析不同语言水平组的词性效应前,先行考察自变量与各潜在干扰因素间的交互效应。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单词词性、音节长度和语言水平对词汇学习效果均存在显著效应(均为P<0.001);但各因素间无交互效应(表4)。

表2 词性水平两两比较结果

表3 同一音节水平不同词性两两比较结果

表4 主效应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由于各因素间无显著交互作用,可以单独对不同语言水平组进行词性效应分析。Post-Hoc Tests 显示,不同语言水平组存在相同的词性效应,即形容词学习效果明显好于名词或动词,名词学习效果好于动词 (表5~6)。
四、讨 论
测试结果回答了本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即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无论英语水平高低,其英语词汇学习均存在相同的词性效应,形容词学习效果好于名词或动词,名词学习效果好于动词。这一词性效应与一些国外研究发现的词性效应结论部分一致,即名词学习效果好于动词。

表5 低水平组词性效应两两比较结果

表6 高水平组词性效应两两比较结果
被试的母语为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的语言族系。两种语言的词汇有迥异的拼写、形态和语法规则等差异,被试在学习和测试中避免了母语与二语词汇因词形或拼写相近等语际同源效应对学习结果造成干扰。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发现,词性因素与单词词长或被试语言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且测试词的词频等匹配条件相当,可以认为词汇学习的测试结果与词性因素紧密相关。本研究认为这一词性效应与各词类的语义网络结构、学习负荷、以及英汉语间的词类差异有关。
英语形容词的语义网络以反义关系为主,网络组织结构有序,形容词的语义突显,方便学习者识别记忆。Cruse认为形容词的反义关系是学习者最容易理解的语义关系[31]。Aitchison也认为形容词间形成的语义关系特别强,有助于词汇联想和习得[12]。形容词的这种语义网络形成的认知便利也得到词汇学习策略研究的证实。王文宇在研究中发现,二语学习者经常利用形容词的反义关系来学习形容词[30]。与形容词相比,名词形成的上下义关系为主的语义网络所提供的学习便利相对弱一些,而动词形成的语义网络结构松散,词项的语义关系复杂,不利于学习[12]。Lennon认为英语动词的复杂语义成分给学习者造成很大的学习困难,即使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也难以顺利习得英语动词[32]。还有学者认为,动词的语义描述经常要涉及施事、受事、动作和结果,语义结构复杂,语文所以习得难度较大[33-34]。
本研究发现,词性效应与各词类本身承载的学习负荷不同有关。英语中各词类需通过不同的词形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给学习者造成的学习负担大小不一。形容词作为一个词类,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相对简单,只有单音节和部分双音节词汇需要变化词形来表示比较意义,其他音节数的词汇多借助统一的形式表达此语法意义。因此,学习者需要注意的词形加工负担减轻;反观名词和动词,它们通过复杂的词形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名词有复杂的数和属格的形式变化;动词有复杂的形式变化来表达时态、体态、语态、语气和非谓语等句法功能。这些形式变化加重了学习者的学习负担,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名词过程中必须了解名词的确指与泛指,以及相应的冠词和数范畴的语法标记,故而英语名词的学习负荷较重[35]。而动词的句法形式和语义复杂性也加大了动词的认知负荷,使其成为最难习得的词类[22]。
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二语词汇的学习负荷大小与双语的相似度密切相关,双语词类越接近,越容易为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提供便利。本次研究的被试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三种词类在英汉语间的相似度存在较大差异,形成的学习便利度也不同。英语形容词与汉语形容词本质是一致的[36],且在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中共享语义表征[37]。此语际相似性方便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英语形容词;相比之下,这些学习者虽然已经建立起牢固的汉语名词和动词表征,但是英汉语间名词和动词在词形变化和句法功能上却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给中国学生造成明显的学习负担[38]。尽管大多数的学习者知道英语名词有可数与不可数、单数与复数之别,但恰恰在这些方面犯错误[39]。同时,英汉语动词在句法形式变化和语义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动词时最为吃力。英语、汉语动词的语法形式差异源于两种语言的动词概念化方式的系统性差别,英语动词的时态变化复杂对中国学习者而言是巨大挑战;在语义上,英语动词的语义含有丰富的方式语义信息,容易被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所忽视,而汉语动词的语义比较清晰,方式语义借助其他方式表达,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动词过程中必须了解英语动词与语境间形成的语义关系,关注动词的方式语义成分的增添,加工的负荷比较重,比名词更难习得[40-43]。因此,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动词时有较重的学习负担。英汉语词类学习负荷不同造成的学习效果差异也得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研究结果的佐证。桂诗春、杨惠中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中发现,不同水平学习者所犯的形容词错误比名词或动词少,说明与动词或名词比,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形容词的学习效果更好[44]。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词汇学习存在词性效应,形容词学习效果最佳,名词居中,动词最差。这一词性效应与各词类所形成的语义网络结构、词类的认知负荷不同以及英汉语间词类差异紧密相关。因此,为了提高英语词汇教学效率,教师和学生必须了解英语单词的词性,分析单词的语义特征、新学词汇与已知词汇的关系,以便新学词汇能够在语义网络中建立起语义联系,使学生能够有效地习得英语词汇;对于语义网络结构松散的词汇,应该采用增添语境等方法使学生对词汇语义的理解更加清晰,以便于记忆。同时,因为词性习得的负荷不同,词汇教学应该摒弃采用同一种方法来讲授单词,教师有必要设计和采用针对性的词汇教学策略,帮助学生顺利地学习各类英语单词。此外,英汉语词类差异也是词汇学习负荷的来源之一,学生在学习词类差异较大的词汇时应有意识地区别其语义和句法特点,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些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