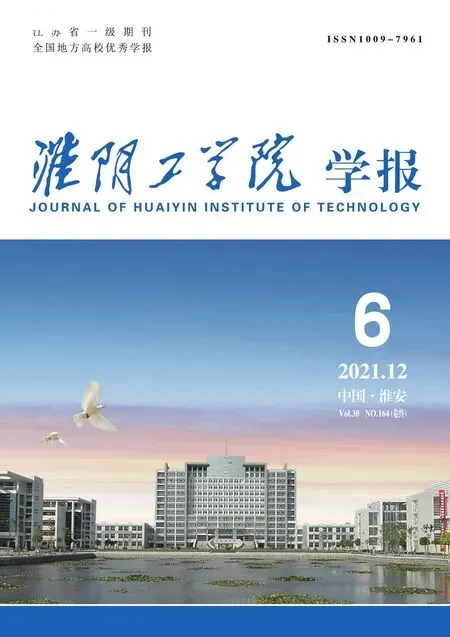谈翻译不确定性的消弭问题
胡庭树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自从蒯因在其代表性名著《语词和对象》(1960)一书中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以来,该论题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持久的讨论。普特南(P. Putnam)称该论题是“自康德的范畴先验演绎以来最令人着迷和讨论最为广泛的哲学论题”[1]159。 至今,人们对此论题依然津津乐道。事实上,翻译的不确定性是针对语句而言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它与指称的不确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论题,但这两个不确定性的交集发生在翻译的层面上,由于指称的不确定性,指称的翻译也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既然如此,翻译的不确定性可以消弭吗?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番考察与探讨。
1 彻底翻译中的确定性
在探讨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之前,先来看一下彻底翻译中哪些翻译是能够确定的。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 又译作“原始翻译”“极端翻译”等,是指语言学家在没有任何译员或翻译手册可资利用的情况下,把一种迄今从未接触过的语言翻译为已知的语言,其依据只能是土著人的言语行为和当下观察到的情景。蒯因的“彻底翻译”思想实验旨在考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刺激条件来把握语言的意义;换言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彻底翻译中,首先能够得到可靠翻译的语句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观察性语句,例如,观察句“天正在下雨”“涨潮了”等。观察句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刺激意义的确定性,也就是在任何场合下都具有主体间的真假自明性。蒯因反对传统语义学中的“意义”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缺乏解释力的,而刺激意义却是蒯因所拥抱的,也是他的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蒯因看来,一个场合句的刺激意义愈是不受观察者已有的背景信息的影响,其刺激意义就愈是逼近它的意义。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一个场合句的可观察性越强,不同说话者之间的刺激意义的契合度便越高,人们越可以凭借刺激意义去进行翻译,因此这类翻译也就越可靠。
这里需要指出的,当语言学家询问土著人“Gavagai?”时,促使他作出肯定回答的是刺激,而不是兔子。严格地来讲,“Gavagai?”的肯定刺激意义应指那些不受观察者背景知识或背景信息的干扰,而仅仅是在当下刺激条件下对“Gavagai?”表示同意的所有倾向的集合。这里所说的背景知识或信息包括近期对附近兔子的观察,对兔蝇生活习性的了解,必要的言语暗示等。例如,土著人通过近期对附近兔子及兔蝇生活习性的观察,仅凭经验对草丛中隐隐一动的兔子的模糊一瞥便能对“Gavagai?”作出肯定回答,但语言学家就很难作如此判断。此外,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光线对观察对象的投射模式也会对刺激意义产生影响。比如,如果光的投射模式只是把兔子极其边缘的部位显示给了观察者,那么就不会促使观察者对“Gavagai?”作出肯定回答。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观察句是指那些观察对象处于观察者最佳位置且不会有任何争议的场合句。但也有一种极端的情形,例如当土著射手清晰地看见兔子的耳朵时,却可能对“Gavagai?”作出否定回答,这是因为兔子不在他要射击的位置上[2]39。可见,彻底翻译中纯粹的观察句是非常少见的。
事实上,彻底翻译中,除了观察句的翻译是相对确定的,其他语句的翻译始终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尤其是理论语句的翻译,因为理论语句独立地看并不等值于任何观察层面的语句,它与观察证据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经验缺口(empirical slack)[3]179,相同的经验证据并不能唯一地确定理论语句的翻译。而检验翻译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要看双方的交流能否顺利进行,要使得交流能够进行下去,从事土语研究的语言学家还得将他听到的土语句子中重叠的词语分离出来,逐一加以语境解释,即诉诸分析假设来编纂“词汇表”或“翻译手册”。总之,观察句是语言学习的起点,是通向彻底翻译的入口,也是理论语句的基础和检验点[4]81。彻底翻译中,语言学家只有先借助对观察性语句的把握,才能逐步扩展到对非观察性语句的翻译。
2 翻译的不确定性
翻译的不确定性是指一个土语表达式可以用两种经验上得到同等辩护的方式(即都符合相关言语行为倾向的整体)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这两种翻译在目标语言中并不是等价的。当然,当语句与非言语刺激的直接联系愈密切,不同翻译之间的差异便会愈小[2]27。
在传统语义学看来,每一个语句的背后都有一个确定的可称为“意义”实体的东西与之对应,因此翻译是确定的。换言之,一个句子有某种意义,另一个句子如果与它具有相同的意义(同义性),那么另一个句子就是该语句的翻译。蒯因把这种未加批判的语义学称为“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转换语言即是更换标签[5]27,于是意义的确定性成了翻译的前提,同义性成了翻译的基础。而根据蒯因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社会的技艺,意义不是精神的存在物,而是行为的属性。语言的功能在于交流,翻译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主要取决于双方之间的交流是否顺利(包括言语的或非言语的)。如果存在意义的话,那也只能是在人们的言语行为倾向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意义,而不是隐藏的内涵意义。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所提供的翻译手册都与相关言语行为倾向整体相符,因而都是正确的,但两种不同的翻译系统之间却是有歧义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这就表明语句(观察句除外)没有唯一确定的意义,不同语句所表达的具有确定意义的命题是不存在的。
蒯因早在他的经典名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就对意义、分析性、同义性等传统语义学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与论证,时隔近十年,又在他的代表性名著《语词和对象》中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具体而言,如果存在意义和同义性的话,对于土著语中的同一个语句S,假设翻译手册A所提供的翻译为S1,翻译手册B所提供的翻译为S2,根据等式的传递性,如果S1﹦S且S2﹦S,那么S1﹦S2,而彻底翻译中S1却为S2所拒绝,换言之,S1和 S2经验上等价(都与相关言语行为倾向整体相符),但逻辑上并不相容(即S1和 S2的真值并不相同)。为什么经验上等价逻辑上不相容的彻底翻译没有对错之分,而日常翻译却有对错之分呢?说日常翻译有对错之分,是因为日常翻译依据的是事先约定的“翻译手册”,而不是当下的言语行为本身,而彻底翻译除了言语行为外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东西,与言语行为倾向整体相符的翻译手册都是正确的。
蒯因在《语词和对象》中将语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词项指称的不确定性笼统地置于“Gavagai”这个例子中加以说明,这确实容易给读者带来误解。但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大写的“Gavagai”和小写的“gavagai”区别。上述谈到,观察句的翻译是确定的,所谓翻译的不确定性是针对非观察句而言的。大写的“Gavagai”是一个独词句,当然也是观察句,其翻译是确定的,而小写的“gavagai”是词项,它的指称是不确定的,可以指兔子、兔子的某个时段、兔子肢体不可分离的部分或兔性等。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即使“Gavagai”作为观察句的翻译已经被唯一地确定下来(如翻译为“兔子”)也不能保证作为词项的“gavagai”与“兔子”具有相同的外延,即适用于同一个对象。也就是说,作为词项“gavagai”的指称是不确定,因而翻译也是不确定的。
3 翻译的不确定性可以消弭吗?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并非是科学理论为经验所不充分决定性的特例,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它不仅适用于意义和内涵,也同样贯穿于指称和外延,那么,翻译的不确定性能够消弭吗?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3.1 分析假设
观察句是蒯因哲学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科学证据的媒介,通向语言的入口。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和学习母语的儿童首先学会的第一批语句便是观察句,而且必须学会表达“同意”和“反对”这样的语言游戏。前面已经分析过,彻底翻译中仅靠纯粹的刺激意义将土语翻译成母语的句子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语句翻译都是以观察句为起点,借助分析假设来完成的。一般来说,彻底翻译的常用方法有两种:一是“询问法”,即在各种不同的刺激条件下,反复询问同一个观察句,以期获得土著人的肯定或否定回答,至于怎么断定土著人的反应是肯定还是否定也是可以通过观察和询问加以解决的。二是“分析假设”。彻底翻译中,语言学家要解决非观察性语句,尤其是理论语句的翻译,则要诉诸分析假设来进行。由于理论语句与观察证据之间存在经验的缺口,观察本身并不能唯一地确定理论语句的翻译,借助分析假设可以弥补这种经验的缺口。那么,分析假设可以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吗?
彻底翻译中,观察句的翻译可以依据刺激意义来加以确定,而对于大多数非观察层面的语句语言学家是无法获得即时共享的刺激来进行翻译的,而只能是记录下这些未经分析的语句,然后借助已有的观察句来加以研究。例如,语言学家会把反复出现在已经分析过的观察句中的片段当作语词来匹配母语中的表达,从而编纂一本关于土著语和母语的“词汇表”,然后利用这些已有的信息去尝试翻译那些未经分析过的语句,这就是分析假设。简言之,分析假设就是建立关于土语单词和母语单词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的猜测。分析假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已经超越了土著人的言语行为倾向所蕴涵的任何内容,从而使得彻底翻译的限度超出了经验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这里需要指出的,猜测和移情在分析假设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彻底翻译中,语言学家和土著人的交往始终少不了猜测和移情的成分;换言之,彻底翻译者始终把自己想象在土著人的生活情境中,假设他们的思维与自己是一样的。可见,翻译手册的形成过程就是借助移情,反复猜测、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检验翻译手册的重要依据就是语言学家能否与土著人进行“顺利交流”,如果在实际交流的过程中,土著人出现反常的表现,如迷惑、震惊,或者其他一些不相关的行为,则表明该翻译系统出了问题[6]8。于是,语言学家还得重新对翻译手册进行分析和修改,直至能够在该翻译系统内顺利地进行交流。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凭借分析假设系统,语言学家与土著人的交流能够顺利进行,那么是否意味着该分析假设能够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呢?
仍以“gavagai”的翻译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根据刺激意义是无法确定词项“gavagai”的正确翻译的,因为“兔子”“兔子的不同生长时段”“兔子不可分离的部位”等具有相同的刺激意义。不过,似乎可以借助土语中表示“同一性”概念的表达式来确定土语词“gavagai”与英语词“rabbit”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或指称,为此,假设“squiggle”是土语中表示同一性概念的词项。在分析假设H1中,把土语表达式“squiggle”翻译成英语表达式“…is the very same as…”或“…is identical with…”。当彻底翻译者在不同的场合指着同一只兔子询问“Gavagai squiggle gavagai?”如果得到土著人的肯定回答,便可判断“gavagai”指的是兔子,而不是兔子的某个时段、兔子肢体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分析假设H2中,把“squiggle”翻译成英语表达式“…is an undetached spatial part of the same extended whole as…”,如果彻底翻译者以相同的方式询问土著人,便可发现“gavagai”指的就是兔子肢体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不是其他。事实上,还可以作出更多的分析假设,每一种假设系统都会对“squiggle”作出不同的解释,显然,“gavagai”的翻译取决于系统对“squiggle”的解释,反之亦然。
上述两个分析假设系统H1和H2都是可能的,对于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而言,每一个分析假设系统都可以在本系统内通过对其他语境中相关表达式的调整而与整个语句的所有可能的翻译相一致,但这两个分析假设系统H1和H2却是互不相容的。此外,土著语言中还有更多的非观察性语句,是无法从经验上加以确定的。换言之,同一个语句的翻译在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中都能够得到同等地辩护但意义却互不相容。可见,分析假设已经超越了土著人的言语行为倾向,并非取决于土著人言语行为倾向中的一种,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就是不同的翻译系统或翻译手册。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不可能进行两次彻底翻译。没有理由并且也不可能要求两位独立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能够提供相互都能接受的翻译手册,两种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都可以与土著人的言语行为倾向相一致。
综上,分析假设并不能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
3.2 掌握双语
翻译不确定性并非是翻译的不可能性,也不是两种语言之间只有一种“正确的”翻译,而是翻译存在多种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是翻译不确定性的要旨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位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将一种语言L1中的同一个语句S分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L2中的语句S1和S2,但S1和S2却具有不同的意义,甚至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S1和S2根据各自的翻译系统又都是正确的翻译。于是,有人就会提出如果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掌握两种语言的话,翻译是不是就可以确定了呢?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宇宙是由原子和虚空组成的,“原子”是宇宙中构成一切事物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原子”在古希腊语言中是“不可再分”的意思)。假定古希腊时期的物理学理论为P,现代物理学理论为P′。在古希腊物理学中,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微粒是“原子”,而在现代物理学中,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微粒是“夸克”。假设用翻译系统T1把理论P中的最小“微粒”翻译为理论P′ 中的“原子”,用另一种翻译系统T2把理论P中的最小“微粒”翻译成理论P′ 中的“夸克”,那么,古希腊物理学理论“最小的微粒是不可再分的”,根据T1被翻译成“原子是不可再分的”(P′1),而根据T2 则被翻译成“夸克是不可再分的”(P′2),其中,P′1不属于P′ 的理论,因为根据现代物理学理论P′,原子是可以进一步再分的,直至分到更小的粒子——夸克,而P′2 属于P′ 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同一个术语“最小的微粒”在两种不同的翻译系统中分别被翻译成两种不同的“不可再分”的概念。再如,理论P中有一个句子S根据T1被翻译成“分子由原子构成”(S′1),同样的语句S根据T2却被翻译为“质子由夸克构成”(S′2),但S′1 和S′2都属于P′ 理论[7]125-129。
那么,上述两种翻译系统T1和T2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换言之,该选择哪一个翻译手册呢?如果两种翻译系统都与土著人的言语行为倾向整体相符,那么无论采用哪一种翻译手册,古希腊哲学家和现代物理学家之间都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即使现代物理学家既掌握现代物理学的理论语言(如英语),又掌握古希腊物理学的理论语言(古希腊语),恐怕也很难确定采用翻译系统T1,还是采用翻译系统T2。可见,认为掌握两种语言便可以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这完全是心理主义语言观在作祟,因为根据心理主义语言观,掌握双语的人心中总会产生一种观念与两种语言中对应的语句相联系,然而,掌握双语的现代物理学家即使找到了心中对应的观念,如分子、原子、质子和夸克等观念,也很难确定是采用T1系统还是采用T2系统,正如把“最小的微粒”翻译成“原子”,还是翻译成“夸克”,古希腊物理学中的理论语句翻译成“分子由原子构成”,还是翻译为“质子由夸克构成”,这并非是掌握双语所能确定的。彻底翻译中,选择翻译手册的依据仅仅取决于最先碰巧发现的那一种[3]180。
可见,掌握两种语言并不能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
3.3 实指辅以询问
实指学习对于从事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和学习母语的儿童来说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最早接触的语句就是通过实指法学会的观察句。蒯因把实指学习分为直接实指和延迟实指两种。这两种实指均涉及到一个概念——实指点,即,手指头首次接触到被指对象的不透明表面的部分。因此,直接实指,就是用手指直接指着某个事物进行解释或说明的学习方法;而所谓延迟实指是相对于直接实指之外的实指,例如,当我们不是指着实物本身,而是指着菜单上的菜肴图片进行点菜时,这种实指就是延迟实指。那么,用实指并辅以询问的方法能否解决指称的不确定性,从而消弭词项翻译的不确定性呢?
当指着一只兔子的时候,同时也是指着兔子肢体不可分割的部位、某一时段的兔子、兔群、兔性等。当指着兔子肢体不可分割的某一部位,甚至遮住兔子身体的其余部位,每一次所指的对象仍然会出现上述几种情况。可见,依靠单纯的实指行为,是无法在兔子、兔子的时段、兔子的不可分离部位、兔群或兔性之间作出区分的。那么,如果实指的同时再伴以必要的询问能否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呢?例如,彻底翻译的语言学家通过向土著人询问:“这个gavagai和那个gavagai是同一个吗?”并伴以多次的实指,这样一来,语言学家能否在兔子、兔子的未分离部分、兔子的时段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呢?事实上,他还是无法解决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因为可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系统,一种系统将一个给定的土语表达式翻译为“与……同一”,而另一种系统却将该土语表达式翻译为“与……有关”。于是,当语言学家问“这个gavagai与那个gavagai是同一个吗?”同时也是在问“这个gavagai与那个gavagai有关吗?”显然,土著人的肯定回答并不能确定“gavagai”的指称。一般认为,意义或内涵是不确定的东西,而指称或外延是确定的东西。事实上,翻译的不确定性既适用于内涵,也适用于外延[5]34-35。翻译的不确定性所暴露的是人类经验的局限性,而不是对蒯因所主张的行为主义的归谬[8]126。
因此,即使是实指伴以询问,还是无法解决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
3.4 个体化装置
既然上述办法均无法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那么,有人可能就会产生怀疑,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是彻底翻译中特有的,因而是无意义的。事实上,即使在母语中,翻译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存在。
既然翻译的不确定性也出现在母语中,那么,能否凭借所熟悉的语法装置对词项的指称加以区分呢?具体而言,看该词项在句子中是否带有冠词或复数词尾,作单称主词,还是作限定语或谓语补足语等。然而,这些标准都要借助母语中特有的语法构造和小品词,以及特殊的个体化装置,而这些个体化装置是相互关联的,也是受翻译的不确定性影响的。换言之,可以借助母语中冠词、系词、代词、单复数等一系列语法装置来相对地确定某个词项的指称,但这些个体化装置是不能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而且也不能由言语行为倾向加以确定。所以,母语中的具体普遍词项与抽象单称词项之间的区别与彻底翻译中兔子、兔子的不可分离部分、兔子的时段之间的区别都面临相同的困境,原因在于具体普遍词项与抽象单称词项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它们的指称对象之间的区别。例如,“white”这个词既可以用作具体普遍词项,也可以用作抽象单称词项,无法借助实指法加以区分。但这个词的两种不同用法所指称的对象是不同的:用作具体普遍词项,它适用于多个具体的对象,而用作抽象单称词项,它命名的是单一的抽象对象。尽管这两种用法可以诉诸特殊的个体化装置加以区分,但是个体化装置本身又是受翻译的不确定性支配的[5]39。
正如蒯因本人所说:“考虑到合理性,我的这个不确定性论题一直是针对原始外来语的,但原则上它甚至也适用于我们的母语[9]48。”可见,指称的不确定性无论在彻底翻译中,还是在母语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即使不谈论彻底翻译中的指称,而仅仅考虑母语中的指称,个体化装置仍然无法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
4 结语
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是翻译的不可能性,相反,翻译存在多种可能性。翻译的不确定性也并非是理论为经验所不充分决定性的一个特例,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论题。它拒斥传统语义学中意义、同义性等缺乏解释力的模糊概念,主张根据外显的言语行为倾向来确定语言的意义。翻译的不确定性不仅发生在彻底翻译中,而且也同样会出现在我们的母语中,通过分析假设、掌握双语、实指兼以询问等方式均无法消弭翻译的不确定性,即使借助母语中的个体化装置,也仍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可见,翻译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