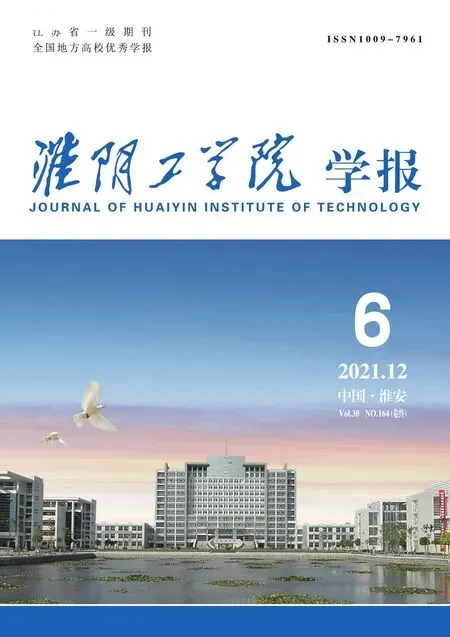《禹贡》“导思想”研究
王 建,徐新强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东曲阜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学文献研究。
《禹贡》是儒家典籍《尚书》中的重要一篇,自草创至今,已逾两千载,期间研究者甚蕃,经学家郑玄、马融、王肃、孔颖达、蔡沈等为其注疏,宋元明清有关著作也是灿若星河,《禹贡》价值可见一斑。历来对《禹贡》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地理、制度、文字、名物的考辨,除此之外,言《禹贡》可以治水也是其研究价值所在,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惟前汉经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1]56。”《尚书》经文尚简不尚繁,《禹贡》篇精炼,凡1194字,于是乎不少学者认为《禹贡》所记九州地理至简而不足以供治水之功用,刘起釪[2]便持此说,“所谓‘以禹贡治河’,这当然是荒谬的。《禹贡》的记载本来就简要,汉代在经常发生黄河灾害的情况下,不顾实际的山川地理形势,却硬要按照《禹贡》所载河道来治理黄河,以图恢复所谓‘禹河’。这是一种愚蠢。”然以《禹贡》或禹贡图治水又的确史有记载,如《汉书·平当传》:“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3]3050。”这句就记载了西汉时平当因为精通《禹贡》而被委任为骑都尉,负责黄河水利工程事宜。又如《后汉书》中对因治河而美誉的王景的记载:“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书[4]2465。”汉明帝赐王景禹贡图以资奖励,王景是治水专家,可见禹贡图对治水还是有所裨益的。关于《禹贡》治水的问题,不能将其贬至百无一用,又不能夸大它在历代治水的功用,它不能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但是它可以作为哲学指导科学治水,正如苏轼所云:“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5]673。”由此看出以前王朝治水系统里的分工问题,水工富于经验进行实际操作,通晓经术的臣子可阐发《禹贡》经文的微言大义作整体的指导。由是观之,《禹贡》与禹贡图是可以对治水作指导的,而笔者以为《禹贡》治水的思想要义在一“导”字,也就是说《禹贡》与禹贡图里是有一种“导思想”的。
1 《禹贡》与禹贡图
《禹贡》,“禹”为此篇经文以大禹治水为背景,水既治,禹依彼时山川形制将天下划为九州;“贡”为九州贡赋,依九州土壤性质分赋税等级为九,又分述九州贡品与贡道。《禹贡》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眼中的“鸿篇大作”,明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下称它为“古今地理志之祖”,后世地理学著作的确大都发轫于《禹贡》。《禹贡》内容可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部分。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大一统思想使中国成为当今之中国,不似欧罗巴般星星点点。导山有“三条”(导岍、西倾、导嶓冢,马融、王肃主此说)“四列”(导岍、西倾、导嶓冢、岷山之阳,郑玄主此说)之说,显示了主要山脉的走向,“三条、四列”之说将自然界随机出现、杂乱无章分布的群岭高山,以大禹的视角予以排列,使之成为行列。导水有导弱水、黑水、河、漾、江、沇、淮、渭、洛,显示了主要河水的分布,其因势利导的理念浸透进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哲学态度里边,又是学者仰追大禹治水假《禹贡》以治水的核心所在。五服有甸、侯、绥、要、荒,是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展示。“三条、四列”之说,以至五服、九州之观念,是对整个九州区域的梳理,其潜在的思想还是古人因势利导的哲学意识。清代胡渭在《禹贡锥指》中将《禹贡》内容归结为十二要义: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可以看出含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因此《禹贡》是不同于神话色彩浓重的《山海经》的,它是体系成熟完备的对远古国家自然政治地理的现实性客观性的表达。
自中晚唐殆至两宋,是儒学的一次“文艺复兴”,儒者归诸元典,讲求经济之学,就如当时于文体上对骈体文的排斥。宋儒开始由实际出发研读经典,加之两宋为边疆外族所累,政治版图朝不保夕,南宋更是偏处一隅,武将力图收复故地,无疑也会刺激文人研究地理之学,而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人文地理学专著的《禹贡》便成为儒者钻研的对象。于是自赵宋始,禹贡学兴盛开来,到清朝时《禹贡》研究则越发为文人所推崇。除却对《禹贡》文本本身的专著,禹贡图的绘制也受学者所重视,两者并行不相悖,且相互促进。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左图右史”的学术传统。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就指出图与书经纬相辅,同等重要,两者不能偏废。唐代虞世南于《北堂书钞》下专条列举了上古地图,宋代王应麟《玉诲·地图篇》也有《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禹九州图》各目,奈何时代太过久远,已无从考证。依《禹贡》所述绘制的禹贡图大抵始自西汉,上文提及汉明帝授王景禹贡图,当时秘府所藏的禹贡图应传自西汉。禹贡图作为古代地图学的重要分支内容不断发展。《晋书·裴秀传》:“秀……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6]1039。”至西晋,裴秀所绘的《禹贡地域图》无疑是达到了禹贡图绘制的最高成就,纵使后世学者诸如南宋程大昌、明郑晓、清胡渭绘制的禹贡图在准确性上亦难望其项背,《禹贡地域图》是有先进的理论支持的,即著名的“制图六体”:“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6]1040。”可惜《禹贡地域图》已失传。 至唐代,贾耽据裴秀的“制图六体”制成以禹贡图为中心的《海内华夷图》,“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7]1786”。这也是禹贡图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可惜也已失传,后来宋人将《禹贡》部分缩绘成《禹迹图》刻于石上,此碑石现藏于西安碑林。
2 《禹贡》“导”字之释义
《禹贡》里“导”字总共出现十二次,多集中在导山、导水部分,从文本上看, “导”的用法与释意可分为三类:导泽、导山、导水。导水又可细分为三类:由某一水开始导,只言水不言山,如导弱水、导黑水、导沇水;由某一山导某一水,先言山后言水,如嶓冢导漾、岷山导江;导某一水自某一山,先言水后言山,如导河(自)积石、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导洛自熊耳。
关于“导”字释义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各家聚讼未决、莫衷一是。许慎《说文解字》释:“导,引也。”导泽之“导”字几无争议,古今学者皆训为疏导、引导、治理之意。
导山之“导”字大体有三种解释,一为“治山通水”。伪《孔传》释:“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8]226。”颜师古对《汉书·地理志》所作注和孔颖达《尚书正义》都沿用此说。二为“刊旅之云”。王夫之《尚书稗疏》:“夫导者有事之辞,水流而禹行之,云导可也。山峙而不行,奚云导哉,然则‘导’者,为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畅茂,下者沮洳潴停,轨迹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导之谓矣。[9]”傅寅《禹贡说断》引张九成《尚书详说》:“山而谓之导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复其本性,随山之势,穷极其首尾,以遂其风土之宜,此言导之意也,岂特导水云乎哉[10]。”三为“循行之谓”。胡渭于《禹贡锥指》下云:“导者,循行之谓。导山犹曰随山。导山时尚未施功,先儒皆以此为通水,曰导山之涧谷而纳之川,殊失经旨[11]339。”
导水之“导”字也有三种解释,一为传统旧注,释为疏导、引导、治理之意,即合大禹治水。二为“溯源”。比至宋代,相较于治水之书,《禹贡》开始被阐释为专叙山川地理脉络之书,因此其导山、导水部分也被从“溯源”角度理解,如南宋蔡沈于《书经集传》下云:“水之疏导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别而详记之,而水之经纬皆可见矣[12]”。三为“循行”。胡渭于《禹贡锥指》下云:“导亦循行之谓,与导菏泽之导异。禹治水或躬亲其事,或遗官属往治之。及九州功毕,其水之大而切于利害者有九,禹舟行从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谓之导,非疏沦决排之谓。先儒皆以导为治。夫治河先积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11]387?”胡渭借大禹治水的施功的合理性,将“导”释为循行,虽能自圆其说,其实是以今之视昔的对不断延伸的解释的再次延伸。
3 《禹贡》与禹贡图的“导思想”
《禹贡》与禹贡图可以指导治水,其治水核心思想就是“导思想”,《禹贡》以经文揭示“导思想”,禹贡图则以图像直观展示“导思想”。其形成的治水模式就是建立在“大禹治水”和《禹贡》、禹贡图基础之上的以“导思想”为核心的洪水治理模式。不管《禹贡》“导”字作何解,其实都是对“导思想”内涵的不同角度阐发。
“导思想”的内涵可由天人观和整体观上概括。远古洪灾频发,是为天灾,大禹以“导”治水,于其中可管窥天人关系。中华文明是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随着“绝地天通”宗教改革的不断推演,古圣哲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上帝之死,语言系统也已经由神话语言转变为哲学语言。《禹贡》里的大禹不是神,是为民请命的圣人,大禹“导”水是制自然而利民的大业,“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13]96”,体现有“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儒家的积极的地理学思想,“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14]126”。“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15]8”人可胜天的先决条件是顺达天意,也就是说要成功改变自然的前提是掌握自然的规律,“导”便是治水成功的规律。《尚书·洪范》记载:“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8]447-448。”可见,禹父鲧用堵塞的方法治水扰乱了五行规律,因而治水失败在流放中死去。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也是“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4]266”“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14]265。”孟子也是讲求遵循天地运行规律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3]5。”
相较于儒家强调人对环境的干预,道家的“不开人之天”不免滞于空谈,对先人从事地理开发有所妨碍。比如两家对待水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老子讲“上善若水”,儒家则讲水是大灾,水灾本是天地运行之常。但大禹以“导”治水也体现有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把“天人合一”归纳为“天人相类”和“天人相通”。其中“天人相类”是讲天人同质同构,庄子的“齐物”“物我为一”即此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6]39。”这也体现了天人一体、天人一源的整体观。儒家也讲“天人合一”,论及两派区别,唐晓峰先生总结得很到位,“儒家所谓‘天人合一’是把自然人文化,以人为本来与天合一,需要时,可以改天换地,用社会价值阐释天道。道家相反,是把人自然化,道家反对以人的欲望支配自然,否则会引发‘灾难’,甚至人文即灾害[17]58。”当然,宋代新儒家因吸收了道家阴阳学说,也出现了相类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张载在《西铭》下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8]15-16。”张载视天地为父母,视人民为同胞,视万物为同类,将仁爱推己及人以至自然万物,如此博爱才会有横渠先生的“四为”之句。水是上古文明之源,大河大江滋养了怏怏华夏文明,人与水理应和谐共生。然水善则养民,水凶则成灾,治水抑灾而保社稷,人水共治而达和谐无疑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主题之一。此外,大禹“导”水“由源及委”,各水所导次序有别,如崔述于《夏考信录》下云:“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于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于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于渭,豫水半归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终之[19]11。”这也体现了一种整体上的秩序观,是整体观的另一个侧面。
4 《禹贡》“导思想”的实践
《禹贡》与禹贡图是历代治水理论化和图像化的成果,《禹贡》与禹贡图的“导思想”是对大禹治水以导不以塞的一以贯之。禹之前的治水者主要是禹父鲧和鲧之前的共工,鲧以“障”治水、共工以堵塞的方法平治水患,皆以失败告终,“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20]103,《国语》记载了昔日共工治水时削平高丘,填塞洼地,结果却给天下带来了祸害。禹之前,先民应对洪水是简单的“水来土掩”而不用“导”,迨至大禹时,治水思路方始改变。而自禹之后,《禹贡》“导水”为后世水患治理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其“导思想”为后世平治水患、兴修水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时期的水患,最早的记载都与黄河有关。因特殊的水质条件和气候条件等因素,黄河自古水患频发,又因其流经地区关乎一朝之命脉,使得治河成为历朝历代不容忽视的大事。西汉哀帝初,待诏贾让上书“治河三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全面的治河论文。其中上策内容是徙冀州之民,决黎阳遮害亭处河堤,使黄河北流入海,这样河西有太行山阻挡,河东又有金堤限制,一月内便可疏导出新的河道。此策被贾让视为保黄河千载无患的最上策,这是《禹贡》“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元至正年间,贾鲁主持治水工程,他主张疏、浚、塞并举,挽河向东南归入故道,疏导出一条经今封丘南、开封北,过东明、兰考之,绕商丘北、虞城南,穿夏邑、砀山之间,自徐州入泗水,由泗入淮的新河道,也就是历史上的疏导而成的“贾鲁河”。
东汉的文学家蔡邕在《京兆樊惠渠颂》下云:“明哲君子,创业农事,因高卑之宜,驱自行之势,以尽水利而富国饶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门起邺,郑国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21]。’”蔡邕在这里提到了我国先秦时期三处著名的水利工程,西门豹所修漳水十二渠、郑国所修郑国渠以及李冰父子所修都江堰,这几人被蔡邕视为“信臣”而推崇,皆因他们深谙治水之道,此道即“因高卑之宜,驱自行之势”,也就是依据地势高下顺应水之就下的习性因势利导,其实也就是《禹贡》的“导”,《禹贡》导水思想对后世水利的兴修影响很大。其中漳水十二渠为战国时魏国人西门豹在邺首创,它是我国最早的多首制引水灌溉大型渠系工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22]3213。”西门豹在破除“河伯娶亲”的无稽之谈后着手整治水利,他依据漳水地形特点,在古邺城以西漳河南岸,利用河道的落差,修筑了十二道引水渠,既能分杀水势减免洪灾,又能溉田养民,历时千载,惠及亿兆,在我国水利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漳水十二渠的实践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导”出了这十二道渠,而不是直线思维的“水来土掩”。
滋养“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更是后大禹时代的“导”思想的直接实践与运用。岷江上游流经的地形为岷山高山峡谷区,故水流湍急且携带有大量泥沙,当经过灌县到达成都平原时水流变缓,导致泥沙大规模淤积拥塞河道,所以成都平原水灾反复。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以去灾兴利为己任,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它的渠首工程包括三部分: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鱼嘴和飞沙堰实现两次分水导流,鱼嘴将岷江之水分别导向内江与外江,外江导水以泄洪,内江引水以灌溉;飞沙堰将内江之水又分别导向外江与成都平原,在满足灌溉的同时又完成了排沙和第二次导洪,两者正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典范。“宝瓶口”则佐证了“治山导水”,相传为李冰用烧石泼水的方式花了八年时间才凿开了玉垒山,即先用大火将山石烧至高温,再浇以冷水,利用温差使山石爆裂,进而才使岷江水流入了成都平原。都江堰综合运用了水力学原理,通过无坝导水实现了防洪、灌溉、排沙,时至今日仍发挥着作用,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可见,都江堰确实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天人观,从而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此外,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部分完美结合、有机配合、协同运作,这又反映了治理的整体观思想。
5 结语
通过导山、导水,从而形成的以《禹贡》、禹贡图“导思想”为核心的古代洪水治理模式对古人治水害、兴水利可谓大有裨益,影响颇深。此外,“导思想”使后人在处理天人之际抑或人人之际时也有所启发。《孟子·离娄》:“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13]162。”孟子说当年大禹治水唯胜在“行其所无事”,意即顺自然之势,其实就是“导”的思想。孟子紧接着说如果聪明的人在治学、修身时能有这种思想,那么他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了。朱熹将孟子说的“利”训为顺,说“天下之理,本皆顺利,小智之人,务为穿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23]277。”显然,朱子也极为推崇大禹的顺自然之势而导,甚而用以阐发他的“天理”。当然,在更早时儒家便将“导”与政治相连,成为其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如郭店楚简《尊德义》下云:“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24]139。”可见,儒家将大禹“导水”与圣王“导”民联系起来,告诫统治者要像大禹引导水流一样引导民众、顺应民众。由是观之,《禹贡》、禹贡图里承继“大禹治水”的“导思想”对后世无论治水还是治学、治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它势必也会对今人兴修水利时的总的策略制定或是为人处世、研究学问时的思维方向选取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