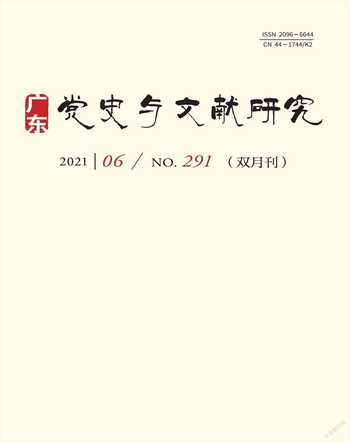1962—1966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会动员
贺文乐
【摘 要】“运动”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重要程式。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断革命”理论在农村社会的一次具体实践。以山西汾阳县为例,从运动开展、各阶层对运动的反应、动员方式等方面以区域微观史视角管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会动员机制。运动中社会动员的广泛开展,在改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以及推进移风易俗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动员;汾阳县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6-0055-10
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曾成为集体化时代国家治理农村社会的一项常规性抑或制度化举措。其中,1962—1966年间在农村开展的社教运动习惯上被称作“四清”运动。与全国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山西不少地区曾推广晋东南“整风整社”经验而进行“三清”(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清理物资),之后才开展“小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大四清”(清理政治、清理经济、清理组织、清理思想)。然而由于该运动并非是一次全局性的政治运动,因而不少公社、生产大队并非严格依照“三清”“小四清”“大四清”的次序进行。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社教运动兴起的原因、过程乃至主要领导人在运动中的分歧、部分省域或县域乃至生产大队(村庄)的实践均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通过考察该运动在山西省汾阳县的具体实践,试图在连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县域时空内阐释该运动中社会动员机制的具体运作及其效果。
一、汾阳县农村社教运动的开展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会后,一场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社教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和农村普遍开展。12月初,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中共晋东南地委《关于“三清”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各地可以普遍仿行,并在今后几年内,在收益分配前都要进行一次‘三清工作。” 12月底,中共汾阳县委提出《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方案》。该方案指出,农村社教运动的开展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纲,重点进行形势、阶级、纪律、技术革命、民主办社以及经营管理等六个方面的教育。该方案尤其强调要开展“三清”工作以便加强财务管理。1963年2月,中共汾阳县委根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中地委相关指示和精神,决定抽调340余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分赴演武等9个公社的82个生产大队开展以“整风整社”为中心的农村社教运动。此次运动历时两个多月,分四个阶段先后开展调查研究、落实政策、整顿干部作风与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等工作,使干部与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教育。1963年5月和11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指导农村社教运动的两个文件,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双十条”)。12月中旬,中共汾阳县委根据“双十条”及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中地委的相关指示,决定抽调200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隊分赴演武等9个公社再次开展以“整风整社”为中心的社教运动,并在部分生产队进行“三清”工作。此次运动历时半年,主要采取学习文件与讲“三史”(即村史、社史、家史)的正面教育方法,团结了多数干部与群众。
1964年6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之后,全国不少地区农村社教运动继续开展下去,汾阳县也不例外。中共汾阳县委决定将运动的重点转为在公社一级开展“小四清”运动,亦称“当年四清”运动。运动的主要步骤有:第一,学习文件,开展以社教为中心的“三史”教育,“忆苦思甜”,启发政治觉悟;第二,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第三,“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落实;第四,组织经济退赔;第五,总结教育。这次运动仍以正面教育为主,着重清理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经济不清”和干部特殊化问题。也就是说,此时“四清”运动主要集中解决经济层面的问题,对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此即“大四清”。 8月中旬,根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中地委的安排,汾阳县被确定为全省第二批“四清”重点县。9月,由各级机关单位2476人组成的16个工作团291个工作队,分两批进驻汾阳县三泉、演武、城子、见喜等16个公社291个生产大队开展“大四清”运动。此次运动的开展有以下七个步骤:第一,宣传中央文件,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第二,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动员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第三,清理大小生产队账目;第四,划清界限,组织经济退赔,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登记阶级成分,开展对敌斗争,清查“两反”(反革命组织、反动会道门)、“三黑”(黑枪、黑弹、黑烟毒);第六,整顿各类基层组织,进行组织处理,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第七,总结教育,“破旧立新”,建章立制,改善经营管理。1966年6月,中共汾阳县委对第一批开展社教运动的14个公社209个生产大队进行检查与验收的收尾工作。7月底,工作团接到上级相关指示后陆续撤离该县,因而石庄、万宝山2个公社82个生产大队实际并未开展“大四清”运动。
综前所述,在1962—1966年期间,汾阳县农村几乎在每年冬春之际都会集中开展有针对性的社教运动,从“整风整社”“三清”“小四清”到“大四清”。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阶级斗争”不断被强化,社教运动由最初的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层面、经济层面,最后上升至政治层面。由于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农村社教运动最终被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所取代。
二、汾阳县农村各主要阶层对社教运动的反应
社教运动开展之初,汾阳县农村各阶层对其反应不一。一般而言,“贫下中农容开面笑;多数中农消极观望;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心神不安,守口如瓶,四处探听风声;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恐慌”。其中,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和“四类分子”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兹从微观层面论述其对运动的反应。
由于各生产大队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即便同一阶层对运动的态度亦很难等量齐观,并非所有贫下中农对运动持积极态度。有的贫农将“四清”视为土改,认为贫农只是运动的工具,所以在贫下中农会议上说:“开会吧能怎的哩,还不是土改来了靠贫农,四清来了找贫农,运动过后,贫农就没人过问。”也有的贫农对“四清”中基层权力重构认识不充分,说:“我们队里问题很大,人家(指干部和四类分子)的势力可不小,这里三清、四清几次了,都没解决问题,谁敢惹呢?”甚至有的贫协主任对工作队并未抱有多大希望,说:“西堡障去年(1964年)搞四清时,又是穿呢子的,又是坐小汽车的,据说还没有搞出个长短,我们东堡障问题也不小,今年凭你们这几个工作队员,就能把我们村搞好?”即便工作队进村后,有些贫下中农也采取消极抵抗或有意逃避的态度。
作为运动惩治对象之一的“四不清”干部,对“四清”的抵制主要体现在轻视国家政策、对付群众尤其是运动的依靠对象贫下中农以及阻止工作队开展工作等方面。当然,这几个方面并非泾渭分明,往往相互交织,进而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图景。
在群众中煽风点火、威胁与恫吓群众是不少“四不清”干部采取的一贯手段。有的干部对群众说:“你们知道四清是干什么?就是给干部撑腰来啦,不然你们就不多出勤”;也有干部对群众说:“四清、八清、十六清,最后一定要清到社员头上”;有的干部则对群众“约法三章”,“一不许在工作队面前‘瞎说……二无事不要去‘打扰工作队……三要一日为工作队做三餐”。有些在“小四清”后上台的干部面对“大四清”产生了埋怨情绪,害怕“引火烧身”,试图明哲保身。如有干部反映:“早知现在这个样,去年(1964年)不该当干部,还不到一年就臭的没人上门吃饭啦。”有些“四不清”干部蓄意抵制“三同”(即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某生产队队长故意将工作队派到其亲戚家、富裕中农家和会计家吃饭。此外,还有些干部采取如下手段对运动进行抵抗,如“打听消息,偷听情况”;“(与工作队)形影相随,蓄意隔离”;“小恩小惠,收买群众”;“装穷装病,逃避运动”;“暗地吃喝,商讨对策”;“刁难工作队,躺倒不干”;“软顶硬抗,对付四清”等,不再一一赘述。
从上述得知,在社教运动的初始阶段,基层干部对运动潜在的抵抗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方面,运动激化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运动之前干群之间的平衡机制被打破。另一方面,干部对工作队的抵抗事实上也增加了开展运动的难度。因之,社教运动在农村社会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1965年11月,汾阳全县开展社教运动的各公社普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基层干部做了革命的精神准备,积极要求检查错误,甩掉包袱。”然而,也有些干部心存“七怕”,即“一怕交代了问题丢人;二怕在会上进行‘武斗;三怕领导偏听偏信冤枉了好人;四怕把自己的问题扩大了;五怕退赔以后生活困难,女人闹离婚;六怕受了处分当不成干部;七怕住了法院,断送了前途”。基层干部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既想顾及面子,又留恋于既有权力;既想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又难以舍弃一己私利。“公”与“私”、“名”与“利”之间的权衡,始终影响着基层干部应对“四清”的总体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四清运动要比任何先前时候都更强调阶级成分”,所以“四类分子”被认定为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其“反动”行为是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据载,汾阳县“大四清”中“阶级斗争”有10种表现,分别为:“写反动标语,散反动传单”;“造谣破坏,惑乱人心”;“千方百计,破坏四清”;“污蔑社会主义”;“威胁干部,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牛鬼蛇神,蠢蠢欲动”;“煽动群众分集体储备粮”;“毁坏工具,破坏生产”;“借少还多,高利剥削”;“盗窃案件,投机倒把”。从中得知,“阶级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表现为破坏集体经济,在思想文化上则表现为以传统文化抵制革命文化。
具体到对“四清”的抵制,既表现在蛊惑人心的精神欺骗方面,也有不良行为的发生,甚至还有对肉体的直接打击。有“坏分子”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这次四清是……先整干部,后整群众,谁也好过不了”;有地主女儿在地里对社员说:“四清能怎哩,清下的东西,公家都要拿走”;也有“坏分子”将“四清”意见箱扔在厕所里;还有“坏分子”在工作队员晚上开会完毕回住所途中向其乱扔砖块。三泉公社巩村大队地主分子武兴在工作队进村后,“内心极端恐慌”,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抵制“四清”,于是干脆借故腿疼而整天躲在家里,开会不到,劳动也不参加。在工作队识破其真面目令其交代历史时,他却“装出一副苦脸,说自己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而拒不承认其反动言行。待工作队调查清楚其历史与身份后,他感到仅凭敷衍很难“过关”,于是便装作“积极”,主动找工作队要求正常工作,说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对敌斗争中,他开始抵赖,“鸡毛蒜皮交代一大堆,對其反动思想却不敢暴露”。从武兴在运动中的言行可以看出,“四类分子”的“罪行”与“四不清”干部有所不同。首先,从犯罪性质来讲。“四类分子”与群众的矛盾是阶级对立之下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而“四不清”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即干群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原则上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斗争矛头从农村社会的上层转向下层,打击面不断扩大。其次,从罪行的危害程度来讲。“四类分子”被认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罪大恶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相比之下,“四不清”干部所犯错误多为“多吃多占”“贪污”以及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多数在坦白事实、经济退赔后留任。
三、汾阳县农村社教运动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
(一)“扎根串联”
在社教运动开展之初,各级领导层认为贫穷与革命呈现正比例关系,一个人或群体越是贫穷,革命性就越强,因为只有贫穷的人才可能申诉对现有村政权不满之苦衷。因之,贫下中农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法定为运动所依靠的对象。然而,要把广大贫下中农发动起来,首先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群众疾苦,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正因如此,大多数“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坚持“三同”接近群众。演武工作队队员每天除坚持利用半天时间下地参加集体劳动外,还利用空闲时间帮助贫下中农挑水、打扫院子,吃派饭时帮助其干活、看孩子。此外,还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群众学“毛选”。不久,工作队员就和贫下中农建立了阶级感情。有的贫下中农甚至感慨地说:“工作队虽然是些年轻娃娃,可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一定能为咱们办事情。”由于认真坚持“三同”,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和100余个贫下中农结成了“知心朋友”。有亲历者回忆说:“工作队里有个年纪最小的干部……他把我看作工作对象,劳动时同我一块干活,休息时同我闲聊,还到我家里来坐,动员我参加会议,给我讲解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还送给我一本毛选。慢慢地我对他有了好感,听他的话,开始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活动,成为一名青年积极分子。”杨家庄工作队进村后,队员挨门逐户访问贫下中农,讲政策,谈思想,进行启发教育。最初,全村仅有3个依靠力量,两个是好党员,一个是老干部。经过工作队深入发动和具体帮助后,这3个对象又串联了11个老贫农,后来又增加到13个。他们每人心里有数,干部谁好谁坏,心知肚明。通过各种形式开始“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以主人翁的思想,协同工作队员,对村里的阶级阵营重新进行内划。经过四五天的串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由原来的3个发展到了38个。
“扎根串联”,由点到面,在工作队不畏艰辛、苦口婆心的动员之下,贫下中农固有的从众心理逐渐被赋予以“阶级”为革命话语、以自身利益为物质保障的政治色彩,进而成为“阶级斗争”的急先锋。
(二)会议规训
社教运动期间,全县各公社先后召开“三干会”(即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以及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各工作队在各生产队召开党支部会议、座谈会、骨干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诉苦会等。其中,“三干会”是集中向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动员会议。城子公社“三干会”召开了18天,前12天进行“思想发动,大揭大议,专题讨论”的思想教育,后6天在“放包袱”过程中也是“边揭,边议,边查(查根源),边放”。演武“四清”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召开由全体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中农积极分子、部分干部家属和表现好的地主与富农子女等共2045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会后分57个小组进行讨论。据载,此次会议“鼓舞了贫下中农的革命勇气”“调动了好党员好干部的革命积极性”“促进了犯错误干部自觉革命的决心”“坚定了中农群众的革命信心”以及“启发了地富子女积极走革命的道路”。为了更好地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意识,社教运动在实践中还延续了土改时期的诉苦会。杏花村公社永安大队在社教运动后期阶级复议阶段召开了一次贫下中农诉苦大会,“诉苦典型”以“苦大仇深,苦情真实”为认定标准,同时兼顾“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结果是,“到会的群众个个倾耳静听,有的被诉苦人的悲惨遭遇感动得流泪,普遍受到了一次较深刻的阶级教育”。
由此可见,会议规训成为开展社教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内容不同的会议,工作队以中央政策为依据,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了政策宣传与思想教育,进而调动了其参与运动的积极性。尤其是诉苦会更是从心灵深处激起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仇恨,同时也是“阶级斗争”这一革命话语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政治效应。
(三)利益引导
尽管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物质刺激”被官方视为“资本主义倾向”。然而,在清理仓库的过程中,维护集体利益的背后其实也隐现出农民对自身利益关切的初心并未因运动的政治化、革命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罗城“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及时抓住清理仓库工作,有力地动员了群众。该工作队首先召开大队主要干部、各工作队长、会计、保管人员会议,讲清了清库的意义。接着,各生产队均由工作队员、会计、保管、贫协代表各一人组成清库小组,逐库进行清查。清查后,发现18个生产队中有12个在小麦方面存在问题。其中,实存大于账面的7个队,小麦多余6081斤;实存小于账面的5个队,小麦缺少1361斤。全大队各种粮食账面没有的品种,而库内实存粮18228斤;账面上有的粮食品种缺少了7115斤。从清理物资看,“有账无物,有物无账,账物不符”等现象十分严重。如第十一生产队,账面应存棉花895斤,库内全无;账面应存棉籽油369斤,实际只存33斤;账面应存石灰23330斤,库内全无。清库小组将所清查问题逐一向群众公布之后,干部、群众震动很大。不少干部“匆匆忙忙跑到工作队交代问题”,广大贫下中农看到问题后“越清越有劲”。如第三生产队贫下中农曹毓礼说:“问题不小,有清头呢,咱们要清就清个彻彻底底,我见我哥就私分过队里的粮食。”在清库以后的两天之内,就有115人找到工作队揭发出问题案件405件,有10个干部主动交代了13项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不难发现,农民对于清理仓库的热情,与其说出于革命觉悟的提高,还不如说是清理仓库背后物质利益的驱动所致。在农民看来,尽管清理仓库所得之财被收归集体,但只有集体物资充实,个人利益才能有所保障。
(四)思想政治教育
任何高效的政治运动都很难离开及时而灵活的思想政治动员。揆诸史实,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革命话语建构之下,社教运动對农村社会各阶层普遍进行了一次革命思想教育的洗礼。城子公社“四清”的重要经验就是在1965年9月到1966年8月的11个多月期间,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与群众。有数据显示,参加学习“毛著”的农民占全公社成年农民总数的85%以上;各大队建立领导核心、学习小组202个;配备辅导员约400人;购买“毛选”5860余套;涌现出标兵单位18个、标兵259人,模范单位35个人、模范951人。通过学习“毛著”,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显著变化,“私”字分家、“公”字当家的农民逐渐增多,不论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思想逐渐革命化,即“思想红,干劲增”与“‘公字增,‘私字减”。由此,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农民社会以政治运动的程式得以普遍树立。
较之学“毛著”,组织观看电影、戏剧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动员方式。有亲历者记载:1963年12月中共汾阳县委组织各级机关干部在县委党校培训期间,曾邀请临县晋剧团演出表现“阶级斗争”的现代剧《东风解冻》,结果“博得了观众们共同赞誉”,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全体演员领会了剧情,有阶级感情”,且贫农、基层干部形象逼真;而缺陷在于地主表现得“不阴险”,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敌人未被很好地“隐藏”。1964年7月汾阳县小麦喜获丰收后,县委党校又组织各级干部观看戏剧《丰收之后》,结果是“每一个观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干部、学生、工人、农民,无一不叫好,无一不喝彩”,其中60多岁的老太太“认识了依靠贫下中农的必要”,十七八岁的姑娘“流下了眼泪”。总之,该剧“生动的剧情,逼真的表演,合理的情节”,尤其是“充满了阶级感情”的“忆苦思甜”一幕,“符合了社会的需要,对上了观众的胃口”。不难发现,较之其他动员手段,戏剧等媒体则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等显著特征,更易于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并产生思想共鸣。
(五)树立典型
社教运动期间,一些模范干部先后被树立为典型。一般而言,模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群众满腔热情,对敌人刻骨仇恨”。换言之,忠于革命、忠于党,密切联系群众,阶级界限分明等是社教运动中培养模范进而树立典型的基本条件。如峪道河公社赵庄生产大队干部赵某为了“保卫革命,保卫群众利益”,“在保夏护秋中,他总是不分白天黑夜,风里来,雨里去,到处巡查,不辞劳苦”,从而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日常工作中,赵某“敌我界限分得清”,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四类分子”则铁面无情地进行打击与斗争。正因如此,他在公社“三干会”上被树立为全公社的标兵,其模范事迹在“社教”展览馆展出后,“数以千计的干部和群众……无不钦佩叹服”,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因之,树立典型对动员干部自觉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社教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工作队往往同时采取多种动员方式,或以一种动员方式为主,其他方式亦不同程度存在。其中,召开会议、诉苦、利益诱导、树立典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与土改中的动员机制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较之土改,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虽然不可避免地打上“左”倾的印记,但“乱打”“乱杀”等过激行为鲜有发生,基本遵循了“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政策原则。不过,笔者认为社教运动中对干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较之前进一步提升,“学毛著”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典例。因之,运动中“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口号不断出现在各类史料之中,并成为继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开展思想革命的历史印记。
四、汾阳县农村社教运动社会动员的效果
综前所述,在汾阳县农村社教运动中,作为社会动员主体的工作队对以贫下中农为主的动员客体进行了一次政治动员。在广大贫下中农被动员起来之后,对不少“四不清”干部和“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教育与斗争,同时还对党支部、妇女、青年、民兵等各类党团与社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正因如此,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层干部的腐化之风,也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动员产生的积极效果理应肯定。
社教运动与“农业学大寨”紧密相连,在运动后期,各地普遍推广大寨经营管理的经验,特别是劳动管理的经验。截至1964年6月,汾阳全县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如下:普遍进行“三算账”(任务、时间、劳力)、“两对口”(需工和投工),加强了生产的计划性;作业小组实行“思想好坏、劳力强弱、技术高低”的“三搭配”,学会了队长抓组长的分级领导办法;实行“定额质量分项计酬”办法,提高了技术活报酬,增强了干群质量意识,促进了青年人学技术思想的新观念;普遍制定了三级验收制,加强了以作业组集体为主的集体、个人相结合的双层责任制,培养了社员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学会了在管理中抓活的思想工作,做到了思想、管理紧密结合。经此,全县劳力出勤人数达到6.5万人以上,干部劳动日超过1963年同期的12.8%。此外,还在财务管理制度方面清理旧账、建立新账,专门培训财会人员,进行记账制度改革;在分配制度方面,强调粮食分配坚持“人七劳三”,管理费不超过生产队收益总额的1%,公积金、公益金提取则控制在8%左右。事实表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集体经济体制。
社教运动在改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强了农业基础建设。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汾阳县在“大四清”时期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起抓。由于运动中思想动员的强化,不少昔日“生产消极”或基本不参加生产的群众和干部开始大量参加集体劳动尤其投身于农田水利和林木建设之中。1965年冬至1966年春,全县有50.4%的劳力投入水利建设,新打井、整修旧井共计561眼,扩大水田26340亩,开凿新渠、整修旧渠共计1860条,建筑水利建筑物479件;建造“大寨田”18218亩、高标准田46649亩,植树49万株、育苗490亩、造林5215亩。与此同时,农村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也较运动之前明显提高,有42个生产大队通电,占通电大队总数的24.6%;农业机械总动力提升43.8%,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加50%,排灌设备增加70.4%,收割设备增加42.9%,农产品加工设备增加103.8%。在农业科技方面,优良品种普及率达到85%以上,其中小麦“农大183”、玉米“维尔156”等优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平川地区的不少社、队推广了“麦田套种三茬栽培法”;化肥施用量增加38.7%,普遍推广贾家庄大队秸秆还田、大堆沤肥的经验,每亩地施农家肥达到30~35担。
此外,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县农村于1964年冬掀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学习运动。全县共举办农闲集中学习、农忙业余学习的季节性半农半读班7个、初级农技夜校11座、冬学(又称“贫下中农讲习所”)310座,参加学习的农民约有2万人。通过学习,试图提高农民的自身素养,进而对农村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不仅如此,社教运动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有利于农村社会风气的重塑。任家堡大队农民被动员起来之后,“一夜之间,全队就交出土地爷、灶王爷、觀音菩萨等泥木塑像四百一十多个,‘聊斋‘玉匣记‘金瓶梅等黄色反动书籍二百多册”。有亲历者记载1965年春节的变化:“将灶君爷的神龛撤除,驮灯马由弟弟给砸碎。土地堂内的瓷神像取掉,香炉扔了。没有给任何人压岁钱,取而代之的是5分钱一个的月历本,上有八首革命歌曲,有公历、农历、星期,有二十四节气,有重要纪念日,有毛主席语录,有学习解放军的社论等。”为此,该亲历者认为该年“是一个破旧立新年”。这样一来,用毛泽东思想填补民间信仰被取缔后农民的精神空白,进而建立了革命信仰体系的合法性权威。
当然,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产生的“左”的偏差亦不容忽视。峪道河公社圪垛大队在运动前是全县的先进典型,大队支书一直是全县的劳模,在运动中只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当兵开小差的人说了一些公道话而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进而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会计、保管因经济问题被定为贪污盗窃分子;管委会主任因私用集体的小麦秸秆抹了自己的窑洞,也被定为“四不清”干部而不再任用。城子公社“郭家庄把一个下台干部一角五分钱的问题也定了性”。“定性偏严”现象的存在使得不少干部心存畏惧感,即便被留任,也很难正常发挥领导才能。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大队则发生“定性偏宽”现象,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甚至普通社员也被迫进行经济赔偿。这些偏差的出现,明显有悖于党发动农村社教运动的初衷,进而影响了运动的实效。
五、结语
20世纪60年代在部分农村开展的以“四清”为重点的社教运动前承“大跃进”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次重大政治运动。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有利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有序完成,尤其是教育了干部和巩固了集体经济。但同时,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前文在梳理山西省汾阳县社教运动发展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不仅对运动中各阶层的反应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对工作队应对反应所采取的动员方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研究表明,汾阳县社教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开展社会动员的一次“在地化”实践。通过汾阳县这一案例,中国共产党在集体化时代以“运动”程式治理农村社会的机理得以呈现。此种程式在短期内往往能够收到一定的预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其对基层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亦值得反思。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叶浩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