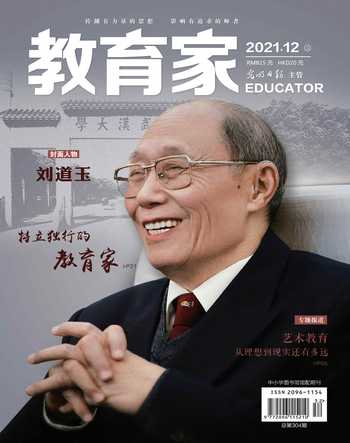三喜老师
白静


他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路一跛一跛,跛着跟钟声进教室,跛着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方方正正的楷书,跛着用乡间方言高声讲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一一得一,一二得二”。
——题记
六岁半的时候,我有幸背上母亲踩着缝纫机、用碎布头拼凑成的单肩包,到家门口一所新建的学校读书。那是一所由乡亲们排成长队,以手传土,义务修建的村学。学校有三间大房子,作为一二三年级的教室;三间小房子,其中两间作为两位老师的办公室,一间作为学前班,一段时期内还充当了村子里的扫盲班;至于两个更小的处于校园角落里的小“厦子”,则作为厕所。那一片被人称为“操场”的空地上,长满了野草,由于学校乃至整个村子都不知道篮球的存在,只能任由草丛里的篮球架生锈、荒废,静静地矗立着。
学校里的两位老师都是“社请”的男老师。一位是本村的叔叔,跟我们一样,都姓白,上班时间可以随时照料家务,课间给家里挑一担水,把家里的小麦扛到教室,让大一些的孩子帮忙用簸箕和筛子“簸磨”。另一位是外村的,似乎也姓白。跟对待其他老师一样,大人们当面称他“老师”,而背地里叫他三喜,其实或许叫“山喜”,因为老家人不分“s”“sh”,只要能叫响就行了。
三喜老师是典型的书生模样:身体清瘦,长相儒雅,面白少髭。一身永远平整洁净的中山装,上衣兜里总是插着一支红墨水钢笔,这让村里的大人心生敬畏,认为“先生”理应如此。其实,三喜老师不仅是儒雅书生,还是柔弱书生。印象中,他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路一跛一跛,跛着跟钟声进教室,跛着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方方正正的楷书,跛着用乡间方言高声讲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从一年级教室跛到二年级教室,再跛到三年级教室,他似乎没有坐下过,只记得他的背部笔直,字迹工整。上完课,他便回到那间靠里一个小小土炕,靠窗一个木头桌子、一把木头凳子的小房子里,往一个罐头瓶子里放几丝春尖茶叶,倒上热水,慢咂一口,再从上衣兜里取出那支塑料钢笔,旋下笔盖,套在笔尾,一行一行地看我们歪歪扭扭的蚯蚓字,划上红红的对号或叉号。
三喜老师家距离学校比较远,他有一辆自行车,然而中午休息时间毕竟短暂,所以他早晨来的时候,挎在车子前面的布袋里,总是装着中午要吃的干粮。冬天是馒头夹咸韭菜、一罐头瓶子春尖茶水,夏天是馒头就青椒、一罐头瓶子春尖茶水,春秋季节会有洋葱头或是其他什么,但是馒头和春尖茶水从没有变过。有时候村里的人看三喜老师馒头啃得多了,会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吃口热乎的饭菜,但他似乎很少去,或许从来没有去过。我一直好奇,他腿脚不便,若遇上刮风下雨,或是大雪封路,他是怎么做到准时推着车子走进校园的。
我们好奇他是外村人,好奇他的馍馍,好奇他的腿,好奇他的车子,更好奇的,是他的病。三喜老师似乎患有癫痫,村里人称“羊羔疯”。他平时总是微笑着,亲和慈祥,一身清雅,而到犯病的时候,很是可怕。学校里总共只有两个大人,其他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遇上三喜老师犯病,口吐白沫,手脚痉挛,就只能是本村的白老师使劲儿地压着他的双手,叫上几个胆子大的男孩子帮忙抓住腿脚,把搭在绳子上的毛巾塞进三喜老师的嘴里。其余的毛孩子,就挤在门口远远地看着,准备随时跑掉。等三喜老师恢复了,苍白着脸坐起来,我们尽管心有余悸,但还是壮着胆子继续围观,直到他拿起书本准备上课,我们才撒腿跑开。
遇上晴暖之日,我们又围着这位笑眯眯的老师,在院子里一人划出一块空地,用树枝,阔气一点的就用从电池里敲打出的碳芯,一边在地上用力划着“a、o、e”,一边扯着嗓子夸张地读着“啊、呕、我”,一边比谁写得多,谁写得整齐,谁喊得响亮。有的学生手里写着“六”,嘴巴里读着“六”的拼音——“拉娃六”;或是几个女生挤在一起,一边高声朗读着“春去花花菜,人来鸟不惊”,一边享受着一年级新生投来的钦佩的目光,一脸灿烂。此时的三喜老师,还是跛着脚,一瘸一拐地来来去去,耐心地纠正那些“拉娃六”和“花花菜”。
冬天就不能总是在院子里读书写字了。那时的风格外有力,掀得房顶呼呼作响,树枝咔咔掉落。雪也不甘落后,一觉醒来,总是“雪盖三层被”。我们只能蜷缩着肿得老高的红彤彤的手,或是皴裂着口子流着脓水的黑乎乎的手,一锨一锨地铲出一条仅能容下双脚的雪中小路,哆嗦着去学校。到校之后,调皮的孩子就互相打赌,用舌头舔舐冻透了的铁大门,看谁的舌头粘不住。有的孩子缺乏经验,速度太慢,舌头就被粘在了铁门上,疼得哇哇叫。这时候本村的白老师来了,外村的三喜老师也来了,和我们一样,手里拄着一把铁锨,身上斜挎一个布包,装着一天的馍馍跟咸菜。老师气得不得了,却也只能叹一口气,让其他的孩子对着那个粘在铁门上的舌头哈气,哈上半天,舌头才重获自由,可也掉了一层皮,只能忍痛吸溜着。大门打开,我们涌进同样冻透了的教室,帮老师抱来码放在教室后面的硬柴,跟老师一起燃起黄泥巴做的小火炉,围着老师,跺着脚,挤着烘烤那早已冻木了的双手。烤一会儿,老师便起身准备上课,我们也散开回到座位上,跺着麻木的脚,搓着麻木过后肿疼的手,开始一天的学习。一节课结束,老师拿出石头一样硬邦邦的馍馍,放在泥炉边上烤。我们也争相拿出自己同样干硬的馍馍,放到老师馍馍的周围,吸溜着鼻涕,贪婪地闻着烤馍馍的香气。相比之下,我们更喜欢围在三喜老师的身边,因为三喜老师拿的馍馍似乎更圆,皮也更光滑,更重要的是,三喜老师会将他的馍馍掰开,投喂我们这些咽着口水的馋猫。有时候,三喜老师还会跟我们分享他罐头瓶子里的咸韭菜或酸白菜,让那个寒冷贫乏的岁月,在多年之后,变成最温暖的回忆,涌上心头。
几年以后,国家进行教育资源整合,所有的孩子一律去大队小学上学,我们的村学自此荒废。本村的白老师,比较有先见之明,努力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摆脱了“社请教师”身份,变为有编制的“正式教师”,调去了离家不远的其他小学。三喜老师则因为“社请老师”的身份被清退,彻底离开了自己跛了几十年的村學讲台,再也无处书写他那方方正正的粉笔字。兜里的那只红墨水钢笔,似乎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只是不知道三喜老师有没有将它继续别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也不知道老师的中山装是否还跟从前一样,干净平整。
已近不惑之年,再回到老家,那所曾经洒满了欢声笑语的村学还在,只是,那个粘过我们舌头的铁大门已经布满了锈迹;教室门窗、墙体早已毁坏,两位老师房子里的小小的土炕也已经倒塌;荒芜的校园先被村长挖开种菜,后来又荒废,后来又有人断断续续地挖开,一些做菜园子,其余便更加破败。
伫立在老家门口,远远地望着那所学校,女儿说:“妈,你的学校里有人进去了,咱们能不能进去看看?”我看着女儿,望望学校,终于不敢走近一步,更没有勇气进去看看。似乎,那些欢声笑语,那些黑乎乎、脏兮兮的笑脸,那位早已去世的白净儒雅的三喜老师,从来未曾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