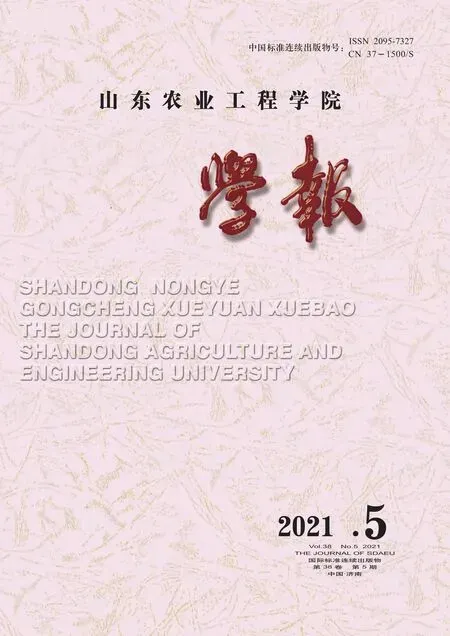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特点探析
——以英美、法德和日本为例
刘志华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现代化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中国有较强借鉴意义。本文将着重考察英语国家英美、欧陆与欧盟国家法德、东亚国家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特别是土地制度领域现代化的特点。
1 英美两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小国寡民的英国和地广人稀的美国先后成为引领世界现代化的头号强国,也是当今世界英语国家与英美法系的代表。但对中国这样面积广大且人口稠密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两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启示作用恐怕不能被过高估计。
1.1 英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是最早启动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而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及特点最受史家关注。16世纪前期,英王亨利八世发起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没收、赏赐并出售修道院的宗教地产,大大削弱宗教界的经济基础;国王甚至还出售王室地产。上述举措使贵族、乡绅、商人、律师等阶层通过获赠或购买等方式获得地产而成为地主。此后两个世纪间,各类地主将土地视为经济收益的来源、政治地位的基础和社会影响的象征,继续扩大自己的地产。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尤其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的大土地所有制达到顶峰,土地高度集中,地主与农业资本家间的租佃制以及农业资本家与农业工人间的雇佣制盛行,直接经营自家地产者寥若晨星,自营的农地面积比重极低(在1887年约15%,到1914年仅有约10%)。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自由贸易的推进、外来产品的冲击、农业产品的降价与农业收益的下滑,还由于议会改革的推进、选民范围的扩大与衰败选区的消失和两次世界大战对粮食安全的要求以及英国政府的政策引导,地主越来越不愿持有和扩大地产,转而开始出售大批地产,导致直接经营自家地产者逐渐增多,自营农地面积比重大大提高,在1950年占四成左右,到1983年达六七成。[1]因此,战后的英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模式的国家,土地经营者往往掌握土地所有权,愿意并能够对土地进行追加投资,土地经营的自由度和收益率有所提升,农业生产力继续得到解放和发展。
1.2 美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生态环境涉及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水文、耕地和人口等诸多地理要素。美国农业生态环境的优势可谓相当全面。美国目前的领土面积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和中国,位居世界第四。但它既不像俄罗斯和加拿大那样大部位于高纬地带,也不像中国那样山峦起伏沙漠广布;美国的光热条件较为适宜,总体地势比较低平,耕地面积位居世界首位,农业资源可谓得天独厚。美国的人口总量次于中国和印度,位居世界第三。它既不像俄罗斯和加拿大那样人口过疏,也不像中国和印度那样人口过密,劳力供应即便不算恰到好处,也只是稍微偏紧。美国不仅是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战后科技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是一百多年来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从科技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受益良多。美国政府还与时俱进,不断依据变化的形势来调整农业政策,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并促进农业发展。因此,美国成为一百多年来农业最先进的国家与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控制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牛肉、猪肉等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农业最强国”[2]。
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美国的土地制度和经营模式,分别是土地私有制与家庭大农场,所有权与经营权通常合二为一,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地广人稀状况相适应。第二,美国私有的家庭大农场,耕地资源非常丰富而劳力供给相对不足,加之地处平坦环境,因而长期致力于提高播种、翻耕、施肥、灭虫、除草、灌溉、收割、脱粒、运输、仓储各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在战后还曾依靠信息与生物科技发展所谓的遥感农业和转基因农业,主要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地狭人稠、精耕细作的日本相比,美国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即土地生产率偏低,而劳动生产率则高得多。对中国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土地生产率,哪个更重要?显然是后者。因为中国耕地十分稀缺而农业劳力相对充裕,类似日本而不像美国。第三,美国私有的家庭农场大多面向国内外市场,养殖单一作物或牲畜,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很高。市场化农业,要求农场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育种、施肥、杀虫和除草等方式极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提高土地生产率。市场化农业,也要求农场主必须慎重考虑水陆运输条件是否具备,以及运输距离和成本。美国能源储量和产量惊人,油气价格低廉;美国本土东邻大西洋、南濒墨西哥湾、西接太平洋,优良海港众多且大多终年不冻,造船业发达,远洋运输能力超群;美国内河航运条件同样卓越,除五大湖与多段运河外,密西西比河水系发达,干流纵贯南北,支流横穿东西,干支流大多水量充沛,水流平稳;美国铁路修建较早,公路四通八达,高速基本免费,陆运条件令人惊叹。优越的水陆运输条件,降低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和终端售价,提高了农产品竞争力和农场主的收益。第四,美国农场主利用自身的选举权和多种农业合作社,影响国会和白宫的涉农立法与行政活动,促使政府采取多项惠农政策,特别是给予农业补贴和开拓别国市场。[3]
2 法德两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法国和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是欧共体和欧盟的创始国与双子星,分别是欧洲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与出口国以及最重要的工业国。
2.1 法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也是较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强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基本完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主要标志是:
在土地制度方面,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与领主特权消失,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方面,机械化、化学化和良种化逐渐发展,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葡萄产量增加,铁路和公路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粮食问题彻底解决,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加速。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大量村民迁入城市,城市人口与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比重极低。在乡村教育方面,乡村教育取得显著进展,农民文化程度大大提高。[4]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乡村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明显加强,农民摆脱农村庇护性社会关系,能够有效利用乡村农业、选举制度和科学知识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政治和精神层面彻底解放。
2.2 德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德国是欧洲较晚建立统一民族国家、较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却后来居上,自19世纪后期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很高,在1990年两德统一以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土地制度方面,以多部法律保障土地私有制,除原民主德国(东德)境内盛行100公顷以上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外,其余地区以30~100公顷的中型家庭农场和2~30公顷的小型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模式,不足2公顷的微型农场数量较少。例如,在2013年德国38万个农场中,大型资本主义农场只有2.93万个,中型家庭农场有10.4万个,小型农场多达21.85万个,其余2.67万个是不足2公顷的微型农场。[5]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方面,德国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和工业优势,耕地平整化、农业标准化、机械化、良种化、信息化为欧洲第一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农业产量特别是饲料与牲畜产量较高,水陆空运路线四通八达,粮食问题彻底解决,农产品市场化水平令人叹为观止。[6]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大量村民迁入城市,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比重较低,城市人口与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大幅上升,普通乡村与中小城镇非常发达,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超越市民。[7]在公共服务方面,德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较早建立惠及村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村民的农学知识丰富,社会福利很高。[8]在生态环境方面,德国政府厉行环保法规,对耕作过程进行精细化监督,严格控制各类肥料和农药的施用时间、重量和方式,并以多种农业补贴诱导农民减少各类肥料和农药对耕地、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德国乡村环境美丽宜人,生物多样性得到维持和发展。[9]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乡村与外界联系紧密,农民能够有效利用各类农业合作组织、选举制度、福利制度、文化素养和环保法规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和生态层面得到彻底解放。
3 日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国土狭小、山地众多而耕地极少的战败国,却成为亚洲最早实现乡村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单位面积产量与土地生产率很高,多数农产品质优价高,农民获得丰厚的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而且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3.1 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承认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土地兼并比较严重,租佃制度盛行,佃农和地主之间仍然存在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村逐渐出现所谓的“寄生地主制”,进而成为军国主义的温床之一。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着力推行土地改革,以清除乡村农业领域的军国主义土壤。1945年12月9日,美国占领当局提出《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又称“解放农民令”,命令日本政府在次年3月15日以前制定农地改革计划,“排除经济民主化的障碍”并“打破几个世纪以来在封建压迫下使日本农民奴隶化的经济桎梏。”1946年10月,日本政府被迫颁布《建立自耕农措施法》与《农地调整法》,在1947年3月—1952年7月进行土改,征购并出售耕地23次,其主要内容是:国家依据1945年11月23日的地价,征购在外地主的全部土地与在村地主的超额土地(区分北海道与其他地区,区分在村不耕作地主与在村耕作地主)共193万町步(占改革前佃耕地面积的八成),将征购的土地以同样地价出售给占农户总数四分之三的430万户佃农或少量“有能力的经营者”,征购与出售地产的期限均为30年,年利均为2.5分以下。随着恶性通胀和地价上涨,到1950年时,征购和出售的地价仅相当于时价的5%—7%,当初的赎买几乎等同于无偿没收,当初的出售几乎等同于免费赠送。[10]土地改革后,日本成为自耕农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寄生地主制”被完全消灭,军国主义的温床之一被彻底清理。土改末期的1950年,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的农户占全国617.6万农户的72.9%,占地1~2公顷的农户所占比重为21.7%,占地大于2公顷的农户比重仅为5.4%。[11]为防止“寄生地主制”死灰复燃,日本政府于1952年公布《农地法》,严格保护每年至少干150天农活的实际耕作者,捍卫自耕农对土地的所有权或租佃权,即着力保护佃农与自耕的土地所有者。[12]1960年,除北海道外,日本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的农户占71.8%,基本保持不变;而占地大于2公顷的农户比重为4.07%。1970年,除北海道外,日本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的农户占69.61%,比重略微下降;而占地大于2公顷的农户比重升至6.83%。[13]到1980年,日本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的农户约占70%,基本保持不变;而占地大于2公顷的农户比重有所上升,为9.0%。[14]
此后,日本鉴于农村的机械化、兼业化、少子化、老龄化与城市化现状,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日本政府多次修改或出台涉农法律,尤其是在1980年颁布实施《农地利用促进法》(在1993年被修改为 《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在2009年大幅修改《农地法》,不断推动农地买卖和租赁,进而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到2015年,日本农户平均经营农地约2.2公顷。[15]有研究者指出,战后土地改革以来,日本业已形成由1952年 《农地法》(后来历经多次修改)、1961年 《农业基本法》、1969年 《农业振兴地域法》、1972年《土地改良法》、1980年《农地利用促进法》和1993年《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简称“农促法”)以及1999年《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等共同组成的农地“制度集”[16]。
3.2 战后日本的粮食安全
战后初期,日本人大多以大米为主食。1960年,种植业产品占农业总产值的80.6%,其中大米占47.4%。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日本国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食物结构日趋复杂,大米的地位渐趋下降。1980年,种植业产品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至67.8%,其中大米所占比重降至30.0%。[17]日本人均大米消费量从1962年的 118公斤降至2006年的 61公斤。[18]尽管如此,大米仍然是日本人的首要口粮。战后日本主要采取三种举措来维护粮食安全特别是大米自给。
一是科技支持,推进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学化。政府和民间持续推动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小型轻便农用机械的广泛应用[19];出台《农作物种苗法》《主要农作物种子法》,形成良种培育、存储和和栽种制度[20];重视灭虫和施肥工作,并妥善解决农药化肥超量使用问题[21]。二是资金支持,政府和民间以农田水利建设、贷款等多种形式向农业融资。日本逐步形成以合作性金融为主导、政策性金融为支撑、商业性金融介入[22]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三是价格支持,一度以保护价收购大米,并对国产大米进行关税保护。1960年后,日本政府开始以较高保护价收购国产大米并以较低市场价销售,价差由政府财政负担。此举提高了稻农的生产积极性,与机械化、良种化和化学化共同导致之后几年大米产量逐渐增长,到1967年实现完全自给自足并出现供大于求。面对新的大米供求形势,日本政府在1969—1970年首次出台所谓的水稻“减反政策”,即限制水稻播种面积与产量,并对限种限产的农户进行补贴的政策。[23]1995年日本开始施行《主要粮食供求及价格稳定法》,又称“粮食法”,公布大米现库存量、拟收购量、转作休耕面积,以此调节稻农的播种面积和大米产量;2008年日本政府修改“粮食法”,改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出台和修改水稻生产方针,引导各地农协和稻农适时调整水稻播种面积和大米产量。[24]上述政策导致水田面积持续缩小,从1970年的344万公顷降至2014年的 247万公顷。[25]到 2018年,日本政府废除沿用数十年的大米“减反政策”,使稻农自行确定水稻播种面积和大米产量。[26]日本政府还抬高大米进口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维持国产大米销售价,保护本国稻农权益。例如,仅在2009年,日本就对进口大米实际征收778%关税,远高于对黄油征收的360%关税,对砂糖征收328%的关税,对小麦征收的252%关税。[27]保护稻农的意图不言自明。
3.3 战后日本的村民流动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日本农村长期经受少子化、老龄化、城市化的影响,出现过疏化、空心化与合并化,农业收入比重、农业人口比重、农户人数比重和农户数量比重持续下降。1970—2005年,日本兼业农户中非农收入大于农业收入的农户比重从51%升至74%,农业人口比重从19%降至4.8%,农户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25%降至8.9%,农村户数占全国户数的比重从18%降至6%。[28]日本农林水产省2009年 《袖珍农林水产业统计》与2010年2月1日 《世界农林业人口普查结果的概要(暂定价值)》提供的数据显示:农村户数在1995年为265.1万户,在2000年为233.7万户,到2009年降至169.9万户(当年农村居民总计698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者为238万人,约占34%),到2010年降至163.1万户。[29]与此同时,日本的总耕地面积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比1961年的耕地面积缩减146万公顷。[30]尽管如此,农户数量减少幅度还是大于耕地总面积的缩减幅度,仍然导致农村居民的户均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在1955年为0.85公顷,在1970年为0.95公顷,到1980年升至1.17公顷,到2005年增至1.27公顷。[31]然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耕地被弃耕,在2000年有34.3万公顷弃耕地,到2010年增加到40万公顷。[32]
3.4 战后日本的农民增收
战后初期,日本城乡居民收入尚存在一定差距。日本农林水产省《农户经济观察》和日本首相管理办公室 《家庭观察》提供的数据显示:195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7万日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7.4万日元;196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7.8万日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11.5万日元。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日本政府着力提高国民收入特别是村民的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致力于消除城乡收入差距。197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2.6万日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5.8万日元,差距已经微乎其微。到1975年,日本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为86.7万日元,已经超过城市居民的76.0万日元。到1980年,日本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为127.3万日元,超过城市居民的111.1万日元。到1985年,日本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为159.6万日元,超过城市居民的142.2万日元。[33]1988年,日本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为174.3万日元,超过城市居民的154.6万日元。非农收入及其在农户收入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在1960年为4万日元和50%,在1970年为22万日元和67%,在1980年为103.9万日元和81%,在1988年为150.9万日元和87%。[34]
4 小结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自由度扩大,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所有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几百年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当代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两国人口、农业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还不及中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农业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的发展中“超级大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无先例可循,也有极大难度。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90%,中国仍将有过亿人口常住农村。由此可见,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开创性、艰巨性、长期性和战略性。
——评《中国现代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