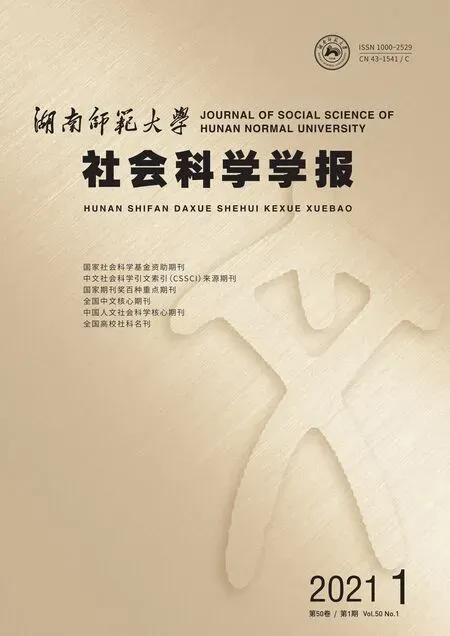排遣与消遣:近代知识群体阅读《红楼梦》的日常心态
温庆新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群体案头的重要读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群体阅读《红楼梦》的方式、特征及其精神体验的结果往往有别,尤其是《红楼梦》如何深入不同读者群体日常生活的缘起及其所形成的接受意见亦多有差异。在近代,知识群体不仅展现了《红楼梦》个体阅读的私密性体验,而且逐渐将阅读《红楼梦》当作一种群体间普遍存在的社会接受现象。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分析近代知识群体品读《红楼梦》的细节,有助于更加细致探讨《红楼梦》在近人日常消遣与精神生活所扮演的角色,丰富《红楼梦》后世接受的若干细节讨论。鉴于学界对《红楼梦》近代阅读的过程环节罕有细致讨论,兹以《红楼梦》之于近代知识群体精神排遣与日常消遣的互动,尝试勾勒近代知识群体阅读《红楼梦》时的若干典型侧面。祈盼方家识之。
一、“发愤著书”说与近代知识群体《红楼梦》品评的精神排遣
《红楼梦》在近代传播过程中,存在当时知识群体将其当作曹雪芹“发愤著书”的一种典型接受,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仕途不顺而寄言于此的思想产物,从而促使《红楼梦》寄寓着曹雪芹暴露彼时社会不公的批判式意图,以至于认为该书具有考察时政与风俗的社会功用。
平子《小说丛话》(1904年)就称,“《红楼梦》一书,系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可知其意矣”,由此形成“字字是血,语语是泪”的写作策略[1]。此举强调曹雪芹发愤著书的意图是“愤满人之作”,从而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有所寄寓的典型之作。黄人《〈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更是认为《红楼梦》系“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者(《石头记》成于先朝遗老之手)”[2],以至于黄人从近代家亡国破的现实来挖掘《红楼梦》寄寓着类似内容的愤懑之悲。我们权且抛开平子将《红楼梦》比附于“排满”的“污名化”行为对《红楼梦》接受的不良影响,单就平子强调《红楼梦》“发愤著书”的认知视角而言,表明近代知识群体已逐渐关注《红楼梦》写作寄寓之于读者接受的影响。黄人的认知趋向亦表明近代知识群体已尝试基于读者自身对《红楼梦》的各自理解来品评《红楼梦》文本的发散式思路,进一步促使近代知识群体以为《红楼梦》是曹雪芹不平遭遇的典型写照[3]。甚至,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年)认为“《红楼梦》之写侈”是曹雪芹“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等情感“假俳偕之文以寄其愤”的结果[4],以至于促使曹雪芹“心伤之,有所不敢言,不屑言,而又不忍不一言者,则姑诡谲游戏以言之,若有意,若无意”[5]。凡此种种,其间的品读思路皆是将曹雪芹的遭遇与《红楼梦》文本旨意相联系。而海绮楼主人《〈霣玉怨〉序》(1914年)更是明确指出“《石头记》一书,尤为写怨而作”,又说“予尝推作是记者,有深怨而无可泄,托焉而为之,亦以鸣其孤愤而已”[6],亦是将“泄怨”与“孤愤”相结合来理解《红楼梦》的文本旨意。
然而,从上引可知,近代知识群体并不太在意深度挖掘曹雪芹如何在《红楼梦》文本中详细描写或再现自身的不平遭遇,而是集中强调曹雪芹在《红楼梦》文本中带有表现自身不平遭遇的书写倾向,从而将曹雪芹的此类书写倾向与阅读者自身的品读意图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近代知识群体对《红楼梦》“发愤著书”的解读逐渐形成一种普遍性态势,以至于在此类认知过程中将曹雪芹的不平遭遇与读者自身的经历相联系,最终在品读《红楼梦》文本过程中展现读者自身的阅读消遣或有所指的言说意图。寅半生《〈小说闲评〉叙》(1906年)曾指出:“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梦》等书是已。”[7]以“抱才不遇,无所表见”来诠解《红楼梦》旨意的阅读倾向,使得近代知识群体更加注意曹雪芹“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的自我心态调节与精神解脱方式,以便最终形成近代知识群体据此展开品读《红楼梦》的逻辑切入点与意义关注点。如洪都百炼生(刘鹗)《〈老残游记〉自叙》(1906年)曾言及“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之举是“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8]等易于感染读者的行动内驱力。所言“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亦是基于“发愤著书”的观察结果。
将《红楼梦》当作读者排遣自身现实不公遭遇的发泄口,使得近代知识群体往往会形成投入《红楼梦》文本而无法自拔的深切感受,从而出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所言“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9]的接受现象。此类接受现象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近人完全代入《红楼梦》文本之中,从而容易从《红楼梦》文本内容及其意义导向中获取相应的情感共鸣或精神体验。可以说,“必有余恋有余悲”的普遍阅读感受,促使近代知识群体容易将自身与《红楼梦》放在同一层面而细品《红楼梦》文本的深层寓意。当然,《红楼梦》深层寓意的接受形成,仍有赖于近代知识群体基于特定人生经历或社会文化的制约而形成的深究欲望。而近代知识群体深究欲望的有效推行,往往是针对读者自身有所感发而探讨的《红楼梦》寄寓意图或《红楼梦》文本的典型描写现象而言。
在上述品读思路的作用下,诸如时政、风俗、恋情及社会不公等最贴近近代大众日常生活及由此形成的心理期待,或日常消遣的《红楼梦》文本内容,将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所喜谈乐道的阅读感受。这促使近代知识群体形成了一种“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乃至“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9]等具有普遍性社会现象的常用阅读模式。此类阅读模式的广泛存在,使得近代知识群体将自身不幸遭遇借品评《红楼梦》而进行外化排泄的意图得以具备展开的可行性——在言说曹雪芹“哭泣”愈深而情感愈发悲痛的同时,亦借此顾影自怜或借机感怀阅读者的现实处境与理想相矛盾时的切肤之痛。故而,近代评论者认为:“《红楼》等之所以有名于社会者,非徒以其宗旨之正大、理想之高尚,亦以其文学之优美也。故作小说犹筑室焉,道德心其基础,阅历知识其材料,文学则运斧斤之匠人也。”[10]强调以“阅历知识”来品读《红楼梦》的宗旨与理想,以至于形成了有意关注《红楼梦》展现曹雪芹“阅历知识”的阅读史价值。正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年)之《红楼梦之精神》所言“《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出”,以至于《红楼梦》成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典范[11]。近代读者,尤其是寻求科考功名、社会变革受挫的士大夫群体,更是在人生失利、精神困顿之时从《红楼梦》阅读过程中寻求相应的精神排遣,以便借机寻找读者自身困顿现状的“解脱”之道。要之,由于近人认为《红楼梦》“历述诸种人物所受之苦痛,亦即吾人生于世界上所受之种种苦痛也”,甚至以为“不能尽如我意,必一一皆有不如我意之处可知也。然则吾人与之并处,复何法以解免苦痛哉”[12],故往往会从曹雪芹“发愤著书”而联想到读者自身的现实遭遇与理性追求之间的矛盾与苦痛,最终成为近代知识群体关注《红楼梦》文本意义及其阅读视角的普遍态势。
典型之例,首聘之《复友人批评红楼梦书》指出:“阔别多日,辄深萦念,正拟笺候,适奉手书。故人而恙,欣慰曷极。寄来《红楼梦评》,独树新意,煞费苦心。士不得志,则从事著述,立言于天下后世。其兄之谓与,嘱加斧正。聘学识浅陋,且于是书,久未披阅,事多遗忘,何敢妄操不律,作画蛇添足之举?但蒙殷殷垂询,讵敢藏拙,以负雅意?只得就管见所及,以供愚者一得,是否有当,仍望足下教我也。来文题目为‘《红楼梦》作者处境’,则此题根本问题之解决,当先洞悉作者姓名、生平及时代三者,下笔始有把握,不致悬猜虚拟,漫无根据。盖自来名作,并非无病呻吟,大抵悲己陈词,感物立论,且恐伤时触忌,更以寓言暗射出之,以饰一时耳目。司马之史,杜甫之诗,可以知矣。故阅者必明作者姓名、生平及时代,始能读其词而会其意。《红楼》为小说中之佳作,真事隐,假语申,为全部主旨。研究此处,舍聘所举三者奚由乎?”并认为“足下天资明敏,文机畅达,若更努力为之,必大有可观也。是匪特聘所希望,亦将为天下后世所仰慕者矣”[13]。据此,首聘之友人批评《红楼梦》的缘起在于其“不得志,则从事著述,立言于天下后世”,意即《红楼梦》成为首聘之友人排遣现实困顿的解脱之道,以至于促使首聘之友人重点关注“《红楼梦》作者处境”的相关内容;此类内容挖掘,显然隐含透过挖掘曹雪芹不平遭遇寻求与首聘之友人自身经历的相似之处,并使之感同身受。故而,首聘之对友人《红楼梦》予以“独树新意,煞费苦心”的评价,一方面表明首聘之友人作为“士不得志”的一员试图借助《红楼梦》进行日常消遣与精神排遣的评阅行为,促使《红楼梦》作为一种与近代知识群体具有相似知识结构的经典文学作品,逐渐深入近代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中;另一方面,近代知识群体挖掘《红楼梦》作者生平经历的缘起,并不全是好奇使然,更与近代知识群体的现实遭遇形成了同步互动。此类互动过程使得近代知识群体关注《红楼梦》时的情感导向与价值建构是以曹雪芹的“阅历知识”为基础,并形成了“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的普遍态势。同时,首聘之强调“必明作者姓名、生平及时代,始能读其词而会其意”,意图以曹雪芹的生平遭遇如何投射于《红楼梦》文本之中来探寻作品“全部主旨”。此举表明“悲己陈词,感物立论”的阅读思路,已成为近代知识群体评阅《红楼梦》的最主要指导。近代知识群体在阅读《红楼梦》文本时,将会有意无意地探究《红楼梦》文本“悲己陈词,感物立论”的内容与书写特色,借此得以有效推进近代知识群体自身的阅读展开及其阅读体验的获取。这就是将《红楼梦》“发愤著书”说与近代知识群体自身的《红楼梦》阅读排遣相联系的典型。
再如,愿为明镜室主人《读红楼梦杂记》(1874年)亦言:“《红楼梦》小说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为好色不淫,得《国风》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镜主人曰:《红楼梦》悟书也,其所遇之人皆阅历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阅历之事,其所写之情与景皆阅历之情与景。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粉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人生数十寒暑,虽圣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萦诸怀抱,而盛衰之境、离合之悰亦所时有,岂能心如木石,漠然无所动哉!缠绵悱恻于始,涕泣悲歌于后,至无可奈何之时,安得不悟为之梦,即一切有为法作如是观也。非悟而能解脱如是乎?”又说:“‘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已往所赖之天恩祖德,锦衣纨库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半生潦倒之罪不可追。’此数语,古往今来人人蹈之而悔不可追者,孰能作为文章劝来世而赎前愆乎?同病相怜,余读《红楼》尤三复焉而涕泪从之。”[14]愿为明镜室主人从明镜室主人“《红楼梦》悟书”的启示中,看到曹雪芹如何叙述其所“阅历”的人、事、情与景,进而从曹雪芹“悔不可追”的情感中形成一种感同身受式的切肤之情,最终促使愿为明镜室主人产生“同病相怜”的哲理追思。而隐含于“同病相怜”的品评过程中,亦是愿为明镜室主人将自身的人生遭遇暗和《红楼梦》文本的典型体现,以至于产生“吾读《红楼梦》仍欲为宝玉,不为贾兰;我之甘为不才也,天下后世之读《红楼梦》者意云何耶”的情感倾向。
综述之,基于与曹雪芹相同的知识结构且以相似价值体系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特殊知识信仰[15],近代知识群体往往在自身不得志的情况下,通过阅读《红楼梦》文本的日常消遣行为来排解自身的心理困顿,进而深入挖掘曹雪芹的不平人生遭遇如何投射于《红楼梦》文本之中,以便借品评《红楼梦》文本寻求读者自身的人生或精神“解脱”之道。这种阅读态势为现代读者广泛从“为人生”角度展开《红楼梦》品评的普遍化接受,导夫先路[16]。大体而言,明镜室主人、愿为明镜室主人等近代知识群体在当时的落魄遭遇,促使其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发愤著书”的中介找到了展现自身自娱自乐与寓意精神寄托的有效结合点。此类“同病相怜”与感同身受式的阅读思路,不仅促使《红楼梦》成为近代知识群体精神排遣的有效途径,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红楼梦》在近代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消遣品意味。甚至,近代知识群体试图通过赞扬曹雪芹的“发愤著书”或《红楼梦》的有所寄寓来控诉当时现实不公的社会干预式批评意图,最终促使《红楼梦》成为近代知识群体的一种典型心灵慰藉品。因此,《红楼梦》得以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最终有效扮演起近代知识群体之间进行日常交流乃至排遣自身情感与精神发泄的重要凭借。
二、对话交流、“题咏”互动与近代知识群体《红楼梦》阅读的消遣环节
近代知识群体在品读《红楼梦》的过程中,除以私密阅读的方式予以展开外,亦存在着知识群体之间多方交流阅读《红楼梦》心得的公开化行为。当时报刊就刊登了为数众多的近代知识群体通过书写往来(如前引首聘之《复友人批评红楼梦书》)与“题咏”互动的阅读交流;甚至,近代知识群体在日常闲暇之时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亦展现了互相切磋《红楼梦》意见的阅读细节。可以说,日常对话交流与刊于报纸杂志的“题咏”互动,成为近代知识群体公开表露自身如何品读《红楼梦》及其过程环节的两种重要方式。通过报纸杂志的刊登与呼应,使得上述两种互动方式于近代普遍存在并广泛流行。这就愈发促使《红楼梦》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消遣读物,乃至成为时人重要的社交话题。
典型之例,即如邱炜萲(1874—1941年)的《红楼梦》品读。早年参加科考落第、因“甲午”战争“上书”畅言改革不获待见,后流寓新加坡承继家业的邱炜萲(菽园),曾发出“世上谁为知己,容得我狂真知”(《自适六首》)[17]的感慨,而后于新加坡兴学办报资助革命,直至家业破产。其间,邱炜萲逐渐假小说以自遣,并展开了诸多小说作品的评阅工作。在谈及《红楼梦》时,其所撰《菽园赘谈》“小说”条(1897年)曾说:“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此外若《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作,皆能自出机杼,不依傍他人篱下。”这种将《红楼梦》当作“言情道俗”的典型代表,使得近人从中批判《红楼梦》文本寓意的同时,又可以借体察时风异俗之机进行一种因现实不得志而致精神压抑的阅读排遣。故而,“小说”条又说:“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遣,犹贤博弈而已。”[18]“取备消遣,犹贤博弈”的态度,使得邱炜萲亦将自身遭遇与《红楼梦》“发愤著书”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更多时候是从《红楼梦》文本品阅到“言情道俗”之类有助于自身困顿排遣的内容。
与此同时,为学界所熟知的《菽园赘谈》涉及《红楼梦》的诸多论断,则是邱炜萲与友人交流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昭琴《小说丛话》(1905 年)曾记载:“友人邱菽园尝语余以《红楼梦》之妙:‘其写宝、黛两人情魔痴恨,尽由一误字逼拶出来,岂惟宝、黛外,此如小红之于芸儿、龄官之于贾蔷、三姐之于湘莲、彩云之于贾环,亦各有一段误会之情魔痴恨,演出空灵妙文。凡以为宝、黛作正反面陪客也。其写宝、黛两人互相误会,几有大书特书不一书之概,总无一处雷同。虽为腾挪布局,排比大部文字,然非此无以达其情使深、拗其笔使曲,故谓善状误会之事实,则即善用深曲之文心可也。’余曰:‘如公言,《红楼梦》一书,直可改题为《红楼误》矣。’邱君为之莞然。越时,邱君复诘余:‘《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两小说内容如何?’余笑曰:‘两下半皆不佳者也。’然公意固不在此,公意仍在《红楼梦》。‘《红楼梦》后半亦何尝佳?鄙见叙至黛玉焚稿、神瑛洒泪那两回,便可斗然而止。’‘或云曹雪芹原本只八十回,以后四十回为高兰墅所续。语殊不信,微论全书百二十回,文笔一律,无补缀痕。试想方叙至八十回之事实,是可以止而止者耶。曹雪芹为底秃豪而搁笔,必如九十八回乃真可以止矣。’邱君首肯者再。余又曰:‘《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两书,一则自承与《红楼梦》争胜,一则暗点从《红楼梦》脱胎。今观其所叙事,颇与公拈误之一字诀,似有悟入。是亦知欲为情书布局,不从误处生情,情便不深、文便不曲矣……’邱君更端诘之曰:‘夫《红楼梦》既以叠传误会之情为优,若乡人冷红生近日所译法国小说《茶花女遗事》,固情书逸品也。何以描写误字?……’邱君大笑。”[19]据此,邱炜萲多次与友朋昭琴就《红楼梦》展开对话,甚至进行争论交流。所谓“公意仍在《红楼梦》”,表明邱炜萲将谈论《红楼梦》作为与友朋日常消遣时的重要交流内容。甚至,昭琴提及邱炜萲与之交流的有关《红楼梦》后十四回、《儿女英雄传》《花月痕》与《红楼梦》的关系、《茶花女遗事》“情事”内容以及金圣叹评点等问题,大多是邱炜萲所撰《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等书籍谈及小说内容的重点话题。如《菽园赘谈》“小说闲评”条言:“《红楼梦》一书,不著作者姓名,或以为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辞。若因篇末有曹雪芹姓名,则此书旧为抄本,只八十回,倪云癯曾见刻本,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后来联缀成文者,究未足为据。”“《儿女英雄传》不及《红楼》,正坐后半不佳。”“《花月痕》一书亦从熟读《红楼梦》得来……若以视《红楼》,则自谢不敏,亦缘后劲失力故也。”[18]又,《挥麈拾遗》“茶花女遗事”条言:“《茶花女遗事》一册,情书也。”[20]凡此内容,皆成为邱炜萲相关著作谈及的焦点。由此,邱炜萲在细细品读《红楼梦》且由此形成“闲评”之日常的过程中,其又与友人多次进行深度交流,以至于其从对话交流之中获得了有关《红楼梦》认知的肯定意见,也形成了诸如“莞然”“大笑”及“复诘”之类的多种情感体验。因此,品读并与友朋进行《红楼梦》的对话交流,成为邱炜萲进行《红楼梦》日常阅读消遣的典型行为。
可以说,友朋之间的对话已成为近代知识群体交流情感与知识的重要手段,以至于促使近代知识群体能够在阅读《红楼梦》等古代小说之后有效寻求相应的日常消遣,最终促使《红楼梦》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日常消遣的重要谈资而得以深入彼时社会之中,乃至进一步扩大《红楼梦》的“知名度”。当然,近代知识群体品评《红楼梦》的日常消遣环节并非仅限于对话交流,另有“题咏”互动的常见方式。邱炜萲就时常以“题咏”《红楼梦》之作馈赠友朋,并多方向友朋征集“题咏”,最终多次获得友朋的复函之作。如《采风报》1898年8月7日曾刊登李冬沅所撰《海澄邱菽园孝廉咏红楼梦诗题词》[21],以附和邱菽园的《偶阅红楼梦有咏》。《新闻报》1898年7月27日亦登有漱石正刊《奉题邱菽园孝廉分咏红楼梦诸人诗后录请》,其一云:“红楼旧梦已如尘,十二金钗尽可人。难得邱迟抒藻丽,替描心事替传神。”并言:“等身著作早推君(近刊《菽园赘谈》《庚寅偶存》《壬辰冬兴》三种行世),涉笔偏教风趣存。画里真真呼欲出,不须剪纸更招魂。沪上瘦蝶词人程联芳稿。”[22]《采风报》1898年8月9日所登《红楼梦绝句题词应邱菽园孝廉征并邀病鸳芷汀同赋》[23],内容大体与《新闻报》相同。此类“题咏”交互关注的重点,不外乎是《偶阅红楼梦有咏》所言“一刹人间事渺茫,前生幻境认仙乡。如何尽领芙蓉号,不断情缘反断肠”(咏晴雯)[18]之类的情爱不定感慨,以及邱炜萲“抒藻丽,替描心事替传神”的有意之举。这种对情爱的慨叹以及关注《红楼梦》人物命运的聚焦视角[24],正是近代知识群体将《红楼梦》当以日常消遣物的典型阅读选择及其闲适的心境流露。
大体而言,近代报刊所载《红楼梦》“题咏”交互的诗词赋咏,均存在以情言说的倾向。如保溶钧《金缕曲·奉题醉红楼主烺甫词兄〈红楼梦十二图咏〉录尘茂苑赋秋生大方家拍正》所言“风流少年、向十二金钗倾倒”[25]云云。凡此种种,大多展现了近代知识群体“题咏”交互时怡情自娱的闲适情调。据此而言,上引近代知识群体于报纸杂志公开的《红楼梦》“题咏”交互行为,不仅提供了近代知识群体如何展开《红楼梦》阅读的前因后果及其阅读推行的细节,更是促使公开谈论《红楼梦》之举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所不避讳的日常行为,甚至在交互交流过程中相应地获得了愉悦的社交感受。而此类“题咏”交互的大量公开表达,促使《红楼梦》越来越成为近代知识群体借此表达一定情感诉求或社会批评意图乃至展现自身心境的重要手段,从而促使近代《红楼梦》品读逐渐形成一种公众化的视野。这就为现代报纸杂志借机强调《红楼梦》的阅读批评应与当时国家自强、民族自立的公共政治领域相联系,以便建构一种能够激发时人对于国家或民族产生“集体认同”的社会文化秩序等“公共表达”行为[26],作了观念先导与操作手段的调试。
要之,《红楼梦》不仅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排遣人生不得志的重要发泄窗口,而且成为其日常消遣的重要依托,乃至成为近代知识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谈资。而不论是对话交流还是“题咏”互动,皆反映出近代知识群体逐渐广泛地将自身的私密阅读行为进行公开化的公众表达,以至于促使此类公开表达展现出了具有相似阅读选择与心理活动且带有一定普遍现象的群体化接受行为,最终促使近代知识群体的《红楼梦》日常阅读成为其人生经历的重要一部分。
三、近代学堂青年学生阅读《红楼梦》的图像再现
在近代知识群体的《红楼梦》阅读与接受过程中,并不唯士人群体的《红楼梦》阅读颇具典型,近代学堂青年学生亦表现出品阅《红楼梦》的巨大热情,从而出现于课堂教育之中偷偷阅读《红楼梦》的普遍现象,引发了当时学堂教育者的注意与警惕。此类阅读行为对进一步挖掘近代知识群体阅读《红楼梦》的过程环节仍有一定文学史启示。不过,有关近代学堂教育的政策制定、推行环节及历史意义等内容,并非此处讨论的重点。我们仅限基于中国古代小说在近代学堂教育中的接受意义等视角,探讨近代学堂青年学生品阅《红楼梦》的行为选择对《红楼梦》近代接受的价值。
由于近代之人普遍意识到“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2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更是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强调小说具有“支配人道”之力及“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等突显小说社会功用的呼吁[9]。故而,在“小说界革命”的极力推动下,近代对古代小说之于教育启蒙、推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而在社会舆论的宣扬与思想启蒙的多重呼应下,尝试在全社会中强化将小说引入学堂教育之中的必要性与紧迫感[28]。此举试图在培养青年学生知识学习的同时,开展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教育。黄伯耀《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指出“东亚学者改良教育,特注重于小说一科,而群视为钥智之导引也”,“教育之为国民造就资格者,自不能不趋就文学之风气,俾借感触力,而为一般之学生,引掖其智慧之进步也”;但其又指出“读《红楼》也,以为诲淫,而警惕骄邪之意不悟也”,强调对《红楼梦》等小说的不良影响应予以警惕[29]。老棣《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科书》亦认为读小说能够“使读者开心胸,增识见”,小说是学堂“欲求进步”的重要保障[30]。然而,诚如黄伯耀所言阅读古代小说容易对青年学生形成不良影响,近代学堂教育引入古代小说的呼吁,容易导致青年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滋生不良习性。在学堂教育中阅读《红楼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年学生对情爱内容的过分偏爱,从而不利于教育启智。
《时事报图画》1910年10月8日(九月初六)曾刊登《学堂造就红楼梦人材(附图)》一则,借此讽刺近代学堂教育推行古代小说的不良效果(图1)。此则图文属一个版体,版式上方有一段讽刺文字,下方为讽刺图。文言:“鄂属荆南学堂,开办已久。日前荆宜道金峙生观察,特往考查,以该堂岁费万余金,七八年来,靡费已逾十万,而毕业仅两班,非力求整顿不可,遂与各教育员讨论改良。观察谓宜先从管理规则入手,次查功课。议毕,参观校舍,适至高等小学自习堂,见冠者五六人,各手执一卷。观察意必诸生温习功课,遂入室检阅。不期各执《红楼梦》一本,观察大不谓然,即面斥监学,云:‘国家一年用去若干巨款,造就一班《红楼梦》人才!’该管堂教员,均面赤耳热而去。”[31]虽说此则讽刺图画强调的是“荆南学堂”的个案现象,但从黄伯耀、老棣等主张推行古代小说进入学堂教育者的担忧看,《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近代学堂教育推行中扮演起反面角色。而彼时青年学生热衷阅读《红楼梦》等小说,且从讽刺图画所刻画青年学生阅读《红楼梦》时的各种身体动作及神态而言,皆是十分入迷的——图中所绘四位青年学生均将《红楼梦》高举眼前,近距离且目聚以视,生怕错过书中任何一个字眼。其中,一人西装笔挺而正襟危坐,左手搭大腿,右手捧书,似乎正看到《红楼梦》文本关键之处而略显紧张;紧接左边一位穿白色西装者,两腿交叉,背微后仰,显然是一种悠悠的阅读姿态;再次左边穿黑色西装不戴眼镜的学生,几乎眼睛紧贴书上,更显入迷之态;背对这三位而留辫子的阅读者,则一旁偷偷阅读,生怕被其他同学发现其在阅读《红楼梦》似的。图中所绘人物阅读场景可谓十分传神,表明《红楼梦》已占据近代青年学生课后安排的中心地位。总之,此图所绘四位学生,既有新式学生亦有坚持传统者,借此寓意《红楼梦》在青年学生当中并不受身份阶层或知识结构、文化观念所限,皆是深深喜爱之。

图1 《学堂造就红楼梦人才》
应该说,此图所绘诸多细节并不一定完全是实有的,却是当时之人对同时代青年学生日常阅读与学堂教育近距离观察结果的真实再现,也是《红楼梦》深受当时青年学生喜爱的细节表征。因此,此图对于了解近代青年学生阅读《红楼梦》的接受意义在于:从爱情故事的精神感染力或人物情节的艺术感染力而言,《红楼梦》不仅成为近代教育改革者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助力,而且成为近代青年学生日常阅读不可或缺的消遣物。甚至,近代青年学生于课堂及课后集体性的偷偷阅读行为,直接展现了《红楼梦》在近代青年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此类阅读现象一方面表明《红楼梦》阅读已成为包括近代青年学生在内的所有知识群体日常消遣的重要一部分,从而引发当时人对相关阅读现象的关注;另一方面,《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在当时的广泛阅读已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以至于促使近代制度或思想变革者对《红楼梦》在教育启迪功用上的否定,最终加剧《红楼梦》全民阅读接受的道德阻力与舆论压力。从这个角度讲,近代学堂青年学生阅读《红楼梦》的细节式图像再现,反映出近代知识群体的《红楼梦》阅读可以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的情形下,一定程度上突破时代道德藩篱而予以自由展开。
四、小结
据前所述,由于近代社会变动、文化更迭导致当时知识群体进身之阶的逼仄,进一步加剧了近代知识群体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近代知识群体形成以著书立言来表达理想或情感的普遍诉求。这种诉求现象势必促使近代知识群体通过一定的写本读物予以展开,以便能够有效地将自身的不平遭遇、人生理想及现实改良诉求等多重情感连接起来。因此,作为一种既能够推进近代知识群体日常消遣的持续展开,亦能够引起近代知识群体之于社会、人生及情爱等方面的阅读感受与兴趣,同时能够满足近代知识群体排遣现实困顿的精神苦痛或心灵创伤并得以成为群体之间互动凭借的重要读物,《红楼梦》一书被近代知识群体广泛接受、成为其日常消遣的主客观环境皆已具备。因此,近代知识群体在精神排遣与日常消遣之间的复杂心境下关注《红楼梦》“发愤著书”与进行阅读消遣的普遍接受行为,最终演变成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于近代的广泛存在,表明近代知识群体困顿遭遇的严重性,以至于近代知识群体有意通过展现自身品评《红楼梦》的过程环节来进行深度的精神排遣。可以说,近代知识群体除了自身发愤著书以示个人心境外,基于《红楼梦》等重要读物的品评、“题咏”写作及群体之间的交流行为,更能推进近代知识群体在精神排遣与日常消遣相结合下的困顿消解,亦有助于更深入展现近代知识群体将自身困顿心态公开表达以便获得时人多方认可的倾诉意图。从这个角度讲,近代知识群体对诸如《红楼梦》等重要读物“发愤著书”主题的深入肯定,或者对此类读物文本内容肯定或强烈向往之意,甚至诸如近代学堂青年学生普遍偷阅的典型行为,表明近代知识群体面对社会现实的无力之感是深切的,对自身困顿状态的无奈之叹亦是深刻的;甚至,对话交流、“题咏”互动程度的突显,愈发显示出近代知识群体困顿心态的严重性。可见,基于阅读史视域,可深入探讨近代知识群体如何采用一种类似于“场景视域”[32]下交互性、体验性的手段而尝试身临其境式进入《红楼梦》文本中,以便揭示近代知识群体日常阅读的典型心态及其历史意义。这方面的探讨应引起更多注意,以便进一步从中国古代小说阅读史迹挖掘不同时期知识群体的日常心态及其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