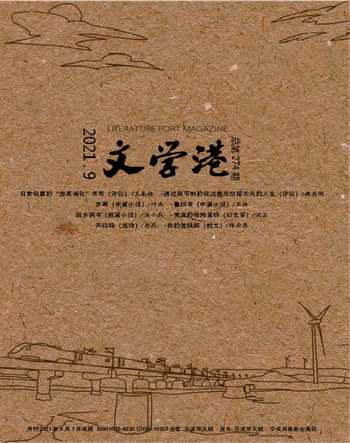我的登陆艇 /陈云其

陈云其,诗人,散文家,词作家,国家一级导演。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中国当代军旅诗坛的重要诗人,其海洋诗水兵诗影响深远。
著有诗集《桅顶上的眼》《往事深吻》《低下头并且记住》《一生都在下雨》《两朵云的故乡》《渐离》《利刃划过时间》等,歌词集《送你一朵黄玫瑰》,艺术专著《晚会策划与导演》,散文集《日影如尘》,旅行笔记《高原伴旅》。
……
我把蓝带到大地
我把蓝带给灯光和窗口
一不小心我成了诗人
我是无意的
我就是蓝……
——摘自旧作组诗《海水回来》
密集的炮弹在水里爆炸,海水陡立起来,像一排排屏障。水花飞扬,整个海洋变成了一片芦苇荡。那些白色杳濛的花,在所有空间里开放,阳光变得寒冷。
轰炸机群在水柱的上空,它们从云层里蹿出来,呼啸着——形成扇面队形。机翼下的炸弹拉着斜线,准确地落在滩头敌方阵地里,火光迸发,硝烟弥漫。
那是1976年的夏日。邻着台湾海峡的海区。
中国军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三军登陆演习。我作为操弄灯光和手旗的信号兵,被分配在由高速护卫艇组成的战斗序列里。
东山岛支前站,排列着一百口棺材。
实弹演习的伤亡,按照参演部队人数,被允许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让所有战斗人員真切地感受到战争与生命的严酷。
我会是最终躺在棺材里的人吗?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恐惧已不存在。它让我突然回到冷兵器时代抬棺出战的英雄壮举里,死亡被勇气所蔑视,献身是如此高尚。
火光和硝烟逐渐向滩头阵地的纵深推进。
登陆艇开始在轰隆声中抢滩。
这些装载着坦克和特战队员的登陆艇,以扁平的艇底,碾压过海水及沙滩,以横线的队形冲刺着,作最后一波的海上攻击。
它让我想起诺曼底,那些燃烧的橡树和路障。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具教科书意义的盟军诺曼底登陆,从根本上宣告了德国军队溃败的时间表。而在英美造船厂里被大批制造出来并秘密集结的登陆艇,成就了诺曼底一役最为壮观的进攻画面。太阳苍白,死尸横陈,海水一片腥红。
我是临时被抽调到护卫艇信号岗位的。
恐惧与紧张,随着艇上三七炮第一发炮弹的出膛发射,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海水陡立,让我成为诗人。
很久以后,我驻足在古雷头兀立的礁石上,眺望那片海,眺望那些在梦里不断浮现过的年轻面影。现在,他们都已衰老,和我一样。但他们依然在海面上行走,他们的一生不可能走出那片海区。
东山岛的烈士陵园肃穆着,我是唯一的祭扫者。石碑上冰凉的名字,在我苍白手指的抚摸下绽开笑容,像海水一样温暖的笑容。
往事被提醒,尤如冬天被雪花提醒。
1977年寒冷的季节,我来到新组建的登陆艇大队,被重新编入蓝色战斗序列。所有的登陆艇企望着那道海峡,昭示了当年的决心。
我始终记着如下地名:
下白石。
三都内澳。
东冲口和西洋岛。
那道浅浅的海峡,无数次被我的登陆艇填充,就像书法的方格被遒劲的魏碑形神所填充一样。战争呈现出诗意的一面,也许是年龄的错。对英勇的崇尚和对金钱的崇拜,若锋刃划开时代,我因此常常羞愧。
每当海水回来,如母亲一样回来!
如歌的潮汛及白梨花,我难以自已。
三都岛西侧的海滩,是当年我们艇群的营地。五十吨位的登陆艇,可装载一辆坦克或一个排的登陆作战兵力。十三人的战斗编制,分别为航海、轮机、报务、枪炮及信号。前舱有六个铺位,后舱置八张吊床。床宽不超过六十公分。也就两平方米的伙房,大家轮流当老炊。艇上配备两门小口径的可平射亦可仰射的炮位,记得是二五口径的炮。
钢铁凫浮于水——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
在钢铁铸造的空间里,居然有老鼠和蟑螂。它们在夜间熄灯后出没,咬我们的裤衩和女朋友的信件,把水兵梦里乡愁咬得支离破碎。
有一回,突然出现一条蛇。顺着缆绳爬进钢铁的花蛇,跟随了我们一次航程后,又悠然地回到高岸。这条蛇有一米来长,风浪大的时候,它蜷缩在沙箱里,晕得一动不动。
我是艇上的老兵,是新兵蛋子眼里的凶神。艇上最怕我的是枪帆兵王留成。
王留成上艇第三天,在厨房帮我烧了一大桶水,然后他十分讨好地叫我:“老班长,你先洗,你洗完后我再洗。”他浓重的苏北口音,把“洗”的发音变成“死”。这个纯朴又热情让我先“死”的王留成,我罚他洗了一个月全艇兵的裤衩。
登滩的日子是寂寞的。集体出操,集体拖甲板,集体读报。
人被圈在几十个平方米的钢铁之中,除了唱歌偶尔使钢铁空间变得温暖些,再就是写信和读信了。只有星期天,艇上才热闹起来,士兵们比赛着擦亮皮鞋,然后去不到一百米的三都街上昂首阔步。那条街上有门诊部的小护士和邮局、储蓄所、书店的女营业员。
光芒开始闪现。
爱情变成臆想,变成那条花蛇。
在寂寞着的荷尔蒙高潮的时序里,光芒虫一样蠕动于我们体内。是诺曼底炸弹爆炸后溅起的水花——它们亲吻了天空的灼热玫瑰,瞬间又消逝。
那天是周末的电影,放《追捕》。
我记得有这样台词:你跳吧,跳下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第一次发现女演员是可以性感的。在高仓健冷峻的表情里,我们被有着蛇一样身段的真由美搞得神魂颠倒。
电影场是快艇支队的水泥操场,正好紧挨那条一百米的岛街。士兵们看电影得点名排队,每人提一张小马扎,从登陆艇的滩头营区走着去,回来也得排着队走,只是不点名了。
副艇长阿国龙却在电影散场后失踪了二十分钟。这段时间阿国龙去干什么了呢?其实我知道,都是被那真由美的水蛇腰给扭出水波纹了。爱情若海,不能有风。
但我不能说哥们犯纪律的事,何况阿国龙和我是乡党,军营里亲不亲老乡分呀。
我们的中队政委姓权,有三十年军龄。爱喝酒,这么多年才混了个营干。
第二天中队点名,喝了酒的权政委说:“好你个阿国龙,昨天夜里那二十分钟你干嘛去了?二十分钟呢,同志们!电影场外有女人。”
阿国龙好上了街上邮电局的杏儿,我们都知道。那姑娘对阿国龙是真好。阿国龙坦白说,和杏儿拉过两次手。
尽管阿国龙是排级军官,但部队条令明确规定不能在驻地找对象,一经发现就得处分。酒后的政委网开一面,要阿国龙赶紧把家乡那位养猪的姑娘娶了,否则后果严重。
海水陡立,如同光滑石壁。
我和阿国龙坐在高高的天台山上,不说话,任时间默然流动。我是好不容易打听到阿国龙副艇长的,他的真名叫叶荣正,四方脸,小眼睛,憨厚老实。他从登陆艇回到天台国清寺背面山村,先是在县里工作,后来帮老婆开了个养猪场,也种茶叶。
三十五年是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
是佝偻的腰,是眼角深刻皱纹,是上山得走几步喘口气。人到花甲,照在身上的只有夕阳。我没有见到应该叫声嫂子的副艇长的老婆,阿国龙说她去县城女儿家了。
我们无言地坐在天台山上,风掠过鬓发。
海水和风景却突然回来!西洋岛外海,阵风达到九级。
艇体剧烈摇摆,甲板上水深淹过足踝。乌云低压着,似乎倒悬的海水。浪不断奔腾,是在我们的身体里奔腾。我们必须在台风过境之前把一条渔船给找回来,这是任务。
蟑螂和老鼠都晕得呕吐。
阿国龙提只铅桶套在我脖子上,他喊着吐在桶里啊!信号位在驾驶室上面,全艇最高位置,摇摆度最大。我朝阿国龙吼,让他赶紧叫王留成拿条绳子来。我只有拿绳子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才能稳住身体。这回王留成同志没让我死,但他报复了我,捆我贼紧。
艇若一枚落叶,滔天大浪里只有绝望。海水顺着后脖往衣服里流,浑身湿透。
望着发黑咆哮的海水,恐惧无声无息地弥漫。新兵时的实战演习和反小股特务,我都没这样紧张过,突然明白炮弹呼啸水花冲天,是可以驱除恐惧的。死亡那么近,但你抓不住它。
你只感到心在发虚,并从此唾弃了那位唱战舰轻轻摇,军港如诗如画的女歌星。
我们用勇敢导航
穿越死亡洋面 穿越群狼
牵着台风这野兽的鼻子
我们回来……
这是我后来写在信号方格纸上的水兵诗。
现在读来,总觉得对不起阿国龙。那次正好艇长休假,是副艇长阿国龙带领我们生还的。
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和阿国龙从此没见过面,尽管他救过我。
婚礼是在那次海上抢险后举行的,阿国龙养猪的妻子,给艇上的士兵们带来了一大包自己炒的花生瓜子和番薯片。她圆脸,总是笑着,让我们在经历风暴后,突然看见一轮安静的太阳。
这样的太阳,美国大兵威尔逊也一定看到过,海明威肯定也看到过。在诺曼底浪涛喧嚣以后,在死亡吻别最后那位渔猎者之前。夕阳,把存在的一切都拉成长长的影子。我知道海水也是能拉长的,就如把我绑在桅杆上的那条绳索。
水兵的服役期为四年。穿呢子服,低皮帮靴;吃一元二毛七的伙食。水兵让当年的年轻人羡慕。要知道那年月的职工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得养活一家子。
我们中队部养了两头猪,猪吃水兵灶的剩菜剩饭,长膘风吹似的快,油光满面。权政委说这猪过年宰,要灌血肠。
我对餐饮的兴趣以及不学自会的厨艺,是登陆艇赐予的。十几个人的伙食单位,每月有六七百元的伙食费。那得天天变着花样吃,早上炸油条,做粢饭糕,蒸牛肉花卷,煮大白米粥。中午和晚上确保四菜一汤。周末加菜,喝酒。
陆军兄弟看着眼馋,他们只有四毛八一天的伙食,每星期见不了几回油腥。水兵还趾高气扬,自由散漫,因此,陆军兄弟除了羡慕还生嫉妒。一回,我们送陆军兄弟一个排去西洋岛,内澳行驶,风平浪静,那帮哥们如坐游轮,兴奋得前后甲板乱蹦跶。没料想,登陆艇一出东冲口,排浪袭来,暗涌蠕动,不一会儿,全排兵们吐得翻肠刮肚,不敢动弹,个个东倒西歪,一地狼藉。艇抵西洋岛,领头的指导员高呼向水兵致敬,他们再也不奢望那每顿饭的四菜一汤。陆军指导员是东北汉,他说艇上的活不好整,吐出来的比吃下去的多。
风浪太大,航途时间长了,我们也呕吐。
轮机班长吐,报务员小诸吐,艇长偶尔也吐。但凡当过水兵的都知道,吐完了必须吃,吃了再吐,这样才能过晕船关。
水兵几乎都有胃病,职业病。
轮机班长叫贾祥来,比我早一年的兵。
机舱狭窄、油腻、噪声大。他晕船厉害,只要机器一发动,就叫手头两兵在下面值班,他独自坐在梯子上,把头伸在舱口。我给他起个绰号,叫“曲项向天歌”。后来大伙儿都这样尊称他,他感觉挺好,这名字有股子诗意。王留成不这样叫,王留成还是喊他贾班长。后来王留成入党,他是介绍人。
贾祥来胃病重了,住院。我带王留成去基地医院看他。
医院里女兵多,很多艇上老兵包括连排级的军官喜欢找点病去医院。但贾祥来是真病,十二指腸溃疡。他跟我说这病恐怕一时半会儿治不好,又担心手头两兵不会捣鼓机器,耽误春季海上编队科目训练。我说要不你偷偷出院,我替你住几天院。王留成在旁边着了急,王留成说:“贾班长,机器的事你放心,你得把病治好,我把你‘孩子’都带来了。”贾祥来一脸紧张迷惘:“王留成你小子别瞎说,我哪来孩子!”王留成一副委屈样,他说贾班长是你的“孩子”。说着从军挎包里掏出一双布鞋。这回又是他苏北发音惹出的笑话。“孩”与“鞋”居然是同音,连声调都一样,属平声。上次让我“死”了,这回给他的贾班长弄出个“孩子”来。
贾祥来老家在曲阜,孔夫子诞生之地。探家时谈了个对象,也是农村的。
那对象手巧,给贾祥来绣了一堆鞋垫。王留成从艇上给带来的那“孩子”,也是她亲手为贾祥来缝制的。千层纳底,青绒鞋面。王留成说班长好福气。
新千年的头一个春节,我从泰山去曲阜,从孔庙出来见一推车卖烤红薯的老汉,他蹒跚地走在寒风里。那天出奇的冷,屋檐下的冰凌滴着水。我梦醒似地喊:“曲项向天歌!”但他没有回头,整个身体紧紧裹在那件已经破旧的深蓝色布大衣里。
雪花飞进我眼帘,我觉得眼睛里的温湿。为往事流泪,在这远离海洋的内陆。
我觉得自己不可理喻,居然不喊他的大名,居然不急忙追上去。我感觉自己是寒风里的一块礁石,身上布满风浪噬咬的齿印。孤独着,被人群所冷落。这样的感觉也属于复员后的贾祥来,属于所有经历长久风浪后回到岸上的人。
贾祥来后来被确诊,是胃穿孔。他三分之一的胃被手术刀切除。只有他的机器声,穿透海水和涌浪,依然在那么完整地运转着,就像大海心脏有节奏地搏动。
夏天终于来了。三都岛中午酷热,早晚倒是凉快。海洋的潮流在夜晚带走热气,把凉爽送到早晚间的每一块滩头上。
权政委宣布中队成立文艺演出队,准备参加登陆艇大队组建以来的第一次会演。中队16艘艇,每艇抽调两三名人员,要我出任副队长。队长是会敲扬琴的林指导员,泉州人。权政委说你俩团结配合争取前三名。
文艺演出队的排练场安排在猪厩边的坑道里,那地方阴凉空旷,唱起歌来回声好。那两头猪每天都成了我们的忠实听众,它们兴奋时也会嚎上几声来加入我们的合唱。
权政委晚饭后会踱步视察那两头猪,顺便也把我们的排练给视察一遍。他听了我写的《登陆舰之歌》后大加赞赏,说到冬天宰了猪一定犒劳我。
阿国龙派王留成来看望我三次。
有一次他说新来的信号兵在出海训练时犯了大错误,把指挥艇发来的灯光信号“返航去下白石运给养”,收译成了“返航去厦门运鸡鸭。”他还说远洋公司来招复员兵,枪帆班长已经谈了话。对第一条消息我不以为然,那新兵不是我带的。但我对枪帆班长被分配去远洋公司当水手有点忿然,那家伙打拖靶,十发炮弹倒有六发脱靶,严重影响全年的考评。怎么不是贾祥来呢?他可是技术兵,一听机器声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有一回38艇机器故障,大队部的轮机业务长都束手无策。贾祥来也不下舱,坐在舱口说发动主机,不出三分钟就找到病根。王留成说贾班长不会有戏,枪帆班长有个同村老乡在基地训练处当副处长呢!
每天,太阳从东冲口升起来,它把三都这座水兵岛一寸一寸地照亮,然后收走它的余晖,让我们看礁头高耸着的黝黑山峰。
那个夏天我痛苦不堪,除了在坑道里带着一帮兵吼唱之外,我找不到还有什么能安慰自己。我甚至憎恨太阳,憎恨它的光热带给我每天的期盼。
龚中民的死讯是厦门那边老乡传过来的。
护卫艇大队在东山港组织武装泗渡,龚中民却突然在海水里消失了。他在第二天被打捞上来,脸色平静,身上的冲锋枪和子弹带一样不少。
我和龚中民一起当兵,一起参加信号训练班。在礁尾港温热的海水里,是他教会了我游泳,让我这旱鸭子不再惧怕海。我们俩是走得最近的老乡,是兄弟。
1976年的登陆演习中,我和他被编在护卫艇的同一个战斗序列里。在灯光手旗的语言中,我们互致平安。他看到第三波攻击时,我所在的42号艇被舰炮所困而焦急万分。他后来告诉我,如果我们艇撤慢十分钟,可能就葬身在炮弹中了。他说他在指挥艇信号位置上看得清楚。
我在第二年年底调离护卫艇后,和龚中民一直保持着军邮通信。知道他在准备探亲假,说回家的包裹里有10斤花生,是东山岛的沙地花生,颗粒饱满,吃起来特别香。
那天傍晚,我走出坑道。我在余晖中,把一捧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撒向海水。我能看见海面上那张白皙的常挂着微笑的脸。
龚中民被埋葬在东山岛烈士陵园里。我们曾经去支前站看过那100具棺材。
我始终记着从宁波到鹰潭的新兵专列里,他偷偷拿出一把小提琴,为满车厢的新兵演奏那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曲。
从他指尖上泻落的音符
跌落在波涛
它们变成鱼游来,围绕着我
就像一朵朵湛蓝的花围绕着我……
这是我后来写给他的诗歌中的句子。陵园安静,能听到风里的涛声,还有依稀小提琴的旋律。我把诗稿烧在他坟前,看纸片在火中飞起来,如黑色海燕在浪间飞舞。
大约在龚中民死讯传来一星期后,我的艇队出海回来,上半年海上训练科目全部结束。但一个噩耗却更让我震惊,我如同遭受电击,文艺队二十几号人当场僵立。坑道里没有一丝声音,静得可怕。
事故出在我们中队的42号艇上,枪帆兵小王殁了。刚入伍才一年的上海兵,阳光、帅气、上进,渴望青春在海战中闪耀。但一条缆绳却夺走了他生命。和龚中民一样,无声无息地倒在岗位上。
42号艇那天是在码头加水,因为礁头方向有条运输船有物资装卸,岸上信号台发信号要42号艇迅速离开码头。艇在倒车时,趸船缆桩上的绳缆没能及时解脱,绳缆瞬间绷紧,小王正巧站在绳缆圈内。绳缆若一条毒蛇,盘缠勒住了小王的颈脖。倒下的时候没听见一声哼,没见一滴血。
十年后,我在京城魏公村斑驳的枣树阴影里,写下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碰垫》,发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上。
槍帆兵小王,临死前手里还紧攥着一只碰垫,那是他的岗位职责,以避免艇体在离靠码头时刮擦和硬碰受损。
碰垫在黑夜里升起来,一颗黑色的太阳。
海水如血液般流经我们的身体,腥咸、动荡,并带着不可预知的暴躁和永远都猜不透的秘密。
那是1979年的夏天。同样的牺牲,但不同于我已经历的1976年的夏天,更不同于1944年的诺曼底——那个夏天。
300万盟军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向诺曼底百余公里扇形的滩头发起攻击。他们呐喊着排山倒海地冲锋,视死如归的精神撕破火力网,生命在硝烟火光和震耳欲聋的声浪里,跳出最为壮烈的舞蹈。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登陆作战。盟军参战的飞机达到13700架,其中有轰炸机5800架,战斗机4900架;遮天蔽日,呼啸和爆炸窒息空间。而英美海军倾其所有,海面上结集了5300艘战斗舰艇,包括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4126艘登陆舰艇。整个英吉利海峡充塞着凫浮的钢铁,工业以其摧枯拉朽般的力量压制了汹涌海浪。
天空中,瞬间就有成吨的炸弹落下来。海面上,爆炸的巨浪犹如海啸,天地顿时失色。而滩头阵地,火与血厮咬迸发,每分钟就倒下数百名士兵。
当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抽着玉米芯烟斗踏上诺曼底时,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胜利在他的这一边,底蕴是当年世界反法斯的正义。
60万的德军在那里灰飞烟灭。
8万具士兵的尸体,倒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它也成就了斯皮尔伯格的战争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最为惨烈的奥马哈登滩一战,盟军显示了其海上舰艇的绝对实力。于是有了美军第五军司令官杰罗发给其上司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利的那份著名电报:“感谢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是的,在二战最残酷的时候上帝复活了,如同信仰活了过来。
我去敲权政委的门,但他始终不开。因为小王的死,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三天。这位参加过南下战役的老兵,声嘶力竭地从门缝里扔出来一句话:“咋就不能评个烈士呢?!”
我也感到内疚,在挑选文艺演出队人员时,本来有小王的名字。小王是城市兵,高中毕业,会唱歌,口琴吹得特别棒,我问权政委要人,但政委和中队长一商量,却卡了下来。原因是42号艇正担任码头执勤,中队长发话:“其他艇上人员都可以动,执勤艇只的岗位人员一个都不能动。”
其实是有变通办法的,不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枪帆兵吗,调换一个就行。但我没有死皮赖脸坚持。大伙儿管小王叫新兵蛋子王上海,他有点臭美,爱在脸上抹点香头上涂点蜡,他的阳光帅气里不乏小资情调。中队长说:“这样的兵要狠劲地在风浪里捶打。”
登陆艇全年训练科目有一项对岸射击,模拟登陆前对滩头敌军阵地作火力压制。中队的检靶报靶组由我领队,每分队派一个兵作检靶员,那一次就有王上海。我让四个兵各自蹲守一个靶位,自己在岩石后的掩体里抽烟。
12.7口径的机枪声刮风似地响起。子弹溅起的泥石和折断的树枝在靶场纷飞。
王留成和我同一个靶位,枪声一响,他就使劲捂住耳朵,嘴里却嚷着:“辣个妈妈不——开——花!”王留成胆子小,我能触觉到他双腿在发抖。
在枪声的间隙里,突然从四号靶位置传来口琴声。那声音就像在汹涌的海平线升起一朵云霞——会唱歌的云霞,它使恐惧和不安潮水般退尽。那声音里有蓝天的鸟鸣,有白桦树的摇曳,有爱情的吻别。
王留成不再紧张,他说:“老班长,是王上海……”是的,是王上海那个新兵蛋;他小小的口琴居然给我们那么强烈的想象和感染,战地如此浪漫!我们听他的《喀秋莎》,听他的《山楂树》和《红莓花儿开》,琴声里有辽阔的大地,英雄岁月,激情燃烧。
直到现在,那口琴声一直活在我心里。那是我們的“致青春”。
小王的死,被作为事故处理,因为艇离码头没有按程序操作。42艇的艇长被记大过处分,分队和中队的军事主管也都背了个处分。其实,真正的肇事者是那艘给养运输船,它靠码头时没有减速,逼得42艇做了一个出人命的高速规避动作,但接受处分的干部没一个有怨言,他们都陷于自责与痛苦中。
权政委终于出现在我们排练的坑道。他铁青着脸吼:“拿不到第一,你们都别回来见我!”他回头又扔给我一句话:“你要多少人合唱,我都给你。”
会演如期进行,是在快艇21支队的水兵礼堂。
我们把《登陆艇之歌》唱得排山倒海,唱得如此悲壮。听不到旋律,只有前进的跳跃的节奏,那是推进器的节奏,是波峰浪谷的节奏,是热血汹涌的节奏。它澎湃着托起神圣蔚蓝,在一个惊天炸雷中突然静止——死一般的静!
120个水兵,变成了礁石的雕像。
掌声暴风雨般响起。
我看到台下权政委沧桑的脸上,有一滴晶莹的东西悄然滑落。
第一名的奖品是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只搪瓷杯,印着三条蓝波纹和铁锚。
文艺队解散后,权政委希望我留在中队部担任文书职务。我坚决说不,哪有水兵安耽在岸上的,我得回艇上去。但我保证中队每年的年终总结一定会写。当年,像我这样肚子里有半瓶子墨水的兵不多,政委视为宝贝,时不时让我到中队部写各种稿子。我们的关系有点不像上下级,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耍脾气。艇上的士兵们调侃我,叫我政委影子。
我离开登陆艇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位一生戎马,从陆军转到海军的老兵。他退役时依然是营级干部,因为资格老,破例进了周宁县的干休所。听说风浪带给他的严重关节炎和胃病,伴随着他的晚年。他依然喝酒——如啜饮台风那样地喝酒。
太阳在厚厚的云层里,它出来的时候,海滩油光发亮。登陆艇齐刷刷地排列在滩头。潮水退尽后,艇平坦的底部就搁在海滩。远远看,像一只只海龟趴在潮头,它们企望着岸上的绿树、繁花和盛满春风的窗台,报以会心的微笑。
我把自己关进厨房。
我不关心岸上的眼光怎么打量或者形容,看似平坦又笨拙的登陆艇。诺曼底离我们那么远,那场战役里锋芒无限的事物,终究会在岁月里暗淡。海峡的风浪正逐渐地被一个女人的歌声覆盖,爱和忧伤同时作用着大陆的内心。海峡最终需要的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登陆艇。但是我和我们的青春不可能改变;无奈、悲愤,曾经勇敢的向往,如同夜潮纷涌,不在其中者不可能感受生命之轻。
在两个平方米的厨房里,用案板作书桌,借助昏暗的舷灯,铺开信号练习纸,我写下了诗歌的第一行字:“我属于海”。
……也许/我会在一次
海战中牺牲/鲜血染红海魂衫
英雄肝胆/海天高悬
但也许/我只是默默地
死在航程中/倒在风涛里
没有隆重的追悼/只有深沉的惋惜
那时/朋友
你又会怎样对待/这不幸的消息
……朋友/我希望于你的
不是眼泪/而是如我/对待海那样地
对待信仰/对待真理
……我会鼓足战士的勇气
整理好出海服/擦拭好火箭炮
沿着昨天的航迹
去保卫每一朵浪花/每一束阳光
……
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抒情,近200行的句式,让我亢奋疲惫了一整夜。我只想说出一生的遗言,它是湛蓝的,孤独寂寞的;它伤口里深藏的玫瑰,是那样地易于粉碎。我是一个倾诉者,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两者之间只有波浪——无始无终的波浪。
《我属于海》在《解放军报》发表时,距1979年那个夏天已有一年多。但诗的传播远早于发表的时间,在我的艇队,它最早被写在黑板上,然后被油印扩散在三都岛的所有舰艇部队和水兵之间。它只属于那个依然有热度和激情的时代——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时代!
“高举着波浪我从海面走过”,我被称为水兵诗人。但我至今都弄不明白,是我在写诗还是诗在写我?
缆桩、碰垫、速率球、太平斧和沙箱。
呕吐、绣球疯、关节炎以及望不断的海水。
这些词所关联的故事与情感,是那么遥远。
而真正能打动内心的,都在这些不太为人知的诗歌构件里。它属于水兵的世界,属于我们白日梦呓。
记得贾祥来的婚礼是在艇上举行的。按照条例,超期服役的老兵可以结婚。
我们把还算宽敞的前舱布置成花团锦簇的洞房,士兵们使劲喊:“背新娘!背新娘!”贾祥来如听到命令似的,毫不犹豫地背上新娘踏上跳板。跳板架在艇首和堤岸之间,板宽不超过50公分,看着就有点悬心。但贾祥来犹如杂技高手,背着媳妇健步而行,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被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胃且有严重关节炎的人。
“老水兵背媳妇,履波浪如履平地”,这是证婚人权政委的开场白。
我们围着这对新人唱歌,唱得波浪翻滚。
贾祥来婚后一个月就退伍了。
他是特意让订了婚的媳妇从曲阜农村老家,辗转千余里赶来艇上结婚的。当他孤独地离开之前,他想给艇上的哥儿们留点喜庆和欢乐。他也想陪过了门的媳妇看看海,看看登陆艇。
多年不见雪的三都岛,那天早晨却洒起了零零碎碎的雪。
我送贾祥来到码头。
临别,他将一叠鞋垫塞在我手里。他说,是媳妇这些天绣的,艇上的弟兄一人一双。我突然无言,眼眶里充满泪水。我看着贾祥来转过头去,他不愿意我看见他掉泪。“多给我写信呀!”他说这句话时明显哽咽。
同样的冬天,只是不同的时空。
我站在曲阜寒冷的风里,看那个佝偻着背推着烤红薯车的老汉,他真的是轮机班长贾祥来吗?
那一轮复员,枪帆班长如愿以偿,去了远洋公司。这是从农村来的复员兵最好结局。
我也是被宣布复员的其中一个,但半途被基地文化部门给截了下来。其中内幕,很多年后我才知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对这常识的解读每个人都一样,但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是不能用常识解读的。
我们为待机时来回传递的一杯淡水感动。
我们为航路上跟随的鸥鸟感动。
我们为锚泊地舷窗里的斑驳月光感动。
我们也为在钢铁利齿中生存的蟑螂和鼠类感动。那些细微或者丑陋的事物,一旦和寂寞辽阔的海洋发生关系,都变得伟岸和美好起来。我把这样的精神写进诗里,并希望通过它来关照我的灵魂。而诺曼底就像是一场夢,那个叫瑞恩的大兵会坐在黑夜的浪岗上,和我们默默地抽烟。
高蹈之海
万物钟情于你胸膛,我钟情于
你砥砺英雄魂魄的浩浩荡荡
铺展开这红氍毹
以豪门的盛宴邀请天地诸神
你牵太阳的骏马催我上路
你让我的身体熠熠生辉
用大潮沐浴,用飓风吹鼓起我金锚飘带
用一千次的死换一千零一次的生
用你的声音唤起所有的声音
……
我在锚地里写下我的献诗,我为西太平洋赋予我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而长久的激动。诗歌将穿透死亡,它散发着腥咸的光芒,会一直伴随我的生命。我庆幸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并走进水兵的队列。
1977年12月,我们从下白石船坞整装出发,去湖州造船厂接艇。“我们”,包括了阿国龙、王留成、贾祥来共九个人。
我们开着登陆艇顺运河而下,经停上海港,出长江口后,走大戢洋、磨盘洋、大目洋、过舟山群岛、渔山列岛、上下大陈岛、南北麂山列岛;然后是沙埕港、福宁湾、西洋岛,进入目的地三都内澳。
那一路波涛不惊,鸥鸟随行。星罗棋布的岛屿镶嵌在水兵心中,并成为我诗歌中与祖国相关的形象和标点。
我永远记着“0037”的白色舷号。
这生命密码中的数字,从此影响着我对所有事物的看法,那是近乎固执的不可改变的习惯。它就像一个人的生日,冥冥中关联的命运。而海水四围的三都岛,承载了我们记忆中的那一份永恒的青春感动。
岁月之手,偶尔会翻开“0037”艇的花名册。
尤如退潮后突然兀立的礁石——你们在我温暖的海水中,伴着小提琴和口琴的声音。
小顾,枪帆兵。圆脸,矮个,唱歌经常跑调。喜欢在锚泊地用箩筐逮鱼,上他当的鱼叫鬼婆鱼,三指宽,脊长硬刺,味极鲜美。
大范,枪帆兵。身高1.93米,是基地篮球队的锋线球员。他分配到艇时让阿国龙困扰,这么高的个咋安排床位?后来是枪帆班长弄了几个炮弹箱将前舱的帆布床加长,终于安顿下来。我们给大范起了个绰号“大对虾”,因为那张床中间软两头硬,人睡进去,虾形顿现。
诸容,报务兵。在湖州接艇时遭遇爱情,女孩叫阿琴,窈窕淑静,典型的江南女子,是造船厂厂花。他俩偷偷去逛过一回公园。诸容跟我坦白,阿琴想拉他手,但他忐忑不敢。他说父母有交代,当兵期间不准在外地找对象,要找等复员后回上海再找。那天,艇离造船厂码头,空空的岸上,远远站着一个女孩。她在空中挥舞着手绢,如一抹流云,追着我们的登陆艇。
时隔三十年后,我重新登上三都岛。
登陆艇的滩涂仍在,但已变成养殖场基地。
登陆艇大队成建制撤销,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三都内澳的水域已成了望不尽的鱼类养殖场,其间夹杂着醒目的广告:“海上天湖,牧鱼沃野”。冬日里游客稀落,我独自坐在宽阔的滩涂之上,如一条搁浅的海豚。
潮水慢慢涨上来,恍惚间我看到我的艇队。
内心的风暴重新喧响,炮火铺天盖地。
众多的登陆艇从我身上碾压而过,它们一字排开,冲向滩头。坦克隆隆,红旗猎猎,登陆部队冲锋的呐喊声犹如巨浪咆哮。
我发现我最终是一朵浪花。
风浪止息后,一切都空空荡荡。